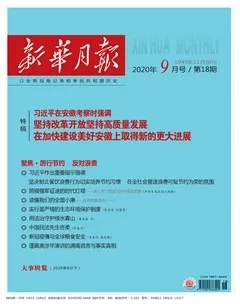別再被文理分科畫地為牢
薛涌
很多家長和同學會問:究竟是學文科還是理科?文理之分,是我們“60后”讀高中時的計劃經濟教育的舊概念。想不到,經歷了互聯網革命,我們的思考仿佛依然固化在那個時代。
疫情是否能夠幫助我們解脫這種框架的桎梏?比如,有些家長和同學透露出這樣的心態:經過這次疫情,很多人覺得在這樣的“硬核”事件面前,一些所謂的文科背景的人寫的文章無非都是牢騷、感慨和發泄,但是像張文宏等等這樣的理科生、醫生、科學家,才是真正“有用”的。
你不能說這樣的感想沒有道理。但是,讓我們換一個角度看問題。這次疫情,世界各國應對的招數不同。有些科技“硬核”非常發達的國家,比如美國,應對的結果是災難性的失敗。有些“硬核”技術并不高的國家,反而相對成功。為什么?因為對付新冠病毒,醫學上沒有辦法,甚至幾乎是無計可施。最終大家借助的,不是“硬核”的科技手段,而是“軟核”的社會政治手段,即隔離、封城,包括戴口罩。后者甚至可以說是文化手段。
以美國為例,科技“硬核”方面,也許幾年內會在新冠防治方面有結果。比如某種“神藥”,現在被炒得火熱,大家期望值非常高。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二十年前,西方有人就已經在那里大談什么人類將告別流行病了。但你永遠不知道未來的病毒是什么,往往還要像現在這樣,在“硬核”技術失效的情況下,借助14世紀黑死病時代發明的社會管理技術——隔離。所以,醫療體制、社會保障體制的問題,成為美國社會的熱點。這些熱點,不會隨著疫情的過去而消失。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將來在這些領域大有市場。
所以,怎么構想一個社會,依然非常關鍵。耶魯大學的流行病史權威Frank Snowden最近指出,現代國家機器的構筑,西方主流學界往往歸之于戰爭。Snowden進一步指出,疫情和戰爭非常類似,也刺激了國家結構的成長,比如一系列公共衛生機構。這次疫情,是否會刺激一系列社會組織的成長?
當然,這一系列社會構想的背后,都必須有技術落實。疫情加劇了這方面的緊迫性,加速了轉化過程。比如韓國等控制疫情比較成功的國家,通過個人手機上的App隨時監察病毒攜帶者的移動方位,非常有效,和美國等西方國家保護隱私的政策形成鮮明對照,并獲得了壓倒性的公眾支持。這方面的技術,當然會日新月異。
所以,很多學者指出,快遞業、遠程服務(包括教育)、自動化……這些都會隨著疫情而加速發展。
這一系列變革,當然會給數據科學、編程、計算機科學、工程等領域提供大量的機會。幾年來,我反復勸學生學習編程、數據、統計、計算機等等。但是,五年、十年后將怎么辦?那時我們又會面臨一個什么樣的世界?這就不僅僅要掌握技術手段(雖然這種手段五年左右必須更新),而且要有一種進行社會構想的能力。否則,你就是一個工具,人家讓你干什么就干什么。這種高技術的工具性人才,在人工智能時代則非常容易被替代。你必須做到不僅僅是聽別人的吩咐(雖然這在事業起步階段也許不可避免),而且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即能夠為人類設計某種生活的面向。那種傳統的中國式“理工男”,未必能夠引領時代潮流。
這里,我還必須提醒一些以“文科生”自居的同學,他們同樣會如以“理工生”自居的同學一樣畫地為牢。經濟學不說,一般的社會科學,很少能離得開統計學等基本的“理科”工具的。比如這次疫情關于是否封城、隔離的辯論,不管你是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流行病學家,根據的都是幾個數學模型。如果完全不掌握這些工具,整天在那里多愁善感,確實給人一種不著邊際的感覺。
21世紀知識更新的主流發生在網上,有各種短平快的證書課程,你每年都可以不停地更新。我就有過這樣的朋友,從一個搞雕塑的藝術家變身為谷歌工程師,讀完雕塑的碩士后就沒有讀過任何學位。這種左道旁門的生涯,日后恐怕將成為正路。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2020年第15期。作者為耶魯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教于美國薩福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