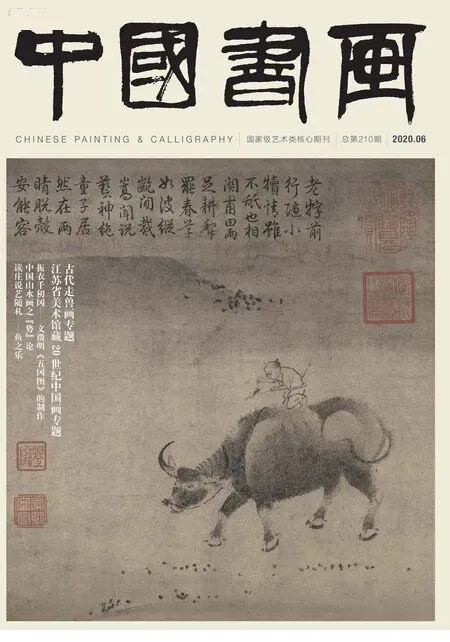古代繪畫里的天然木家具
◇ 屈峰
天然木家具是中國古典家具中的一個特殊的類別。這種稱謂在古代并不是統(tǒng)一的,《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中關于此種類型的家具有多種說法,主要有“樹根”某家具〔1〕、“天然樹根”某家具〔2〕和“天然木根”某家具等〔3〕。其中“樹根”某家具用得最多。通過對這些稱謂的檔案進行梳理,發(fā)現(xiàn)其所指實際上就是一類即“樹根”某家具。今天將其稱為天然木家具。此類家具是如何發(fā)展而來的,沒有明確的記載,現(xiàn)存實物可考的最早只到明晚期,且數(shù)量極少。
在現(xiàn)有資料中,此類家具出現(xiàn)大多在古代繪畫里。繪畫既是一種藝術形式,也是時代生活的記錄。古代繪畫雖然不能完全展現(xiàn)當時的真實,但卻能反映時代生活,揭示審美風尚。
當前關于古典家具的研究有著豐富的成果,但是涉及天然木家具的研究卻鳳毛麟角。王世襄先生《略談明清家具款識及偽作舉例》〔4〕和胡德生的《最大的樹根藝術品 天然木流云槎》〔5〕均對天然木家具中的明代流云槎做了介紹和考證。張德祥主編的《古家具收藏鑒賞百科》〔6〕對天然木家具的歷史和制作做了粗略的介紹。利用繪畫資料來研究家具的成果也有一些,例如邵曉峰的《中國宋代家具研究》、周京南的《管窺明清繪畫中的家具(上)》〔7〕等。但是所有的研究基本都沒有涉及天然木家具。而天然木家具作為中國古典家具中特有的一類,對它的研究作為探討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窗口是很有意義的。

圖1 上、中、下分別為遼寧省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和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的《蕭翼賺蘭亭圖》

圖2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琉璃堂人物圖》(局部)

圖3 有天然木家具的日本高臺寺本《羅漢圖》

圖4 自左至右分別為中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宋人《果老仙蹤圖軸》(局部)、故宮博物院藏南宋佚名《柳蔭群盲圖》(局部),以及日本大德寺藏南宋周季常、林庭珪繪的《五百羅漢圖》(局部)

圖5 中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傳五代貫休作的《羅漢圖》和美國國立亞洲美術館藏《大阿羅漢尊者像》

圖7 遼寧省博物館藏明戴進《達摩六代祖師圖》(局部)和故宮博物院藏明王上宮《十八尊者像》(局部)

圖8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明丁云鵬《十八羅漢圖冊》之一

圖6 故宮博物院藏元代王振鵬《伯牙鼓琴圖》

圖9 故宮博物院藏明崔子忠《蘇軾留帶圖》(局部),上海博物館藏曾鯨的《沛然像軸》(局部)和故宮博物院藏焦秉貞《歷朝賢后故事冊》之一
一、古代繪畫中天然木家具概況
現(xiàn)存書畫里出現(xiàn)天然木家具較早的有《蕭翼賺蘭亭圖》《琉璃堂人物圖》和傳為五代貫休作品的《羅漢圖》等。其中《蕭翼賺蘭亭圖》共有三個版本,均被認為是宋人摹本,原畫為唐代閻立本所作(圖1)。三件摹本中藏于遼寧省博物館的摹本被認定是北宋時期的。藏于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琉璃堂人物圖》也被認為是宋代摹本,原畫為五代周文矩所作(圖2)。而藏于日本高臺寺傳為貫休所做的《羅漢圖》也被認定為宋人摹本(圖3)。在《蕭翼賺蘭亭圖》三個版本中,畫上和尚辯才所坐的椅子是一把天然木類型的椅子(參見圖1)。《琉璃堂人物圖》中,僧人法慎所坐的椅子也是一件天然木類型的椅子。《羅漢圖》中有三位羅漢所坐的家具是天然木家具類型。《蕭翼賺蘭亭圖》三個摹本均被認為是對唐代閻立本原畫的臨摹,雖然三件摹本中的椅子略有區(qū)別,但均是天然木類型,可推斷其對原畫畫面基本元素特點的尊重,而原畫作者閻立本在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被評為“閻(立本)六法該備,萬象不失”〔8〕,說明了其畫具有很強的寫真性,所以由此可推論此類家具在唐代已經出現(xiàn)。《琉璃堂人物圖》中的椅子與《蕭翼賺蘭亭圖》北宋摹本比,沒有其蒼古、樸素,倒是與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南宋摹本有很大相似,在造型上,更加曲折、多姿,而且椅子的形態(tài)明顯晚于北宋《蕭翼賺蘭亭圖》摹本。但是作為摹本,它很大程度也能反映出原畫的基本事物特點,同樣能夠體現(xiàn)此類家具在當時已經出現(xiàn)。高臺寺的《羅漢圖》也具有這樣的作用。雖然此畫所畫內容為虛構的形象,非現(xiàn)實真實反映,但中國繪畫一向所秉持的“傳移模寫”傳統(tǒng),決定了作者在繪畫中設置這樣的家具必然不會是憑空創(chuàng)造,一定會有現(xiàn)實的依據(jù)和啟發(fā),所以繪畫中的家具類型在當時一定是存在的,而且是相對成熟的。將這些線索穿起來,基本可以斷定此類家具在唐代已經出現(xiàn),五代時已有所發(fā)展了。
南宋時期的繪畫中這種類型的家具就多了起來。《果老仙蹤圖軸》《柳蔭群盲圖》和《五百羅漢圖》等均有此種類型家具的出現(xiàn)(圖4)。相比之前的繪畫,這時出現(xiàn)的天然木家具有兩個變化:一是出現(xiàn)的場景不再僅是表現(xiàn)僧人、羅漢,表現(xiàn)仙人和異怪生活的題材也出現(xiàn)了;二是出現(xiàn)的家具形式不再僅是坐具,香幾、小桌等呈具形式也出現(xiàn)了。這種發(fā)展說明了南宋時期此類家具已相對成熟,這也進一步佐證了此類家具的出現(xiàn)應該在宋代之前。
現(xiàn)存的元代繪畫中,出現(xiàn)天然木家具的畫不多,羅漢題材的有幾幅,多為對宋代此類題材繪畫模式繼承,例如中國臺北故宮博物院和美國國力亞洲美術館各藏的傳為五代貫休作的《羅漢圖》和《大阿羅漢尊者像》等(圖5)。元代繪畫中最為顯著的變化就是這一類型的家具出現(xiàn)在了對于先賢、名士表現(xiàn)的繪畫中,例如元代王振鵬所作的《伯牙鼓琴圖》中的香幾家具(圖6)。
明代繪畫中,天然木家具在畫上出現(xiàn)的概率較大,明顯地超越了之前。其表現(xiàn)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羅漢畫題材中,此類家具的形式和數(shù)量多了起來,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戴進的《達摩六代祖師圖》、王上宮的《十八尊者像》和明晚期的畫家丁云鵬的多張作品,例如他的《十八羅漢圖冊》(圖7、8)等。另一方面除了僧人、羅漢繪畫外,此類家具也大量出現(xiàn)在了對于高士、名流、文人、仕女等的表現(xiàn)中,特別是對于文人現(xiàn)實生活的表現(xiàn)比較突出。例如,崔子忠的《蘇軾留帶圖》、曾鯨的《沛然像軸》、焦秉貞的《歷朝賢后故事冊》等(圖9)。不僅如此,在此時的一些畫家的繪畫中,天然木家具的描繪已然成為了繪畫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特色,陳洪綬的作品就是典型(圖10)。
清代繪畫中,天然木家具的出現(xiàn)成為普遍的現(xiàn)象。除了表現(xiàn)僧道、羅漢和高士的繪畫題材外,一般的繪畫中也常有出現(xiàn),特別是一些具體人物的肖像畫中也大量出現(xiàn)了此類家具。從帝王、妃子、文人墨客到市井凡人,就連表現(xiàn)小說故事情節(jié)的插圖式繪畫都是如此。具體來看,清早期,天然木家具的出現(xiàn)還相對集中在表現(xiàn)僧道、羅漢和名士、名流題材的繪畫中,例如,這一時期較有名的畫家禹之鼎,在這兩類題材繪畫中天然木家具都出現(xiàn)得比較多(圖11)。清中期,除了繼續(xù)秉承僧道、羅漢繪畫多出現(xiàn)天然木家具的潛在傳統(tǒng)外,此類家具較為廣泛地出現(xiàn)在帝王、妃子、官員、宮娥、兒童等表現(xiàn)現(xiàn)實市井生活和具體人物肖像的繪畫場景里。關于這一時期僧道、羅漢繪畫中的天然木家具存在情況,從冷枚的《羅漢書畫冊》窺見一斑(圖12)。而帝王、妃子等繪畫中出現(xiàn)天然木家具較有名的作品有《雍正十二美人圖》《清人畫弘歷觀月圖》《允祥像軸》《盆照嬰戲圖》等(圖13、14)。到了清晚期天然木家具在繪畫中出現(xiàn)得非常普遍,特別是具體人物的肖像畫和一些現(xiàn)實生活場景的描繪畫作。除此之外,表現(xiàn)故事、小說情節(jié)的插圖式繪畫、祈祥繪畫中此類家具也常常繪在其中,例如《耿格庵圖像冊》《鐵保像軸》《姚大海詩意冊》《西廂記圖冊》《歲朝圖屏》等等(圖15)。
整體考量這些不同時代繪畫中的天然木家具,基本能夠梳理出此類家具在繪畫中的一般發(fā)展路徑。它出現(xiàn)于唐代表現(xiàn)僧人的繪畫中,五代到南宋時開始突破表現(xiàn)范圍,元明時期進一步擴大范圍,明中晚期開始被推崇,成為一種特殊藝術語言形象,到了清代取得了廣泛的認可,并全面進入世俗生活表現(xiàn)中。依據(jù)繪畫與現(xiàn)實的對應關系,這條路徑實際上也是現(xiàn)實生活中此類家具的一般發(fā)展路徑,興于唐、經過五代到元及明代早期的發(fā)展,到了明中晚期開始被推崇,繼而鼎盛于清代。
二、古代繪畫中天然木家具繪制風格和形式傳承
從繪畫的具體表現(xiàn)來看,天然木家具從出現(xiàn)時就有兩種形態(tài),一種形態(tài)是以樹干、樹根、藤莖等材料按照一般家具的基本樣式和結構“構成”一件家具。這些材料在功能上等同于一般家具的各個構成部件,只是外觀上保持了自身天然的形態(tài)。例如三件摹本的《蕭翼賺蘭亭圖》中的椅子,家具的形態(tài)是一般椅子的形態(tài),而構成椅子的各個部件保持了自身外觀的天然形態(tài)(參見圖1)。另一種是利用樹根的天然形態(tài)進行相應的加工,從而使其具有了家具的功能成為一件家具。其主體形態(tài)是樹根的形態(tài)。例如傳為五代貫休做的《羅漢圖》中的三件家具,它們在功能上是一件坐具,但整體形態(tài)上依然保持了樹根的主體形態(tài)(參見圖3)。這兩種形式實際上也是天然木家具的兩種構成方式,在隨后的繪畫里也一直延續(xù)著這兩種基本形式。

圖10 明陳洪綬繪畫中的天然木家具

圖11 清禹之鼎不同題材繪畫中的天然木家具

圖12 故宮博物院藏清冷枚《羅漢書畫冊》中的四幅

圖13 故宮博物院藏清《雍正十二美人圖》中的三幅

圖14 故宮博物院藏清《清人畫弘歷觀月圖》(局部)、蔣和馮昭合作《允祥像軸》和丁觀鵬《盆照嬰戲圖》

圖15 故宮博物院藏清李宗《耿格庵圖像冊》之一、丁以誠《鐵保像軸》、任熊《姚大海詩意冊》之一、任薰《西廂記圖冊》之一和胡正升《歲朝圖屏》

圖16 故宮博物院藏明陳洪綬《陳字人物故事冊》之一

圖17 《果老仙蹤圖軸》《雍正十二美人圖》和冷枚《春閨倦讀圖》(故宮博物院藏)中的天然木香幾
兩種基本構成形態(tài),在繪畫語言上也表現(xiàn)出了兩種基本風格:一種是樸素寫實的風格。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這些家具所體現(xiàn)的形制和結構關系符合當時現(xiàn)實技術能力,沒有超出自然材料的合理性,也與畫面整體寫實風格相統(tǒng)一。例如《果老仙蹤圖》中的香幾、《雍正十二美人圖》中的家具等。一般而言,這種寫實性通常會基于現(xiàn)實的視覺經驗,要么是現(xiàn)實的重現(xiàn),要么是依據(jù)視覺經驗的重構,但不管是哪種,都是現(xiàn)實的真實映照,所以這些繪畫中的天然木家具可以反映當時此類家具的基本狀況和制作水平。另一種具有很強的夸張性,其造型形態(tài)或表面肌理超出了當時的技術水平,也超出了自然材料的正常形態(tài)。雖然從繪畫語言形式來審視它具有合理性并且充滿藝術感染力,但現(xiàn)實生活中是無法實現(xiàn)的。例如陳洪綬《陳字人物故事冊》(圖16)、冷枚《羅漢書畫冊》、任熊《姚大海詩意冊》中的部分家具,這些繪畫中家具樣式的特點已經超越了家具形制的現(xiàn)實語匯,更應該被看作是繪畫中的造型設置,是繪畫語言在畫面表現(xiàn)中的需要。比如對于樹根玲瓏扭曲、錯落盤繞的繪制,其重點不是為了表現(xiàn)家具的特色,而是為了畫面構成需要和筆墨語言的彰顯,甚至是個人繪畫形式語言的一部分。但是這并不代表這類作品中的天然木家具與現(xiàn)實情況就沒有關系。中國繪畫“外師造化,中的心源”的思維方式,注定了繪畫中的夸張也是對現(xiàn)實的反映,是藝術對于現(xiàn)實經驗的再加工,并映射了人們對現(xiàn)實的態(tài)度。尤其當某個時期有多位畫家的作品都具有某種相似的藝術特點時,就更能反映出現(xiàn)實的某種“普遍性”。這類繪畫中的天然木家具能夠間接體現(xiàn)出人們對此類家具所持的審美要求。而隨著繪畫藝術的社會傳播,這種審美也會反映到現(xiàn)實社會中此類家具的生產與制作中去。
將這兩種繪畫風格結合起來審視天然木家具繪畫,可以發(fā)現(xiàn)明代晚期之前的繪畫中,寫實性占主導,天然木家具的描繪呈現(xiàn)出質樸、粗拙、結構簡單的特點。這種特點也反映了同時期此類家具所具有的特點。雖然貫休的作品被元代夏文彥《圖繪寶鑒》評為 “其畫像多作古野之貌,不類世間所傳”〔9〕,但從高臺寺的摹本作品來看,對于天然木家具的描繪,雖然樹根的呈現(xiàn)都能體現(xiàn)出很強的繪畫語言特點,但夸張性則主要體現(xiàn)在對于局部造型和表面肌理的描繪上,而整體結構關系是簡單質樸的。明中晚期繪畫中天然木家具的夸張表現(xiàn)多了起來,例如陳洪綬、冷枚、禹之鼎的作品。這些作品玲瓏、輕巧、結構復雜,在描繪上除了肌理和局部造型的夸張外,更重要的是整體形態(tài)結構的夸張,超出了現(xiàn)實的可能性。到了清代,繪畫作品中天然木家具的存在除了數(shù)量更多外,寫實性風格也成為表現(xiàn)主流。將一些繪畫中的家具結構關系與現(xiàn)實家具對照,發(fā)現(xiàn)具有很強的對應性。
繪畫中的天然木家具的題材設置和家具形式具有一定的傳承性。例如,表現(xiàn)高僧特別是羅漢,常會設置一件天然木家具。從貫休的《羅漢圖》到周季常、林庭珪的《五百羅漢圖》,到《達摩六代祖師圖》,再到《面佛圖》等等,天然木家具的設置在此類人物畫中已成慣例。不僅如此,有一些形制的家具也在不斷地傳承,例如《果老仙蹤圖》、《春閨倦讀圖》(圖17)和《雍正十二美人圖》里的天然木香幾,基本為一種形式。這兩種現(xiàn)象,一方面是繪畫語言傳承性所致。中國傳統(tǒng)繪畫注重形式及語言的繼承性,運用臨摹、仿照、重構的學習和創(chuàng)作方式,在已有的形式構建上不斷地調整、創(chuàng)造,是中國傳統(tǒng)繪畫的重要特點。天然木家具與佛教人物的結合設置就是這種傳承的一部分。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些家具就會與其所處的時代現(xiàn)實脫節(jié),它的出現(xiàn)僅僅只是繪畫語言傳統(tǒng)的繼承性體現(xiàn)。
三、天然木家具繪畫題材的轉變和其審美意義的消解與轉換
一般而言,在中國古代繪畫中,表現(xiàn)具體事件或人物的題材,其人物所對應的特殊器物必然與人物有著一定的邏輯聯(lián)系,而且這種邏輯關系就是現(xiàn)實聯(lián)系,只有這樣才能對人物身份實現(xiàn)認同或強調。唐、五代時期,天然木家具作為表現(xiàn)高僧、羅漢時所用的素材,它與主體之間一定存在某種特定的關系,辯才、法慎、羅漢所坐的椅子應該與他們身份的特殊性有一定的內在聯(lián)系。先看僧人所坐的器具。樓月《攻媿集》卷七十一,記載了袁起巖藏閻立本《取蘭亭圖》跋文,文中有言“不應僧據(jù)禪床而客在下坐”〔10〕,指出了這件坐具是禪床。禪床是僧人坐禪用具。這類器具在唐代已經存在,詩人賈島《送天臺僧》詩中云:“寒蔬修浄食,夜浪動禪床。”器具彰顯了人物的身份,而人物的身份也規(guī)定了器具的類屬。再看羅漢所坐的此類器具。我國十六羅漢的崇拜始于唐代,一般認為其來源于玄奘所譯的《大阿羅漢提密多羅所說法住記》,而這十六個羅漢的原形就是僧人,所以其所坐的器具在屬性上也就是禪床,只不過因畫家藝術風格的影響,造型較之一般禪床更具有藝術性而已。
從審美的角度來衡量,這種作為與僧人、羅漢身份相呼應的天然木家具,它在畫面上的出現(xiàn)是一種源于內在邏輯需要而確定的特殊器具。天然樹木的形制是僧人特殊身份所規(guī)定的,它的外形迎合了僧人所追求的意境,體現(xiàn)出一種簡素、超凡的美感。這種美感既是現(xiàn)實的反應,也是身份的象征。可以說這類家具的審美性源于它的功用性,而它的功用性又規(guī)定了它的審美性。
到了南宋,當這類器具不再僅是禪床,不再只用于表現(xiàn)僧人、羅漢時,此類家具原本具有的那種特殊身份的象征意義被消解,而在這消解的過程中,天然樹木形制本身所具有的審美性卻開始被拓展。一些與其相近的仙道、特殊人物開始進入,一些其他形制的器具開始出現(xiàn),此類家具的特殊功能性和身份專屬性被瓦解,而其所具有的審美功能使其成為一種特殊的符號,變成了超凡脫俗、奇異的代表。但是,此時只是一個開始,天然木家具所具有的審美功能僅僅在與僧人、羅漢身份接近的神仙、異人身份的表現(xiàn)上拓展,它的表現(xiàn)范圍仍具有很強的局限性。

圖18 故宮博物院藏明代天然木家具《流云槎》及其題記
元代此類家具所具有的審美精神進一步被擴展,其外化的符號性被加強。從僧道、羅漢、神仙拓展到了高士、賢人,它的審美精神所指更加泛化,從紅塵之外邁向世俗社會的過程中逐漸消解了之前的審美寓意,在與所表現(xiàn)的人物相應襯時,其具有的超凡奇異的寓意逐漸向自然典雅轉向,這種轉向是其審美性步入世俗化的開始。
明代中晚期,這種家具取得突破性大發(fā)展,發(fā)展的基礎就在于此類家具審美性的轉化和拓展。從繪畫中出現(xiàn)的變化和繪制此類家具的畫家身份可以發(fā)現(xiàn),此類家具在明代得到了文人的賞識和推崇。明代文人尚奇、尚趣味。袁宏道在《敘陳正甫會心集》中開宗明義道:“世人所難得者唯趣。”〔11〕趣為何物?他進一步論述:“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tài),雖善說者不能一語,唯會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辯說書畫,涉獵古董,以為清;寄意玄虛,脫跡塵紛,以為遠,又其下,則有如蘇州之燒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關神情。”〔12〕那么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趣呢?他指出“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13〕。可見“得之自然”是明代文人崇尚的審美趣味。天然木家具最大的特點就是對材料自然特性的利用,是對自然美的強調,這一點深深地契合了明代文人的審美追求。天然木家具在進入世人生活的過程中,其自然典雅的審美特質也轉向為自然天成、新奇有趣了。故宮博物院現(xiàn)存的一件明代天然木家具《流云槎》就是典型的例子。此槎以樹根原形為基,將流云形態(tài)與樹根形態(tài)結合,形成了天然形家具。這件家具原屬于弘治時期的狀元康海故物,趙宦光在其上題“流云”二字,后董其昌、陳繼儒各題銘(圖18)。其中董銘有語:“連蜷而離奇,仙查與舟伐。”陳銘有云:“翔書云鄉(xiāng),瑞星化木告吉祥。”可見此時文人對與此類家具審美性的推崇,這種推崇也促使這類家具成為了雅玩器物,其結果是一方面此類家具的形式在畫面中不斷被演化,出現(xiàn)普遍的夸張性表現(xiàn),另一方面這種被推崇的審美意趣也推動了此類家具的更大發(fā)展。
清代是明代文人崇尚趣味之風的延續(xù)和拓展,尤其清中期以后,從廟堂到民間,寄情于物、品賞雅玩之風日盛,推動了各項工藝的發(fā)展。乾隆時期《清宮內務府活計檔案》中記載,在乾隆朝就制造過此類家具近百件。而畫家們對此類家具的描繪也樂此不疲,天然木家具的繪畫題材和數(shù)量都遠遠地超過了之前的朝代。明代文人對天然木家具的認定與推崇,在清代得到了進一步認可和拓展,而這使得此類家具審美意義不斷地消解和轉向。
明代文人崇尚自然、新奇的審美趣味,此類家具的審美性隨之開始了世俗化。清代則是對這種世俗化的進一步推進,這時繪畫作者以及題材已不再如明代那樣以文人為主,而是各類題材和畫家都有。明代文人所推崇的自然、新奇審美趣味被淡化,也不再像之前那樣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被演變成了大眾化的審美趣味。明代時期,此類家具在繪畫中的目的在于表達自然、新奇的審美趣味,代表某種文人性身份和品格,而到了清代,這種象征性則逐漸失去,而現(xiàn)實卻因其審美意義的逐漸消解和轉向反而變得繁榮起來。
小結
天然木家具出現(xiàn)在古代繪畫中,既是藝術語言發(fā)展的需要,也是現(xiàn)實中此類家具發(fā)展的結果。從唐代繪畫中最早出現(xiàn)此類家具,到清代此類家具在繪畫中大量出現(xiàn),不管繪畫的語言風格是寫實的還是夸張的,繪畫題材的變化與現(xiàn)實發(fā)展都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二者相互影響和促進。從唐代到清代,天然木家具在繪畫表現(xiàn)題材上的變化,反映了其審美意義在不斷消解、拓展和轉換。這種過程既是此類家具作為一種繪畫語言形式不斷符號化的過程,也是此類家具在現(xiàn)實中逐漸世俗化、逐漸走向日常生活的過程。
注釋:
〔1〕 “(木作)乾隆十六年農歷六月二十七日,員外郎白世秀來說,太監(jiān)胡世杰交樹根寶座一件、樹根香幾二件、樹根陳設二件,傳旨將寶座收拾呈進,其香幾并陳設或做材料用,或改做,先交出收拾樹根香幾用,欽此。”引自《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18·乾隆十六年起乾隆十七年止(1751 1752)》,第273頁。
〔2〕 “(廣木作)雍正四年農歷正月二十三日,據(jù)圓明園來帖內稱,員外郎海望持出黑漆里天然樹根香幾一件,青玉長方片一片,奉旨將此玉安在香幾犄角上,木頭漆水俱不可傷,用銅掐絲頂頭螺螄安住,欽此。” 引自《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1·雍正元年起雍正四年止(1723 1726)》,第700頁。
〔3〕 “(雜錄)雍正六年農歷十月二十五日,首領太監(jiān)李久明、薩木哈持出壞玻璃福海來朝圍屏一架、紫檀木甜香靠背一分(隨繡黃緞面紅綾里靠背坐褥一分)、五彩繡緞色木胎香幾二件(隨盤二個,內盛通草佛手九個、桃九個)、天然木根香幾一個(隨紫檀木座銅燒古爐一件、洋漆磬式盒一件)、嵌玉紫檀木大小柜二件,傳旨,著人送至圓明園交園內總管太監(jiān)應陳設在何處即陳設在何處,其佛手不像個東西,著園內太監(jiān)陳設在背眼處。” 引自《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3·雍正六年起雍正七年止(1728 1729)》,第148頁。
〔4〕 王世襄:《略談明清家具款式及偽作舉例》,《故宮博物院院刊》,1979年03期,第72 76頁、第96 100頁。
〔5〕 胡德勝:《最大的樹根藝術品 天然木流云槎》,《紫禁城》,1984年05期。
〔6〕 張德祥主編:《古家具收藏鑒賞百科》,華齡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201頁。
〔7〕 周京南:《管窺明清繪畫中的家具(上)》,《家具與室內裝飾》,2014年09期,第28 29頁。
〔8〕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九,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年5月版,第167頁。
〔9〕 〔元〕夏文彥撰:《圖繪寶鑒》卷二,頁二十六,《四庫全書·子部》。
〔10〕 轉引自李艷婷《遼博本〈蕭翼賺蘭亭圖〉作者考辨》,《北方美術》,2007年03期,第70頁。
〔11〕〔12〕〔13〕轉引自濮安國:《幾案一具 閑遠之思 明清家具的文人情趣》,《粵海風》,2016年05期,第1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