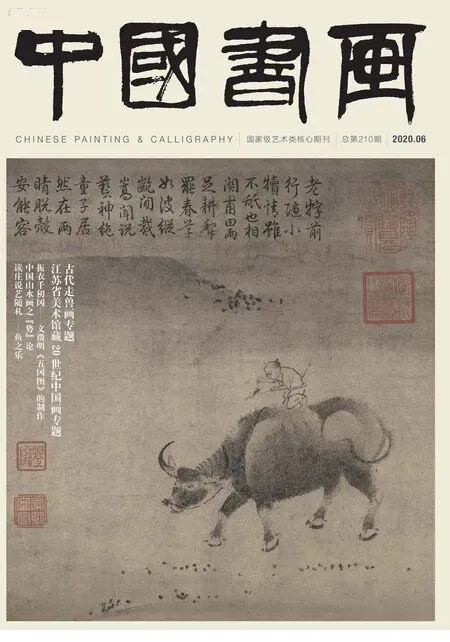高華唯芝蘭可佩
——懷念陳佩秋先生
◇ 劉波
2020年端午,一位滋蘭樹蕙的丹青詩人走了。
她的健筆,飽蘸濃情,志潔物芳,錦繡成堆。其所圖繪,畫中有詩,其所言說,詩中有畫。那里溪山清遠、雁陣驚寒,那里綠肥紅瘦、林幽禽棲。宋人斬截的運筆、文人清華的墨韻,印象派恣縱的色彩熔冶一爐,可居可游,予賞予悟,令人流連忘返。
循健碧陳佩秋先生遠去的身影,回溯近代以來的中國畫,同中國社會一樣,處在一個復雜多變的歷史節點。革命和改良曾經代表了兩種民族命運的主張。折射到中國畫領域,藝術家們也受時代的裹挾,需要在延續守成還是另起爐灶中做出抉擇,從而在后天的發展中開出不同的道路。
從形上之道到形下之器,中國文明不斷受到外來文明的補充和改變,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自足體系,這一體系在近代受到了沖擊。我以之比于一棟老宅,被拆解,被毀壞,被移易。至今斷瓦殘磚,雖然收藏者視若珍寶,奉若拱璧,可是完整的宅子不見了。當今國家提倡對于傳統文化的復歸,其指向應該并不僅僅在于一磚一瓦的收集,而是會著眼于傳統價值體系的重建。在此進程中,秉持傳統,又能在新的時代表現出新的生命、開辟出新的格局的人士,當然就是我們首先應該認真加以追尋、研究和繼承、發揚的所在。
基于對傳統人文價值整體的考察和追索,陳佩秋先生成為中國畫領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先生正是這樣一位傳統的集大成者,一位銳意革新者和積極傳播者。她的藝術是當代畫壇一座體系完備、庭廡闊大的苑囿。在其中我們可以領略到完整的中國畫藝術圖景。她的許多探索和堅持,給予今天尚在思考和實踐道路上的人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參照。

陳佩秋 九月海棠 絹本設色
先生用她自己的實踐和思考,給巨變中的中國畫傳承和發展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范例。她幸運地處在了這樣的歷史節點,也沒有辜負時代賦予她的使命,在創作上開出新的格局,為中國畫貢獻了新的樣式,增添了新的內容,在鑒定上梳理了許多歷史懸案,從而為美術史的重構奠定了新的基礎。
先生是當時少數的真正領略到中國正統繪畫魅力的人士。當時尚沒有博物館之開設,而先生則通過對公私藏家的大量藏品的觀摩和學習,早早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她的藝術道路之所以能數十年如一日沿著中國畫精神的正脈積層發展,也正得益于對傳統的深入理解和精準把握。而當時對于所謂中國畫腐朽沒落的指責,也大體來自對于晉唐宋元等豐厚繪畫傳統并不了解的人群。因明清末流繪畫的萎靡而否定整個中國畫的論說,在今天也越來越顯出其谫陋。
筆者何幸,二十年踵隨問道,獲益良多,體認先生道德文章,竊以為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先生是傳統繪畫的集大成者。
中國詩歌的歷史漫長而豐富,后世推舉杜甫為詩圣非無由也。其中,老杜對于五古、七古、律詩、絕句諸體皆能嫻熟駕馭,更能在此基礎上新意迭出,當是“集大成”的最好范例。繪畫上“集大成”云者,也不是單純從筆墨技法而言,是一種對于經典的全面、系統的繼承和積累。歷代名家的典型樣式,都表現了對于自然物象的天才的概括和提煉,透露出深厚的人文涵養。臨摹的高級狀態應該是對于隱藏在筆墨背后的文脈的發掘和繼承。這種從思想、文學、書法、繪畫、鑒賞全面入手的繼承,正體現了對于中國畫這一巍峨大廈的整體理解和全方位體察。不同于那種捉襟見肘的“惡補”式學習,步履蹣跚的“惡補”不僅痛苦,更顯其偏狹。
二、先生是中國畫現代化的搴旗者。
“現代化”也是一個被不斷提及的熱詞。可是,“現代化”又是一個令人莫衷一是的概念。現代化就是西方化嗎?于是,各種對于古典繪畫的“解構”和對西方現代派繪畫的“抄襲”洶涌而來。膚淺之外,帶著一種迷失的惶恐。靜言思之,這種想法仍舊是把自身放在一個從屬的位置,仍舊不能脫離仰望西方的奴仆心態。其實,任何文化步入現代,都存在一個現代化的問題,而現代化是沒有固定模式的。中國畫亦然。
先生每每在風云中能立定精神。對于傳統的積累,一點沒有成為她故步自封的理由,反而是藝術上勇猛進取的資源。她的繪畫大體有三個來源,除了傳統理論技法的集大成之外,對于自然的深入觀察和提煉,以及對于現代西方藝術的吸納和融合,都構成了先生藝術面貌的重要部分。所有這些部分其實都是沿著一個堂皇正大的藝術道路自然生成。臨摹古典,目標在于揣摩古人對于生活和自然的體察與概括,然后又應用到自己對生活和自然的觀察、感知當中,去印證古人筆墨的程式。先生晚年參訪大量國外的美術館,對于印象派藝術獨具只眼,但她對印象派藝術的吸收,非徒外在形式,更不在色彩斑斕,乃在于她充分理解并欣賞印象派對于自然生機的捕捉和表現,遺貌取神。先生將那種自由奔放、豐富厚重的色彩與中國畫的骨法用筆找到了最佳結合點。她在畫作上大膽潑辣的用色,恒能統攝于筆墨的意蘊,而不失中國畫的本色。
如此對待外來藝術的虹吸鯨飲的氣度、心志和手段,來源是對中國畫的充分的自信和明確的文化意識。這也正是數千年來,中國文化不斷吸納、融合外來文化的一貫方式。先生的藝術探索代表了這種精神的延續。
三、先生還是當代鑒定理論和實踐的承前啟后者。
與謝稚柳先生一道,從繪畫出發去鑒定、鑒賞古典,她的創作和鑒賞都找到了堅實的依托。繪畫實踐積累和大量觀覽古典的積累,在晚年逐漸升華成為對中國畫這筆豐厚遺產系統的認知。這也體現在她對歷史上諸多懸而未決的疑案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和挖掘。她把歷史上許多冤假錯案正本清源,對重構美術史打下了最堅實的基礎。在這一領域,先生沒有門戶之見,沒有學閥之私,也沒有成見之偏。說到底,還是那種從內心洋溢著的文化自信使然。淡然之心、單純之心,唯理是求、唯真是求,就是先生給當代學界的身教。
四、先生也是傳統人文精神的守護者。

陳佩秋 梅竹雙禽 絹本設色

陳佩秋 山泉幽鳥 絹本設色

陳佩秋 仿唐寅沉沉良夜圖 絹本設色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恒心”必須是單純質樸之心。單純生博大,唯有單純的內心,才能給自己的生命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永葆藝術的青春。沒有世俗的功利計較,遠離世俗的短長紛爭,深居簡出,心無旁騖,精勤藝事,是先生日常的生活狀態。豐富的人生、豐厚的積淀,百煉鋼化成繞指柔,先生恢宏的筆墨、樸素的文字承載著厚重的文化內涵,她和這個時代若即若離,她的存在超越了時代的拘囿。歷經時代風云洗禮,保持了完備自足的精神圖景,這也是先生能留給當下和未來的最大財富。
如今先生孑然羽化,她和她的前輩們在理想國相會,留給世間一片繁華,以及繁華背后豐沛的元氣,等待著無數后繼者懷醑計程,勇猛精進。
畫閣高華唯芝蘭可佩,
溪山清遠仰雁影橫秋。
從心底流出的這兩句話,庶幾能代表我此刻的心情。愿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