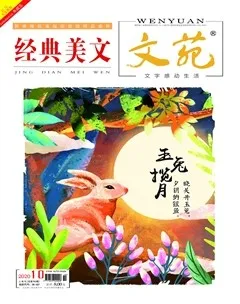王勃: 如果能重來, 我選擇不坑爹
齊桐

………… 01 …………
公元673年,唐高宗咸亨四年,天地之間悶熱而潮濕,雨水如注。一個中年男人戴著斗笠,身披一件深色的蓑衣。這是大唐交趾縣境內,道路崎嶇而泥濘,他一邊往前埋著頭趕路,一邊嘆出一口氣來。那氣息里仿佛氤氳著他朦朧又難測的前程運數,未及細想便被斗笠上滴落的雨水敲碎了。心底是一洼無奈與委屈,更與何人說。
這個男人叫王福疇,他所在的這片土地在1400年后叫作越南;他有一個很爭氣又很不爭氣的兒子,叫作王勃。據說每一個學渣兒子來到世上都是報恩的,但他的兒子是個學霸,是來報仇的。論“坑爹”,王勃說自己排第二,沒有人敢說排第一。
在被趕到交趾當縣令之前,王福疇是正七品的雍州司功參軍,管理整個雍州的倉庫、納稅以及戶籍。雍州當時就在長安城的附近,是最大的州縣,皇上極為看重。
而他今天能夠到此上任,完全拜他那個坑爹的兒子所賜。
………… 02 …………
王勃的一生,可以形容為:少年坑爹,青年坑爹……對不起,他只活到青年。
如果一個人二十六歲離開這個世界,而他已經在江湖有了十幾載的美名,你便猜得出他出道與成名有多早。當然,單單說初唐四杰,王勃也并不是出道和成名最早的那位,但論及文章才學,王勃終歸是四杰之首。
初唐四杰,相當于初唐時期詩界的四大優秀杰出青年。但這個名號很不吉利,自從評上了“優青”,四位都沒能夠活到老年。
雖說六歲的時候,王勃就已經能夠寫出很通順的文章了,但駱賓王七歲的時候就寫出來“鵝鵝鵝”,楊炯九歲就考上了“童子舉”。所以說,這個世界上優秀的人有很多,活法也很多,活得真正明白與通透的,并不多。
………… 03 …………
王勃在短暫的一生里,全心全意干了兩件事兒:一是當官,二是作文章。
這兩件事兒,他做得都很好,并且這兩件事兒也是一脈相承的。因為作文章當了官,也因為作文章丟了官,甚至差點丟了命。在這作文章、當官、丟官的時光里,王勃得到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那一些得到,很風光;那一些付出,很沉痛。
九歲的王勃當時非常之猛,讀顏師古注的《漢書》后撰寫了《指瑕》十卷,指出顏師古著作的錯誤之處。
十二歲的王勃覺得詩書讀得也不少了,開始決定進入醫藥行業。十二歲時他的這個選擇,為他的余生悄悄地埋下了伏筆。十二歲到十四歲這三年間,王勃跟隨曹元在長安學醫,先后學習了《周易》 《黃帝內經》《難經》等,對“三才六甲之事,明堂玉匱之數”有所知曉。
中醫和藥學雙學位學習畢業以后,王勃回到山西老家。十四歲的他,心中那個關于“修齊治平”的理想越來越強烈,認認真真地寫了《上絳州上官司馬書》等文章,尋找機會,積極入仕。
麟德元年秋(664年), 王勃上書劉祥道,直陳政見,并表明自己積極用世的決心。劉祥道驚呆了:“此神童也!”麟德二年,王勃通過皇甫常伯向唐高宗獻《乾元殿頌》,之后又通過李常伯上《宸游東岳頌》一篇,接著應幽素科試及第,授朝散郎。從這一刻起,十六歲的王勃成為了當時最年少的命官。唐高宗見此詞美義壯的《乾元殿頌》,乃是未及弱冠的神童所為,不禁也驚呆了,贊嘆道:“奇才,奇才,我大唐奇才!”
青春期的王勃當上朝散郎后,渾身的荷爾蒙都揮灑在了官場上。經主考官的介紹,贏得了沛王李賢的歡心,并擔任了沛王府修撰,跟著沛王一起愉快地玩耍。
當時朝廷里的公子哥兒們喜歡斗雞,有一天沛王李賢和英王李顯約好了第二天要斗雞。頭一天晚上沛王突發奇想,問王勃:明天就斗雞了,你說咱整點啥助助興、造造勢呢?
王勃想了一會說:寫一篇討伐英王的雞的文章吧,就叫《檄英王雞》。
李賢拍手稱快:太好了太好了,明天一早你就寫起來……
然后,這篇文采與用典幾乎可與《滕王閣序》相提并論的文章被高宗看到了。高宗一看就怒了:讓你帶著沛王學習,你整個討伐英王的雞的文章,你怎么不上天呢?
于是,王勃就被逐出了王府,逐出了長安,逐出了他一心營構的核心仕途圈。那一年他十八歲。這個十八歲被逐出皇城的王勃,送別好朋友阿杜遠任蜀州,寫下了那首千百年來我最喜歡的五言律詩——《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我最喜歡一句不是“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而是“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一語成讖,子安哥哥的一生,都“在歧路”,都“兒女共沾巾”。
………… 04 …………
幾年過后,二十一歲的王勃悄悄從蜀地回到長安,悄悄地參加了科選。他有一個朋友叫凌季友,當時為虢州司法。虢州藥物豐富,知道王勃有臨床和藥學雙學位,便為他在虢州謀得了一個參軍之職。
結果王勃沒一段時間就殺死了一個官奴曹達,被人揭發打入了死牢。若不是幸遇了大赦,他連二十六歲都活不到。當然,從這一刻起,小王的政治生涯算是徹底宣告結束了。
一年的牢獄生活讓二十歲出頭的王勃看上去成熟了許多。他想起了這些年的過往,那一番又一番的得意,令自己似乎有些忘乎所以了。此時他心中最深的苦痛,不是逐出長安,不是打入死牢,不是仕途終結……而是因殺死官奴曹達,連累了他的父親王福疇。
王福疇從雍州司功參軍被貶為交趾縣令,遠謫到南荒之外。王勃在《上百里昌言疏》中表達了對父親的內疚心情:“今大人上延國譴,遠宰邊邑。出三江而浮五湖,越東甌而渡南海。嗟乎!此勃之罪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矣。”
王勃出獄后在家里停留了一年多,這時朝廷宣布恢復他的舊職,他已視宦海為畏途,沒有接受。他決定南下去探望遠謫的父親,當然也正是此次南下遠行,才會讓他在那個合適的時間,出現在那個合適的地點——洪州。
當你現在再去讀這句“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的時候,你一定看不到那個激揚文字、自如灑脫的少年。如今的他早已千帆過盡、心靜如水。也正因此,《滕王閣序》那樣流傳,而《檄英王雞》卻早已不常被提起。
當你重新去讀《滕王閣序》的時候,文字里有著那么多的無奈與感慨。他寫道“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他寫道“童子何知,躬逢勝餞”……
世上哪里有什么天才,不過是在各自的命數里登攀,好些落寞,偶爾成全。帶著愧意離開這南昌故郡,然后命運給他送上了生命里最后一盆冷水,在中國的南海,淹沒了子安王郎二十六歲的華年。
………… 05 …………
那日的王勃站在滕王閣頂,極目遠望滔滔長江天際流,眼里觥籌交錯絲竹聲聲,而心里卻全是自己十六歲時的樣子。仿佛看見了自己心中“修齊治平”的理想,看到了“高朋滿座,勝友如云”……他也看到了遠在交趾的父親,一目望去,十載光陰。
如果當年跟著恩師曹元繼續留在長安學醫,給京城的百姓針灸、配藥,而不是去寫什么文章、逐什么功名,或許會有不一樣的人生。父親,也會有不一樣的人生。當二十六歲的王勃探望過交趾的父親而歸,溺水的那一刻,他或許會后悔這似夏花般絢爛而又短暫的一生。
當初如果不那么作,就不會那么坑爹;如果不那么坑爹,自己的人生或許會大不同。
摘自“桐話”
- 文苑·經典美文的其它文章
- 今夜月華如水, 人間團圓成雙
- 心理分析在文學上的應用
- 童年
- 飼火
- 景致
- 青春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