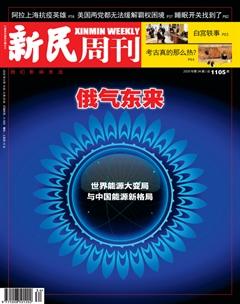神奇的睡眠開關找到了!
陳冰

人為什么要睡覺?科學家還沒有弄清楚這個生命科學中的重要未解之謎。
“人為什么要睡覺?為什么要把1/3的生命浪費在睡覺上?令人遺憾的是,迄今為止,科學家還沒有弄清楚這個生命科學中的重要未解之謎。
與此同時,現代人因為生活和工作壓力巨大,卻開始飽受失眠的困擾。明明很想睡覺,卻無論如何也睡不著;連續數日乃至數個星期沒有睡過安穩覺,在忍受失眠痛苦折磨的同時,又對失眠的后果陷入了深深的恐懼和焦慮之中——“這樣下去我會不會瘋掉?”“一直不睡覺的話,我會熬死嗎?”這種恐懼不僅不會改善睡眠,反而會使失眠變得根深蒂固,成為頑疾。
有沒有一種方法,讓人即使熬了夜,不睡覺,也不再犯困?
來自上海的科學家告訴你,還真有這個可能!
“困意”究竟是如何產生的?
9月4日,頂級學術期刊《科學》雜志發表了一篇關于睡眠的最新論文,來自中科院腦科學與智能技術卓越創新中心(神經科學研究所)的徐敏研究組與北京大學李毓龍研究組,合作揭示了“困意”究竟是如何在腦中產生的。
睡眠是動物界普遍存在的現象,人類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用于睡眠。睡眠不足可能會導致精神類疾病(例如抑郁癥)、退行性疾病(例如阿茲海默癥)、免疫力下降、心血管疾病以及代謝紊亂(肥胖、糖尿病),而成年人通常需要7-9小時的睡眠時間。
科學家曾經對美國一名17歲的高中生進行睡眠剝奪實驗,就是利用各種刺激方法阻止他睡眠。
第1天,他心情愉悅,似乎很享受這樣的安靜時光,能夠把不睡覺的時間用來看書、聽音樂;第2天,他有些疲憊,但情緒仍然積極,在實驗室中表現得平靜而安靜;第4天,他情緒低落、煩躁不安,開始出現幻想、妄想,本來沒有什么滑稽可笑的事,他卻捧腹大笑;本來不值得悲哀的事,他卻嚎啕大哭;還說自己頭上壓了一頂帽子,使他感到難受。
第5天,他開始發狂,大吵大嚷:一會兒說別人身上有蟲子在爬動;一會兒說自己在另一個城市,好像剛從著了火的房子里跑出來……第8天,他出現言語不清,明顯的記憶力、注意力下降。第11天,他的思維能力明顯下降。實驗人員要求他從100開始反復減去7,在這期間總共停止了65次。被問及為什么的時候,他回答說忘記了自己在做什么……
在睡眠剝奪11天12分鐘后,他不可抗拒地睡著了,無論用什么方法都不能將其喚醒,連續睡了14小時45分鐘后醒來并且恢復正常,實驗中出現的各種癥狀消失。
這個實驗說明兩個問題:一個是睡眠是必要的,不睡眠可以引起各種精神癥狀;另一方面偶爾幾天睡眠不好也并無大礙。但是睡眠究竟是怎么被調節的呢?依然未知。


徐敏在實驗室研究睡眠穩態調控的神經環路機制。圖片提供/ 中科院科技攝影聯盟
2014年,美國俄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神經學家 杰夫·利夫在一次名為《One more reason to get a good sleep》(一定要睡個好覺——有一個重要的原因)的 TED 演講里說到了一個實驗結論——睡覺會刷新和清潔我們的頭腦。
簡單來說,就是大腦在緊張工作的時候,它一直將清理那些細胞空隙間廢物的工作推遲。然后,在大腦要休息時,就切換到了“清理模式”,開始清理腦細胞間隙之間已經積累了一天的廢物。這有點像我們在工作日工作的時候沒有時間做家務,于是將家務推遲了。等周末到了,我們就會把所有要做的家務都做好。
當我們睡覺的時候,大腦里的腦脊液便開始給大腦洗澡,洗掉積累了一天的代謝垃圾,這個過程一般需要持續 8 小時左右,正好符合人類最佳睡眠時間為 8 小時的說法。
所以,這個研究的結論就是告訴我們——睡眠是維持大腦運轉的必要條件,而大腦是維持生命運轉的必要條件。它通過探究睡眠的作用,告訴我們“不睡不行”。并且,當睡眠不夠,腦內的垃圾不能完全清除,就會積累到第二天,從而加重大腦的負擔,降低它的運轉的能量,而這種能量不足,表現在人身上就是無法集中注意力,無法思考。所以,當我們周末補覺的時候,就是在花更多的時間來給大腦定期做大掃除。
經典的睡眠調控模型認為,睡眠的調節分為兩個方面,晝夜節律和睡眠穩態。晝夜節律通過內在的生物鐘控制一天中睡眠覺醒的時間;睡眠穩態主要由睡眠壓力進行調控,控制機體獲得一定的睡眠量。
隨著清醒時間的延長,睡眠壓力逐漸增加;隨著睡眠的進行,睡眠壓力被逐漸清除。睡眠穩態調節系統會在睡眠受到干擾的時候發揮作用。比如熬夜之后,人們往往睡得更“香”,并且時間更長。

徐敏及其研究組成員為探索睡眠障礙的治療方法提供了新的思路。圖片提供/ 中科院科技攝影聯盟
目前,睡眠調控的研究主要可以分成兩個“學派”:一個是從神經環路角度入手,研究不同腦區對睡眠覺醒的調控;另一個是從基因分子等入手,研究睡眠穩態的調控。在過去幾十年,這兩個方向都取得了巨大的進步。與此同時,這兩個方向的研究又基本上是相互獨立的。
此番,中國的科學家將這兩個方向有機結合了起來。科學家們在小鼠的大腦中找到了一群可以調控困意的神經元,減少這些神經元后,小鼠每天需要的睡眠時間大大減少——相當于人類每天可以少睡1.5小時,而且還不會犯困!
神奇的睡眠開關
根據多年來的研究,目前普遍認為,困意與一種叫“腺苷”的分子不斷積累有關。腺苷是細胞能量分子三磷酸腺苷(ATP)的“副產物”。大體來說,清醒越久,ATP不斷消耗,細胞外的腺苷分子越多,它們與相應的受體相結合,抑制了神經活動,于是人就越來越困。而咖啡之所以具有提神醒腦作用,就是因為其主要成分咖啡因可以通過阻斷腺苷與其受體的結合而達到促進清醒的效果。
基底前腦被認為是腺苷參與睡眠穩態調控的重要腦區,環路層面的研究表明,該區域的局部神經環路參與到睡眠覺醒的調控中,然而神經元活動調控腺苷釋放的機制目前還不清楚。這限制了人們對睡眠覺醒調控機制的深入解析。
為了實現在睡眠覺醒周期中對基底前腦區胞外腺苷濃度高時空分辨率的檢測,李毓龍研究組開發了一種新型的遺傳編碼的腺苷探針,該探針可以將胞外腺苷濃度的變化轉化為探針熒光強度的快速變化。通過觀察探針熒光強度的變化就可以知道胞外腺苷濃度的變化。
借助這種技術手段,徐敏團隊的研究人員針對小鼠的基底前腦區(basal forebrain,簡稱BF區)——大腦中調控睡眠/覺醒的關鍵部位,觀察了胞外腺苷濃度的變化。他們發現基底前腦區的腺苷濃度在清醒狀態時較高,在非快速眼動睡眠時較低,這與之前采用微透析法測量腺苷濃度變化的研究結果相一致。
然而,小鼠的快速眼動睡眠時長較短,傳統的微透析檢測方法每10分鐘才能測一下腺苷濃度,無法對快速眼動期睡眠時期的腺苷濃度進行精確測量。得益于新型的腺苷探針的高時間分辨率,科學家們可以看到小鼠在快速眼動睡眠期每0.1秒之內發生的快速變化。他們首次發現,腺苷在快速眼動睡眠時期也存在很高的濃度,并且高于清醒和非快速眼動期。不僅如此,他們還觀察到,腺苷濃度在睡眠不同時期的轉變時存在快速的變化,這意味著神經元活動與腺苷濃度密切相關。
為進一步探究腺苷濃度增加與神經元活動的關系,徐敏團隊進一步利用鈣成像和光遺傳學等技術,在小鼠的基底前腦區找到了負責調控腺苷釋放的兩類神經元:乙酰膽堿能神經元和谷氨酸能神經元,其中谷氨酸能神經元的活動是引起胞外腺苷積累的主要原因。
那么,如果讓這些谷氨酸能神經元不起作用,減少腺苷的積累,可以減少困意嗎?為了檢驗這種猜測,研究人員設法損毀了小鼠基底前腦區的谷氨酸能神經元。他們發現,小鼠睡眠壓力顯著降低,清醒的時間顯著增加,并且睡眠穩態也發生了改變——睡眠剝奪后睡眠時長的增加顯著低于對照組小鼠,并且睡眠壓力的清除速率顯著快于對照組小鼠。相比對照組,這些小鼠全天可以少睡20%的時間,整個晚上(對它們來說相當于人類的白天)幾乎完全不犯困。

綜合這些結果,研究人員指出,在長時間清醒而積累困意的過程中,大腦基底前腦區的谷氨酸能神經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些神經元既維持和促進了覺醒,又通過刺激腺苷釋放導致了困意增加,從而形成從覺醒到睡眠的轉換。
制造神人?
盡管在目前,研究人員僅僅采用了有創傷性的干預方式來調控睡眠,但這組神經元提供了一個潛在靶點,未來或許可以用于治療睡眠相關問題。
“我們希望通過理解大腦調控睡眠的神經機理,最終為臨床上睡眠相關疾病的治療提供理論基礎。”中科院腦智卓越中心徐敏研究員特別指出,研究使用小鼠作為動物模型,不能忽略人和小鼠之間可能存在物種差異。“睡眠調控的神經機制非常復雜,我們計劃在目前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確定上述調控機制的普適性,最終揭開‘我們為什么需要睡眠這一睡眠領域終極問題的答案。”
也許在不遠的將來,科學家們基于這個發現,能開發出一種新的藥物或簡便的干預方式,讓我們能夠更靈活地調節自己的睡眠時間,并避免犯困造成的危險。這一點,像極了尤瓦爾·赫拉利在《未來簡史》中對人類未來的描述。通過基因改造與人工智能,一個人或者機器人,輕輕松松就可以具備原本需要幾十年積累的知識與智慧,并擁有“神力”參與實踐。
如果能夠從漫長一生中三分之一的睡眠時間中摳出20%的清醒時間,你愿意嗎?對于想要多出一些時間的人來說,肯定是一個福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