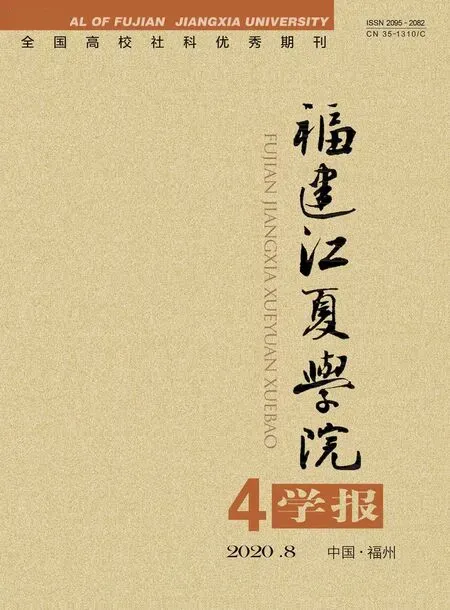外交話語的語篇構建與敘事策略
——以崔天凱大使在美國主流媒體上的篇章為例
徐品晶
(福建工程學院人文學院,福建福州,350003)
一、研究背景
媒體是一個國家對外話語傳播的重要途徑。媒體不僅影響受眾“想什么”,而且在價值觀上影響他們“怎么想”。在當今世界輿論場中,中國應當超越自說自話或自證清白的境界,從“以我為主表達”到“世界為我表達”的傳播方式轉變,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1]
2020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地球,目前已持續擴散蔓延至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據報道,截至2020年5月30日,全球累計確診病例已超過600萬(其中美國已超過178萬),全球累計死亡病例近37萬(其中美國已超過10萬),而且還在呈上升趨勢。[2]為應對這一全球重大突發事件,中國既同世界衛生組織(WHO)緊密合作,又與相關國家密切配合,公開、透明地向世界闡明中國政府針對疫情所采取的防控措施,分享防控經驗,捐贈防疫物資,馳援國外抗疫。而與此同時,一些西方國家,如美國的部分政客和主流媒體則將其本國利益置于全球公共衛生安全之上,大肆散布“政治病毒”和“信息病毒”,挑起種族歧視和排外情緒等。與新冠病毒這一有形病毒相比,這些“無形病毒”更具毒害性和迷惑性,為此,外交部發言人、駐外使節紛紛借助各種外交場合,向世界發出中國聲音,展現了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和擔當。
批評性語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簡稱“CDA”)又稱“批評性話語分析”,屬于“批評語言學(Critical Linguistics)”范疇。本文運用CDA的相關理論,基于崔天凱大使2020年2月6日、2月9日、2月13日分別接受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視公司(PBS)、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全國公共廣播電臺(NPR)的系列專訪,2月28日在《今日美國報》(USA Today)發表題為“中國筑起抗疫長城”的署名文章,以及2月1日在美國圣迭戈市“中美關系論壇”上發表演講的語篇內容,分析語篇的文本建構與句式功能,進而從語篇的范式構建和語篇的社會實踐層面,審視文本結構背后復雜的語言、權力和意識形態之間的相互關系,從外交話語的敘事策略角度為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提供一種范式參考。
二、語篇的文本構建:詞性、語態與句式的功能意義
媒體報道往往是一個被動書寫的過程,也就是一連串角色與事件的“議程設置”(agenda -setting)過程,所選擇的角色與事件由于其重要性的差異,有些被強調,有些被邊緣化。[3]費爾克勞(N.Fairclough)與盧曼(T.Leeuman)都指出,在處理文本的書寫策略時,哪些人該突出和現身,哪些該納入背景或引入預設等,固然有一些技術性的選擇,但主要是與文本的建構意圖和媒體的立場觀點密切相關,通過語言要素對角色配置的選擇與安排,展現交際雙方背后所秉持的原則和立場。[4]
(一)詞頻分析與角色意義
語篇分析通過對各種書面或口頭的符號、象征、文本進行解剖,批判地審視權力與意識形態如何在話語中得到適切的表達,其方法論主要基于以韓禮德(M. A. K. Halliday)為代表的系統功能語言學上,但也包含其他語言理論中的有關概念與方法,如奧斯丁(J.L. Austin)與塞爾(J.R.Searle)的言語行為理論、喬姆斯基(N.Chomsky)的轉換生成語法等。[5]為從整體上洞悉文本的建構意圖,在本章節中,筆者應用Wordsmith5.0軟件,選取崔大使接受上述專訪中具有代表性的NPR記者的實錄文本進行了詞頻分析,剔除文本中的虛詞與小品詞,產生出有意義的詞云圖,見圖1。

圖1 崔大使接受NPR記者專訪實錄詞云圖
從批評語言學的觀點來看,人稱代詞的選擇往往受到交際雙方的社會地位、權力關系和親疏程度的限制。[6]從詞云圖的顯示情況和人稱代詞的詞頻檢測結果來看,“we”高居榜首,其次是“you”。經筆者進一步比對文本發現,“we”絕大部分體現在崔大使的話語中,“you”絕大部分出現在記者的提問中。從聽話者的角度來劃分,英語中的人稱代詞往往分為內包(inclusive)和外排(exclusive)兩種用法。“we”通常旨在拉近與聽話者之間的距離,給人一種平等參與、休戚與共的效果;“you”則可疏遠與聽話者的距離,產生一種不信任或界限分明的陌生感。面對正在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區的新冠疫情,崔大使的觀點是:我們正全力防控(We're doing our utmost to…);我們兩國應該緊密合作(…our two countries should really work closely together to…);我們這樣做是為了更廣泛的全世界的利益(We're doing this in the larger interests of the entire world),從他的言語中,“we”不斷擴大,從中國,到中美,再到世界,把讀者納入與發言人同樣的群體和位置。畢竟在全球化時代,各國利益交融,命運與共,面對公共衛生事件,只有團結合作,才能真正維護好共同的利益。相比之下,美方的言行既不符合事實,更不合時宜,從指責(You needed…)到懷疑(I need to ask about…)再到脫鉤(the idea of decoupling)等,充斥著他人的話語和面對“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排他性思維,與一段時期以來美國一些媒體針對疫情的種種不實報道以及部分官員的逆向做法如出一轍。
從意義分類上看,情態動詞可分為表達愿望、期盼的“will, would, can, could”,表達強調、加強語氣的“must, need to, have to”,以及表達委婉建議與請求的“shall, should, may, might, would rather to”等。根據詞頻分析,在文本中,have to,should,could的使用頻率依次排在崔大使話語中的前三位,如,We have to do our best to reach that goal;You have to base yourself on evidence and science; I don't think that should happen. And I don't think that could happen…話語主體通過情態動詞的反復使用,意在強調、表達這樣一種觀點:在疫情面前,必須以人民的健康為唯一目標,強調信息發布的科學性和疫情防控的成效性;中美關系如此緊密,不應該、也不可能出現倒退或所謂的“脫鉤”等現象,委婉地表達了中美兩國合則兩利、斗則俱傷的相互依存關系。
通過對文本中不同詞性的詞頻分析得出,位居形容詞、名詞、動詞前三位的分別是“economic,public, political”,“China, people, government”和“have, do,make”等。經進一步分析文本中這些高頻詞的搭配組合可以看出,NPR記者關注的是由疫情可能引發的經濟損失、公共恐慌、政府失信于民、中美關系倒退等消極的主題,企圖以負面的信息量構建一個不透明的、在某些地方出了問題的中國政府形象。相比之下,在崔大使的詞語搭配中,遵循經濟規律、尊重科學抗疫、關注公共健康、政府有為有力、中美合作共贏等構成了他的主要話題,展示了中國政府寧可遭受經濟損失也要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責任意識,寧可被誤解也要堅持以證據說話的科學態度,寧可自己付出高昂的代價也要顧及全世界人民更大利益的原則立場。
(二)語態、句式與交際效果
韓禮德將語言所必須完成的功能歸納為三類,即概念(ideational)功能、人際(interpersonal)功能和語篇(textual)功能。概念功能表達主客觀世界存在的人物和事件;人際功能反映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語篇功能把語篇與語境相聯系。[7]在新聞語篇中,表達人際功能的情態系統除了情態動詞、情態形容詞和情態副詞外,還包括時態、語態、句式等,這有助于語篇分析者從整體上了解語篇的交際目的和以言行事的施動效果。
在許多情況下,現在時態并不表示時間,而是表示普遍性的真理、始終存在的狀態、習慣性或連續性的行為和過程等。[8]在專訪中,崔大使的話輪(turn)所體現的時態大多以交替使用的一般現在時和現在進行時為主,“we are doing…”的句式被他多次反復應用于抗擊疫情的行動中,尤其引人注目,如,“We are doing utmost to contain and control the virus.”“We are providing…all the figures… to make people reassured that…”等等,它傳遞一種“疫情就是命令”的交際意圖,強調行為動作的緊迫性和任務的艱巨性;又如,“We take care of public health needs…we respond to epidemics.” “We welcome experts of all countries to come to help us.”“We appreciate that the world is helping us.”等等,這些句子的謂語動詞本來也可以用進行時態來表達動作的時效性,但與時效性相比,用一般現在時來表達動作的習慣性或連續性更符合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和負責任態度。
在新聞語篇中,語態反映的是施動者、過程、目標之間的關系,體現說話者對某種行為的態度。[9]專訪中的主動語態占了絕對的優勢,主動語句突出施動者的立場意志,其語序安排方式更能準確反映出抗擊疫情所采取的“以我為主、快速反應”的主體行為,反映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主動擔當態度。專訪中也有以目標為主語的被動句,把施動者放在不顯著位置或取消施動者,如,“People's daily necessities have to be provided”;“So everyone who needs, who requires medical treatment will be included, will be covered”等,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政府執政理念。新冠疫情在中國迅速得到控制,國內現有累計確診病例82999例,累計死亡病例4634例。[10]對比美國超170萬的確診病例、超10萬人死亡的慘狀[11],不管從數量上看,還是從兩國的人口比例結構上看,都相差懸殊,中國政府防控疫情的成效與社會治理能力在這些數字對比面前不證自明。
僅憑擺事實講道理,往往不足以達到說服他人的目的,而句式運用卻常常能加強發話人應用語言影響他人的能力和權力。就文本的主體部分而言,其表達方式以敘述為主,通過動作小句,增強抗擊疫情的緊張感,以當事人的主體位置統領幾個復句,增強語篇的節奏感,同時又用一連串的情態助詞與句型短語,構成排比形式,增強話語的氣勢與感染力,以言行事,達到說服別人或影響并改變別人態度和行為的意義潛勢。如在首個話輪中,針對NPR記者把肺炎疫情夸大為3個“危機(crisis)”的提問,崔大使連續用了6個“we”做了概述性的回答,等于含而不露地告訴記者,這只是一次面臨病毒的挑戰,而不是對方所說的經濟或政治危機。又如,在回答中美經濟是否“脫鉤”時,崔大使連續用了3個排比句,寥寥數句,卻一語中的,與NPR記者為美國商務部長的不當言論做結巴饒舌的辯解形成強烈的反差。
三、語篇的范式構建:外交敘事的國家印記
話語實踐分析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弄清說話者對話語命題所承擔的責任程度;二是了解說話者與聽話者之間的社會距離與權力關系。作為駐外使節,崔大使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而是處于一個國家關系網絡中的代言人,其話語的生成并非完全是其個人的自由創造,它必定要與特定的國家意志相聯系并受其制約。[12]對外話語敘事可以從大度與氣度、適度與力度等方面考察文本的范式構建,通過語境化的解讀,識別其所處的時代層面,展現外交話語在社會領域中的位置與影響力。[13]
(一)外交話語的大度與氣度
一個人的思想取決于他的社會站位,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人的存在,而是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意識。[14]崔天凱大使的教育背景和工作履歷印證了其話語生成的社會學邏輯,早年的專業外語學習與留學經歷,長期在外交部、聯合國以及駐日、美使館等多部門、多崗位的職業外交生涯,其話語實踐不可避免地體現了大國應有的自信風度與包容氣度。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特朗普和美國一些主流媒體將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Chinese Virus or China Virus)[15];《華爾街日報》甚至在標題中稱中國為“亞洲病夫”(Sick Man of Asia),將病毒與中國國家形象捆綁在一起[16];美商務部長羅斯稱,疫情有助于部分就業崗位回流美國等[17]。這些“無形病毒”違背了國際法準則,也悖離了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作為駐外使節,駁斥那些對華不友善言論,不僅要有高度,還要提高準度,把握尺度。崔大使接受專訪的3家媒體,都是美國全國性的傳播機構,擁有廣大的受眾和相當的影響力;其發表署名文章的《今日美國報》也是全國性發行的報刊,發行量居主流報刊前列;“中美關系論壇”是中美政、商、學界精英的輿論平臺,對中美關系走向有很強的導向作用。在這些媒體、平臺上面對面講述中國故事,不僅能最大程度上改變或者消除不真實的或被扭曲的對華印象,還可以加大對外宣傳和爭取美國民眾支持的力度。如,PBS記者借助此次疫情危機,企圖以偏概全,偷換“政府”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直接歪曲中國政府“出了問題”(something wrong),崔大使對此明確予以指正:正如美國政府一樣,中國政府也分為多個層級。政府出現失誤,這是自然不過的現象,美國也不例外;但如果將每一個基層政府的失誤都歸咎于中央政府,這是偏頗且不客觀的。正如幾年前卡特里娜颶風給美國路易斯安那州一些城市帶來的混亂與無序,其道理就不證自明。又如,CBS記者認為武漢“封城”舉措限制了人的自由,暴露了中國治理體系的弱點,崔大使則強調指出,“封城”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范例(a real example of one-for-all , and all-for-all situation),這才是中國為防止疫情擴散,對世界所持的負責任態度。事實證明,該采訪后3個月,在全球范圍內眾多城市不但“封城”,英國、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南非等眾多國家甚至“封國”。
(二)外交話語的適度與力度
新聞語篇總是試圖在言語中植入意識形態的力量,話語中的價值觀選擇并不一定全部是講話人有意識的傾向性表達,相當一部分是源于話語類型本身的意義潛勢。作為一種社會身份的特殊形式,國家形象的產生、再生產,形成或是瓦解都是通過這樣的話語形式來完成的。[18]
西方發達國家憑藉自身媒體的強大影響力,對他國進行帶有偏見、不客觀的分析報道,容易給一個國家形象的建構與解釋帶來消極負面的影響。有研究指出,相比于國內新聞,美國媒體在外交新聞報道上顯得更加偏頗,其構建的中國國家形象具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19]作為維護國家利益的外交戰線和捍衛客觀事實的輿論陣地,外交部近年來越來越注重及時發聲與主動回應。通過梳理崔大使接受上述媒體訪談的幾次話語文本,發現其重點圍繞疫情防控、中美關系和國際合作等3個主題,體現其內容意義的遣詞造句也是對國家外交政策的再闡述過程,展示了中國外交話語一以貫之的立場原則,如在“中美關系論壇”演講中,崔大使指出,“一個健康穩定的中美關系,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20];在 “中國筑起抗疫長城”的署名文章中,他再次強調,“中美作為國際社會重要成員、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更是需要合作應對全球性挑戰和問題,因為這攸關兩國17億人和世界70多億人的福祉。”[21]
可見,中國的國際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外交層面上的話語實踐。駐外使節的話語策略,既要針鋒相對,選準角度,也要講究共情,把握尺度;既要講好本國國家故事,又應選擇與之相適應的駐在國媒體平臺,及時回應國內外公眾關切的話題,不給國際媒體造謠、傳謠、捧殺或唱衰的機會。
四、國家話語權構建:語篇的社會實踐意義
批評語言學理論認為,哪里有話語,哪里就有權力。權力始終是在交鋒與斗爭中被贏得、被使用、被維護或喪失。[22]對語篇的分析,離不開對話語實踐過程及其所發生的社會語境的分析。話語的社會實踐分析把話語置于相互交鋒的社會關系中,注重分析話語實踐如何影響并重構已有的話語秩序和敘事方式,甚至影響國家形象的形塑過程。
(一)話輪交互與主體博弈
語言并非一種客觀的思維工具,話語參與者在實際會話中所擁有的權力,以及他們的身份和地位,通常是不對等的,每一次的語言運用都是行使、再生或者顛覆權力的工具,體現了話語者對已有話語秩序的表達與抗爭。作為展現國家氣質和闡述對外政策的窗口,大使的講述,便是中國故事,與其相適應的話語博弈,也體現在話輪的分配與取舍中。
媒體的每一次訪談或報道實際上就是一次對他人或他國輻射影響、施加權力的延伸。在訪談類語篇中,記者往往處于支配地位,掌握著生成話語的主導權,可以決定語篇中“說什么”和“不說什么”,以及“怎么說”。處于權力較小一方的受訪者,如果認為權力較大一方的內容和措辭不能接受,就會試圖采取行動,依賴他所能調動的各種資源,干預事件順序,改變事件進程,使之產生一種特殊的意義和效果。[23]如,NPR記者把新冠疫情定性為由公共衛生危機引發的經濟和政治危機(crises),而崔大使認為疫情是對中國和整個國際社會的一個巨大挑戰(big challenge);在疫情的防控舉措上,NPR記者的態度是質疑與不信任(doubt and lost credibility),崔大使表達的是信心與責任(confidence and responsibility);在中美關系方面,NPR記者習慣使用“緊張”(strains)、“脫鉤”(decoupling)等消極詞匯,而崔大使側重的是“合作”(cooperate)、“緊密聯系”(intertwined)且“相互依存”(interconnected)等積極詞匯。類似的成對詞在PBS、CBS記者訪談中也比比皆是,它們被選擇和應用,無不取決于這些媒體的立場和觀點,也宣示著話語具有的社會建構功能,既形塑社會實踐主體的行動方式,又被社會實踐主體所形塑,與之相應的話語權也在相互博弈中此消彼長,影響或重構著現有的話語秩序。
由此可見,用語言給事物加貼的標簽,不一定反映事物本身的固有特性,人們對事物和經驗的不同看法,會導致不同的社會實踐結果,具有鮮明的敘事策略。特魯(T.Trew)把上述這樣的成對詞(組)叫做“爭議性縱聚合關系語言項”(dispute paradigm),即在某一場合可供選擇的一組詞,其中每一個都表明一種不同的意識形態立場。[24]
(二)作為新聞的語篇價值與話語權的傳播技巧
權力通過話語的社會實踐與媒體傳播實現權力的控制過程。費爾克勞(Fairclough)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社會組織機構分為三個層次,即,機構的(constitutional) 、情境的(situational)和社會的(societal),見圖2。

圖2 費爾克勞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次對語篇產生的意義分析
圖2表明,語篇是一種社會空間,任何發生在語篇中的權力斗爭都可以在這三個層面上進行分析。[25]這為進一步探索在多極化的世界中,一國媒體怎樣應用話語體系來爭奪國際話語權提供了基本的理論指導。
首先,從機構層次上看,西方的傳播媒體總試圖向世人灌輸一種言論與新聞自由、新聞報道客觀公正的價值觀。而實際上,任何新聞報道都取決于一整套人為的選擇標準和被規約化了的篩選程序。[26]不管是PBS,還是CBS或NPR,都將中國視為美國最重要的政治和經濟競爭對手,被選中的報道不可避免地會把所描述的內容置于某種信念或價值觀的框架之內,不可能反映客觀事實。代表國家利益和形象的大使閣下,不僅需要借助這些媒體闡明中方觀點,也要采取必要的敘事策略,去抗擊意識形態上的偏見和冷戰過后的殘余“病毒”。
其次,在情景層次上,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的提升,提高對外傳播能力,爭取更多國際話語權,已成為一種必然。然而,面對處于主導地位的西方媒體及其早已形成的傲慢與偏見,讓世界接受真實的“中國故事”和“中國聲音”并非易事。崔大使在美國主流媒體和刊物上的系列訪談及署名文章,改變了傳統的對外傳播方式和技巧,并借助西方話語體系的運作機制,讓受眾更便捷、更客觀地獲取有關中國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抵銷了美國部分主流媒體扭曲中國的主觀傾向。
最后,從社會層次上看,對中國駐美大使的專訪,表面上只是記者與大使間的話輪交鋒,實際上它代表了美國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對中國的政治偏見與冷戰思維,也映射了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價值觀上的差異和沖突。雖然中美兩國在經濟、金融等領域已形成深度的相互依賴關系,但由于特朗普推行“美國優先”政策,中美之間仍可能發生一些潛在沖突,因此,雙方都有必要保持暢通的溝通渠道,本著同舟共濟的合作精神相向而行。值得一提的是,語言的智慧影響人們對事物的態度和他們的行為,由于崔大使應對得當,一個全力維護人民生命健康、為全球公共衛生安全作出貢獻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得以真實體現;一個信守承諾、謀求合作發展、不干涉別國內政的中國形象也通過國際電波和互聯網得到有效的傳遞,并產生積極的影響。
結語
語言通過人類賦予世界意義,媒體傳播作為一種話語權爭奪的社會實踐,又反過來影響或塑造人類的思維和世界觀。崔大使以言行事,既有理有節,又綿里藏針,其態度坦誠,話鋒犀利,將美國“兩把尺子量世界”的價值觀層層挑明,既表達了中國政府的執政理念,又樹立了正面、積極的對外國家形象。
21世紀前后,批評性語篇分析與新聞傳播研究的結合日益緊密,在新媒體時代,新聞的即時性、交互性及其跨時空性決定了新聞話語在及時、有效傳遞信息中的重要作用。當前中美關系復雜多變,兩國雖然存在制度差異和理念分歧,但兩國擁有廣泛重要的共同利益。中美作為兩個大國,在包括此次疫情防控等許多全球性問題上都需要進一步加強合作,才能共同維護兩國關系和各方利益。通過此次國際社會共同戰“疫”,身處一個地球村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將更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