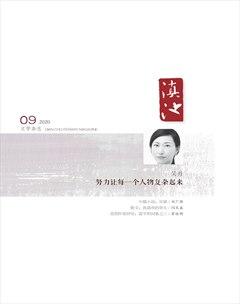洗滌我的骨頭

閆文盛1978年生。山西文學(xué)院專業(yè)作家。出版散文集《失蹤者的旅行》《你往哪里去》《主觀書(shū)Ⅰ:我一無(wú)所是》《主觀書(shū)筆記》,小說(shuō)集《在危崖上》,人文專著《天脊上的祖先》等多部。獲趙樹(shù)理文學(xué)獎(jiǎng)、《詩(shī)歌月刊》特等獎(jiǎng)、滇池文學(xué)獎(jiǎng)、山西省文藝評(píng)論獎(jiǎng)一等獎(jiǎng)、安徽文學(xué)獎(jiǎng)等。曾任文學(xué)雜志《都市》執(zhí)行主編。2017年入讀魯迅文學(xué)院與北京師范大學(xué)合辦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方向碩士研究生班。
布谷
1
只要我誠(chéng)懇地望她,便不會(huì)再想她,因?yàn)樗驮谖疑磉叄谖倚睦铮俏业难夂挽`魂養(yǎng)育的,是愛(ài)的不絕于心,是愛(ài)的無(wú)怨無(wú)悔!
愛(ài)“從未止歇”。經(jīng)年以來(lái),我們從未徘徊不定或使出愛(ài)的大力。但是,峭壁上生出綠色枝葉的一刻,愛(ài)已經(jīng)來(lái)了(“時(shí)間開(kāi)始了”)。愛(ài)“從未止歇”:你所明白的愛(ài),可以言喻的愛(ài),從來(lái)不是來(lái)自上帝創(chuàng)造性的遲滯,它只是來(lái)自天地間呼吸的形色。你當(dāng)明白,愛(ài)“從未遲滯”,它是最為透明和猛烈及時(shí)的——它從未窒息(無(wú)邊的遲滯),它是永遠(yuǎn)在蓬勃生長(zhǎng)的(“愛(ài)的居息”)!
我們熱愛(ài)的是“愛(ài)”的生長(zhǎng)性,未必?zé)釔?ài)“愛(ài)”的結(jié)果,更不熱愛(ài)“愛(ài)”的變異。
2
布谷給我們提供的指示并非迷途,但事實(shí)上,它只是如此懵懂的一物。
我們希望有個(gè)平靜的天臺(tái),它容納我們的思緒和愛(ài)。
是生活使我們相愛(ài)?還是因?yàn)橄鄲?ài)我們才能生活下去?這不僅僅是思維的變奏,這是世俗對(duì)于我們存在之悲的集中反饋。我們對(duì)于人間殘留的愛(ài)惜,構(gòu)成了地平線上的蒼茫風(fēng)景。
飛鳥(niǎo)越過(guò)了我們的頭頂,攜帶著它們的自由和愛(ài)情。
3
一句詩(shī),或一顆釘子:“我對(duì)愛(ài)與不愛(ài)毫無(wú)怨言。”我的此生,都在致力于與愛(ài)情及生活的和解。但我還是經(jīng)常刺疼它們,我覺(jué)得我是一個(gè)十足的魯鈍的人。
我們不能“受累于愛(ài)”,但我們可以受累于一場(chǎng)奔赴昆侖山的旅行,我們可以受累于熱帶的暴雨和漫長(zhǎng)而靜謐的香格里拉。
思念的明晰對(duì)于“宇宙奇趣”可能是一種傷害。所以,我常常站在穩(wěn)定生活的側(cè)翼,我需要確知我的疑慮和重生“比昨日更多一些”。
我們有太多太多的愛(ài)需要釋放出來(lái),但是,沒(méi)有一絲空氣會(huì)支持我們。(空氣中擠滿了各種物質(zhì),它們是對(duì)于愛(ài)與悲憫的無(wú)情的稀釋。)
4
一切都需要忍受。包括遲滯與衰頹,莫名的“愛(ài)與痛覺(jué)”……
我從未想要刺疼我所愛(ài)的這個(gè)世間,但我常常把離我最近的人給刺疼了,反之亦然。就這樣,我收獲了我從未想要獲得的滄桑之感。
只有我們的愛(ài)有一種藝術(shù)的精確性,它是澆灌花圃的雨水和春季融雪的會(huì)合。我們是一種反復(fù)流動(dòng)的物質(zhì),在每一個(gè)可以形成障礙的棱柱上留下了不愿意離別和死亡的唾液。
5
生活是寫(xiě)給亡靈的獻(xiàn)詩(shī)?是的,死亡和藝術(shù)都太破碎了,只有生活構(gòu)成了一切:盡管無(wú)所見(jiàn),但卻是唯一的獻(xiàn)詩(shī)。生活是真實(shí)的、唯一的消逝。疼痛不可察覺(jué)(漸趨消隱)的幻變,靈魂(不變的枕頭)的唯一的獻(xiàn)詩(shī)。我們都將在未來(lái)體會(huì)亡靈的寂靜(亡靈的獻(xiàn)詩(shī))?我們獻(xiàn)給自身的消逝,沒(méi)有絲毫感傷,只有隱秘的亡靈的消逝。這當(dāng)真是唯一的獻(xiàn)詩(shī)!
沒(méi)有充分地認(rèn)識(shí)到自我是對(duì)的?這所有的一切說(shuō)明我們?nèi)栽诔砷L(zhǎng)中。未死未亡,足證我們的一輩子都在誕生。我看著那壓迫我的兩個(gè)夢(mèng)境,我在為我無(wú)感的人而陷入了焦灼。我把時(shí)間的韻律交付給你,請(qǐng)引領(lǐng)你的情欲入此籠中。
6
世界上不只有布谷鳥(niǎo)的叫聲。
我在聆聽(tīng)中感受到的,卻只是布谷鳥(niǎo)的叫聲。
我在聆聽(tīng),感受,但我不僅僅是在聆聽(tīng),感受。
而像是一次聆聽(tīng)的降生。而像是一次聲音的降生。
我的感受如此簡(jiǎn)單,呈現(xiàn)出聆聽(tīng)之中復(fù)雜的萬(wàn)象。
我從未看到過(guò)一只布谷鳥(niǎo),我從未看到過(guò)一株植物。
我似乎凝固了與它們的不識(shí)。
萬(wàn)物,只是我在無(wú)路可逃時(shí)的一個(gè)出口。
它對(duì)我形成遮擋。
我在它的盡頭繞回來(lái)。
但仍是萬(wàn)物,仍是布谷。
我在聆聽(tīng),感受,停泊在人世的河岸上。
世界上不只有布谷鳥(niǎo)的叫聲。
但我在聆聽(tīng)時(shí)所感受到的,卻是它的,唯一的聲音。
沒(méi)有萬(wàn)物和出口,我的聆聽(tīng)如此專注。
我在聆聽(tīng)中遺忘了的,還包括困倦和沉睡,還包括厚達(dá)尺余的詩(shī)歌冊(cè)頁(yè)。
還包括我的各種生活……好了,還包括我的各種感受。
總而言之,這只是布谷鳥(niǎo)的叫聲,但它卻形如招魂。
我在傾聽(tīng)之中,遺落了我的傾聽(tīng)之外的各種贅余。
我僅僅只是,記住了一個(gè)下午,一只布谷,許多只布谷。許多種萬(wàn)物。
我封鎖了、埋葬了我的愚鈍,我只剩下了傾聽(tīng)的盈實(shí)和虛無(wú)……
7
我們的欲望是黑黝黝的石柱,它有著難以言喻的非愛(ài)的本質(zhì)。
我們自以為心意相通,可以絮語(yǔ)相及,但是,錯(cuò)了,我從未看到你的心,你也從未看到我的。
激情在遠(yuǎn)未充分達(dá)到之前才有價(jià)值,風(fēng)景也只存活于想象之中,包括一切愛(ài)戀和尚在旅途中的事物,都充分地占據(jù)過(guò)我們遐想時(shí)的領(lǐng)空。所以,未名狀態(tài)才是可以真正接近內(nèi)心喧囂的時(shí)刻,而忙于思考之外的一切瑣事才是思考的真正哺育。(不要奢侈地享樂(lè),因?yàn)樗鼤?huì)損壞你、去除你。)
讓我回憶一下,我確實(shí)會(huì)迷戀肉體的芬芳,但只是一種單調(diào)而熱情的迷戀,像迷戀我們初生人世時(shí)的純潔思想。
8
我們的存在是真誠(chéng)的,但我們總是難免死后之亡。我們看不到死后的日出,所以現(xiàn)在就可以盡情地想象了:一輪朝陽(yáng)……
愛(ài),僅僅是一輪朝陽(yáng)。
我們經(jīng)過(guò)的區(qū)域還活著,我們愛(ài)過(guò)的人還活著,我們觀察過(guò)的草木死后榮枯,所以,它們還活著。
但我們已經(jīng)不可想象了,作為灰燼和塵土,我們?cè)陲L(fēng)中飄散了。
但我們已經(jīng)不可想象了,作為靈異的先生,我們卻唯獨(dú)沒(méi)有魔鬼的鏡子送人。
以不被發(fā)現(xiàn)和珍視表達(dá)我們的驚喜,以無(wú)感覺(jué)的存在表達(dá)我們的失落的愛(ài),以一個(gè)繁華或落寞的街區(qū)去替代已經(jīng)逝去的往昔的垢灰。
時(shí)間繼續(xù)洋溢著它授予人的無(wú)窮慨嘆:
來(lái)吧,上帝,讓我們坐在沙灘上席地談?wù)劇D闼匆?jiàn)的,都是那些慵懶的群山造成的。
而我們?cè)隗w驗(yàn)著一種經(jīng)驗(yàn)的亡靈,它們是無(wú)法被描摹和彌補(bǔ)的原始人一般的往昔。
我們像不占據(jù)任何空間的幻影一般游蕩在時(shí)間的暗倉(cāng),天地的蒼老只是一個(gè)小小的教條。
我們有一個(gè)堪為自我替身的小盒,它的圓融無(wú)礙救贖了我們……
我們不僅是草木的彌補(bǔ),我們還是造出了這一切生與死的人。
9
我是一種饑餓的食人獸嗎?我想吞掉你的心、你們的心,作為我正在經(jīng)歷的空洞的補(bǔ)白、荒涼的補(bǔ)白。
讓激情自然消退下去,讓生活回歸日常。讓絕望繼續(xù)延伸下去,讓美成為你并不覬覦的,讓愛(ài)成為你的限定。讓時(shí)間變得最不像時(shí)間。那么好了,你終于回到了起點(diǎn)上……我們可以握手言歡的時(shí)刻,你變得最不像你。那么好了,你之中本來(lái)沒(méi)有你。
我們的幻象是不同的,但還大體集中。這或許由于我們的生活尚處在一個(gè)平面。只有我們的愛(ài)的傾斜、思想的源頭仍在分解。即使我們的時(shí)空繼續(xù)集中也是無(wú)濟(jì)于事的。我們的一切都在重合(異常中的重合)?看起來(lái)如此。我們一直在趨同的進(jìn)程中加速奔涌,我們沒(méi)有自己鋪就的道路,不需要時(shí)常發(fā)聲。但那些獨(dú)立的河流在不斷地沿途滲漏,不斷地留下它在循環(huán)更迭的時(shí)空中的種種缺口。我們的感受力在不斷地分解,愛(ài)的傾斜變成一個(gè)確定無(wú)疑的常數(shù)。我們蒞臨的區(qū)域都變成一個(gè)傾斜。那些城鎮(zhèn)大體上是不存在的。這或許是我們時(shí)常惶惑的緣由。我們已經(jīng)有太多時(shí)候沒(méi)有看到河流了,那些蓄滿源頭的事物已經(jīng)有太多時(shí)候不與我們共晤。我們思想的平面仍在傾斜,愛(ài)的力仍在傾斜。在我們拘謹(jǐn)于事物的時(shí)空,宇宙仍未是一個(gè)確數(shù)。我們?cè)诳帐幨幍臒o(wú)窮中無(wú)盡地上溯?但河流的上方積雪正在消融,我們的歷史像一梁山脈藉由寒熱交替的時(shí)序種植……有豐收的秋景存在過(guò)嗎?有真正的時(shí)光(愛(ài)與永恒)的不朽存在過(guò)嗎?
10
溫暖的情欲是我們?nèi)松囊环N填補(bǔ),但是,我從來(lái)無(wú)法洞悉我“心中的萬(wàn)千須臾”。它們都比我活得年輕、率性。我從何時(shí)開(kāi)始,已經(jīng)感到了“身心蒼老”。
必須讓身體的靜默符合心靈的潮流,否則,連你的所思都是臭的。我見(jiàn)識(shí)過(guò)許多喧鬧而淺薄的花蕊,因?yàn)樽匀欢坏匾?jiàn)識(shí)過(guò)它們而真誠(chéng)地鄙視它們。喧鬧的花蕊丟失了寧?kù)o中的芳香,從而使我們的聽(tīng)覺(jué)和視覺(jué)都受到了污染。我從此后不再刻意地培育自己的感官,我只要認(rèn)識(shí)到它們喧鬧而純明的卑微就夠了。也許我應(yīng)該為我的同樣卑微的認(rèn)識(shí)而愛(ài)它們?那些苦楚的、露骨地綻放的花蕊?
11
悵然或茫然總是如此復(fù)雜,復(fù)雜得不容再
有任何夢(mèng)想
“只研究和理解往事便夠了”
我有時(shí)會(huì)站在一個(gè)愛(ài)人的角度去理解我們
的青春
當(dāng)然,那時(shí)有蔚藍(lán)或嬌艷的天空,我們便
是為了夢(mèng)想去找人傾訴
夜讀愛(ài)情,那些恬然的激蕩四方的寧?kù)o會(huì)
讓我們感動(dòng)落淚
然而這莫名的憂愁,它引領(lǐng)我們,發(fā)動(dòng)一
場(chǎng)虛妄的戰(zhàn)爭(zhēng)
我希望自己可以保持一貫的純真
就像見(jiàn)了陌生的人心臟會(huì)怦怦跳的戰(zhàn)爭(zhēng),
我們?cè)趷?ài)情中落下病根
讓婚姻來(lái)拯救我們
然而這莫名的憂愁,它導(dǎo)致了無(wú)數(shù)戰(zhàn)爭(zhēng)以
及紅色的鳥(niǎo),以及墨綠的樹(shù)
我想象童年的時(shí)辰就像遲到的解咒,我很
仔細(xì)地端詳你的面容
愛(ài)情不會(huì)持續(xù)太久,但生命卻堅(jiān)定地相沿
下來(lái)
那些昏睡和失眠過(guò)于等同了,就像天空
它們都既悲傷又空曠,就像原野
它們都既空洞又憂愁,我制造了秘密的蘆
根
它們傾盡了我的所有
上帝啊,我們把整個(gè)人間都獻(xiàn)出來(lái)了
那些大森林中的鳥(niǎo)獸,它們各自?shī)^斗,
“它們并不識(shí)得任何一個(gè)人類”
它們只是風(fēng)中之瀑
上帝啊,那些愛(ài)他的人都在種植,他們都
因?yàn)椴磺笊踅舛畹脧娜?/p>
我們都因?yàn)樯系鄱兊糜H近起來(lái)
那些樹(shù)木,“也是我們的夢(mèng)境、臉譜和無(wú)
數(shù)風(fēng)聲”
12
花木會(huì)凋落嗎?似乎是不會(huì)的……(它們比人類的生命感更為強(qiáng)烈……)(但它們不會(huì)感知自己的生命?)(是的,它們活著是天然的……)
我從未以熱淚迎迓。我討厭贊頌。我們同樣忍受心靈的悲苦:你無(wú)情無(wú)愛(ài)的生命已經(jīng)去遠(yuǎn)了。你是一個(gè)死亡的圓心。你一定執(zhí)著地踟躕、邂逅。你一定有過(guò)熱血,但已經(jīng)冷卻。你靈魂的直徑中沒(méi)有刀器,因此是無(wú)力的。你一定茫然于命運(yùn)的邂逅,茫然于歲月的梗阻,茫然于無(wú)愛(ài)的悲傷(令他人深感戲謔的悲傷:“從何談起”的愛(ài)與悲傷)。你一定是無(wú)力的,但有過(guò)勇敢的熱血的末路?但有過(guò)曾經(jīng)的高谷的囚縛?但有過(guò)熾熱的迷戀和朽壞的雙手:拼卻一生的意志,迎來(lái)生命的朽壞的雙手!我們同樣忍受心靈的悲苦。我從未以熱淚贊頌。我們都是孤舟之上的幽囚,沒(méi)有一片鳥(niǎo)羽為死后的我們守墳!
13
“動(dòng)態(tài)戀愛(ài)”可以使感情迅速地生殖,它極其富有表演性,因而可以使我們“回味無(wú)窮”,但也正因如此,當(dāng)它的衰敗來(lái)臨的時(shí)候,那失戀者就會(huì)覺(jué)得他(她)的悲傷更重一些。我們應(yīng)該對(duì)黯然神傷的人賦以更高的理解。
美貌而單純的人也頗有聒噪的動(dòng)力,因?yàn)樗齻冇袝r(shí)也知道自己已經(jīng)被寵壞了。她們以這種感覺(jué)性的聒噪來(lái)表達(dá)對(duì)這個(gè)世界的熱愛(ài)。
我很清楚,她們的經(jīng)驗(yàn)來(lái)自感同身受,她們以為這種壓力是內(nèi)在而長(zhǎng)遠(yuǎn)的,因此她們也在為了事實(shí)獻(xiàn)身。她們是不斷被創(chuàng)造的、不斷被(自我的判斷力)扼殺的一代人。
正因?yàn)橐磺袆?dòng)因都不可預(yù)見(jiàn),所以我們才會(huì)對(duì)動(dòng)人的美貌吃驚。但假如這一切只屬于我們自身(大自然),只屬于花開(kāi)葉落,那困境就不必再有;我們引入、信服自然的歧途(美貌)即可。有一年我在歸鄉(xiāng)的時(shí)候想到了(也看到了)鳥(niǎo)巢,也看到了守候在墓地旁的婦人。在剛剛開(kāi)墾出來(lái)的鄉(xiāng)村道路上,僅僅有一個(gè)像她這樣的婦人。她喃喃自語(yǔ)著,也忽視著萬(wàn)物(過(guò)路的人和車輛造成的喧囂)。就是這樣:我離開(kāi)的時(shí)候天空晦暗下來(lái),鳥(niǎo)鳴也始終不見(jiàn)一發(fā)。但天空卻突地晦暗下來(lái)……
斜陽(yáng)金燦燦
陽(yáng)光多亮啊,我想不出比它更為“金燦燦”的事物了!
生活剛剛開(kāi)始,但我們尚未付出任何努力便目睹陽(yáng)光西移(生活的流逝),許多樓廈的墻體已被遮蔽而形成一大坨陰影——這一切真使人觸目驚心。目下我站在高處憑空遠(yuǎn)眺,但我什么都抓不住。光線侵入的地界落在遠(yuǎn)處的懸崖之下,坦白而論,這便是我從未意識(shí)到的溝壑之一種。
我的一大部分命運(yùn)(作為練習(xí)期的生命體)已經(jīng)終結(jié)。無(wú)論如何,我的各種遭逢不會(huì)重新來(lái)過(guò)。我不會(huì)一味地誠(chéng)實(shí),也不會(huì)成為奸滑之徒。我不會(huì)淪落,也不會(huì)上升。在各種星座的羽翼下,那持守如一的戀人們都是堅(jiān)韌和快活的。在各種生活的羽翼下,雨水會(huì)變成瀑布而不歇地涌流——我固然會(huì)因此身受未來(lái)的脅迫,但也僅僅如此而已!
十九年前我穿過(guò)柵欄,我的生活教會(huì)我的——我的意思是——我穿過(guò)柵欄——十九年了。我快樂(lè)地生活著?十九年了。昔日已歿,該死的都死了。該死的,十九年了。我的昔日的姿勢(shì)已歿。我的青春的容顏、渴望愛(ài)的歡樂(lè)和惆悵已歿。我無(wú)法說(shuō)出的一切無(wú)所見(jiàn)已歿。惆悵的,動(dòng)物家園已歿。高山精髓已歿。對(duì)于我來(lái)說(shuō),該死的都死了。我的九曲舊日的我已歿。那些富有震撼力的生活啊真是好極。登臨天梯的痛快已歿。
我完全地住了下來(lái)……這樣,我的心便可以離你更近一些。我致力多年的那個(gè)謎題已經(jīng)與你相知相依,我的心里也長(zhǎng)枝長(zhǎng)葉,它們撐得我好不難受。但是,既然選擇了這樣一種生活,我便只能離斜陽(yáng)更遠(yuǎn)。天色浩蕩,你沿大路行去便可。如果路遇你的祖父母或些許美女,你徑直走過(guò)去罷了。這樣的生活既不需要承載,又無(wú)關(guān)統(tǒng)屬,那它便只能停留于永恒的記憶。你正在經(jīng)歷的生活、希望與記憶的根脈是一樣的。斜陽(yáng)一至,有多少山水都是一樣的。它涂抹在那里的金色日漸黯淡,亦或從無(wú)凋落?但無(wú)論如何,它們的本質(zhì)是一樣的。自天地分極以來(lái),屋頂斜陽(yáng),地穴斜陽(yáng),它們的本質(zhì)是一樣的。如果萬(wàn)物都不存活,光明的朗闊與勞逸也是一樣的。我完全地住了下來(lái),愧怍于再無(wú)一顆斗士心,這樣,我與你的心便是一樣的……
這種迷戀不對(duì),因?yàn)樗赶虻氖亲屏业氖セ稹K鼤?huì)視這種“將你烤為灰燼的歷程”為迷戀的反叛(堆積)。好了,在只有兩人相攜而行的漫步中,天邊暮色泛起,春天次第蒞臨。你看到的是一些殘破的墻體。差不多有五百年的光陰了,樹(shù)木的根部已被燒焦。你如何呈現(xiàn)這個(gè)漫長(zhǎng)的時(shí)間的度量?在繁重的尺幅之間,那些鏡子般的精細(xì)的雕刻已經(jīng)被灰塵浸透了(塵世之色),你再也不會(huì)看見(jiàn)匠人們生動(dòng)的創(chuàng)造性手指。他刻畫(huà)的是哪一日的古老斜陽(yáng)?他刻畫(huà)的是哪一日的生死未盡、茫茫別離?他刻畫(huà)的是哪一堵剩余的墻?至于那根本未在的秩序、已經(jīng)湮滅的地理學(xué)、刻意鑄造成贗品的匠心也都是孤獨(dú)(未在)、嘆息和逃逸的。至于那一晝夜的翻騰、一晝夜的想象力的饑餓現(xiàn)場(chǎng)、一晝夜的溫差小丑,也都是孤獨(dú)和逃逸的饕餮盛宴。也都是從一面斜坡上下來(lái),僅僅是一念之間的“從一面斜坡上下來(lái)”(滾落下來(lái)),充滿了忐忑和畏懼心的生物性的逃逸!也都是你已行行至遠(yuǎn),而人間復(fù)濁流清酒,看不到一處溫暖的峽谷(供隱居者在?供暢談的豪奢的情意在?),看不到剛剛過(guò)去的一個(gè)分秒,而斜陽(yáng)在山外青山!而斜陽(yáng)已在山外青山?!
即是你可以激發(fā)自己的無(wú)窮幻象,但也沒(méi)有任何一種征兆可以預(yù)示你最終將完成它。意義的增長(zhǎng)看起來(lái)將覆蓋和埋葬一切,之后重新蒞臨的事物將抵消這種自我內(nèi)部的期冀和奮爭(zhēng)。有時(shí),你不必采用任何譬喻便可以接近你的結(jié)論,在你的內(nèi)心中,它是重點(diǎn)隱沒(méi)的部分,不需要昭然顯示,卻最有可能在一絲微光中向未來(lái)延展。這是敞開(kāi)的事物(結(jié)論),如同重復(fù)過(guò)的一日重新流動(dòng)。你自然寵信,征引過(guò)這樣的結(jié)論,像流連于怨天尤人的人間芳草。水聲潺湲的時(shí)日來(lái)到了,你高佇于峰頂?shù)囊股校軌蝰雎?tīng)和感受天籟之應(yīng)許。多重幻象經(jīng)過(guò),你吃力地看到“多重幻象經(jīng)過(guò)”,在光滑的“看到”和尖利幻象的“刺入”中,這可能是最重要的時(shí)刻卻須臾不可得。你無(wú)法抓捕和貼近這樣的時(shí)刻(斜陽(yáng)),它似乎常在須臾和物外而不可負(fù)載(沒(méi)有承受力和歸宿心)。你餓了嗎?面對(duì)幻象(渡河之恐懼),你會(huì)產(chǎn)生無(wú)窮的饑餓?但上帝卻吝惜他最后的日出,大地上從此一片凋敝和荒蕪。
一只斜陽(yáng)迷路了,從此它便向萬(wàn)物(速度)屈服。它是迄今最高的屈服的力量。它本是一無(wú)所知的燃盡的力量,但就在它的若即若離中成為一種更高的榮耀的斜陽(yáng)。無(wú)情的生命被漸漸埋葬:在花叢中,一個(gè)國(guó)王和他的仆人們迷路了。追蹤而來(lái)的旅人們都迷路了(望梅止渴的旅人們)。一只斜陽(yáng)以無(wú)窮的盲目的自信派遣無(wú)數(shù)部伍出行,但是雛鷹和瀚海都迷路了。從此它便向自己的無(wú)知屈服。萬(wàn)物都被一無(wú)所知地燃盡了,除了那凜冽的風(fēng)再?zèng)]有任何榮耀的殘存等著……一只斜陽(yáng)迷路了,從此便是無(wú)盡的殘骸和碧波,它一無(wú)所知,但也從未突破地迷路了(日出的快樂(lè)和時(shí)光的殘局)!
死亡的破碎
1
在最觸及呼吸之痛的民間,死亡的爆裂可能是不存在的。它是“日常性的,呼吸之痛和死亡”。
許多不想死的人后來(lái)都死了(將來(lái)?卻未必),但許多不想生的人是否還可以生存下去,這是個(gè)事關(guān)宇宙構(gòu)建的大問(wèn)題?不,人類的存在向來(lái)渺小如塵埃。這里沒(méi)有任何問(wèn)題。破碎的宇宙也從來(lái)不容納此類思考。
我們死前的依依別情,深為上帝所不喜,因?yàn)樗赡芊鬯榱松系刍没暗乃杏洃洝?/p>
2
真正徹底地將我塑型的是這些秋雨里的秘密詩(shī)意,是這五年中次第而來(lái)的“死亡消息”,是我的閱讀中使我“哽咽”的那一面,是影響力的殘余值;但根本不是他們的名字和面相。真正徹底地將我塑型的,是我不自知的“感覺(jué)主義”詩(shī)句?真正徹底地將我塑型的是我的“出生”,但根本不是我在這世界上所經(jīng)歷的一生“命運(yùn)”(命運(yùn)有時(shí)兼帶了他人感,但出生、落地卻是不可更改的真實(shí)的“虛擬”)。真正徹底地將我塑型的是我的內(nèi)心音律,但根本不是那些外物。我因此是死亡的感覺(jué)的殘余值?(“死亡”,才是真正徹底地將我塑型的“萬(wàn)千造物”!)
3
我是見(jiàn)證自己的人
我是見(jiàn)證自己生和死的人
我見(jiàn)證這一切,只需要幾個(gè)須臾
但我卻跨越了一生
在我生下來(lái)的時(shí)候,一切都與現(xiàn)在不同
在我死的時(shí)候,一切都與現(xiàn)在不同
我只是在小心翼翼的一瞥中發(fā)現(xiàn)了
一切天機(jī):我是見(jiàn)證者卻不覺(jué)察的人生
行走和冥思帶走了我
閱讀和寂靜帶走了我
怒火和喜悅帶走了我
我是見(jiàn)證者,這沒(méi)有過(guò)錯(cuò)
但我為什么只是見(jiàn)證者,我沒(méi)有投入地活
過(guò)
這深情的人世啊,它只是怪我沒(méi)有深情地
活過(guò)
我覺(jué)得多么恐慌、單調(diào)和饑餓……
4
若思之過(guò)深,則人生的無(wú)數(shù)奮爭(zhēng)和糾結(jié)顯然沒(méi)有太大的意思。我們除了向窮途(老邁、心神的衰敗)奔突,還哪里有什么道路可走?
或者,是為了使自己回味往事時(shí)的遺憾少些,才努力和莊重地活著,但生命如秋風(fēng)落葉,我們又何曾知道自己的命運(yùn)之樹(shù)能結(jié)出怎樣的果子?
5
只有活著才能感受一切?而死亡是泯滅、破碎。但人間如此擁堵,如此近于“部分破碎”,一點(diǎn)一滴的“泯滅、破碎”。
只有活著才可看到江河、花果?而死亡形同空洞山川,“小小寰球,無(wú)窮天宇”。死亡是“天地大荒,萬(wàn)物皆老”?
只有活著才可看到人間儀容、云中錦繡?而死亡只是一小捧灰。死亡是與永恒的團(tuán)聚?是徹徹底底的風(fēng)之靜謐:無(wú)窮的靜謐,“宙斯之流動(dòng)”?
只有活著才可觸摸世界方圓、愛(ài)恨之萬(wàn)千形象?而死亡并非永生。沒(méi)有永生:只有一小捧“不可言喻”,形如不存之灰。死亡是宇宙的收縮。
沒(méi)有蟲(chóng)蟻,沒(méi)有識(shí)別,形容枯槁,只有與自我(無(wú)知覺(jué)的)團(tuán)圓?“死去元知萬(wàn)事空”之團(tuán)圓?死亡是自我的無(wú)窮收縮。
只有死亡才能粉碎一切?而活著只是寓言、象征,人生無(wú)意義的說(shuō)明書(shū):自我之空曠、無(wú)聊賴之說(shuō)明書(shū)。活著是人生未來(lái)之預(yù)設(shè)?是對(duì)世界的無(wú)窮想象、縮小之感知?
只有生死之無(wú)知?jiǎng)e、不趨同。只有死亡如此:曾經(jīng)無(wú)比的熟悉、親近,形如“陌生之虛構(gòu)”。我們與無(wú)窮生者不識(shí),與無(wú)窮已逝不識(shí)。生死是無(wú)窮的見(jiàn)證與不識(shí)。
“我如我佛如來(lái),賜爾風(fēng)清月白”。
6
我們能否確切地感知自己的存在?即使在如同死亡一般的睡眠中(做夢(mèng)只是死亡的一種過(guò)渡形式)?那些昨日之風(fēng)吹動(dòng)我們身體的外圍,一切活著的外物都籠罩在我們身體的外圍。一切外物都不會(huì)真正地進(jìn)入,除了夢(mèng)幻之時(shí)不可遏制的真實(shí)。但它是死亡的一種過(guò)渡形式。我們?cè)趬?mèng)境中,看到了生命這棵卑微之樹(shù)的“沉淀的形式”。
有時(shí),是某個(gè)熟人的死亡帶走了你自足的觀望(生命永無(wú)盡頭),帶走了你生命的物質(zhì)的一部分,因此死亡才是生命的最高形式。在此之前,所有生命的秩序都是混亂而盲目的。你不可能知道你的未來(lái),即使把一切外在的理想都算計(jì)在內(nèi),你仍然不可能知道你的未來(lái)。河水流過(guò)的河床,偉大君王締造的國(guó)度,都在“流動(dòng)的風(fēng)”的吹拂之中變成了陳舊的生命事實(shí)。它們是曲折的,不在現(xiàn)實(shí)境遇內(nèi)的古物。
鄰人的消逝和遠(yuǎn)方親人的消逝,共同作用于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命消逝也僅僅只是風(fēng)中流動(dòng)的曲折、柔軟、不可觸摸的帳幕。我們慢慢地懷想著一次一次的死亡,所有懷想的作用力共同指向我們的最終消逝。我們能夠確切地感知自己的死亡之時(shí),一切可以形諸記錄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也不必存在了。因?yàn)樗劳鋈缤覀儽拔⒌鼗钪氖聦?shí),它從來(lái)沒(méi)有自己的確切名字。
7
院子里的生靈都漸漸地消逝了,那些誕生在二○○○年之前的生靈(作為我記憶中夢(mèng)幻的一面),都漸漸地消逝了。我以為這是永久性的,永不會(huì)復(fù)生的消逝。不會(huì)在空氣中再度長(zhǎng)出翅羽的消逝,也不會(huì)再度噴著響鼻站在牛欄里的消逝。我在大路上碰到的行人,也在部分消逝中降低了記憶中事物(生靈)的濃度。為了捕捉這樣“不可消逝”(一種期冀)的靈魂勝境,我站在院子里(曾經(jīng)“砌筑”有牛欄的院子)仰望藍(lán)色星空,我幻想在一個(gè)跺足之間便可躍上星空(不再降落凡塵)的消逝。我在仰望和站立之中迷茫頓生,因?yàn)槲乙呀?jīng)回想不起最為具體的生靈的誕辰和他(它)的消逝。我甚至無(wú)法悉知我們的生死(時(shí)光狙擊?)和消逝。天將暮時(shí),夜色變得廣闊起來(lái),我感到了一種無(wú)與倫比的“美麗消逝”:我們何曾活過(guò)(思索過(guò))?我們只是站立在時(shí)光濃縮儀前的渺小囚徒罷了(一種簡(jiǎn)潔的筆墨的暈染、消逝!)。
8
死亡,對(duì)絕大多數(shù)人的生命來(lái)說(shuō),都是完整的終結(jié)。因?yàn)樗廊サ纳粫?huì)思考,不再建功立業(yè),不會(huì)再作為具有深度存活價(jià)值的個(gè)案激發(fā)他人的任何思考。“死亡”,是真正的終結(jié)!有形的遺產(chǎn)也是。渺小的,凡俗意義上的死亡并不關(guān)切死亡的任何本相,所謂“死亡的灰塵”罷了。在這個(gè)意義上,任何遺書(shū)的效用都不顯明。因?yàn)檫z書(shū)也是僵死的,而真正能使死亡復(fù)蘇的,只有死亡肌體內(nèi)的力。可以穿越時(shí)光的力!或許,閱讀之內(nèi)所蘊(yùn)藏的,便是這樣的力。我經(jīng)常會(huì)以為羅扎諾夫未死,佩索阿未死,尼采未死,卡夫卡未死,羅蘭·巴特未死,齊奧朗未死,因?yàn)槲乙呀?jīng)用了很長(zhǎng)時(shí)間在與他們對(duì)話。至少,在如我者的內(nèi)心里,“逝者”是永生的,因?yàn)槭耪呶此馈N蚁騺?lái)不曾在他們的生命中看到“死亡的灰塵”罷了!
9
假如你死后有人懷念你
你的靈魂和夢(mèng)幻都已無(wú)法感知
你已經(jīng)活過(guò)了一生,睡了一生
醒了一生,動(dòng)蕩了一生
那些木頭人都已成真,那些木頭人慢吞吞
它們都已長(zhǎng)大成人,而你已然活過(guò)了一生
那些靈魂和夢(mèng)幻都不正確
它們應(yīng)該果斷地傳送、截?cái)啵衩鎸?duì)一座
大如宇宙的高山
有時(shí)靈魂就是一些路人、旅人、巨人
當(dāng)你死后,那些出神的部分也開(kāi)始懷念你
看你漸漸變成死灰的面容
肆意地談?wù)撃愕囊簧路鹉愕慕?jīng)過(guò)不是
真的
這個(gè)世界上,沒(méi)有你的體溫,沒(méi)有任何錯(cuò)
誤
但是假如有人懷念你,你已無(wú)法感知
但是假如你無(wú)法感知,這便是真的
你的死和殘存的愛(ài)是真的,我們真是慶幸
啊
終于這樣“緩慢地活過(guò)了一生”
你毫無(wú)怨言,已無(wú)怨言,雖然日出仍在繼
續(xù)
但光芒無(wú)限,它們?nèi)绾窝絹?lái)
它們?nèi)绾卫^續(xù)盤旋呢,那臭烘烘的熱焰
像你經(jīng)過(guò)的大大的時(shí)間,像你已經(jīng)開(kāi)始腐
爛的大大的臉
虛幻的臉
如果這要放到從前是多么不可思議的事
但是現(xiàn)在,這所有的種種都無(wú)比正確
我們只是在懷念中度過(guò)一生,并利用漫長(zhǎng)
的祭奠
將你描繪成不存在的星辰
10
我想親手埋葬我。我看著一個(gè)我躺下去,他真的是我的全部生活?那高墻阻擋了我,我建立了非我的學(xué)說(shuō)……
從我的尸體上誕出我的法身,我即是我的悟空。
時(shí)間的創(chuàng)造是上帝有生以來(lái)最偉大的藝術(shù),而我的隱憂在于“無(wú)法全神貫注”。我常常會(huì)想到,上帝已經(jīng)去往別處,但我們卻在一個(gè)無(wú)人看管的荒野中放任自流。
遠(yuǎn)在九十九年前,他死了。那時(shí),我還沒(méi)有出生。現(xiàn)在的我,一部分已經(jīng)死了,另一部分仍然沒(méi)有出生。我的我不會(huì)全部都死了,永遠(yuǎn)都不會(huì)。因?yàn)槲襾?lái)過(guò)這個(gè)世界,所以,我們都一樣的。我們都會(huì)進(jìn)入一個(gè)輪回,也許我們的未來(lái),是我先生,也許我們的未來(lái),是我不至。但無(wú)論如何,我們的生與死都一樣的:反反復(fù)復(fù),沒(méi)有絲毫不同。
11
離我們最近的年輕朋友(寫(xiě)作者)去世后,我們有一種突然理解了死亡的感傷?這種凸起的“觸探死亡”(注視他的遺容)是我們無(wú)法回避的中年功課。我們必然離不開(kāi)這樣分外切近的注視。目睹這種“形容的消瘦”會(huì)使我們想到去日如流、生命如泡影、忽忽如電!因此,能夠站在陽(yáng)光照徹的曠原上觀察萬(wàn)物(流連于人世風(fēng)景)是好的:一種幸運(yùn)感的降生?即使是“命運(yùn)多舛”的賜予也極為不朽,可為我們庸碌生活中的珍肴!因此,我們隱蔽的心理中存有萬(wàn)物最終的言語(yǔ)(灰燼),但天籟靜極,天籟望斷山川,天籟說(shuō)不出話來(lái)?!
責(zé)任編輯?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