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際更替視角下中國(guó)第六代導(dǎo)演的內(nèi)卷化現(xiàn)象
孟 君
(武漢大學(xué) 藝術(shù)學(xué)院, 湖北 武漢 430072)
一、代際更替中的第六代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斷言:“歷史不外是各個(gè)世代的依次交替。”①中國(guó)電影的歷史敘述方式有多種傳統(tǒng),其中的一個(gè)傳統(tǒng)便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shuō)的代際更替方式,以各代導(dǎo)演的依次更替勾描出自中國(guó)電影發(fā)生迄今的整個(gè)歷史。社會(huì)學(xué)語(yǔ)境中的代際更替是指代際間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位置的變動(dòng)和社會(huì)成員階層地位的變動(dòng),人文學(xué)科領(lǐng)域中的代際更替有所不同,既體察外部事實(shí)的物質(zhì)變動(dòng),更注重主體內(nèi)在的體驗(yàn)和觀念衍變。以代際更替的視角觀照中國(guó)電影,不同代際電影導(dǎo)演群體的先后更迭構(gòu)成了百余年來(lái)中國(guó)電影的發(fā)展史脈,他們的結(jié)構(gòu)和地位在不斷變動(dòng),同時(shí)他們的電影美學(xué)觀念也在發(fā)生變化。
第六代導(dǎo)演的代際更替是中國(guó)電影史宏大敘述的一個(gè)微觀環(huán)節(jié),梳理第六代自20世紀(jì)90年代初至今“長(zhǎng)大成人”的時(shí)間鏈,可以看出第六代在致力于“我代”構(gòu)型的同時(shí),完成了從誕生到成熟的代際更替過(guò)程。第六代導(dǎo)演20世紀(jì)90年代初先后開始創(chuàng)作,在90年代中后期確定了由路學(xué)長(zhǎng)、張?jiān)①Z樟柯、章明、王小帥、婁燁、張楊、管虎、施潤(rùn)玖、李欣等構(gòu)成的導(dǎo)演群體,他們?cè)谧髡呱矸荨㈦娪爸黝}、故事題材、電影人物、敘事話語(yǔ)、影像風(fēng)格、制片方式等方面形成較為趨同的特征,并由此取得合法的代際命名,使得第六代最初尋求身份認(rèn)同的焦慮得以釋放。
前后代際的更替不可避免地存在代際交疊與沖突。事實(shí)上,第六代的“成人”與第五代的“退場(chǎng)”有長(zhǎng)達(dá)十多年的重疊期,這是此消彼長(zhǎng)、矛盾叢生的一個(gè)時(shí)期,也是當(dāng)代中國(guó)電影極為精彩的一個(gè)時(shí)期。最具象征性的沖突發(fā)生在2006年,《三峽好人》和《滿城盡帶黃金甲》兩部影片同期上映,因院線排片大幅度傾斜而引發(fā)沖突,雙方公開表達(dá)不滿。結(jié)果是,《滿城盡帶黃金甲》在排片和票房上大獲全勝,但在口碑上被廣泛詬病。與此同時(shí),《三峽好人》雖然票房不佳,卻斬獲威尼斯電影節(jié)金獅獎(jiǎng)。這一事件標(biāo)志著第五代和第六代導(dǎo)演的激烈交鋒,焦點(diǎn)是彼時(shí)兩代導(dǎo)演在電影觀念和價(jià)值立場(chǎng)上的不同選擇。選擇商業(yè)大片的第五代由此集體走向衰敗,陷入在電影票房和藝術(shù)審美之間艱難尋求平衡的泥沼中;而堅(jiān)持作者主體性的第六代則在經(jīng)濟(jì)、意識(shí)形態(tài)和大眾審美的壁壘下尋求突圍,試圖踐行電影的審美功能和社會(huì)功能。最終,由于第六代導(dǎo)演及其作品獲得國(guó)際電影節(jié)認(rèn)可,并逐漸被國(guó)內(nèi)觀眾所接納,第六代逐漸從中國(guó)電影生態(tài)域的邊緣游弋至中心,取代第五代導(dǎo)演成為當(dāng)下中國(guó)電影的主流創(chuàng)作群體。管虎的《八佰》、張楊的《岡波仁齊》、章明的《冥王星時(shí)刻》、賈樟柯的《江湖兒女》、王小帥的《地久天長(zhǎng)》、婁燁的《風(fēng)中有朵雨做的云》等新近作品上映后產(chǎn)生的影響表明第六代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yàn)、認(rèn)知度和號(hào)召力均處于成熟期和高峰期,這標(biāo)志著中國(guó)電影已完成新一輪的代際更替。
以“代”命名導(dǎo)演群體,這一慣用的影史探賾方式植根于導(dǎo)演群體存在大量的共同特征。回溯第六代導(dǎo)演的創(chuàng)作可以發(fā)現(xiàn),完成代際更替后的第六代始終保持著整體上的趨同性,盡管因種種原因在路學(xué)長(zhǎng)、張?jiān)垪睢⒐芑⒌热松砩铣霈F(xiàn)分化,但是作為群體的第六代在當(dāng)下呈現(xiàn)出許多頗為穩(wěn)定的代際特征,尤其是在賈樟柯、王小帥、婁燁、章明等人身上表現(xiàn)得最為顯著。從《小武》《世界》《三峽好人》《二十四城記》《天注定》《山河故人》到《江湖兒女》的電影序列便具有顯著的穩(wěn)定性,盡管賈樟柯嘗試了不同的敘事時(shí)空,但在題材、人物、話語(yǔ)、風(fēng)格等諸多層面始終保持著統(tǒng)一性和穩(wěn)定性。不僅是賈樟柯,王小帥、婁燁、章明也是如此。第六代導(dǎo)演群體在近三十年來(lái)具備許多共同之處——他們秉持作者身份,關(guān)注中國(guó)現(xiàn)實(shí),描摹邊緣人物,強(qiáng)化敘事方式,突出電影風(fēng)格,敘說(shuō)個(gè)人感受,在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意識(shí)形態(tài)和全球化浪潮的夾縫中堅(jiān)持以個(gè)體方式進(jìn)行思考和表達(dá)。
上述穩(wěn)定的代際特征已成為辨識(shí)第六代的根本依據(jù),并成為第六代的身份標(biāo)志。與此同時(shí),第六代另一極為重要的動(dòng)態(tài)特征,即他們的成長(zhǎng)性卻容易被忽略。成長(zhǎng)性是指導(dǎo)演在不同創(chuàng)作時(shí)期呈現(xiàn)出的差異性變化,從誕生、獲得命名到成為主流,第六代在不同時(shí)期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呈現(xiàn)出動(dòng)態(tài)的變化。不穩(wěn)定的成長(zhǎng)性表明,僅以靜態(tài)的、標(biāo)簽化的方式考察處于動(dòng)態(tài)更替進(jìn)程的第六代并不全面,從代際更替的視角辨析第六代如何以及為何呈現(xiàn)出整體性的變化是更契合第六代現(xiàn)狀的應(yīng)對(duì)方式。比較第六代的處女作和新作可以發(fā)現(xiàn),第六代大體上仍然堅(jiān)持“一生只拍一部電影”的純粹作者觀念,但“個(gè)人風(fēng)格的連續(xù)性”的作者立場(chǎng)在時(shí)間的游涉中又發(fā)生著細(xì)微的變化:他們的主人公從“少年我”變?yōu)椤俺赡晁?她”,尖銳的主觀視角變?yōu)槔潇o的旁觀視角,凝固的歷史時(shí)間變?yōu)槁L(zhǎng)的宏闊史詩(shī),異質(zhì)性的小鎮(zhèn)意象變?yōu)槠者m性的城市意象,單一的自傳空間變?yōu)槎鄻印⒆儎?dòng)的社會(huì)空間……如此大量而趨同的變化無(wú)疑是第六代逐步走向成熟而產(chǎn)生的結(jié)果,這一普遍性的動(dòng)態(tài)演變趨勢(shì)可稱之為“內(nèi)卷化”(involution)現(xiàn)象。
“內(nèi)卷化”最初由美國(guó)學(xué)者戈登威澤(Alexander Goldenweiser)和格爾茨(Cliford Geertz)分別用于對(duì)文化模式和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的分析,其基本含義是指系統(tǒng)在外部擴(kuò)張條件受到嚴(yán)格限定的條件下,內(nèi)部不斷精細(xì)化和復(fù)雜化的過(guò)程②。“內(nèi)卷化”后來(lái)被廣泛應(yīng)用于社會(huì)學(xué)乃至整個(gè)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領(lǐng)域的研究,指一個(gè)社會(huì)或組織既沒有突變式的發(fā)展,也沒有漸進(jìn)式的增長(zhǎng),而是處于一種不斷內(nèi)卷、自我復(fù)制與精細(xì)化的狀態(tài)。就賈樟柯、婁燁、王小帥為代表的中國(guó)第六代導(dǎo)演而言,比較他們的早期作品與新作可以發(fā)現(xiàn),第六代呈現(xiàn)出典型的雙重內(nèi)卷化趨勢(shì):一方面,第六代導(dǎo)演的敘述技巧和影像技術(shù)較之以往普遍變得越來(lái)越成熟,敘事話語(yǔ)趨于精細(xì)化;另一方面,他們的敘述對(duì)象和電影主題陷入自我重復(fù),意義生產(chǎn)趨于收縮化。
二、敘事話語(yǔ)的精細(xì)化
第六代在登場(chǎng)之初便以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觀和獨(dú)特的影像風(fēng)格著稱,以賈樟柯為代表的寫實(shí)主義風(fēng)格和以?shī)錈顬榇淼男问街髁x風(fēng)格均用于指涉當(dāng)代中國(guó)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以不無(wú)激進(jìn)的抗?fàn)幏绞絽^(qū)別于第五代的宏大敘事和歷史寓言。事實(shí)上,“敘事遠(yuǎn)非一個(gè)中立的媒介,以完美的透明性表現(xiàn)虛構(gòu)或真實(shí)的事件,敘事是一個(gè)獨(dú)特的體驗(yàn)和思考世界及其結(jié)構(gòu)和進(jìn)程的話語(yǔ)表達(dá)方式”③。第六代的敘事從來(lái)都不是“中立的”和“透明的”,他們集體選擇以風(fēng)格化的敘事技巧描述邊緣化的社會(huì)生態(tài),這是自覺的文化身份抗?fàn)幒驼勁校聦?shí)證明這也是極為有效的代際更替策略。正如海登·懷特所說(shuō),“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出現(xiàn),除了具有其他意義之外,還意味著拒絕寓言,尋找一個(gè)更完美的文學(xué)表達(dá)方式,來(lái)排除任何修辭技巧。”④對(duì)第六代而言,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敘事策略既用于“拒絕寓言”的意義悖逆,也用于“修辭技巧”的話語(yǔ)抗?fàn)帲诹且袁F(xiàn)實(shí)主義的電影觀和極度風(fēng)格化的敘事話語(yǔ)作為“方法”進(jìn)行代際更替的,并穩(wěn)固下來(lái)成為第六代的可識(shí)標(biāo)簽。
第六代的兩種敘事風(fēng)格殊途同歸,指向同一個(gè)敘事目的。寫實(shí)主義是第六代的主要敘事風(fēng)格,表現(xiàn)為:敘事話語(yǔ)偏好使用長(zhǎng)鏡頭、自然光效、同期錄音、客觀鏡頭、聲畫對(duì)位;在故事結(jié)構(gòu)上采用線性敘事,情節(jié)線簡(jiǎn)潔連貫;敘事焦點(diǎn)并不總是聚焦于主要人物,而是游離主要人物對(duì)人物群體進(jìn)行散點(diǎn)透視。賈樟柯的《小武》、王小帥的《青紅》、路學(xué)長(zhǎng)的《卡拉是條狗》、張楊的《洗澡》、施潤(rùn)玖的《美麗新世界》等大量的第六代電影都是典型的寫實(shí)主義風(fēng)格作品,這些作品以冷靜克制的敘述和沉穩(wěn)緩慢的鏡語(yǔ)反映了中國(guó)社會(huì)的歷史變遷、邊緣人群和社會(huì)現(xiàn)狀。形式主義是第六代的另一種重要敘事風(fēng)格,常采用限知式獨(dú)白或全知式旁白、主觀鏡頭、手持?jǐn)z影、特異性調(diào)色、聲畫錯(cuò)位等話語(yǔ)策略。與實(shí)驗(yàn)電影和先鋒電影有所區(qū)別的是,第六代的形式主義實(shí)踐不是為了運(yùn)用形式的游戲去表達(dá)抽象的思想或邏輯,而是一種用敘事主體的內(nèi)在精神世界詮釋外部現(xiàn)實(shí)的敘事策略,婁燁的《蘇州河》、章明的《巫山云雨》、王小帥的《冬春的日子》、李欣的《花眼》、張?jiān)摹稏|宮西宮》、路學(xué)長(zhǎng)的《長(zhǎng)大成人》、管虎的《頭發(fā)亂了》等數(shù)量可觀的第六代作品普遍運(yùn)用形式主義的敘事風(fēng)格表現(xiàn)中國(guó)社會(huì)的種種現(xiàn)實(shí)及其對(duì)人的精神世界的作用。可見,寫實(shí)主義風(fēng)格和形式主義風(fēng)格是第六代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觀的一體兩面,無(wú)論是客觀寫實(shí)還是主觀表現(xiàn),其敘事目的都是描述當(dāng)代中國(guó)社會(huì)現(xiàn)狀和人的生活狀態(tài)。
無(wú)論是奉行寫實(shí)主義風(fēng)格還是形式主義風(fēng)格的導(dǎo)演,在早期創(chuàng)作階段第六代的敘事話語(yǔ)均相對(duì)較為質(zhì)樸,譬如故事情節(jié)簡(jiǎn)單、敘事節(jié)奏緩慢、取景真實(shí)原生、聲音自然粗糙,這種樸拙的話語(yǔ)既形成形式感強(qiáng)烈的風(fēng)格,也造成影片的沉悶和晦澀。亞里士多德在論及詩(shī)和人的天性時(shí)說(shuō):“倘若觀賞者從未見過(guò)作品的原型,他就不會(huì)從作為摹仿品的形象中獲取快感——在此種情況下,能夠引發(fā)快感的便是作品的技術(shù)處理、色彩或諸如此類的原因。”⑤逐步成熟的第六代敏銳地意識(shí)到提升觀影快感的必要性和行之有效的技術(shù)方法,隨著自我身份的確立和地位從邊緣到中心的遷徙,第六代的敘事話語(yǔ)明顯發(fā)生了從質(zhì)樸粗糙到華麗精致的轉(zhuǎn)變。比較賈樟柯的《小武》《站臺(tái)》《任逍遙》和《天注定》《山河故人》《江湖兒女》,王小帥的《冬春的日子》《十七歲的單車》《青紅》和《我11》《闖入者》《地久天長(zhǎng)》,婁燁的《周末情人》《危情少女》《蘇州河》和《浮城謎事》《推拿》《風(fēng)中有朵雨做的云》,從三位導(dǎo)演不同階段作品的差異可以看出,第六代的敘事話語(yǔ)整體上呈現(xiàn)了逐步精細(xì)化的“內(nèi)卷化”編織過(guò)程,在敘事時(shí)間、敘事空間和敘事結(jié)構(gòu)方面的轉(zhuǎn)變尤為明顯。
在敘事時(shí)間方面,第六代早期致力于在精心截取的微觀歷史片段中顯微鏡式地放大當(dāng)代中國(guó)的社會(huì)變遷,新作則集體出現(xiàn)了從節(jié)點(diǎn)性微觀敘事轉(zhuǎn)向史詩(shī)性宏觀敘事的變化。對(duì)史詩(shī)來(lái)說(shuō),主人公的經(jīng)歷就是人類命運(yùn)本身的象征性統(tǒng)一,因?yàn)椤笆吩?shī)中的英雄絕不是一個(gè)個(gè)人。這一點(diǎn)自古以來(lái)就被看作為史詩(shī)的本質(zhì)標(biāo)志,以致史詩(shī)的對(duì)象并不是個(gè)人的命運(yùn),而是共同體的命運(yùn)”⑥。第六代新作普遍使用史詩(shī)性敘事時(shí)間并非純粹話語(yǔ)層面的變化,其中潛藏的雄心是借助宏闊的時(shí)間表現(xiàn)人類整體的命運(yùn)。
賈樟柯是一位具有強(qiáng)烈時(shí)間意識(shí)的導(dǎo)演,他的敘事時(shí)間和故事時(shí)間統(tǒng)一,故事時(shí)間從不抽象虛指,而是選擇具體、清晰的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同時(shí)使用流行音樂、電視新聞、宣傳標(biāo)語(yǔ)等醒目的歷史時(shí)間符碼標(biāo)識(shí)故事時(shí)間,將人物嵌入歷史進(jìn)程和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中。賈樟柯的電影序列清晰展示了從微觀時(shí)間到宏觀時(shí)間的漸變:1997年的《小武》、2004年的《世界》和2006年的《三峽好人》分別選取1997年、2003年和2005年作為故事時(shí)間,故事時(shí)間與現(xiàn)實(shí)時(shí)間基本對(duì)應(yīng);從2008年的《二十四城記》開始,賈樟柯的電影故事具有數(shù)十年的時(shí)間跨度,四段式的故事分別選取1958年、1978年、1982年、2008年四個(gè)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進(jìn)行講述,是點(diǎn)面結(jié)合的時(shí)間設(shè)置;到2015年的《山河故人》,故事時(shí)間得到大幅度的持續(xù)性延展,史詩(shī)性的物質(zhì)時(shí)間降格到人物身上,在漫長(zhǎng)時(shí)間中游涉的人物成為中國(guó)社會(huì)的在場(chǎng)者和見證者。2018年的新作《江湖兒女》的故事時(shí)間長(zhǎng)達(dá)16年,三段式的敘事結(jié)構(gòu)將其分割為三個(gè)時(shí)間點(diǎn)(見圖1)。第一個(gè)時(shí)間點(diǎn)是2001年,巧巧和男友斌斌在大同混跡江湖,巧巧為保護(hù)斌斌入獄5年;第二個(gè)時(shí)間點(diǎn)是2006年,出獄后的巧巧前往三峽尋找斌斌,遭斌斌拒絕后回大同;第三個(gè)時(shí)間點(diǎn)是2017年,斌斌因中風(fēng)回到大同被巧巧收留,結(jié)尾是2018年新年伊始斌斌獨(dú)自離開。賈樟柯采取了慣用的點(diǎn)面結(jié)合方法來(lái)處理敘事時(shí)間,在16年的巨大時(shí)間跨度中截取2001年、2006年和2017年三個(gè)核心時(shí)間,對(duì)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外的時(shí)間進(jìn)行“省略(ellipsis)”處理,這一省略法的特點(diǎn)是“話語(yǔ)終止了,而故事中時(shí)間仍在繼續(xù)流駛”⑦,使得擁有漫長(zhǎng)故事時(shí)間的敘事仍然凝練和緊湊。有趣的是,王小帥和婁燁在新作《地久天長(zhǎng)》和《風(fēng)中有朵雨做的云》中也將微觀的節(jié)點(diǎn)敘事變成巨幅的史詩(shī)篇章,并采用了相似的“省略”法:《風(fēng)中有朵雨做的云》在24年的故事時(shí)間中截取了11個(gè)時(shí)間點(diǎn)(見圖2),《地久天長(zhǎng)》在24年的故事時(shí)間里截取了6個(gè)時(shí)間點(diǎn)(見圖3)。對(duì)敘事時(shí)間游刃有余的技術(shù)性編織和掌控表明,處于成熟期的第六代導(dǎo)演已經(jīng)具備強(qiáng)大的敘事控制能力。
伴隨著時(shí)間的大幅延伸,第六代導(dǎo)演作品的敘事空間也從簡(jiǎn)單的局部空間擴(kuò)展為復(fù)雜的多元空間。在電影敘事中,空間對(duì)故事的組織具有重要意義,它構(gòu)成文本的基本語(yǔ)境,在后現(xiàn)代學(xué)者那里空間甚至“在建立某種總體性、某種邏輯、某種系統(tǒng)的過(guò)程中可能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起著決定性的作用”⑧。和時(shí)間意識(shí)一樣,第六代的空間意識(shí)也具有強(qiáng)烈的自覺性,賈樟柯的山西縣城、章明的巫山縣城、王小帥的貴州小鎮(zhèn)、婁燁的上海都市都在他們的早期電影中承擔(dān)著極其重要的敘事功能。在創(chuàng)作早期,第六代作品的敘事空間與導(dǎo)演個(gè)人的生活空間密切相關(guān),導(dǎo)演選取的敘事空間多為其出生和成長(zhǎng)的故鄉(xiāng),故鄉(xiāng)視點(diǎn)雖然有限卻是創(chuàng)作者激發(fā)情感和欲望的源泉,因此這一時(shí)期的敘事空間雖然簡(jiǎn)單、有限,意義卻豐富雋永。隨著創(chuàng)作進(jìn)入成熟期,導(dǎo)演的生命經(jīng)驗(yàn)遠(yuǎn)遠(yuǎn)超逸故鄉(xiāng)視點(diǎn),他們的視野更為開闊,敘事空間也從各自的故鄉(xiāng)擴(kuò)展為更加廣袤的社會(huì)空間,譬如賈樟柯從山西縣城轉(zhuǎn)向北京、三峽、武漢、新疆甚至是加拿大,王小帥的敘事空間則從貴州小鎮(zhèn)、福建小鎮(zhèn)、武漢轉(zhuǎn)向北京、重慶、包頭。顯然,故事空間上的上述拓展在某種程度上對(duì)應(yīng)著導(dǎo)演個(gè)人生活軌跡的變化。
在第六代導(dǎo)演中,婁燁始終執(zhí)著地書寫都市神話,其電影序列的敘事空間在不同的中國(guó)城市之間遷移,從上海轉(zhuǎn)向北京、武漢、南京、重慶、廣州、香港、臺(tái)北等不同城市,婁燁的空間敘事編碼呈現(xiàn)出從單一到多地、從線性到交叉的精細(xì)化趨勢(shì)。婁燁的早期作品均選取故鄉(xiāng)上海作為敘事空間,最典型的是2000年的《蘇州河》,通過(guò)敘事主體“我”的視角主觀式地展現(xiàn)和闡釋以蘇州河為中心的、處于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的上海,之后是分別于2009年和2014年在南京取景的《春風(fēng)沉醉的夜晚》和《推拿》,再到2012年在武漢取景的《浮城迷事》,婁燁電影中的都市始終是現(xiàn)代人的孤獨(dú)與迷失的單晶喻體。相較而言,2019年的新作《風(fēng)中有朵雨做的云》的空間敘事通過(guò)精心地編織變得十分精致(見圖2),敘事空間從單一城市變成多個(gè)城市,并且多個(gè)城市在史詩(shī)化的時(shí)間線中反復(fù)交叉,交錯(cuò)的空間和漫長(zhǎng)的時(shí)間交織成一個(gè)極為復(fù)雜的電影時(shí)空體。影片的敘事始于2012年的廣州,進(jìn)而故事在1989、1990、1992、1996、2000和2006年的廣州相繼推進(jìn)。在同一時(shí)間點(diǎn)上,作為主要空間的廣州被切分出被拆遷區(qū)、警察局、慧鳴酒樓、游戲廳、養(yǎng)老院、房車等多個(gè)具象空間。影片的敘事還在多個(gè)時(shí)間截片中織入香港和臺(tái)北兩個(gè)次要空間,廣州、臺(tái)北和香港三個(gè)都市在史詩(shī)性的故事時(shí)間里被反復(fù)拆解與重置。時(shí)間與空間經(jīng)過(guò)精密而嚴(yán)謹(jǐn)?shù)慕徊婢幙棙?gòu)成精細(xì)化的復(fù)雜敘事,繁復(fù)的時(shí)空體承載起姜紫成、林慧和唐奕杰等人物的恩怨糾葛,史詩(shī)性地展現(xiàn)了中國(guó)社會(huì)轉(zhuǎn)型期的巨變。流動(dòng)、異質(zhì)的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風(fēng)格是婁燁一以貫之的敘事話語(yǔ)特征,《風(fēng)中有朵雨做的云》中交叉、拼貼的城市迷宮無(wú)疑使得影片的謎樣風(fēng)格更為濃郁。

圖1 《江湖兒女》敘事圖


圖2 《風(fēng)中有朵雨做的云》敘事圖

圖3 《地久天長(zhǎng)》敘事圖
第六代是最偏離中國(guó)電影敘事傳統(tǒng)的一代,在敘事結(jié)構(gòu)方面表現(xiàn)為從早期的單線順敘式結(jié)構(gòu)到復(fù)雜的多段交叉式結(jié)構(gòu)的轉(zhuǎn)變。賈樟柯較為常用的結(jié)構(gòu)方式是線性順敘式結(jié)構(gòu),《站臺(tái)》《任逍遙》《世界》都在既定的故事時(shí)間里按時(shí)間順序進(jìn)行敘述。同時(shí),賈樟柯在結(jié)構(gòu)上偏好使用多段式結(jié)構(gòu),在每個(gè)段落中循用線性敘事,自《小武》開始至《三峽好人》《二十四城記》《天注定》《山河故人》《江湖兒女》中始終沿用這樣的三/四段式結(jié)構(gòu)。如果說(shuō)賈樟柯的敘事結(jié)構(gòu)相對(duì)較為穩(wěn)定,那么王小帥在敘事結(jié)構(gòu)上的轉(zhuǎn)變則較為突兀。從早期的《冬春的日子》《扁擔(dān)姑娘》《十七歲的單車》《青紅》到后來(lái)的《日照重慶》《我11》《闖入者》,王小帥大都是在固定時(shí)空中開展線性敘事,《地久天長(zhǎng)》的敘事結(jié)構(gòu)發(fā)生明顯變化,事件被打散和重新編排,故事敘述變成時(shí)空錯(cuò)位銜接的交叉式敘事結(jié)構(gòu)(見圖3)。影片從1993年劉耀軍夫婦獨(dú)子劉星的溺亡事件開始敘事,接著跳切至2002年講述已舉家搬遷到福建的劉耀軍夫婦與養(yǎng)子的矛盾,隨后影片跳回1986年交代劉耀軍和沈英明兩家人在國(guó)營(yíng)鋼廠時(shí)期的友情和因計(jì)劃生育埋下的悲劇因子,此后影片在三個(gè)時(shí)間點(diǎn)之間反復(fù)交叉推進(jìn)故事,結(jié)尾部分跳切到2010年,完成多重情節(jié)線的綜合處理。精細(xì)復(fù)雜的敘事方式顯然出自精心的設(shè)計(jì),王小帥如此解釋其精細(xì)的編織過(guò)程:“我先把時(shí)間抽掉,然后按照單個(gè)小故事發(fā)展的情節(jié)結(jié)構(gòu)和人物關(guān)系去寫,這樣我就知道是什么情況,接著再插入不同的時(shí)間。我知道如果只用或者不用閃回都不行,而且也要避免平鋪直敘。所以我選擇從中間開始往兩邊倒著發(fā)展,前兩個(gè)小時(shí)我想給觀眾造成海邊是現(xiàn)代時(shí)空的映像,等到后面觀眾才發(fā)現(xiàn)外面還有一層時(shí)空,多時(shí)空同時(shí)交疊,然后形成一個(gè)巨大的情感沖擊。”⑨可見,王小帥對(duì)敘事結(jié)構(gòu)進(jìn)行精細(xì)化處理具有高度的自覺性,懸疑設(shè)置、情緒累積以及對(duì)觀眾的調(diào)動(dòng)能力是其敘事話語(yǔ)上的有意追求。這樣的轉(zhuǎn)變婁燁走得更遠(yuǎn),在早期的《蘇州河》中婁燁已經(jīng)開始嘗試雙重交織的嵌套式敘事結(jié)構(gòu),《風(fēng)中有朵雨做的云》在敘事結(jié)構(gòu)上有更為復(fù)雜的設(shè)計(jì)和處理(見圖2),甚至比《地久天長(zhǎng)》更加精細(xì)。第六代共同轉(zhuǎn)向復(fù)雜的敘事結(jié)構(gòu)帶來(lái)了明顯的效果,精確的設(shè)計(jì)和控制有效地提升了觀眾接受故事的準(zhǔn)確性和穩(wěn)定性,為第六代贏得更多的價(jià)值認(rèn)同和情感共鳴。
《江湖兒女》《風(fēng)中有朵雨做的云》《地久天長(zhǎng)》在敘事時(shí)間和敘事空間方面均進(jìn)行了巨大的擴(kuò)展,敘事結(jié)構(gòu)也在擴(kuò)充的時(shí)間與空間中進(jìn)行繁復(fù)和精致的編織。賈樟柯、婁燁和王小帥新作敘事話語(yǔ)的變化表明,第六代在共同推進(jìn)敘事話語(yǔ)的精細(xì)化。話語(yǔ)的轉(zhuǎn)變產(chǎn)生了顯著的結(jié)果,第六代作品中的沉悶和晦澀被祛除,精細(xì)化的話語(yǔ)使觀眾能夠不費(fèi)力地把握故事并理解導(dǎo)演的表意,這正是第六代內(nèi)卷化現(xiàn)象積極的一面。但是,相應(yīng)付出的代價(jià)是,原本由散亂的情節(jié)、粗糲的影像、開放的結(jié)構(gòu)形成的巨大意義闡釋空間被壓縮。
三、意義生產(chǎn)的收縮化
作為一種系統(tǒng)化的發(fā)展模式,內(nèi)卷化是在邊界固定前提下的內(nèi)生性發(fā)展,內(nèi)部的向外發(fā)展與邊界的對(duì)內(nèi)限制相互作用。對(duì)處于內(nèi)卷化過(guò)程中的第六代導(dǎo)演來(lái)說(shuō),內(nèi)部敘事話語(yǔ)的精細(xì)化受制于外部邊界的限制,導(dǎo)致意義生產(chǎn)不斷收縮,第六代對(duì)中國(guó)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意義闡釋陷入自我重復(fù)。意義生產(chǎn)的收縮化意味著第六代的成熟化并不是不斷自我突破的變化,豐盈的話語(yǔ)掩蓋了代際更替初期敘事動(dòng)力和生命欲望的喪失,“賈樟柯電影宇宙”的出現(xiàn)便是典型的例證。
電影是一個(gè)復(fù)雜的表征系統(tǒng),“表征是通過(guò)語(yǔ)言生產(chǎn)意義”⑩。經(jīng)過(guò)早期的電影實(shí)踐,第六代在語(yǔ)言系統(tǒng)和意義生產(chǎn)之間創(chuàng)造了具有代際特色的表征系統(tǒng),意義的生產(chǎn)也相應(yīng)憑借多種表征方式實(shí)現(xiàn),其中最為顯見的方式是題材的選取。第六代的題材普遍聚焦底層社會(huì)的生存狀態(tài),通過(guò)“真實(shí)影像”展現(xiàn)被第五代所忽略和遮蔽的底層社會(huì)景觀,這也是當(dāng)初第六代作為新生代獲得承認(rèn)的重要原因。第六代的早期作品便大量書寫異質(zhì)的底層社會(huì)景觀,譬如《小武》中與主流社會(huì)格格不入的縣城江湖,《蘇州河》中沿河兩岸船工的灰色生活,《三峽好人》中即將淹沒的移民搬遷區(qū),《洗澡》中被時(shí)代淘汰的老澡堂,《安陽(yáng)嬰兒》中相互取暖的下崗工人和妓女,《東宮西宮》中同性戀群體的邊緣生存,《十七歲的單車》中城市外來(lái)人員的身份困境……王超在談及《安陽(yáng)嬰兒》的題材時(shí)說(shuō):“我希望這是一份獨(dú)特的中國(guó)底層社會(huì)人民生活的影像文獻(xiàn),構(gòu)思和拍攝這部影片我都希望建立在我對(duì)他們現(xiàn)實(shí)生存狀態(tài)之上的精神壓力的觸摸。”歷史地看第六代集體書寫的當(dāng)代中國(guó)底層社會(huì)是中國(guó)電影史中的新景觀,使電影的意指實(shí)踐回歸中國(guó)電影的社會(huì)派傳統(tǒng),以文化表征的方式“介入社會(huì)”,這無(wú)疑是第六代極有價(jià)值的意義生產(chǎn)。
近三十年來(lái),第六代持續(xù)表現(xiàn)廣闊的底層社會(huì)景觀,更為廣泛的底層社會(huì)題材被增添至第六代的電影作品中。譬如《天注定》對(duì)鄉(xiāng)村與城鎮(zhèn)真實(shí)暴力事件的組合與闡釋,《江湖兒女》對(duì)縣城江湖的史詩(shī)化重釋,《推拿》對(duì)失明人群的顯微式展現(xiàn),《冥王星時(shí)刻》對(duì)西部山村傳說(shuō)與文明的追尋,《地久天長(zhǎng)》對(duì)失獨(dú)父母和下崗工人的悲憫……然而,不斷拓展的多樣化底層社會(huì)題材一方面豐富了第六代的語(yǔ)言表象,另一方面也造成意義生產(chǎn)的同質(zhì)化,因?yàn)榇罅繀s同質(zhì)的底層社會(huì)景觀已不復(fù)具有最初的新異性。賈樟柯在《江湖兒女》中基于早期電影空間、人物和情節(jié)建構(gòu)的“電影宇宙”就是同質(zhì)化的電影語(yǔ)言,其意義生產(chǎn)在此收縮和停滯。
與此同時(shí),將邊緣人物作為表意的中介也是第六代的重要表征方式之一。當(dāng)人物作為電影的主要視點(diǎn)時(shí),“他的感知視點(diǎn)是支配性的。這種奇特現(xiàn)象——某人物既是我們觀察的對(duì)象,又是我們的視覺之媒介——經(jīng)常出現(xiàn)于視覺敘事藝術(shù)當(dāng)中”。第六代最初便傾向于描摹社會(huì)邊緣人物的生存狀態(tài),各種社會(huì)邊緣人成為電影的敘事中心:《小武》中四處游蕩的小偷,《北京雜種》中困頓的搖滾歌手,《冬春的日子》中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畫家,《十七歲的單車》中無(wú)法融入城市的農(nóng)村少年,《巫山云雨》中在臆想與現(xiàn)實(shí)之間游離的河道信號(hào)工,《蘇州河》中孤獨(dú)迷茫的都市青年,《長(zhǎng)大成人》中尋找精神之父的北京少年……在中國(guó)電影史上,這些邊緣人物從未以如此廣泛而直接的方式得到創(chuàng)作者的關(guān)注和表現(xiàn)。對(duì)導(dǎo)演而言,這些人物是自我指代的符碼,既是無(wú)法獲得合法話語(yǔ)權(quán)的導(dǎo)演個(gè)體表達(dá)身份焦慮的話語(yǔ)能指,也是處于電影生態(tài)邊緣的新生代導(dǎo)演群體發(fā)出的代際更替宣言。婁燁在談及《蘇州河》時(shí)坦陳:“在這部影片里,我在試圖表現(xiàn)這樣的一種今天中國(guó)大城市的年輕一代人的生活狀態(tài),試圖從一個(gè)電影制作人的角度去觀察這樣的一種狀態(tài),有趣的是這個(gè)電影制作人實(shí)際上也是這一代中的一員,所以實(shí)際上觀看者和被察者成了一回事。”事實(shí)上,也正因?yàn)榈诹鷮⑦吘壢宋镒鳛樽晕視鴮懙谋碚鞣绞剑@些人物才如此獨(dú)特、準(zhǔn)確、深入、動(dòng)人。
令人遺憾的是,第六代導(dǎo)演從電影生態(tài)的邊緣進(jìn)入主流后集體出現(xiàn)自我表達(dá)的乏力,處于電影生態(tài)中心的他們喪失了書寫邊緣人物的動(dòng)機(jī)和生命欲望,逐漸將鏡頭從指代自我的邊緣個(gè)體人物轉(zhuǎn)向泛指他者的邊緣社會(huì)人群。無(wú)論是《江湖兒女》中的沒落幫派成員,《地久天長(zhǎng)》中的失獨(dú)工人家庭,還是《風(fēng)中有朵雨做的云》中的基層官員和暴發(fā)戶,這些角色都是從日常生活中提取的類型人物,是作為客體的他者,而非自我指代的個(gè)體。這一表征方式上的轉(zhuǎn)變導(dǎo)致的結(jié)果是意義生產(chǎn)的收縮,即第六代雖然仍然普遍聚焦邊緣人物,甚至人物的種類更為寬泛和多樣,但這些人物明顯不再承載珍貴的個(gè)人經(jīng)驗(yàn),喪失了曾經(jīng)可貴的生命激情,更大程度上他們只是第六代表現(xiàn)社會(huì)議題的素材。他者化的邊緣人物導(dǎo)致的意義收縮體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一方面,人物群像化。與早期作品中將單個(gè)人物作為主要人物的敘事方式相比,第六代新作發(fā)生了明顯變化,《天注定》《地久天長(zhǎng)》《風(fēng)中有朵雨做的云》中主要人物的數(shù)量大比例地增加,人物群像化導(dǎo)致的結(jié)果是單個(gè)人物所承載的意義被減損,所有人物均退居次要地位。最為典型的是正在上映的《八佰》,盡管管虎自稱“關(guān)注的就不是戰(zhàn)役,而是戰(zhàn)役中的人,普通的個(gè)體”,但是他對(duì)描述歷史事件和探討戰(zhàn)爭(zhēng)意義的重視明顯高于塑造人物,蘇州河兩岸的眾多人物都是完成戰(zhàn)爭(zhēng)史詩(shī)這一宏大敘事的微小意象,人物的群像化使得每個(gè)個(gè)體都深陷于宏大的歷史和戰(zhàn)爭(zhēng)框架中,成為觀者散點(diǎn)觀看的客體和意義流失的符碼。另一方面,人物扁平化。第六代導(dǎo)演早期普遍致力于塑造圓形人物,賈樟柯的小武和趙小桃、王小帥的青紅和小貴、婁燁的李欣和馬達(dá)都是涵義豐富的人物,他們的新作卻明顯地削減了人物的深度,《三峽好人》《江湖兒女》《地久天長(zhǎng)》《風(fēng)中有朵雨做的云》致力于表現(xiàn)當(dāng)代史詩(shī)和社會(huì)變遷,大量扁平人物由此誕生,與早期生動(dòng)的邊緣人物相比,這些扁平人物具有臉譜化和符號(hào)化的特征。人物的群像化和扁平化意味著人物意義的減損和人物價(jià)值的退化,也意味著邊緣人物不再是第六代進(jìn)行表征的主要方式,對(duì)社會(huì)問(wèn)題的關(guān)注取代了對(duì)人的關(guān)注,這是第六代深度嵌入社會(huì)、思想更為成熟的表現(xiàn),也是第六代對(duì)成長(zhǎng)主題和個(gè)體經(jīng)驗(yàn)書寫逐步乏力的結(jié)果。
在題材和人物之外,空間也是第六代進(jìn)行意義生產(chǎn)的重要表征方式。第六代是具有強(qiáng)烈空間意識(shí)的一代,與第五代不同,第五代生長(zhǎng)于城市然后被下放至農(nóng)村,他們并將城市和農(nóng)村作為電影的敘事空間,而第六代生長(zhǎng)于大都市或小城鎮(zhèn),因此大都市和小城鎮(zhèn)成為第六代電影的敘事空間。賈樟柯“故鄉(xiāng)三部曲”中的縣城成為中國(guó)社會(huì)的核心意象和西方讀解中國(guó)的關(guān)鍵符碼,王小帥“三線三部曲”中的貴州小鎮(zhèn)是當(dāng)代中國(guó)社會(huì)的一種集體記憶,章明的敘事大多圍繞故鄉(xiāng)巫山縣城進(jìn)行,婁燁則始終堅(jiān)持通過(guò)都市表現(xiàn)人的欲望與迷失,在第六代的表征系統(tǒng)里空間越過(guò)情節(jié)、人物、時(shí)間,成為意義生產(chǎn)的重要中介。
但是,第六代新作中空間的敘事功能明顯下降,空間承載的意義相應(yīng)削減,從具有獨(dú)立功能的敘事元素退居成為故事發(fā)生的背景。與以往相比,賈樟柯、婁燁和王小帥的新作都不再局限于單個(gè)的都市或小城鎮(zhèn),恢宏的故事在多個(gè)空間交叉編織,早期意義豐沛的生活空間和社會(huì)空間轉(zhuǎn)變?yōu)榉?hào)化的地理空間和歷史空間。譬如,《山河故人》的敘事空間包括山西小城、上海和澳大利亞三個(gè)空間,分別對(duì)應(yīng)時(shí)間上的過(guò)去、現(xiàn)在和未來(lái)與空間上的故鄉(xiāng)、他鄉(xiāng)和異鄉(xiāng),空間視點(diǎn)的移動(dòng)使每處空間降格為故事的背景,過(guò)去縣城因小城青年的憤怒與激情而生意盎然,現(xiàn)在不過(guò)是用于懷舊的布景;又如,《風(fēng)中有朵雨做的云》中的都市包括廣州、香港和臺(tái)北三個(gè)空間,婁燁選取它們的原因在于廣州是真實(shí)社會(huì)事件的發(fā)生地,這樣選擇的原因顯然是外因,因此這三處空間的意義與《蘇州河》中的上海是截然不同的;再如,《地久天長(zhǎng)》的空間設(shè)置同樣包括三個(gè)空間,故事在傳統(tǒng)的重工業(yè)基地包頭市、海南和福建海邊小鎮(zhèn)之間往返交織,多樣、交叉的空間分散了每個(gè)空間所承擔(dān)的敘事功能。第六代的空間表征方式發(fā)生轉(zhuǎn)換的目的是展現(xiàn)更為宏闊的社會(huì)變遷,代價(jià)是空間的意義變得萎縮和空洞。王小帥說(shuō):“《地久天長(zhǎng)》的故事不僅僅時(shí)間跨度比較長(zhǎng),涉及幾代人的經(jīng)歷,幾代人的內(nèi)心軌跡,我希望能夠從幾個(gè)時(shí)間切片入手,把一個(gè)家庭的變故和整個(gè)社會(huì)的變化聯(lián)系在一起。”可見,試圖講述我們身處的時(shí)代和社會(huì)是第六代的自覺追求,從微觀敘事轉(zhuǎn)向宏大敘事的必然途徑是時(shí)間、空間、人物和情節(jié)等各種敘事元素被無(wú)限擴(kuò)充,頗富意味的是,宏大敘事是第六代曾經(jīng)反對(duì)的電影傳統(tǒng)。
經(jīng)過(guò)近三十年的累積,第六代已確立一系列成熟的話語(yǔ)范式,作為醒目的標(biāo)識(shí),底層題材、邊緣人物和城鎮(zhèn)空間在第六代的早期電影文本中是重要的表征方式,各自從事著繁復(fù)的意義生產(chǎn)。但是,范式的確立也意味著邊界的固化,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這些話語(yǔ)表征所指涉的意義都在退位和減損,表現(xiàn)為題材的自我重復(fù)、人物的泛指化和空間的背景化。與此同時(shí),敘述的立場(chǎng)從個(gè)體轉(zhuǎn)向社會(huì),情緒從激烈轉(zhuǎn)向平和,時(shí)空從凝滯轉(zhuǎn)向流動(dòng),視點(diǎn)從主觀轉(zhuǎn)向客觀,這些共同推動(dòng)第六代意義生產(chǎn)的收縮。第六代敘事中的“我”變成“他們”,意味著曾經(jīng)叛逆的一代拋開主觀視角換以上帝視角俯視時(shí)代、社會(huì)與人,拋棄他們?cè)?jīng)賴以獲取認(rèn)可的基礎(chǔ),正是從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意義生產(chǎn)的收縮化是第六代內(nèi)卷化現(xiàn)象的消極一面。
四、內(nèi)卷化與第六代的危機(jī)
代際更替是一個(gè)動(dòng)態(tài)的進(jìn)程,每一代都必然經(jīng)歷進(jìn)場(chǎng)、在場(chǎng)和退場(chǎng)的歷史進(jìn)程。在中國(guó)電影史上,從第一代導(dǎo)演到第六代導(dǎo)演都遵循這一代際更替模式,新一代導(dǎo)演的進(jìn)場(chǎng)都與上一代導(dǎo)演的漸次退場(chǎng)共時(shí)發(fā)生。每一代的退場(chǎng)原因各不相同,不同時(shí)期的社會(huì)狀況、意識(shí)形態(tài)、文化語(yǔ)境和電影生態(tài)等因素影響著中國(guó)各代導(dǎo)演,第一代至第四代導(dǎo)演的起步和終結(jié)受制于20世紀(jì)上半葉中國(guó)社會(huì)的大轉(zhuǎn)型,上述代際更替過(guò)程在前四代導(dǎo)演身上沒有得到自然而充足的孕育和發(fā)展,內(nèi)卷化過(guò)程也未能真正完形。與以往導(dǎo)演多受外部因素的影響而退場(chǎng)不同,當(dāng)下正處于成熟期的第六代面臨的危機(jī)更多是自身的內(nèi)卷化。
作為一種利弊兼?zhèn)涞陌l(fā)展模態(tài),格爾茨認(rèn)為,“內(nèi)卷化”在積極意義上使得藝術(shù)或文化“內(nèi)部的修飾性和裝飾性逐步增強(qiáng);技術(shù)性細(xì)節(jié)逐步增強(qiáng);鑒賞性就會(huì)變得沒有止境”。但在消極意義上,“‘內(nèi)卷化’是指已經(jīng)建立的模式阻滯了外部擴(kuò)張的可能性,為了生存,內(nèi)部必須向更為精細(xì)化的方向擴(kuò)展,以致使系統(tǒng)越來(lái)越僵化”。因此,內(nèi)卷化并非有害無(wú)益,從積極方面來(lái)說(shuō),第六代的內(nèi)卷化使得敘事話語(yǔ)從粗糙變得精致,在技術(shù)上更加成熟,在審美上更具有可接受性。當(dāng)然,敘事話語(yǔ)層面的“內(nèi)卷化”并非集體無(wú)意識(shí),而是第六代為了應(yīng)對(duì)市場(chǎng)趨向、審美變化和媒介變遷所進(jìn)行的集體有意識(shí)行為,王小帥在采訪中就坦言,“我其實(shí)不希望我的電影唯美,但還是希望畫面在構(gòu)圖或者整體后期剪輯上呈現(xiàn)出的效果是比較精致的”。與此同時(shí),內(nèi)卷化的消極方面體現(xiàn)在意義生產(chǎn)的收縮,這導(dǎo)致第六代陷入日趨保守、缺乏創(chuàng)新的危機(jī),因此對(duì)內(nèi)卷化現(xiàn)象應(yīng)予以警惕和反省。
本文認(rèn)為,第六代的內(nèi)卷化至少可歸因于代際更替的演進(jìn)規(guī)律、作者觀念的自我抵牾和商業(yè)力量的高度侵蝕三個(gè)方面。首先,從電影社會(huì)學(xué)的角度來(lái)說(shuō),第六代是中國(guó)電影代際更替的一個(gè)環(huán)節(jié),其發(fā)展進(jìn)程符合代際演進(jìn)的自然規(guī)律,內(nèi)卷化是第六代進(jìn)入代際演進(jìn)的成熟期的表現(xiàn),是結(jié)構(gòu)性演變的結(jié)果。“一個(gè)時(shí)期的藝術(shù)與當(dāng)時(shí)普遍盛行的‘生活方式’存在密切的必然聯(lián)系,因此審美判斷、道德判斷和社會(huì)判斷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相互關(guān)系。”電影藝術(shù)是社會(huì)歷史的產(chǎn)物,紛繁復(fù)雜的電影生態(tài)與特定時(shí)期的社會(huì)生活密切相關(guān),也大致遵循社會(huì)演變的規(guī)律。一般來(lái)說(shuō),導(dǎo)演在早期具有最為強(qiáng)烈的創(chuàng)作沖動(dòng),無(wú)論是在題材、風(fēng)格還是主題上都試圖創(chuàng)新,這一時(shí)期往往有較大可能奏出電影史上的華章,會(huì)涌現(xiàn)數(shù)量可觀的重要導(dǎo)演和偉大作品。但是,一旦導(dǎo)演獲得命名并穩(wěn)固下來(lái),群體的共同范式既成為標(biāo)識(shí),也成為抑制創(chuàng)新和束縛自我的標(biāo)簽。從個(gè)人的角度來(lái)說(shuō),創(chuàng)作初期在題材和風(fēng)格上獲得突破的主要原因是他們擁有獨(dú)特的成長(zhǎng)經(jīng)驗(yàn)和表達(dá)欲望,然而這也導(dǎo)致后續(xù)性的突破極為困難。從社會(huì)的角度來(lái)說(shuō),“一個(gè)社會(huì)系統(tǒng)的結(jié)構(gòu)可以促進(jìn)或阻礙創(chuàng)新在這個(gè)社會(huì)系統(tǒng)中的擴(kuò)散”,一個(gè)已經(jīng)穩(wěn)固的系統(tǒng)并不鼓勵(lì)創(chuàng)新,因此,當(dāng)?shù)诹Q身主流創(chuàng)作群體時(shí),電影美學(xué)、制作、傳播、接受方面的穩(wěn)定結(jié)構(gòu)反過(guò)來(lái)成為抑制第六代的力量,驅(qū)使第六代的創(chuàng)作逐步內(nèi)卷化。
其次,第六代大多在20世紀(jì)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接受電影教育,各國(guó)新浪潮電影作者是他們的啟蒙者,因此第六代普遍具有堅(jiān)定的作者信念,然而對(duì)作者觀念的秉持也是第六代產(chǎn)生內(nèi)卷化的一個(gè)動(dòng)因。第六代早期深受電影作者和作者電影的影響,奉行“一生只拍一部電影”的作者精神,堅(jiān)持“導(dǎo)演為中心”的作者策略。但是,作者論本身具有自我悖反性,新浪潮作者以激進(jìn)、反叛、先鋒的姿態(tài)載入世界影史,同時(shí)作者論又倡導(dǎo)“個(gè)人風(fēng)格的連續(xù)性”,因?yàn)椤笆澜缬^這個(gè)觀念從來(lái)就是作者論的試金石,因?yàn)樗耆灰蛴捌闹黝}改變而改變”。由于作者論包含創(chuàng)新與重復(fù)、革新與保守兩種相互抵牾的電影觀念,堅(jiān)持作者信念的第六代也日益表現(xiàn)出作者論的互悖性,一方面在底層題材、邊緣人物和社會(huì)空間上與第五代構(gòu)成逆反和決裂,另一方面在新的題材、人物和敘事上自我重復(fù)、趨于保守,后者正是第六代內(nèi)卷化的消極方面。
再次,第六代的成熟與2003年以來(lái)中國(guó)電影產(chǎn)業(yè)的快速發(fā)展進(jìn)程疊合,商業(yè)因素對(duì)第六代的影響在與時(shí)俱增,商業(yè)力量的過(guò)度侵蝕也是第六代內(nèi)卷化的重要原因。在資本化、現(xiàn)代化和全球化的社會(huì)語(yǔ)境中,產(chǎn)業(yè)化是世界各國(guó)電影無(wú)法回避的問(wèn)題,中國(guó)自2003年開始啟動(dòng)產(chǎn)業(yè)化改革。電影產(chǎn)業(yè)構(gòu)型的核心是經(jīng)濟(jì)向度,中國(guó)電影的產(chǎn)業(yè)化使得資本、市場(chǎng)及與之相關(guān)的技術(shù)、觀眾等因素大力作用于第六代,藝術(shù)質(zhì)量不再是被作者電影哺育的第六代的唯一追求,獲獎(jiǎng)和票房共同影響著第六代的電影創(chuàng)作。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顯示,《江湖兒女》的最終票房為6994萬(wàn),《風(fēng)中有朵雨做的云》為6480萬(wàn),《地久天長(zhǎng)》為4519萬(wàn),這三部電影的票房均為三位導(dǎo)演的票房歷史最高紀(jì)錄。2020年新冠疫情導(dǎo)致全球電影市場(chǎng)極度低迷,八月上映的《八佰》被寄予厚望,成為恢復(fù)和振興中國(guó)電影市場(chǎng)的一劑猛藥,敘事精細(xì)、技術(shù)精良的《八佰》在票房上的表現(xiàn)也確實(shí)不負(fù)眾望。對(duì)票房的重視意味著對(duì)大眾審美的傾斜,結(jié)果是進(jìn)一步鼓勵(lì)電影敘事話語(yǔ)的精細(xì)化,但是損蝕的是電影作者所重視的意義生產(chǎn)和表達(dá),商業(yè)侵蝕致使第六代內(nèi)卷化的程度不斷加深。
代際演進(jìn)、風(fēng)格延續(xù)和商業(yè)侵蝕磨滅了第六代可貴的先鋒性和創(chuàng)新性,導(dǎo)致內(nèi)卷化的消極后果日益突出,第六代已深度陷入話語(yǔ)精致和意義收縮的兩極互悖。這一困境已經(jīng)明顯影響到第六代當(dāng)下的創(chuàng)作,也無(wú)疑會(huì)影響第六代未來(lái)的創(chuàng)作。對(duì)內(nèi)卷化現(xiàn)象反思的關(guān)鍵是如何突破邊界的困鎖,在敘事話語(yǔ)精細(xì)化的同時(shí)避免意義生產(chǎn)的收縮化。回溯第六代的電影創(chuàng)作,回到第六代最令人激動(dòng)的誕生期去尋找答案,或許可以找到從內(nèi)卷化困境中突圍而出的有效途徑。
五、結(jié)語(yǔ)
第六代共同秉持兩種電影觀。其一是堅(jiān)持作者精神。電影作者是電影王國(guó)的主人,作者論制定的種種策略,本質(zhì)上都是對(duì)導(dǎo)演實(shí)踐個(gè)體表達(dá)的保證,也正是因?yàn)榈诹餐铝τ趥€(gè)人表達(dá),才使他們的作品具有豐富的意義,形成尖銳、獨(dú)特、多樣的美學(xué)風(fēng)格。其二是關(guān)注中國(guó)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現(xiàn)實(shí)主義是和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無(wú)限逼近”的藝術(shù)立場(chǎng)和方法,表現(xiàn)為電影內(nèi)容層面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主題和電影話語(yǔ)層面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風(fēng)格,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觀在第六代的創(chuàng)作中一以貫之。正是對(duì)作者個(gè)人表達(dá)和現(xiàn)實(shí)主義觀念的堅(jiān)守使得第六代獲得身份命名,并使得第六代整體上達(dá)到現(xiàn)有的藝術(shù)高度,今天,作者個(gè)人表達(dá)和現(xiàn)實(shí)主義觀念仍然是第六代抵抗內(nèi)卷化趨勢(shì)的武器。
內(nèi)卷化的根本問(wèn)題是意義生產(chǎn)的收縮化,即電影內(nèi)容層面的固化,第六代共同面臨的困境是頹勢(shì)明顯的經(jīng)驗(yàn)與欲望、故步自封的自我重復(fù)、緊密裹挾的商業(yè)力量,事實(shí)上這些因素造成的困擾不是電影如何表達(dá),更大程度上是電影表達(dá)什么。第六代對(duì)表達(dá)方式和表達(dá)內(nèi)容孰輕孰重有清醒的認(rèn)識(shí),正如章明所說(shuō),“電影形態(tài)的變化,包括一種表達(dá)和被表達(dá)的東西在里面,不存在純粹的形式。表達(dá)方式的重要是指創(chuàng)作者站在什么角度,想表現(xiàn)什么”。敘事話語(yǔ)的精細(xì)化其實(shí)無(wú)須詬病,真正威脅第六代的是意義生產(chǎn)的匱乏,因此以作者立場(chǎng)對(duì)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進(jìn)行富有價(jià)值的描述與闡釋應(yīng)該是第六代進(jìn)行突圍的有效方法。當(dāng)然,這需要第六代拒絕來(lái)自自我和外部的干擾,以審慎的態(tài)度轉(zhuǎn)向宏大敘事和話語(yǔ)虛構(gòu),在嘗試突破的同時(shí)堅(jiān)持現(xiàn)實(shí)關(guān)懷、主觀視點(diǎn)和微觀敘事的代際特色。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8頁(yè)。
②劉世定、邱澤奇:《“內(nèi)卷化”概念辨析》,《社會(huì)學(xué)研究》2004第5期。
③④海登·懷特:《敘事的虛構(gòu)性:有關(guān)歷史、文學(xué)和理論的論文(1957-2007)》,馬麗莉、馬云、孫晶姝譯,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9年,第342頁(yè),第224頁(yè)。
⑤亞里士多德:《詩(shī)學(xué)》,陳中梅譯注,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6年,第47頁(yè)。
⑥盧卡奇:《小說(shuō)理論》,燕宏遠(yuǎn)、李懷濤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2年,第59頁(yè)。
⑧亨利·列斐伏爾:《空間與政治》,李春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9頁(yè)。
⑨王小帥、侯克明、文靜:《〈地久天長(zhǎng)〉:現(xiàn)實(shí)主義與東方美學(xué)的“平民史詩(shī)”——王小帥訪談》,《電影藝術(shù)》2019年第3期。
⑩斯圖爾特·霍爾編:《表征——文化表象與意指實(shí)踐》,徐亮、陸興華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3年,第16頁(y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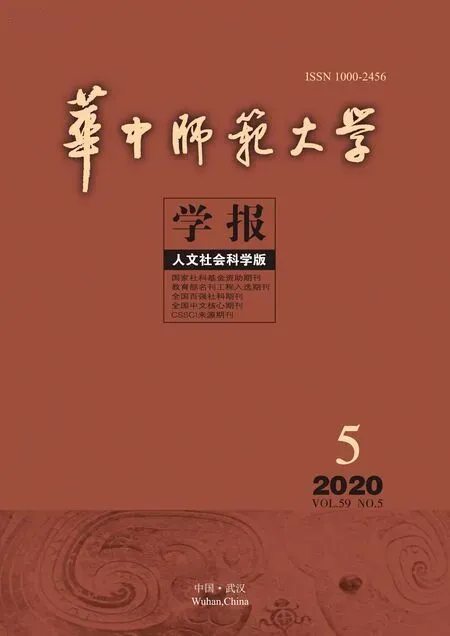 華中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0年5期
華中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0年5期
- 華中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中國(guó)三千年疫災(zāi)史料匯編(五卷本)》出版
- 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背景下多元化鄉(xiāng)村治理問(wèn)題研究
- 家庭的收入和特征對(duì)家庭教育支出的影響研究
- 人口流動(dòng)的影響機(jī)制研究
——基于氣候變化及區(qū)域差異 - 我國(guó)地方財(cái)政實(shí)施預(yù)算績(jī)效管理的效果、問(wèn)題與政策建議
——基于湖北省直預(yù)算單位和市縣財(cái)政局的問(wèn)卷調(diào)查 - “健康中國(guó)”戰(zhàn)略下的農(nóng)村老年人醫(yī)療消費(fèi)行為
——基于收入不平等與基本醫(yī)保的視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