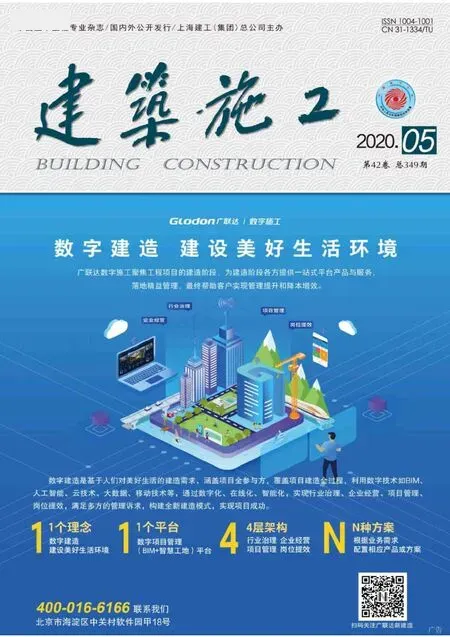軟土深基坑開挖對(duì)鄰近地鐵結(jié)構(gòu)的影響規(guī)律分析
褚 峰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mào)易區(qū)開發(f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200126
城市多條地鐵線路交會(huì)地段,往往會(huì)成為開發(fā)建設(shè)的熱點(diǎn)區(qū)域。與此伴生的就是大規(guī)模深基坑開挖對(duì)緊鄰地鐵服役安全的潛在威脅。諸多案例表明,軟土地區(qū)基坑開挖時(shí)的土體卸荷會(huì)引起地鐵隧道位移場(chǎng)和應(yīng)力場(chǎng)的改變[1-2],若不做好先期周圍土體加固措施及采取實(shí)時(shí)變形監(jiān)測(cè)手段,地鐵結(jié)構(gòu)往往會(huì)因開挖出現(xiàn)形變超限、不均勻沉降過大等現(xiàn)象,繼而引發(fā)管片開裂、螺栓屈服及滲漏水等嚴(yán)重工程問題[2]。例如,臺(tái)北某地鐵隧道就曾因緊鄰基坑開挖而隆起高達(dá)33 mm,導(dǎo)致結(jié)構(gòu)裂損破壞[3];在北京、廣州、上海等地均發(fā)生過因基坑施工引發(fā)的鄰近地鐵隧道事故,造成人員傷亡和極大的經(jīng)濟(jì)損失。因此,如何有效控制深基坑開挖對(duì)緊鄰地鐵的不利影響是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近年來,諸多學(xué)者從理論解析[4-5]、數(shù)值模擬[6-8]、模型試驗(yàn)[8-9]及現(xiàn)場(chǎng)監(jiān)測(cè)[10-12]等不同維度對(duì)該問題展開研究。其中:理論方法雖簡(jiǎn)便明了,但不適合用于進(jìn)行復(fù)雜工況分析[2,8];數(shù)值計(jì)算和模型試驗(yàn)可在一定程度上模擬現(xiàn)場(chǎng)工況。但前者受限于本構(gòu)模型及參數(shù)選取的準(zhǔn)確度,后者存在尺度差異問題,應(yīng)對(duì)大規(guī)模高復(fù)雜度巖土工程問題時(shí),定性解釋作用強(qiáng)于定量分析[5]。現(xiàn)場(chǎng)監(jiān)測(cè)數(shù)據(jù)作為寶貴的第一手資料,能夠直接、全面地反映工程實(shí)際,對(duì)類似工程具有重要的指導(dǎo)意義[10-12]。本文以上海軟土地區(qū)某緊鄰地鐵的深基坑工程為例,基于實(shí)測(cè)資料對(duì)基坑開挖過程中地鐵結(jié)構(gòu)沉降變化展開分析,并提出現(xiàn)象解釋及建議措施,旨在為類似工程提供一定參考。
1 工程概況及地質(zhì)條件
1.1 工程概況
背景項(xiàng)目位于上海軌交6號(hào)線、8號(hào)線和11號(hào)線三線交會(huì)換乘點(diǎn)——東方體育中心站附近。本文研究該工程中的25-1北區(qū)地塊,該地塊擬建成地下2層地下室及地上4幢建筑,均為鋼筋混凝土框架結(jié)構(gòu),房屋建筑面積48 895 m2,其中地上建筑面積28 253 m2,地下建筑面積20 642 m2。地塊基坑分布如圖1所示,總面積約9 953 m2,共分7個(gè)區(qū)進(jìn)行開挖,其中①—⑥區(qū)開挖深度均為10.4 m,⑦區(qū)開挖深度為6.45 m。

圖1 基坑平面布置示意
1.2 水文地質(zhì)條件
基坑所在地屬濱海平原地貌,場(chǎng)地內(nèi)地勢(shì)較平坦,地面高程為3.5~6.0 m。工程場(chǎng)地的地基土根據(jù)成因及性質(zhì)可劃分為12個(gè)工程地質(zhì)單元體,自上而下依次為①1填土、 ①2濱底淤泥、②粉質(zhì)黏土、③1淤泥質(zhì)粉質(zhì)黏土、④淤泥質(zhì)黏土、⑤2-1砂質(zhì)粉土夾粉質(zhì)黏土、⑤2-2粉砂、⑤3-1粉質(zhì)黏土、⑤3-2砂質(zhì)粉土夾粉質(zhì)黏土、⑤3-3粉質(zhì)黏土、⑦粉細(xì)砂和⑧粉質(zhì)黏土與粉砂互層。
其中潛水主要分布于①1層,該層以耕植土、碎石和混凝土塊為主,屬透水性較好的相對(duì)含水層。②、③1層以淤泥質(zhì)土為主,滲透性差。⑤2-1、⑤2-2層為微承壓水層,含砂質(zhì)粉土和粉砂,滲透性相對(duì)較好,滲透系數(shù)為9.52×10-5~1.45×10-4cm/s,屬中等透水層。⑦層為上海市第一承壓含水層,屬良好含水層,富水性與滲透性較好,滲透系數(shù)為1.25×10-4~1.49×10-4cm/s,屬?gòu)?qiáng)透水層。值得注意的是,場(chǎng)地淺層分布的③1、④層是影響工程的主要軟土層,土質(zhì)松軟、靈敏度高,對(duì)基坑圍護(hù)結(jié)構(gòu)施工有不利影響。此外,場(chǎng)地內(nèi)含埋深淺、水量大的潛水和微承壓含水層,對(duì)基坑邊坡穩(wěn)定性具有潛在威脅。
2 開挖與監(jiān)測(cè)方案
2.1 基坑開挖與圍護(hù)方案
表1為基坑施工的順序。采用先挖中心大坑,再挖邊緣小坑的步驟進(jìn)行開挖,遵循“分層、分塊、留土護(hù)壁、對(duì)稱、限時(shí)開挖支撐”的原則,開挖過程中充分利用時(shí)空效應(yīng)原理,盡量減少基坑暴露時(shí)間,嚴(yán)格控制基坑變形。
基坑以地下連續(xù)墻作為圍護(hù)結(jié)構(gòu),迎土側(cè)采用厚600 mm的TRD工法槽壁加固,開挖側(cè)采用三軸攪拌樁槽壁加固,各分區(qū)槽壁厚度不同。基坑平面內(nèi)采用整體對(duì)撐的形式,①區(qū)設(shè)置2道鋼筋混凝土支撐,②—⑤區(qū)頭道為混凝土支撐,二、三道為φ609 mm×16 mm鋼管支撐,⑥區(qū)設(shè)置3道鋼筋混凝土支撐,⑦區(qū)為1道混凝土支撐。

表1 基坑施工順序
2.2 地鐵結(jié)構(gòu)監(jiān)測(cè)方案
本基坑與地鐵隧道的最近距離僅為10 m,兩者部分結(jié)構(gòu)共墻,屬一級(jí)保護(hù)基坑。出于對(duì)緊鄰地鐵的保護(hù),開挖前分區(qū)采用三軸攪拌樁對(duì)土體進(jìn)行加固,并在靠近軌交6號(hào)線、8號(hào)線風(fēng)井處實(shí)施止水措施。地鐵結(jié)構(gòu)的變形控制標(biāo)準(zhǔn)十分嚴(yán)格,因此需預(yù)設(shè)監(jiān)測(cè)點(diǎn)以對(duì)基坑施工過程中道床垂直位移和側(cè)墻垂直位移進(jìn)行嚴(yán)密監(jiān)控,一旦發(fā)現(xiàn)變形超限立即啟動(dòng)報(bào)警程序,兩者的監(jiān)測(cè)點(diǎn)布置如圖2所示。

圖2 地鐵結(jié)構(gòu)監(jiān)測(cè)點(diǎn)布置
道床垂直位移是反映地鐵管線縱向位移的直接指標(biāo),軌交6號(hào)線、11號(hào)線位于基坑南側(cè),沿軌交6號(hào)線上行線和軌交11號(hào)線下行線自西向東分別布置42個(gè)道床位移監(jiān)測(cè)點(diǎn),分別為6SX01—6SX42和11XX01—11XX42。軌交8號(hào)線位于基坑西北側(cè),沿其上、下行線自南向北分別布置43個(gè)道床位移監(jiān)測(cè)點(diǎn),分別為8SX01—8SX43和8XX01—8XX43。
側(cè)墻作為地鐵結(jié)構(gòu)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內(nèi)力及變形同地鐵安全息息相關(guān),沿軌交6號(hào)線上行線和軌交11號(hào)線下行線自西向東分別布置15個(gè)側(cè)墻位移監(jiān)測(cè)點(diǎn),分別為6CZ01—6CZ15和11CZ01—11CZ15。沿軌交8號(hào)線下行線自南向北布置11個(gè)測(cè)點(diǎn),為8CZ01—8CZ11。
3 監(jiān)測(cè)結(jié)果分析
3.1 道床垂直位移分析
圖3分別為軌交6號(hào)線上行線、軌交11號(hào)線下行線和軌交8號(hào)線上、下行線道床垂直位移隨基坑施工發(fā)展的變化情況(圖中1—6區(qū)域分別對(duì)應(yīng)表2中不同的施工階段)。同一地鐵線各測(cè)點(diǎn)位移僅在數(shù)值上有所差別,而隨時(shí)間變化,模式總體接近,可在一定程度上佐證監(jiān)測(cè)的可靠性。

圖3 道床垂直位移
在①區(qū)基坑的首層開挖階段,各線隧道均發(fā)生較大沉降,其中累計(jì)最大沉降值可達(dá)10 mm,同時(shí)注意到各監(jiān)測(cè)點(diǎn)累計(jì)垂直位移值存在差異,說明地鐵管線出現(xiàn)不均勻沉降。 此后,隨著首道支撐的布置,軌交6號(hào)線和軌交11號(hào)線各點(diǎn)均發(fā)生不同程度的上浮,軌交8號(hào)線的沉降速率也相應(yīng)減小。首道支撐布置完成后,①區(qū)基坑后續(xù)工序(包括二道支撐、底板及B1板施工)均未導(dǎo)致各線地鐵發(fā)生明顯垂直位移,說明大型基坑首層開挖對(duì)緊鄰地鐵的影響大于后續(xù)開挖,此階段應(yīng)作為施工與監(jiān)測(cè)的重點(diǎn)環(huán)節(jié)。
與①區(qū)基坑開挖時(shí)的顯著沉降相反,此后隨著各小基坑的施工,各條地鐵隧道都持續(xù)發(fā)生均勻、緩慢的上浮,此過程雖相對(duì)緩慢,但最終仍達(dá)到一個(gè)可觀的累計(jì)上浮量。此現(xiàn)象說明:基坑工程中,主基坑開挖的大規(guī)模卸荷作用會(huì)使緊鄰地鐵發(fā)生沉降,而次基坑開挖時(shí)的小規(guī)模卸荷則會(huì)引發(fā)緊鄰地鐵的上浮,類似工程中在不同階段應(yīng)采取不同的控制和保護(hù)措施。
3.2 側(cè)墻垂直位移分析
圖4所示為各線地鐵側(cè)墻受基坑施工引起垂直位移的變化情況。對(duì)比可發(fā)現(xiàn),在該工程基坑施工過程中,地鐵側(cè)墻和道床的垂直位移響應(yīng)模式十分類似。在主基坑施工階段,基坑分層開挖會(huì)使結(jié)構(gòu)發(fā)生沉降,而布置支撐又會(huì)導(dǎo)致結(jié)構(gòu)上浮。這其中,又以首層基坑施工階段對(duì)結(jié)構(gòu)的影響最大。在此之后,次要的小型基坑施工會(huì)引發(fā)結(jié)構(gòu)持續(xù)上浮,并最終累積到一個(gè)相對(duì)可觀的上浮量。

圖4 側(cè)墻垂直位移
相比道床位移,側(cè)墻的垂直位移曲線坡度更陡,說明其對(duì)外界環(huán)境的變化更為敏感。這種差異或是兩者剛度不同所致,地鐵隧道為圓環(huán)截面,剛度較低,而側(cè)墻的截面剛度則比較高。
3.3 最大沉降差異分析
圖5分別為各線地鐵道床和側(cè)墻在基坑施工過程中豎向最大沉降差異的變化情況。分析圖5(a)可發(fā)現(xiàn),距基坑相對(duì)更近的2條線路(8SX和11XX)因位于先期三軸攪拌樁加固區(qū)內(nèi),故而不均勻沉降較小。與此相反,距基坑相對(duì)更遠(yuǎn)的線路(6SX和8XX)則發(fā)生更大的不均勻沉降。此外,對(duì)比各沉降差異曲線的變化模式發(fā)現(xiàn),6SX和8XX兩線變化模式較接近,11XX和8SX也更接近,說明地鐵與基坑的水平距離和地鐵線周圍地基加固效果是影響本工程地鐵不均勻沉降的主要因素。在類似工程中,對(duì)緊鄰基坑地鐵線路采取周圍地基土加固措施時(shí),距離較遠(yuǎn)處的地鐵線應(yīng)同樣受到重視。
而分析圖5(b)發(fā)現(xiàn),側(cè)墻的沉降差異則沒有明顯的變化規(guī)律,且最大沉降差異值普遍小于道床的最大沉降差,此現(xiàn)象同樣由于側(cè)墻更大的剛度所致。
4 結(jié)語
本文通過對(duì)上海軟土地區(qū)某深基坑開挖過程中緊鄰地鐵道床位移和側(cè)墻位移監(jiān)測(cè)結(jié)果的分析,研究了不同施工階段對(duì)地鐵結(jié)構(gòu)變形響應(yīng)的影響,得出以下結(jié)論:

圖5 道床與側(cè)墻最大沉降差異
1)主基坑開挖引起的大規(guī)模卸荷效應(yīng)會(huì)引起緊鄰地鐵道床和側(cè)墻發(fā)生豎向沉降,而次基坑開挖時(shí)的小規(guī)模卸荷效應(yīng)會(huì)引起地鐵結(jié)構(gòu)產(chǎn)生上浮,類似工程中在不同施工階段應(yīng)采取不同控制手段。
2)地鐵道床和側(cè)墻的豎向位移主要發(fā)生在周邊大型基坑首層土體開挖的階段,此過程應(yīng)當(dāng)作為基坑施工控制的重點(diǎn)。
3)地鐵與基坑的水平距離和地鐵線周圍地基加固效果是影響地鐵道床不均勻沉降的主要因素,而剛度更高的側(cè)墻則不易發(fā)生不均勻沉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