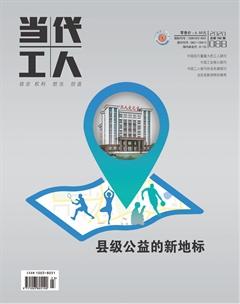別成了哭不出來(lái)的大人
葛璐

對(duì)于大多數(shù)中國(guó)家長(zhǎng)而言,可能還來(lái)不及思考和探索“理想教育”這個(gè)問(wèn)題,便會(huì)被沉重的“戶籍制度”“學(xué)區(qū)房”“教育資源分配”“高考”“唯分?jǐn)?shù)論”拉回現(xiàn)實(shí)。
中國(guó)式家長(zhǎng)的焦慮蔓延至孩子的童年。時(shí)下,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虎媽、狼爸們不停地讓孩子去拼搏,不斷地給孩子打雞血,把孩子打造成了“雞娃”。除了要用錢砸出一條滿足孩子物質(zhì)和精神需求的通道,雞娃父母還對(duì)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先“雞”自己,幫孩子做手工做簡(jiǎn)歷做課題都不算什么,更雞血的家長(zhǎng)已經(jīng)在跑步機(jī)上刷完了各大常青藤名校公開(kāi)課,三四歲便讓孩子混跡于大學(xué)實(shí)驗(yàn)室——那些并不曾“為了自己”而有過(guò)的努力,如今卻“為了孩子”而改變著。
尼爾·波茲曼在《童年的消逝》中就揭示:“兒童被迫提早進(jìn)入充滿沖突的成人世界。”在成人沖突世界中長(zhǎng)大的孩子,如何找尋到純粹本真的童年?我們讓孩子來(lái)到這個(gè)世界,不是為了讓他們?cè)诮箲]的成人規(guī)則中焦灼成長(zhǎng),也不是為了借由他們掩蓋或是改變那些我們自己并不圓滿的努力和人生,更不是為了培養(yǎng)最終可能被時(shí)代和社會(huì)所吞沒(méi)的高分低能孩子。
理想的教育應(yīng)該是面向現(xiàn)實(shí),面向人生,面向未來(lái)的。
周軼君導(dǎo)演在教育紀(jì)錄片《他鄉(xiāng)的童年》中,通過(guò)走訪日本、芬蘭、印度、以色列及英國(guó)這5個(gè)國(guó)家,呈現(xiàn)出了不同的童年教育方式,日本教育中的“細(xì)節(jié)追求”以及“集體觀念”,芬蘭教育中“避免競(jìng)爭(zhēng),追求平等”的理念,印度教育中在資源匱乏下通過(guò)創(chuàng)新來(lái)找到替代方案的Jugaad精神,以色列教育中鼓勵(lì)再次嘗試的耐心,英國(guó)“強(qiáng)調(diào)參與社會(huì)”的貴族教育模式,這些都是各國(guó)教育中的突出特色。
借由他鄉(xiāng)啟發(fā)激活本土,反觀當(dāng)下,我們?nèi)绾尾拍転楹⒆觿?chuàng)造出更為理想的童年教育?
高壓競(jìng)爭(zhēng)的教育令孩子背負(fù)著沉重的功利心求學(xué),學(xué)習(xí)過(guò)程難以知覺(jué)幸福。在東方很多國(guó)家,教育的功能首先是為了選拔,教育者常常錯(cuò)誤地把教育的選拔“功能”當(dāng)成教育的最終“目的”,“人”的多元培養(yǎng)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變得標(biāo)準(zhǔn)化和程式化。
在錯(cuò)誤目的地驅(qū)使下,孩子被傳遞了錯(cuò)誤的學(xué)習(xí)觀念:學(xué)習(xí)是為了得高分讀名校,完成這個(gè)選拔的過(guò)程。學(xué)習(xí)根本不是幸福本身,而只是獲得幸福的手段。漫漫求學(xué)路,手段很殘酷,幸福很遙遠(yuǎn)。
為了緩解壓力,減負(fù)的政策每年都有,有時(shí)甚至出現(xiàn)一刀切,反作用激化家長(zhǎng)情緒,比如去年南京家長(zhǎng)反而被“不許補(bǔ)課,不許考試,減少課時(shí),提早放學(xué)”逼瘋,中式教育下的孩子早已適應(yīng)了壓力狀態(tài),一下子零壓力的整改反而會(huì)遭致觸底反彈。
關(guān)于競(jìng)爭(zhēng)壓力,《他鄉(xiāng)的童年》中芬蘭的教育模式可以給我們提供一個(gè)對(duì)照。
作為全球最幸福的國(guó)家,避免競(jìng)爭(zhēng),追求平等的觀念滲透在芬蘭的教育中。政府一系列的高福利保障了孩子零壓力的受教育環(huán)境,芬蘭的家長(zhǎng)不需要焦慮,“最好的學(xué)校是最近的那一所”“任何工作都是好工作”。在很多孩子眼里,“如果有一份工作,一個(gè)妻子,一點(diǎn)兒錢,已經(jīng)算是成功”,這種快樂(lè)教育的模式大概是很多中國(guó)家長(zhǎng)夢(mèng)寐以求的。
這種去競(jìng)爭(zhēng)的快樂(lè)教育模式雖然可以給學(xué)生提供更加自由的發(fā)展空間,但也很可能成為滋生惰性的溫室,越來(lái)越多的芬蘭人自己也開(kāi)始反思甚至質(zhì)疑。
理想的教育需要合理的壓力閾值,如果教育消除了競(jìng)爭(zhēng),個(gè)體努力的意義將被稀釋;如果工作消除了差別,我們對(duì)價(jià)值創(chuàng)造的肯定也將變得無(wú)力。同時(shí),教育者也更需要讓孩子明白,壓力和競(jìng)爭(zhēng)的目的從來(lái)不是背離人生幸福。
“集體主義”和“細(xì)節(jié)”教育的危險(xiǎn)
從幼兒園開(kāi)始,我們的教育理念便極其關(guān)注孩子在集體中的表現(xiàn),我們強(qiáng)調(diào)關(guān)心集體,為集體爭(zhēng)榮譽(yù),注重整齊劃一的規(guī)范。
集體主義環(huán)境中的學(xué)生,被評(píng)價(jià)的體系更多來(lái)自群體,這要求他們更多地去考慮他人的感受,不給別人添麻煩。這種教育理念是否仍然完全適用于今天的00后、10后?
紀(jì)錄片《零零后》中有一集講一個(gè)00后孩子,老師問(wèn)她為什么不和別人一起玩,她說(shuō):“我就喜歡一個(gè)人玩。”如果我們?nèi)挥眉w主義的標(biāo)準(zhǔn)去衡量這個(gè)孩子,她在群體中不是所謂標(biāo)準(zhǔn)化的好學(xué)生,因?yàn)樗龥](méi)有集體觀念。
對(duì)于越來(lái)越多具有個(gè)體意識(shí)的00后和10后,教育者不能用一種標(biāo)準(zhǔn)模板去培養(yǎng)一個(gè)個(gè)失去個(gè)性色彩的模子,而是需要尊重和鼓勵(lì)生命個(gè)體的自由和創(chuàng)造性價(jià)值。
《他鄉(xiāng)的童年》中,日本幼兒園通過(guò)各種細(xì)節(jié)設(shè)計(jì)幫助孩子建立集體觀念,如日本藤幼兒園的推拉門故意設(shè)計(jì)成以孩子的力量無(wú)法一下子關(guān)上,天冷的時(shí)候坐在門邊的同學(xué)會(huì)受到影響,關(guān)門的孩子需要重新回來(lái)把門關(guān)嚴(yán),進(jìn)門鞋子脫放的位置被印好在地上。
過(guò)度強(qiáng)調(diào)集體而忽略個(gè)體的教育方式,在制造“高情商”的同時(shí),也制造了壓抑。日本的“感淚療法師”即是針對(duì)這種教育問(wèn)題而越來(lái)越受歡迎的一個(gè)職業(yè)。那些過(guò)于強(qiáng)調(diào)集體的童年,長(zhǎng)大后變成了哭不出來(lái)的大人,需要釋放真實(shí)的自我。
前段時(shí)間很火的日劇《風(fēng)平浪靜的閑暇》,便講述了在日本職場(chǎng)中總是照顧別人、察言觀色的“氛圍”是如何令人窒息的。過(guò)于換位思考為他人著想的極端,帶來(lái)了自我的壓抑,這種緊箍咒式的教育并不能稱之為面向未來(lái)的教育。
集體教育應(yīng)該具有包容差異的氛圍,認(rèn)同個(gè)體的差異,“細(xì)節(jié)”教育的內(nèi)容需要更加關(guān)注教育內(nèi)容本身,而非流于形式,以致從小成為孩子的心理負(fù)荷。
教育工作者都深諳耐心之道,但教育中最大的耐心不是教育者面對(duì)題目時(shí)表現(xiàn)的耐心,而應(yīng)該是教育者教會(huì)孩子面向人生和生活的耐心。教育者能夠包容失敗,鼓勵(lì)嘗試,愿意等待和陪伴孩子成長(zhǎng)。
韓國(guó)KBS電視臺(tái)曾經(jīng)制作了一部紀(jì)錄片《怎樣才是最好的學(xué)習(xí)》,片中哈佛學(xué)霸走訪東西方教育,最終得出觀點(diǎn):“最好的學(xué)習(xí)”屬于猶太族群。
《他鄉(xiāng)的童年》通過(guò)以色列的青少年創(chuàng)業(yè)公司基地展現(xiàn)了這個(gè)創(chuàng)業(yè)大國(guó)的特色。這里很多CEO才16歲,盡管這些創(chuàng)業(yè)公司最后可能會(huì)失敗,但失敗的人反而在二次創(chuàng)業(yè)中會(huì)獲得更多的投資,因?yàn)槿藗冋J(rèn)為失敗者也是英雄,這便是一個(gè)國(guó)家對(duì)教育展現(xiàn)出的巨大耐心。
如今國(guó)內(nèi)教育中的評(píng)價(jià)體系已經(jīng)逐漸多維和完善,但關(guān)鍵在于很多維度很難在短時(shí)間里對(duì)學(xué)生做出客觀有效的評(píng)價(jià),于是立竿見(jiàn)影的成績(jī)常常變成教育過(guò)程中最輕易最重要的那個(gè)維度,教育者“拒絕失敗”的心態(tài),將會(huì)直接導(dǎo)致學(xué)生“不敢嘗試”的懦弱。
教育需要慢下來(lái)的耐心,芬蘭學(xué)校不通過(guò)考試而是過(guò)程評(píng)估學(xué)生,英國(guó)貴族私校注重從參與社會(huì)的服務(wù)意識(shí)評(píng)價(jià)學(xué)生,這些都是令教育舒緩不緊繃的評(píng)估方式。在《他鄉(xiāng)的童年》中,我最喜歡的一個(gè)理念來(lái)自一位印度老師,他說(shuō):老師的存在是為了“把馬帶到水邊,并讓它覺(jué)得口渴”。這個(gè)過(guò)程其實(shí)是“激發(fā)學(xué)生發(fā)現(xiàn)真實(shí)自我的過(guò)程”,這是教育中的喚醒。
不同教育之間的距離首先來(lái)自于觀念之間的差距,站在觀念彼岸的人們無(wú)從呼應(yīng),但是從彼岸到此岸,有時(shí)只需一點(diǎn)兒打破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