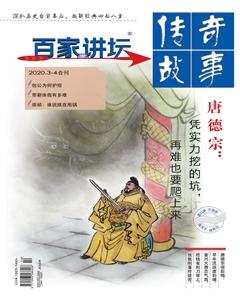東漢就有“五講四美”
三水小牘
談及東漢,無(wú)不是皇帝昏聵、外戚干政、宦官專權(quán)、朝政黑暗等負(fù)面形象。但明末清初的大儒顧炎武說(shuō),“三代以來(lái),風(fēng)俗之美,無(wú)尚于東漢”,清人趙翼說(shuō)“東漢尚名節(jié)”,簡(jiǎn)而言之,東漢就是個(gè)“五講四美”的時(shí)代。
西漢開(kāi)國(guó)功臣多是市井無(wú)賴,東漢開(kāi)國(guó)功臣則是一派儒者氣象。光武帝少年時(shí)曾在長(zhǎng)安太學(xué)讀書(shū),功臣鄧禹與他是同窗,就連皇帝的警備部隊(duì)都要人人通曉《孝經(jīng)》。在這樣的社會(huì)風(fēng)俗下,人人重名節(jié)、講節(jié)操。表現(xiàn)在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中,被害的名士多是主動(dòng)投案或自裁的。
李膺所謂“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jié)也”,主動(dòng)詣獄投死。與他一起赴死的茍?jiān)偹狼胺Q:“求仁得仁,又誰(shuí)恨也。”侍御史景毅的兒子是李膺的門徒,因被漏掉而沒(méi)被計(jì)入黨人名單,居然主動(dòng)辭官,并申請(qǐng)把自己的名字補(bǔ)上。名將皇甫歸因黨錮名單中沒(méi)有自己的家鄉(xiāng)人士,于是自表為黨人。
范滂是汝南郡的功曹,在黨錮之禍中的名聲很大。漢靈帝繼位后,大誅黨人。詔書(shū)下來(lái),要抓范滂,本郡的督郵抱著詔書(shū),把自己關(guān)在驛站的傳舍里,趴在床上哭。范滂聽(tīng)說(shuō)后,主動(dòng)投案自首。縣令聽(tīng)說(shuō)后,把官印和綬帶解下,準(zhǔn)備和范滂一起逃亡。范滂對(duì)縣令說(shuō):“我不能拖累你,更不能讓我的老母親一起逃亡。”范滂被殺時(shí),母親來(lái)看他,說(shuō):“今天你和賢士大夫李膺齊名了,沒(méi)什么好后悔的。”
另一個(gè)著名人物是張儉。朝廷的通緝令下達(dá)后,他從家鄉(xiāng)逃亡,途中困迫遁走,就去路旁敲百姓的家門尋求幫助。聽(tīng)說(shuō)他是張儉,大家都冒著被連坐的危險(xiǎn)來(lái)保護(hù)他并幫助他逃亡。后來(lái)張儉逃到山東東萊縣,住在李篤家中,縣令毛欽拿著兵器追到李篤家門口,李篤拉著毛欽說(shuō):“張儉是天下聞名的君子,大家都知道他是無(wú)辜的,今天你就是抓了張儉,忍心把他帶走嗎?”
毛欽拍著李篤的肩膀說(shuō):“你怎能說(shuō)只有你保護(hù)張儉,我呢?”李篤說(shuō):“如果你這么說(shuō),就是分走我一半的道義了。”毛欽嘆息而去,李篤就想辦法把張儉送出關(guān)塞。后來(lái),凡是張儉逃命經(jīng)過(guò)的地方,因保護(hù)過(guò)他而被滅族的有數(shù)十家。
王勃在《滕王閣序》里寫“徐孺下陳藩之榻”,陳藩在漢靈帝時(shí)官至太尉,黨錮之禍時(shí)他已七十多歲,因?yàn)樗敲迹鹿俦緵](méi)想動(dòng)他,可他聽(tīng)說(shuō)事發(fā)就帶著學(xué)生和下屬?zèng)_進(jìn)皇宮,跟宦官做最后的斗爭(zhēng),結(jié)果被抓起來(lái)害死在獄中。《后漢書(shū)》評(píng)價(jià)他:沒(méi)有獨(dú)善其身地隱居起來(lái)逃避社會(huì)責(zé)任,而是擔(dān)負(fù)起儒者的社會(huì)責(zé)任感,以死相爭(zhēng)。
無(wú)論是黨錮名士的不畏強(qiáng)暴、殺身成仁,還是天下百姓的奮迅感慨、波蕩而從,至今讀來(lái)仍令人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