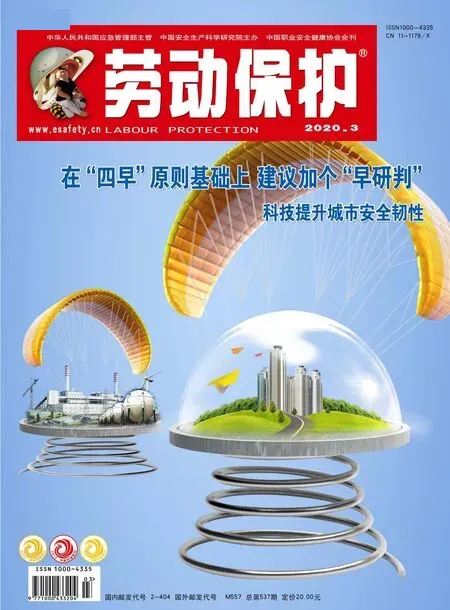健全應急管理體系的五大路徑
——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思考
文/王宏偉
2020年新年伊始,我國發生了嚴重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國在應急響應方面表現出空前的組織力、動員力。但與此同時,也暴露出我國應急體系還有許多亟待接長的短板,應急管理現代化水平還有待于進一步提升。本文提出了5個路徑健全應急管理體系。
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中國面對著各種威脅的挑戰。2020 年新年伊始,我國發生的嚴重新型冠狀病毒(以下簡稱“新冠”)肺炎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應急管理既是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組成部分,又為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總體建設保駕護航,責任重大,使命光榮。
2020 年2 月3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研究加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時指出:“我們一定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要針對這次疫情應對中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國家應急管理體系,提高處理急難險重任務能力”。
時間倒退回兩個月前,2019 年11 月29 日,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體學習時發表了重要講話(以下簡稱“集體學習講話”),為應急管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指明了方向。未來,我國健全應急管理體系、提高處理急難險重任務的能力,必須認真總結新冠肺炎疫情應對的教訓與經驗,奮力推進中國應急管理現代化。
新冠肺炎疫情應對急難險重的特點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個由生物致災因子引發的社會危機,超越了衛生部門應對的能力。它跨越了地理范圍,從武漢傳播到湖北其他市州,從湖北擴散到全國各地,從中國擴散到世界多個國家。同時,它也跨越了部門界限。疫情防控不只是醫藥衛生一家的事情,而是全方位的工作,需要黨政軍群協同應對。此外,新冠肺炎疫情應對中,網上網下、輿情疫情相互交織,處置起來異常復雜。
說它急,是因為病毒在人群中裂變式擴散。應急響應受時間的約束,如果不采取斷然措施,越來越多的人的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將會受到威脅。然而,新冠病毒來無影、去無蹤,形成一種難以感知與控制的風險。沒有特效藥物和疫苗,人們只能用古老的方法加以應對:隔離傳染源,切斷傳染鏈,保護脆弱性群體。一種恐慌的情緒在公眾中間散播,威脅著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行。
說它難,是因為處置難度高。新冠肺炎疫情不是一個常規突發事件。盡管新冠病毒與17 年前的SARS 冠狀病毒是“近親”,但缺少危機意識和感知能力的地方決策者還是習以為常地將其與從容應對過的諸多傳染病劃等號,從而錯過了早期防控的黃金期。等到人們認識到它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危機時,卻發現疫源地的醫療資源與就醫需求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缺口,而不得不采取“封城”、限制市內交通等“極端”措施。得不到及時收治的疑似病人或居家隔離,造成全家感染;或奔波在就醫的路上,成為移動的傳染源。由于疫情恰逢春節假期,大面積密集的人口流動給防控工作造成巨大的壓力。而“封城”前,武漢500 萬人的向外流動,使得全國都面臨著沉重的防疫任務。
說它險,是因為新冠病毒具有強大的傳染性,可能會造成醫護人員的感染。17 年前的SARS 冠狀病毒就造成醫護人員大量感染。“非典”期間,全國確診病例5 327 例,其中醫護人員感染約占1/5;死亡病例349 例,其中醫護人員約占1/3。2020 年2 月24 日,中國-世界衛生組織新冠肺炎聯合專家考察組在北京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稱,全國共有476 家醫療機構3 387 例醫務人員感染新冠肺炎。面對大批患者,武漢市醫生雖全力以赴,但也難以應對。從除夕夜開始,解放軍和全國各地派來的醫療隊紛紛趕來。但是,武漢市及湖北其他城市防護服、護目鏡、N95 口罩等醫療物資的短缺現象卻一時難以全部解決。
說它重,是因為新冠肺炎造成了大量的感染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病例。截至2 月24 日,全國累計確診病例7.7 萬余人,累計死亡2 663 人。如 果 從1 月20 日 武 漢市正式成立疫情防控指揮算起,疫情爆發僅1 個多月,但確診病例是SARS 的14 倍多,死亡人數是SARS 的7 倍 多,而SARS 流 行 的時間長達半年之久。
健全應急管理體系的五大路徑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中央成立疫情應對工作領導小組,國務院啟動聯防聯控機制。黨政軍群協同應對,群防群控,群防群治,穩防穩控。全國馳援武漢和湖北,16 省份啟動對口支援模式。習近平提出“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的16 字原則。在此基礎上,中國形成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3-3-4-4-5-2”模式:在戰略布局上,做到“三個全面”(全面動員、全面部署、全面加強工作);在應急戰術上,做到“三個統一”(統一指揮、統一領導、統一調度);在應急策略上,“四早”(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四集中”(集中患者、集中專家、集中資源、集中救治);在應急行動上,落實“五方責任”(屬地、部門、單位、社區和部門責任),努力做到“兩防”(內防輸入、外防輸出)。我國在應急響應方面表現出空前的組織力、動員力,令世界矚目。與此同時,我國應急體系還有許多亟待接長的短板,應急管理現代化水平還有待于進一步提升。提升的路徑包括5 個方面:

路徑一:堅持預防為主,立足于解決重救輕防的痼疾
從2019 年12 月8 日起,武漢就陸續出現新冠肺炎病人。這并沒有引起武漢市政府的關注。2020 年1 月上旬,武漢醫務人員出現感染。但是,官方媒體一再聲稱“可防可治”,人際傳播概率低。直到1 月20 日,鐘南山揭開“蓋子”,武漢市才開始認真應對,成立指揮部,其風險防范和危機應對意識十分薄弱,反應遲緩。
以往,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主要表現在應急響應、特別是巨災的應急救援方面,而突發事件的預防成為一個明顯的弱項與短板。國外相關研究表明,預防上1 美元的投入,未來可以帶來4 美元的收益。中國也有“一針及時省九針”的諺語。但是,預防是一種難以印證的隱績,人們似乎更愿意“轟轟烈烈救災當英雄”。而不愿意“默默無聞防災做模范”。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治國理政的實踐中,在應急管理方面強調“兩個堅持,三個轉變”,即“堅持以防為主、防抗救相結合,堅持常態減災和非常態救災相統一,從注重災后救助向注重災前預防轉變,從應對單一災種向綜合減災轉變,從減少災害損失向減輕災害風險轉變。”這同樣適用于重大疫情防控。但是,地方政府官員的風險防范意識弱,危機感知能力低。
在集體學習講話中,習近平特別強調了風險管理和綜合減災。在風險管理方面,他強調“健全風險防范化解機制,堅持從源頭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風險,真正把問題解決在萌芽之時、成災之前”,具體包括落實風險評估、監測預警、隱患排查等各項措施。在綜合減災方面,他強調各類事故隱患和安全風險的交織疊加性,要求提升對多災種、災害鏈綜合的監測,從而系統性地應對復雜風險。
路徑二:提高應急準備能力,立足于解決準備不足的問題
以往對于傳染病疫情,許多地方政府的習慣性做法是“內緊外松”。但是,從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武漢政府的官員因為沒有意識到危機的到來,并沒有采取明顯的臨時性減緩措施,“外松內不緊”。應急準備就是應急響應準備。長期以來,我國應急管理準備不足,甚至出現表面化、形式化、懸空化的弊端。應急預案在一些部門和地方僅僅是“紙上畫畫,墻上掛掛”,不能發揮未雨綢繆、有備無患的作用。武漢市此次應對就反映了這一問題。疫情不太嚴重的一些省市啟動了一級響應,而武漢還停留在二級響應。至于醫護人員、床位、物資短缺,更讓武漢的疫情應對忙亂不堪、毫無章法。
在集體學習講話中,習近平把應急響應的關口前移到應急響應準備、將重心從靜態的應急預案轉落到動態的預案管理,提出了應急管理能力建設的“預案管理+三大保障”的總體構想,體現了真打實備的理念。
良好的應急準備能力離不開完善的應急保障體系。在這一方面,習近平在集體學習講話中重點論述了三大保障,分別是隊伍保障、裝備技術保障和法制保障。應急隊伍包括管理隊伍和救援隊伍。他肯定、褒揚了應急管理部門常年堅持值守、隨時面對極端情況和生死考驗的奉獻精神,極大鼓舞了應急管理干部。同時,他要求應急救援隊伍“對黨忠誠、紀律嚴明、赴湯蹈火、竭誠為民”,提出了“專常兼備、反應靈敏、作風過硬、本領高強”的建設目標。圍繞這一目標,國家綜合性救援力量與地方專業力量、志愿者隊伍共訓共練,形成協同救援能力。通過拳頭力量的鍛造、區域性應急救援中心的建設、應急指揮機制的加強、航空和高鐵等現代化運輸手段的運用,應急救援隊伍要提升快速反應能力、應急機動能力、合成應急能力,以實現就近調配、快速行動、有序救援的目標。此外,習近平還指出,要加強應急管理學科建設,培養優質的應急管理人才,這有利于應急隊伍的長期穩定和持續發展。
在應急裝備技術保障方面,習近平提出要依靠科技實現應急管理的“四化”,即科學化、專業化、智能化、精細化。特別是,要以信息化推進應急管理的現代化。這些要求無疑將會提升我國應急救援的裝備技術水平,成為我國應急管理事業跨越式發展的新引擎。
在應急法制保障方面,習近平提出堅持依法應急,實現應急管理的法治化,在修訂既有法律的基礎上,抓緊制定應急管理法、自然災害防治法、應急救援組織法、國家消防救援人員法、危險化學品安全法等重要法律法規。這將給我國應急管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提供法律“加持”。在此次疫情防控的關鍵時刻,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強調要依法有序防控疫情。
此次疫情應對給我們最大的教訓是,即便我國改革開放后積累了豐厚的物質財富,但大規模突發事件發生后需求與供給之間也可能產生結構性、階段性缺口,必須加強建立醫療物資等戰略儲備體系。
路徑三:實現全過程精準治理,立足于改變“人多力量大”的粗放應急模式
曾經,一些巨災救援的現場經常會出現規模龐大、無序低效的問題。粗放式的應急模式基于“人多力量大”的陳舊思維,不能滿足應對系統性、復雜性突發事件的需要。無序的救援力量不僅會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費,還會導致救援通道的阻塞、隊伍之間的沖突、不必要的次生災害等。精準救援是克服以上弊端的法寶。
在集體學習講話中,習近平強調應急管理要實施全過程的精準治理,除了精準救援外,他還強調預警發布、恢復重建、監管執法要精準。預警發布的精準可以減少虛警、空警,提高預警的權威性、針對性,減少不必要的擾民;恢復重建的精準可以避免“大水漫灌”、聚焦弱勢群體的利益、體現公平正義原則,把好鋼用在刀刃上;監管執法的精準可以統籌安全與發展、避免“一人得病,全家吃藥”的弊病。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漢市在中央指導組的指導下,對確診、疑似、發熱與密切接觸者進行分類,重癥到定點機構、輕癥在方艙醫院分別收治,其他疑似、發熱、密切接觸者到征用的酒店、賓館、培訓中心、黨校、高校等地集中隔離觀察,分級分類管理,體現了精準施策。但是,此次疫情警示我們,精準并不一定意味著規模小的“精干”,關鍵是目標要準確、行動要有序、措施要有力、結果要有效。
路徑四:推動以人為本的社會共治,立足于改變單純依靠政府力量救援的局面
我國是一個政府主動型的社會,且處于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公眾公共安全意識和自救互救的技能不足,基層社會單元的應急管理能力薄弱,存在著單純依賴政府救災的傾向。現代社會的風險具有高度的流動性、跨界性與分散性。只有將應急管理的責任落實到每個社會單元、甚至每個社會成員身上,政府才能夠牽頭構建起一道無縫隙的公共安全網絡。
習近平在集體學習講話中特別強調要發揮我黨群眾路線、群眾觀點的優勢,大力培育安全文化,推動宣教“五進入”,引導社區公眾參與隱患排查和治理,筑牢防災減災救災的人民防線。這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在應急管理領域的必然體現,有助于我國強化應急管理的基層基礎,形成對突發事件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
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黨和政府充分動員群眾、組織群眾、凝聚群眾,形成群防群治的網絡。基層社區采取網格化管理,社區干部、政府機關的下沉干部、片警、社區醫生與志愿者對社區居民進行滾動式排查,提供便民服務。武漢市社區還建立了初級分診制度,為公眾有序就醫提供醫療服務。但是,我國應急捐贈管理體系有待于進一步完善,要對統一接受并使用捐贈的做法進行反思和評估,建立統一與分散相結合的機制,具體做法是:社會自行對接,政府調劑余缺。
路徑五:壓實政治責任,立足于解決應急管理改革的體制性難題
2018 年,在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中,我國組建應急管理部,上與下、防與救關系問題逐漸浮現、突出。首先,受機構編制的局限,越到基層,應急管理越是遭遇“事多人少責任大”的尷尬。一些地方的主要領導干部對應急管理工作的重視不夠,特別是對自然災害防治的責任意識不強,導致上下聯動困難。其次,防與救的關系不理順,許多部門錯誤地認為“應急管理是應急管理部門一家的事情”,推諉扯皮,造成應急管理的完整鏈條人為地被割裂。
在集體學習講話中,習近平強調各級黨委要擔負起“促一方發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責任”。自然災害管理與安全生產一樣,都要強調黨政同責、一崗雙責。而且,問責要建立在重大自然災害和安全生產事故調查評估的基礎上,以維護問責的嚴肅性和科學性。這樣,壓實政治責任就能夠進一步喚起地方黨政領導對災害事故管理的重視,激發地方主動性、創造性開展工作的熱情,有效解決上與下的聯動問題。
此外,防與救之間的關系是難以做到斷然切割、涇渭分明的,二者之間是犬牙交錯、相互嵌套的。應急管理與水利、林草等部門之間要相互協同、密切配合,才能高效應對災害事故。習近平指出,要發揮應急管理部門的綜合優勢和相關部門的專業優勢。這樣,應急管理部門與其他部門就能夠實現優勢互補、形成整合力,進而解決應急管理部門權責有邊界與突發事件風險無邊界的沖突。
新冠肺炎應對是一場總體戰,需要多個部門、多元主體的參與。為了協調各方,各地都按照中央的要求,成立了疫情防控指揮部,由黨委一把手負責。在應急管理改革背景下,許多地方都成立、改組了應急委,辦公室設在應急管理廳局,應急委的領導是政府領導。新成立指揮部的做法一方面提升指揮、協調的層次,但另一方面也使平時建立的指揮體系處于閑置狀態,不利于經驗的積累。我國應進一步加強應急管理頂層架構設計,建立由黨中央統一領導的特別重大突發事件指揮機構,辦公室可以設在應急管理部。這個機構常態運轉,平常負責督促落實各級政府的應急準備工作、磨合部門協同機制,災時協助中央指派的領導同志進行指揮調度。同時,這也可以從根本上有效解決應急管理改革中存在的統分、上下關系。
習近平說,中華民族是從艱難困苦中走過來。我們要善于從災難中學會如何應對災難,通過認真思考此次疫情應對中的經驗和教訓,拿出有針對性的戰略舉措,提升應急管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水平,不斷將中國顯著的政治優勢轉化為應急管理的效能,為中華民族復興的偉業提供更堅強、更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