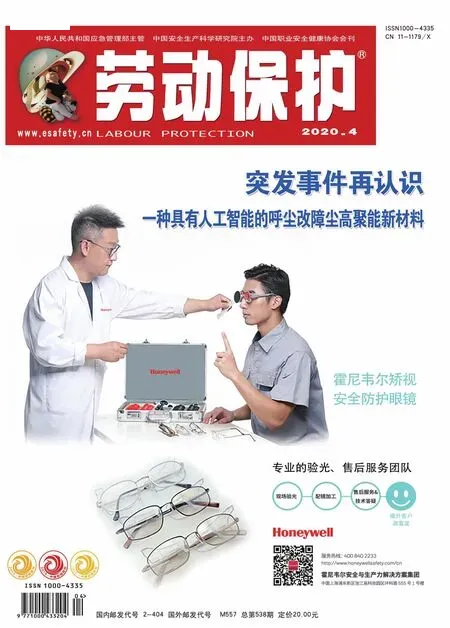“疫后重建”應急法律體系何去何從
——訪中國政法大學應急管理法律與政策研究基地主任林鴻潮
文/本刊記者 趙苡萱
2020 年春節,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肺炎疫情(以下簡稱“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了中國大地,我們在積極應對的同時,也發現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引起了應急領域專家、學者們對突發事件的新認識和新思考——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國應急法律體系存在哪些不足?《突發事件應對法》是否到了必須修改的階段?如若修改,將何去何從?下一步,我國應急管理法律法規,應該完善哪些工作?帶著這些問題,本刊記者采訪了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應急管理法律與政策研究基地主任林鴻潮,請他詳細回答。
記者(以下簡稱“記”):2020年春節遭遇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影響全國的突發衛生公共安全事件。此外,我國還曾遇到過多次突發的自然災害、生產安全事故等。請問,這些突發事件暴露出我國應急法律體系存在哪些方面的不足,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林鴻潮(以下簡稱“林”):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國應急法律體系存在的問題,我覺得可以從3個方面來講。
首先,我國應急法律體系內部不統一、理念沖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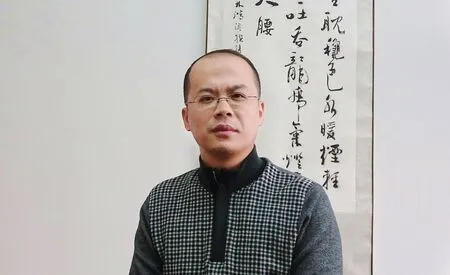
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應急管理法律與政策研究基地主任林鴻潮
我國在2003 年“非典”疫情之后,吸取了很多教訓,意識到應急管理體制不能以部門為主,原因在于應急管理的跨部門、跨種類性質非常明顯。雖然還是需要借助部門的專業判斷,但是要應對突發事件,政府的綜合統籌能力就凸顯出來,這主要得益于地方政府考慮全局、處理突發事件的眼光和視野都會優于部門。在應對突發事件的問題上,一個部門的統籌能力跟一級政府沒有可比性。
我國在制定《突發事件應對法》時,確立了政府綜合協調、屬地管理為主、應急響應重心下移等基本原則,這些都符合應急管理的基本規律。但是,這些思想并沒有同步貫徹到應急管理體系的其他單行性法律法規中,使得應急領域的一些單行法還保持著部門為主,“條”重于“塊”的色彩。
以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信息的發布為例,《突發事件應對法》是一般法,適用于四大類(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社會安全)突發事件;《傳染病防治法》是特別法,只適用于傳染病防治。按照《立法法》第83 條規定:“同一機關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特別規定與一般規定不一致的,適用特別規定。
所以,雖然《突發事件應對法》中規定的屬地管理、重心下移這些原則是不錯的,但在實踐中就會被架空。在傳染病疫情信息發布的問題上,只能適用《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而《傳染病防治法》就比較重視“條”的管理機制,如果把新冠肺炎疫情當作傳染病來進行管理,那就需要先進入“傳染病目錄”,而進入“傳染病目錄”就需要層層審批;未進入“傳染病目錄”,就不能適用傳染病的相關制度,這就容易造成疫情信息發布不及時。這與我們經常講的應急管理理念、原則并不符合。總的說來,我國目前的應急管理體系還存在著這樣的沖突。
其次,我國應急法律的實施機制不夠科學。
目前,我國應急法律體系沒有一套科學的實施機制。應急預案本應作為應急法律的重要實施機制,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應急預案性質的理解并不準確。
政府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科層制體系,基層獲得信息之后層層上報,直到觸發決策層,決策層決策之后再逐級下達去執行。這樣的運行機制嚴謹、規范,在常態下是沒問題的。但突發事件的處置對效率的要求非常高,依靠平常的科層制體系實施法律是行不通的,必須代之以有效的預決策機制。就是在法律制定之后,只要預先假設的危機情景出現,相關主體就應該直接采取法定措施,無需層層請示匯報,以保證決策的及時性。這個預決策機制就是應急預案。
我國的應急預案在“非典”疫情之后開始建設。在2006 年前后,應急預案體系基本做到了“縱向到底、橫向到邊”,但在實踐中作用卻不大,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應急預案的性質理解得不準確。我們長期將應急預案理解為法律制度的細化和延伸,導致其可操作性差,更新迭代慢。應急預案沒有發揮出法律實施預決策機制的作用。
第三,傳統立法理念導致我國應急領域法律比較粗糙。
目前,我國的法律體系還比較粗糙。我們在立法時經常受到一些傳統觀念的影響,比如說“宜粗不宜細”“幾個不談”(不談機構、不談人員、不談錢)的原則等。但突發事件是能力本位的概念,在事件發生之后,政府乃至全社會的能力和這個事件應對的需求之間存在差距,這個事件才能夠被稱為突發事件。要應對突發事件,就要在短時間內補齊能力差距。而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無非是人力、財力和物力的組合。要保證人、財、物有一個比較高的準備水平,需要在法律上有十分明確的、剛性的、嚴格的制度要求。
這樣一來,法律一旦規定得比較模糊,突發事件發生時,需要的人力、財力和物力肯定落實不下去。最后,這些模糊、原則的法律條款只能起到軟約束或倡導作用。
我認為,以上3 點,是我國整個應急法律體系,包括《突發事件應對法》和應急領域其他單行性法律實施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
記:具體到《突發事件應對法》,您認為,是否已經到了必須修改的階段?原因是什么?
林:我認為《突發事件應對法》必須要改,需要修改的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介紹。
從應對非常規突發事件的層面來看,《突發事件應對法》并沒有解決宣告“緊急狀態”的問題。因為2003 年“非典”疫情時,觸發了一些法律問題,使得全國人大在2004年將原來憲法上的戒嚴制度修改為宣告緊急狀態制度,同時決定制定一部“緊急狀態法”,將所有突發事件可能引起的緊急狀態全部涵蓋。后來,因為立法思路的改變,最后沒有制定“緊急狀態法”,而是制定了主要應對那些還不至于構成緊急狀態常規性突發事件的《突發事件應對法》。
從功能定位上來看,《突發事件應對法》與最初設想的“緊急狀態法”有一些偏差,使得已經寫進憲法的緊急狀態制度沒有辦法落實。這就造成一些應該宣告緊急狀態的情況,由于沒有可以操作的具體制度,并沒有宣告。比如,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后,各級政府采取了很多的非常措施,但并沒有宣告進入緊急狀態。
從應對常規突發事件的層面來看,《突發事件應對法》也沒有解決好。這是由于《突發事件應對法》適用于四大類突發事件應對的全過程,要從中抽取各種突發事件共同的應對方法,提取“最大公約數”,結果使得《突發事件應對法》變得非常抽象,可操作性和可實施性降低,沒有達到預想的效果。
記:如若修改《突發事件應對法》,您認為,應該著重于哪些方面的修改,以解決當下面臨的主要難題?
林:如果要修改《突發事件應對法》,我建議放棄四大類突發事件全過程大包大攬的想法,回到最初的設定,將《突發事件應對法》改造為“緊急狀態法”。在“緊急狀態法”中,可以覆蓋四大類突發事件比較嚴重的情況,并對其進行提煉和統籌,不再具體規定四大類突發事件全過程的常態管理和一般應對過程。統籌之后,在突發事件影響嚴重的情況下,宣告進入緊急狀態。同時,對宣告緊急狀態的門檻要適當下調。
緊急狀態可以劃分類型,如自然災害緊急狀態、事故災難緊急狀態、公共衛生事件緊急狀態、社會安全事件緊急狀態、戒嚴狀態,明確將前4 種緊急狀態和戒嚴區別開來,以達到全社會對緊急狀態“脫敏”的作用。
記:對于我國的應急管理法律法規,您認為,下一步應該完善哪些工作?
林:我國的應急管理法律法規體系,按照2019 年11 月29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體學習中講的立法思路:要堅持依法管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提高應急管理的法治化、規范化水平,系統梳理和修訂應急管理相關法律法規,抓緊研究制定應急管理、自然災害防治、應急救援組織、國家消防救援人員、危險化學品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規。
按照總書記闡述的立法思路,從突發事件的四大類型來看,可以把自然災害、事故災難這兩類高頻的突發事件應對工作,和應急救援、應急救助、應急物資儲備等跨種類、綜合性的工作,納入一部綜合的應急管理法律中,這也比較符合應急管理部的職責,也就是“應急管理法”。
自然災害有其自身的特點和規律。目前,我國自然災害領域的法律制度相對完善,主要的單災種都有其法律、法規,數量也比較齊全,但這些法律還是立足于單災種、單部門而制定。實際上,很多災害管理工作是可以跨災種綜合進行的,這些工作“合著干比分著干好”,比如災害風險評估、救災物資儲備、災害監測網絡、避災場所建設、災害應急救援隊伍、救災資金撥付管理等工作。這時候,就需要歸納、總結自然災害應對的共同特點和規律,制定一部綜合性的“自然災害防治法”,從應對單一災種向綜合減災轉變,達到節省資源、提高效率的目的。
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法律體系中,已有《傳染病防治法》《食品安全法》《疫苗管理法》等相關法律,下一步還將要制定“生物安全法”。2019 年12 月28 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了《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將來可以把公共衛生應急最核心的制度加入到這部法律當中,起到公共衛生領域應急基本法的作用。
對于社會安全事件來說,本沒有統一的可能性。因為社會安全突發事件種類復雜,有暴力型的群體性沖突,經濟型的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等,還有糧食危機或能源危機,這些種類突發事件的應對方法都不一樣,所以沒有統一建立社會安全突發事件法律體系的必要性。
記:2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機制體制,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是會議的重要內容。會上,習近平就此提到15個體系、9種機制、4項制度。這個體系的提出,是否對除公共衛生安全領域以外的應急管理領域,同樣會產生影響?會產生哪些影響?是否像“非典”疫情一樣,成為我國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的關鍵節點?
林:2 月14 日習近平總書記提到的15 個體系、9 種機制、4 項制度,這些體系、機制、制度的提出,對應急管理體系的影響,我認為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一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這就有可能帶動其他重大突發事件的應對也納入國家安全體系,如重大自然災害應對。目前,這類事件有時會涉及國家安全問題,但一直沒有納入國家安全的框架。
另一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健全統一的應急物資保障體系,把應急物資保障作為國家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目前,我國的應急物資還沒有統一,分散在各個部門,如有的分散在應急管理部,有的分散在國家衛生健康委等。這些應急物資,有些是相同的,有些是專業性的,但無論哪種應急物資,物資儲備、物資調配、物流組織等工作都可以進行統籌管理。這時候,就需要出臺相應的應急物資保障條例,為應急物資保障體系的統一提供法律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