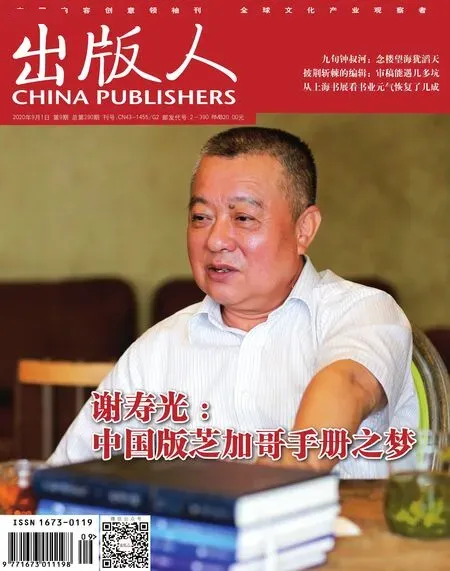披荊斬棘的編輯:審稿能遇幾多坑?
文丨淡 霞
審稿路上,陷阱、大坑小坑無數(shù),編輯不得不步步驚心,時刻提防。

1200 多年前,“詩仙”李白一邊苦悶著“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一邊逸興遄飛地吟出“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1200 多年后的今天,庚子鼠年上半場,一邊是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流行的大瘟疫讓各國陷入行路難的困境;一邊是綜藝節(jié)目《乘風破浪的姐姐》大紅大紫,“乘風破浪”迅疾成為爆款時髦詞。
實則,相較于熱鬧喧騰的娛樂圈,2020 年上半年的出版圈在新冠疫情影響下,乘風破浪的少,行路難、多歧路的多。而編輯,作為出版圈的傳統(tǒng)骨干力量和內(nèi)容審查主體,無論外部環(huán)境如何變化,其審稿的程序和標準是較為穩(wěn)定的。雖則穩(wěn)定,但對于每一個編輯來說,將一部新書稿打磨成一本合格的甚至是優(yōu)秀的讀物,不啻一段披荊斬棘的行路歷程。
披荊斬棘,櫛風沐雨,為的是經(jīng)過艱苦作業(yè),打造出合格的出版物。然而,審稿路上,陷阱、大坑小坑無數(shù),編輯不得不步步驚心,時刻提防。
導向、基調(diào)坑:于無聲處驚雷
俗話說:國有國法,家有家規(guī)。行業(yè)也有行業(yè)的規(guī)矩和制度,對出版行業(yè)來說,國務(wù)院2016 年修訂并頒布的《出版管理條例》就是編輯審查書稿主題時要參考和遵照的重要依據(jù)。條例規(guī)定,“出版單位實行編輯責任制度,保障出版物刊載的內(nèi)容符合本條例的規(guī)定”,也就是說編輯對書稿的內(nèi)容審查負有主體責任。
同時,《出版管理條例》明確規(guī)定了出版物不得含有的內(nèi)容,比如“危害國家統(tǒng)一、主權(quán)和領(lǐng)土完整的”,那么有關(guān)香港、臺灣、西藏、新疆、南海等內(nèi)容表述就值得特別關(guān)注,比如稱呼香港為“殖民地”,將臺灣與其他國家并列,繪制中國地圖時漏掉南海九段線等,這些表述都是錯誤的,屬于典型的、嚴重的政治性差錯。編輯審稿時對此應(yīng)高度重視,避免一頭栽進政治導向坑中。比如“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破壞民族團結(jié),或者侵害民族風俗、習慣的”,有的書稿會在不經(jīng)意間涉及少數(shù)民族的信仰、風俗和飲食習慣等方面的信息,措辭稍有疏忽,便會造成不良影響和后果。這屬于民族問題導向坑。比如“宣揚邪教、迷信的”,有的書稿打著學術(shù)研究的幌子,在書稿中大幅宣揚邪教的宗旨和傳教過程,誤導人們“確信其事”,或者打著傳承傳統(tǒng)文化的旗子,在書稿中大肆描摹風水、算命等封建迷信內(nèi)容,都是不可取的。編輯在審稿時要有分辨的能力,及時處理相關(guān)文字,以免掉進這個“邪教、迷信”的坑。另外,還有宣揚“淫穢、賭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這種 “黃、賭、毒、罪”的傳播不良風氣的導向坑,也是編輯審稿中應(yīng)該著重關(guān)注和警惕的部分。
除了以上較為明顯的政治性差錯坑、民族問題導向坑、宣揚邪教迷信坑、宣揚違法犯罪坑等,審稿時,還應(yīng)特別關(guān)注某些與現(xiàn)行憲法不一致的主題言論,比如憲法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shè)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tǒng)一和尊嚴”,有的書稿內(nèi)容卻出現(xiàn)“法治是以約束為主的,把人捆綁起來是其主要機制”“在以法治為中心的神教教義或政治哲學中,根本沒有人的向上成長這個維度”,這樣的表述即為明顯的錯誤導向坑,應(yīng)該警惕并處理。
與主題導向坑相比,基調(diào)歪斜的坑就顯得更為隱蔽和低調(diào)。
書稿基調(diào)不正確也是個大坑,大約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為歷史人物翻案的所謂新銳前沿思想,比如對漢奸、賣國賊汪精衛(wèi)的評價,近年來有學者打著學術(shù)探討的名義撰寫文章,認為汪精衛(wèi)做漢奸是特殊歷史時期的另一種曲線救國,試圖以此為汪精衛(wèi)正名。這類論述極易形成基調(diào)歪斜的坑,審稿編輯不得不慎重。
此外,隨著近年來傳統(tǒng)文化熱潮興起,人們對傳統(tǒng)文化和古代圣賢的推崇也水漲船高到一個新的頂點,但對其評價不應(yīng)過度用力、過分吹噓,比如“沒有圣人就沒有中國,沒有堯舜禹這樣的圣王,就沒有今天的中國”。此等溢美之詞,可以休矣。
第二類是立場偏頗的基調(diào)。在涉及古代一些歷史事實的表述時,作者應(yīng)保持較為公正中性的立場進行評騭,不應(yīng)代入過多個人主觀的意愿,尤其是這種主觀意愿與現(xiàn)行的意識形態(tài)相左,由此得出的結(jié)論自然是片面的,甚至是偏離的。比如有的書稿中談及清軍,尤其是湘軍、楚軍和太平天國軍隊之間的戰(zhàn)爭,作者行文時,對太平天國、太平軍的用語,沿襲清朝、湘軍、楚軍立場,多以“匪”“賊”“寇”稱之。于湘軍、楚軍,譽其為“禮儀之師”;于太平軍,則冠以“野蠻之師”,讀者閱文后,正邪立判。
類似的句子、論述,從編輯審稿的角度看,如果屬于引用歷史文獻,為保持原文狀態(tài),這些字眼可一仍其舊以存其真,不煩改竄;但若為作者自己的敘述文字,則當中正平和,一視同仁,不宜厚此薄彼。
第三類是所謂的宣傳正能量實則違背現(xiàn)代文明探索精神的基調(diào)。這類書稿,大多頂著政治正確的帽子,往往從宣揚中國強大,以至于引領(lǐng)世界,或者極力鼓吹夸大傳統(tǒng)社會的優(yōu)越性出發(fā),發(fā)出罔顧現(xiàn)實、唯我獨尊的“自信”言論。比如“今日世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國的復興”“沒有中國技術(shù),歐洲根本不可能重新煥發(fā)出生命力”“沒有儒家思想,根本不可能有啟蒙運動”。諸如此類的話語,表面上看是傳遞正能量,增強民族自信,實則為盲目自大,荒誕無根,違背實事求是和科學論證的原則,無論從效果上還是從學理上都難以服人。這類書稿基調(diào)歪斜得較為隱蔽,需要引起編輯的特別關(guān)注。
導向坑、基調(diào)坑,坑坑險象環(huán)生,且坑坑決定一部書稿是否能順利變成書籍。編輯在披荊斬棘地審稿中,首先要把握和跨越的就是此類大坑,這些大坑不處理,會留下巨大隱患,一來可能導致整部書稿被斃掉,二來后面的編輯工作將無從談起,即使有時在書稿的細枝末節(jié)上處理得相當完善與精美,也無法補救這些根本性錯誤。
決定書稿命運的大坑,不可回避,亦無法回避,唯有謹慎面對。
結(jié)構(gòu)、材料坑:不畏浮云遮望眼
一部書稿,如同人的身體,有血有肉,更重要的是要有骨架。有了骨架,人才能立起來,于書稿而言,篇章結(jié)構(gòu)和內(nèi)容的內(nèi)在邏輯就是它的骨架。茅盾文學獎獲得者、著名作家陳忠實曾經(jīng)寫道:“長篇小說如果沒有一種好的結(jié)構(gòu),就像剔除了骨頭的肉,提起來是一串子,放下去是一攤子。”雖然他說的是長篇小說,但這個原則同樣適合其他文學體裁的創(chuàng)作。
幸運的編輯,或許會遇到結(jié)構(gòu)完整、邏輯清晰的整部書稿,如此便會節(jié)省很多審稿的力氣和時間;但哪個編輯又能保證自己每次拿到的新書稿都是幸運氣球加持的呢?或多或少,編輯在職業(yè)生涯中都會遇到一些結(jié)構(gòu)松散、邏輯混亂的書稿,這時便意味著,審稿路程中的第一個中坑出現(xiàn)了:結(jié)構(gòu)坑。
存在結(jié)構(gòu)缺陷的書稿,或許是作者沒來得及整理,只是將所有文章收集在一起就發(fā)給編輯;或者是作者自己有大致的想法,但這種構(gòu)想不太理想或者不符合當下的市場需求;或許是作者已去世,作品龐雜無序,后人沒有能力整理,這時就需要理出一種思路,用這思路將所有文章按照某種規(guī)律組織起來。
比如一個作者的書稿,可以按照創(chuàng)作時間來編排,可以按照歸納出的主題來編排,還可以按照文學題材來分門別類地編排。如果是小說,按照創(chuàng)作時間來串聯(lián),可以看出一個作家早、中、晚等各個時期的創(chuàng)作特點,具有時間的延續(xù)性;如果按照篇幅來分類,可以分為短篇、中篇、長篇等,如此可顯示出作家對各種篇幅作品的駕馭能力,“豆腐塊”精煉簡潔,長篇則宏大精深;如果是主題編排模式,則彰顯出作家創(chuàng)作內(nèi)容和角度的寬廣開闊、豐富多樣性。如此,不一而足。
總之,無論是哪種結(jié)構(gòu)編排方式,都隱含著這部書稿的內(nèi)在邏輯性,有了內(nèi)在邏輯性,整部書稿的主旨和獨特性就顯示出來;同樣,無論是哪種內(nèi)在邏輯性,都需要在書稿的結(jié)構(gòu)(目錄、大綱、導語等)中實實在在地體現(xiàn)出來。這結(jié)構(gòu),就是串起書稿血和肉的骨架;這結(jié)構(gòu)坑,是編輯必須正視和跨越的。
同時,能將或意向模糊,或個性鮮明的一篇篇獨立文章搭建成有血有肉有骨架有精氣神的一本書稿杰作,也是一個杰出編輯的獨到策劃思想的體現(xiàn)。從這個角度說,這結(jié)構(gòu)坑既是風險,也是機遇。
如果說結(jié)構(gòu)是骨架,是串起珍珠項鏈的一根線,那么書稿中的材料就是這串項鏈的顆顆珍珠。這些珍珠,魚龍混雜,良莠不齊,質(zhì)量上乘的珍珠會為整部作品增光添彩,錦上添花;品質(zhì)低劣的珍珠不僅起不到有益的作用,有時還會成為累贅,乃至禍害,也會成為質(zhì)檢專家、讀者、批評家的把柄。
書稿中不當?shù)牟牧铣蔀閷徃宓臄r路虎,甚至是危險系數(shù)較高的中坑,這是很多編輯始料未及的。概括起來,這些不當材料大約可分為兩種,一種是重復的材料和觀點,這類情況大多出現(xiàn)在演講稿文集、發(fā)言稿文集,以及一些主題較為單一的評論文集中。比如某個專門研究某一類文化的專家,在歐美、在東亞、在非洲等各種場合都做演講,囿于自身知識儲備的專業(yè)性,他演講的內(nèi)容和主題大多為同一個方向,因此,同一種材料、引文,甚至是觀點,重復出現(xiàn)的幾率很高。每篇演講稿或評論文單獨展示時,尚無大礙,但若將這些文章結(jié)集出版,材料重復、觀點雷同的劣勢就暴露無遺。此時,若編輯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這個陷阱,就要及時跟作者溝通文稿處理事宜。
不當材料的另一種表現(xiàn)是過時材料和觀點的使用。比如關(guān)于抗日戰(zhàn)爭時間的說法,如今正確的提法應(yīng)該是“抗日戰(zhàn)爭進行了14 年”,之前“8 年抗日戰(zhàn)爭”的表述不再提倡,但現(xiàn)在有些書稿中還使用舊的、過時的說法。
不當材料的使用還有文不對題、邏輯不通、錯誤使用等情況,需要編輯一一仔細辨別。
使用材料,是為了佐證或反證自己的觀點,某種程度上說,材料即觀點。秉持著觀點要守正、傳承、創(chuàng)新的理念,篩選起材料來才不會走入迷途,如墜五里云霧中。
重復的、過時的材料和觀點,如同冷兵器時代的大刀長矛,用它來對抗現(xiàn)代化學術(shù)探索領(lǐng)域的堅船利炮,必定會落荒而逃、貽笑大方。作為書稿最重要的內(nèi)容審核官,奮斗在消滅荊棘和雜草路上的編輯,若輕易繞過材料觀點坑,怎會沒有遺憾和愧疚呢?
知識、字詞、標點坑:野火燒不盡
“苦為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此詩雖然是寫唐朝貧苦人家的繡娘,但經(jīng)常被拿來形容編輯的奉獻及其工作的辛苦。編輯的辛苦不僅體現(xiàn)在跨越作者書稿中時常隱藏的大坑、中坑,這些都是大毛病、大問題,自然值得特別關(guān)注和警惕,然而,日常工作中大多數(shù)編輯的大量時間和精力都花費在處理書稿的無數(shù)小坑上。這些小坑種類繁多,瑣碎幽微,即便清理好幾次,還是會經(jīng)常讓人防不勝防,像極了漫漫征途中讓人跌倒、崴腳卻總被忽略的無數(shù)小坑洼。
小坑洼的第一個成員是知識坑。編輯作為文化人、知識分子,雖然每天都跟書本和各種知識打交道,但能學到的知識還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審稿工作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挑錯,找出知識和邏輯錯誤并改正,顯得尤其重要。那么,問題來了,怎么找錯?怎么改正?
打鐵還需自身硬。對付知識性錯誤,只能動用自己的儲備,儲備豐富,就容易找到錯誤;儲備匱乏,就容易在小坑中吃虧。除此,沒有別的捷徑可走。如此,編輯就需要時刻帶著常識、帶著問號去審稿。
比如:“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為了戰(zhàn)勝中國,英國派出了四千人的軍隊。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八國聯(lián)軍數(shù)量為兩萬人。”眾所周知,八國聯(lián)軍侵華戰(zhàn)爭發(fā)生在1900 年,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發(fā)生在1856 年到1860 年,著名的圓明園就是在1860 年被英法聯(lián)軍焚毀的。因此,上述句子中,八國聯(lián)軍應(yīng)該改為英法聯(lián)軍,兩萬人改為兩萬五千人。
比如:“這套房子的好,就好在外部環(huán)境。一出門就是三里屯village(后來更名為三里屯太古里),這個建筑據(jù)說獲了當年的普利策獎。”普利策獎也稱普利策新聞獎,是美國新聞界一項最高榮譽獎。普利茲克獎也稱普利茲克建筑獎,有建筑界的諾貝爾獎之稱。因此,上述句子中,普利策獎應(yīng)改為普利茲克獎。
知識的欠缺、常識的錯位,使得書稿不時會出現(xiàn)關(guān)公戰(zhàn)秦瓊的鬧劇。此鬧劇,實在不應(yīng)上演。
囿于個人經(jīng)驗,考驗知識儲備的錯誤或許會被遺漏,但若編輯愿意靜下心來認真審稿,有些錯誤利用常識和邏輯推理即可發(fā)現(xiàn)其謬誤之處。
比如一部書稿中將意大利畫家喬托·迪·邦多納的生卒年月寫為:約1266—1377 年,如此推算,這個畫家活了111 歲,這在700 多年前不大可能。后經(jīng)查證,喬托的正確生卒年月應(yīng)為1266—1337 年。
面對不同類型和專業(yè)的書稿的知識性錯誤,動用學識儲備也好,開動腦筋多想一步也罷,只要對消滅錯誤小坑洼有用,皆可為編輯所用。
錯誤小坑洼的第二個成員是字詞句錯誤坑。消滅錯別字,是所有編輯的基本功之一,除了發(fā)揮個人主觀能動性,多看多記多練之外,還可借助黑馬軟件的力量來事半功倍。黑馬軟件的好處在于,一是可以查出書稿中大多數(shù)明顯的字詞錯誤,對查找人的肉眼容易忽略的多字、少字、漏字問題也很有幫助。使用黑馬軟件的第二個好處是可以提示選用《現(xiàn)代漢語詞典》里的首選字。這對那些記不住首選字的編輯來說,是個不錯的幫手。
和語言文字一樣,標點符號的使用也要遵循一定的規(guī)則和規(guī)范。一般的標點符號用法,編輯大多能熟練掌握,但遇到較為生僻的,不大常用的,或者是雖然一直使用,但總能出錯的,編輯就需要時刻學習并記住。
身為編輯,除了現(xiàn)漢、辭海等工具書必買必查之外,還有些編輯業(yè)務(wù)書籍,亦要時時翻閱,比如北大教授蘇培成的《怎樣使用標點符號》(增訂本)即為一本極其實用的案頭必備。
語言的原始叢林
“繩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圓合,條貫統(tǒng)序”,1000 多年前的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如此裁決一篇好文的誕生過程,一部佳作、一本經(jīng)典書籍的誕生,亦如此。整日奮斗在審稿一線、對書稿文字砍砍伐伐、修修剪剪的編輯對此當有所體悟。
審稿編輯的日常工作就是跟書稿打交道,幾乎是天天、月月、年年穿梭在語言的莽莽叢林中。一部書稿里,郁郁蔥蔥的文字原始叢林中,有荊棘,有絆腳石,更有大坑、中坑和無數(shù)的小坑。編輯要做的,就是從大到小,從外到內(nèi),從上到下,從主到次,從宏觀到微觀,從主題思想到每個標點,像梳頭一樣將某個特定叢林捋上三遍。
若問一個編輯在職業(yè)生涯中最擔憂的是什么,相信大多數(shù)編輯都會答出兩點:一個是書籍的效益,另一個就是成書中出現(xiàn)錯誤。后者更容易讓人遺憾連連。如果,打開一本書,映入眼簾的第一頁中就有錯誤,而且這錯誤還是無可爭議的硬傷,試想編輯此刻的心理陰影有多大?
語言即思想。每部書稿的語言都是作者思想的體現(xiàn),有人說只需要忠實呈現(xiàn)作者的原文原意即可,編輯不必在語言的原始叢林里排兵布陣、圍追堵截,這樣斤斤計較,費時費力還不討好,何必呢。是的,作者有呈現(xiàn)思想的創(chuàng)作自由,但編輯有堅持原則的職業(yè)責任。若沒有編輯處理政治、民族、宗教、基調(diào)、不良習俗等大坑,社會的輿論導向、民眾的凝聚力、青少年價值觀的塑造和教育等也許會偏離與迷失;若沒有編輯提煉書稿的結(jié)構(gòu)、淘汰過時錯誤的信息和觀點,呈現(xiàn)出來的書籍內(nèi)容雜亂無章且陳陳相因,怕也是令人不忍卒讀的;若沒有編輯無怨無悔、盡心竭力地核對知識點、修改病句和錯別字、規(guī)范標點符號的用法,或許以訛傳訛、張冠李戴、荒謬絕倫、誤人子弟的文字會充斥整個語言原始叢林的各種角落。黑云壓城城欲摧,如此,一切都自由了,然而,一切也都亂套了。
這,便是書籍中語言和思想生存的叢林法則。每一個有責任心、事業(yè)心和使命感的編輯,在審稿時,身兼兩職,既是思想解放的披荊斬棘的開拓者,也是讓語言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護航者。
43 歲時,一生追慕游俠之風的李白,寫下名篇《俠客行》,詩句曰“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身與名,不重要,完事后,藏起來。說的是千年前的俠客,又何嘗不是現(xiàn)在的編輯?辛苦改稿,默默奉獻,精心打磨出爐的書籍是合格出版物,甚好;編了一本優(yōu)秀的、經(jīng)典的、暢銷或長銷的作品,更好。
那邊廂,聚光燈下的作者光彩照人,光環(huán)屬于他,他心安理得。
這邊廂,隱蔽角落里的編輯,拍拍身上的塵土,落寞而孤傲地轉(zhuǎn)過身,俯身鉆進下一個語言的原始叢林。又一段篳路藍縷、砥礪前行的孤獨旅程,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