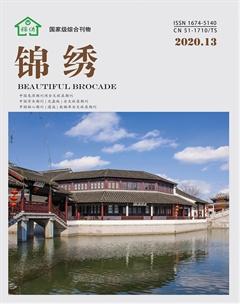漫話“禮”的樂舞表達
衛盼
摘 要:中國自古便得有“禮儀之邦”的美稱,“禮”的傳達方式有很多,除言傳身教外,在古代禮樂文化著重要的體現。用“禮”的內容賦予“樂”的形式,借藝術化的手段體現禮的要求,從而達到教化的目的,成為統治者的工具,這是古代的禮樂制度,從制禮作樂到禮崩樂壞都說明了“禮”與“樂”存在著一種內在的聯系。本文結合文獻史料與田野個案,以樂舞表現為對象,淺談古今對照中“禮”與“樂舞”發生有怎樣的碰撞。
關鍵詞:“禮”;樂舞表達;功能;影響
引言
“禮”,繁體字“禮”,最初是原始人類祭祀鬼神、先輩以求得賜福而舉行的儀式活動,并演化成禮儀約束人的行為準則、符合道德觀念和風俗習慣而形成的儀節。在古代“樂”、“舞”緊密聯系在一起,是為歌、樂、舞三位一體的藝術綜合體,本文這里的“樂舞”主要以舞蹈作為研究對象展開論述。
《荀子·樂論篇》載:“……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鼓群物皆別”。“禮”,區別等級貴賤之分,有著嚴格的制度規范;“樂”思想是“和”。一方面,“樂”之“和”是對“禮”之“分”的補充;另一方面,“和”要達到理性的狀態需要“禮”來約制,實現“樂”的“中和”。因此,“禮”與“樂”雖各自功能不同,但互為補充、內在聯系、相互制約。
一、“禮”的前世記憶
古代帝王運用禮樂制度來達到尊卑有序、遠近和合的統治目的。“制禮作樂”成為統治階級治國的一種政治手段,“雅樂”的建立并被歷代所承襲,“文舞”、“武舞”的設定,朝會大典、接見使臣、郊廟祭祀、宴饗娛樂等場景逐漸發展形成了專門的禮儀樂舞,宮廷樂舞機構的設置,甚至具體到舞蹈人數的限定,如天子八佾,諸侯、士大夫逐次減少等無不體現出樂舞中的等級觀念、禮法意識。西周從“制禮作樂”到“禮崩樂壞”,漢代“以舞相屬”,明代朱載堉創制的舞譜憑舞姿動態圖像、借“轉”等方式表禮法之象等各個朝代均有所體現。
除此之外,樂舞功能較具明顯的代表如“以舞相屬”,一種固定儀式化的宴饗雜舞,兼具禮儀性和娛樂性質的社交舞蹈,其規則由宴會中的主人先舞后邀請客人,客人要以舞為報,舞畢再相屬于另一人,以此循環接連,直至盡興方可停止,在這個過程中有嚴格的禮儀規矩,姿態儀容也都有講究,違反了規矩就是失禮。其目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如聯絡感情、活躍氣氛、抒發情感、增進友誼、實現某種目的等等。
二、“禮”的今生表達
新疆錫伯族,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由盛京(沈陽)遷至新疆伊犁屯墾戍邊,現分布于新疆察布查爾自治縣(簡稱察縣)、霍城縣伊車嘎善錫伯族鄉(簡稱伊車鄉)等地。重視禮節、尊敬長輩和長者是錫伯族古往今來優良的傳統文化,面對不同場合、不同人群等有著相應的行禮方式。“打千”禮是錫伯族日常生活常行的禮節,只限于本民族內使用,男子行禮時,左腳向前邁出半步,雙膝彎曲,右手在上雙手交疊放置在左膝上,身體往下坐曲;女子請安時,左右手分別放置在左右膝上,屈膝身體坐曲,這樣的禮節一直延續至今,同時在往后的生活中逐漸升華為一種行禮舞,察縣錫伯語稱“多若羅貝倫”,伊車鄉稱“阿吾勒”(孔爺爺解釋也特指雙手合十的動作)。
本人于2019年7月前往察縣、伊車鄉進行調研,并有幸請到幾位熱情的錫伯族阿姨為我們進行了現場表演,行禮舞表演形式以“平跺步”作為基本步伐貫穿始終,合著音樂節奏三步一行禮,彼此間做出行禮動作,其中除本民族的行禮動作外,還融入有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民族的行禮動作,動因是民族遷徙引起社會變遷,進而發生文化變遷,借用伊車鄉孔爺爺的話“我們錫伯族很擅長吸收其他民族優秀的文化”。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環境下自然受其影響,不同民族禮節的融入正是錫伯族與生活環境中諸民族文化互動的結果,行禮中有雙手合十的動作,即伊車鄉所稱的阿吾勒,可能是與佛教的影響有關,在這里行禮禮儀借以舞蹈的形式為人們所容易接受,同時也達到了宣揚教育、傳承文化、溝通交流等目的。表演當中舞者可自由發揮,又可靈活掌握,
另外在新疆哈密賽乃姆中有借助道具手帕折成花朵(維吾爾族語言稱“普塔”)的表演形式,與古代“以舞相屬”有異曲同工之效。首先入場的舞者手持此花束,在他(她)去邀請另一個舞伴時,要將花束遞交給被邀請者,以此進行,互動性強,氣氛熱烈融洽。
三、樂舞反映的禮俗觀念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從中可以感受到樂與政相通。在古代禮樂既有政治功能,又具有教化作用,從而使得社會出于等級化、制度化且平和的狀態中。如今“以舞相屬”的形式變換、錫伯族行禮貝倫、維吾爾族舞蹈表演前的行禮動作等,禮樂從最初嚴格的等級制度、秩序觀念到道德倫理、社會和諧、人際關系、情感交流,盡管時代不斷變遷,禮樂被賦予著不同的形式,但“禮樂”精神一直在在延續。
參考文獻
[1](先秦)戴圣.禮記·樂記[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