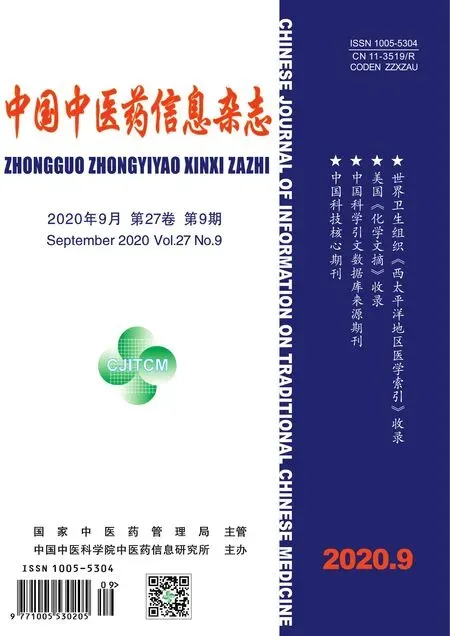基于文獻探討膜原學說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的臨床應用
王進忠,謝文源,覃小蘭,侯時昭,李玉明,鄭杰超,張曉春
基于文獻探討膜原學說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的臨床應用
王進忠,謝文源,覃小蘭,侯時昭,李玉明,鄭杰超,張曉春
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廣東省中醫院)急診科,廣東 廣州 510120
膜原學說認為,癘氣致病乃邪伏膜原,臨床以祛邪為主要治法,長期用于指導瘟疫治療。本文結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爆發以來有關文獻報道,探討膜原學說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的應用意義,為病毒傳染性疾病的治療提供參考。
膜原學說;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醫藥療法
明末瘟疫流行,吳又可結合臨床實踐,系統提出膜原學說,認為瘟疫乃癘氣所致,潛伏膜原,阻遏氣機,臨床當以疏通氣機、驅除邪毒為主要治法。該理論被后世醫家廣泛用于瘟疫治療,在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ARS)[1-2]救治中也體現了極高的臨床意義。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為2019年12月以來爆發的新型傳染病,目前有關中醫診療方案及病例報道已陸續發表。茲結合相關文獻,探討膜原學說在其中的應用,為COVID-19診治提供參考。
1 膜原學說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認識
1.1 病因
《素問?刺法論篇》有“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提示疫病具有廣泛的傳染性和癥狀相似性。因此,結合COVID-19臨床表現,可將其歸屬中醫學“疫病”“瘟疫”范疇。
關于瘟疫,吳又可提出乃癘氣所傷,“疫者感天地之癘氣”,“瘟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此次COVID-19相關報道對其病因論述較為統一和明確,即外受疫癘(戾)之邪。而有些專家進一步提出其為“濕毒”[3-5]。
但分析有關癘氣特征的古籍文獻可知,吳又可認為癘氣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之邪。吳鞠通《溫病條辨》將溫病分為9種,多具有明顯的季節特性(秋燥、冬溫)、病理屬性(風溫、溫毒、濕溫、暑溫、溫熱)和證候特征(溫瘧),唯獨對瘟疫以致病特點命名。由此可見,瘟疫有別于一般外感疾病,癘氣明顯不同于六淫邪氣,本身并無六淫屬性。
癘氣無病性,但其所致疾病有共同的臨床特點[6],如吳又可所言“一病自有一氣”,提示不同癘氣引起瘟疫的臨床表現不同,但同種癘氣所致疾病則有共同特征。臨床所見不同癘氣致病特點也有規律可循,且往往導致濕證。吳又可提出“蓋溫疫之來,邪自口鼻而入,感于膜原,伏而未發者,不知不覺”。邪氣內伏膜原,成為后續產生各種病機變化的主要決定因素,這與膜原位置和功用的特殊性有關。
膜原之名首見于《素問?舉痛論篇》“寒氣客于腸胃之間,膜原之下,血不得散”,但其具體位置歷來眾說紛紜。吳又可認為,膜原處表里之間,為半表半里,主要功能為聯系臟腑,與消化系及肺系臟器關系密切,可溝通上下、內外、表里之氣機。癘氣盤踞膜原,阻礙氣機,氣滯而濕阻,故其病多見濕證。實際上,不論何種瘟疫,癘氣伏于膜原,總以“濕”為主要病理特點。其病未發時如常人,與傳染病學之潛伏期相對應,但病發時的舌象多表現為明顯膩苔,濕證已然明顯存在,此時接診患者往往易誤認為感受“濕毒”。此情況在與新型冠狀病毒同屬的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SARS-CoVs)發病期間也可見到[7]。因此,“濕”乃COVID-19病理產物,非癘氣之病性。
1.2 病機與病位
關于COVID-19總體病機特點,學術界有不同認識,或為“毒、燥、濕、寒、虛、瘀”[8],或為“寒、濕、瘀、虛”[9],或為“濕、熱、瘀、毒、虛”[10],以及“濕、熱、毒、虛”[11]等;此外,還有學者分析已有的26個中醫藥防治COVID-19診療方案(1個國家方案、25個地方方案),得出“濕、毒、閉、虛”的病機特點[12]。膜原學說認為,邪伏膜原,影響氣機運行,導致濕濁內生。現有報道符合以“濕”為病理核心的特點,且有寒濕與濕熱之不同[4,13]。吳又可指出,病邪發于膜原,內外不相通,氣壅而有余,有余便為火,未免發熱,故病性終是陽證,臨床應以濕熱為主要病機變化。關于“寒”證病機的報道多具有地域特點,如“寒濕疫”主要結合了武漢地區COVID-19初起時的氣候特點與居民飲食習慣[8,14],而其他區域以“寒”證作為主要病機的報道并不多。
COVID-19病位在肺,其次在衛表、脾胃。臨床以肺系及消化系癥狀多見。膜原學說認為,正邪相爭,癘氣自膜原向表里兩端傳變。其傳至表者,可見惡寒、舌上白苔;傳入里者,以胃為主,則見舌上黃苔。“白苔潤澤者,邪在膜原也,邪微苔亦微,邪氣盛,苔如積粉”(《溫疫論》),白苔越厚,癘氣越重,病情往往進展越快。
關于COVID-19病期分型,一般參考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制訂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治療方案(試行第五版)》(國衛辦醫函〔2020〕103號),具體名稱略有差別,即初期(早期[10])、中期(進展期[15])、重癥期(危重期[16]或極期[10,17])和恢復期4個階段,受限于不同地域、季節、體質等因素,其中相聯2個階段的臨床癥狀部分存在重疊。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第六版及第七版診療方案未設定病程分期,而是基于病情嚴重程度,分為輕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4個病型,將辨證與辨病相結合,這為相關治療拓展了思路,也符合瘟疫的治療原則。
1.3 臨床治療
膜原學說將祛邪作為第一治療要義,是由瘟疫癘氣致病的獨有特點所決定。瘟疫之為病,發展迅速,病情易惡化,但同一種瘟疫具有相同的致病因素以及共有的臨床表現,其病情演變也有一定的規律可循。臨證當以辨病為主線,以驅除癘氣為核心,而非只專注于證的治療。吳又可強調“但治其證,不治其邪,同歸于誤一也”。祛邪并非殺毒,貴在給邪以出路,這在SARS治療中得到充分佐證[2,18]。祛邪則需知邪之所在,包括未發病時(潛伏期)及發病后(發病期)的各種傳變過程中。吳又可善于觀察舌苔變化,確定邪之所在,如“白苔潤澤者,邪在膜原也”,“邪在膜原,舌上白苔;邪在胃家,舌上黃苔。苔老變為沉香色也。白苔未可下,黃苔宜下”。后世醫家結合癘氣正邪相爭出現的各系統傳變,發展出衛氣營血及三焦辨證,雖方法有別,但祛邪目的相同,總以給邪以出路為要務。
疫病總體治療原則為宣暢氣機、辟穢化濁、疏利透達,同時根據不同階段扶正祛邪[12,19]。
早期邪伏膜原,氣機不暢,肺氣不宣,表現為濕濁內蘊、邪氣閉肺,治以辟穢化濁、宣肺透邪,方選達原飲、藿樸夏苓湯、麻杏石甘湯、升降散、麻杏苡甘湯、小柴胡湯、銀翹散、清瘟敗毒飲等。其中達原飲為吳又可結合膜原理論所創,“溫疫初起……其時邪在夾脊之前,腸胃之后,雖有頭疼身痛,此邪熱浮越于經,不可認為傷寒表證,用麻黃、桂枝之類強發其汗。此邪不在經,汗之徒傷表氣,熱亦不減。又不可下,此邪不在里,下之徒傷胃氣,其渴愈甚。宜達原飲。達原飲:檳榔二錢,厚樸一錢,草果五分,知母一餞,芍藥一錢,黃芩一錢,甘草五分”(《溫疫論》),方中“檳榔除嶺南瘴氣,厚樸破戾氣,草果除伏邪”,三味協力,直達膜原,使邪氣潰敗,速離膜原;且檳榔、厚樸可通腑降氣,助壅塞之肺熱隨腑氣得降,取釜底抽薪之意,一方多效。達原飲為后世治療瘟疫常用方,曾為治療SARS屢建奇功[1-2]。此外,針對大便黏滯不爽,三焦表里火熱,其證治不可名狀者,可合用楊栗山所創之升降散。升降散由僵蠶、蟬蛻、姜黃、大黃四味藥組成。方中蟬蛻、僵蠶升陽中之清陽,姜黃、大黃降陰中之濁陰,一升一降,內外通和。達原飲+升降散+三仁湯、藿樸夏苓湯系列復方疏利透達、宣肺化濁,用于治療SARS及COVID-19均有較好療效。
若COVID-19初期未得到及時或有效治療,則邪入肺、胃或大腸,正邪相爭,熱毒深重,易傷津液,此時進入中期或進展期。患者出現發熱、氣喘、胸悶、痰多黃稠,亦或出現腑實癥狀,治宜清熱宣肺、通腑瀉熱,方選麻杏石甘湯、達原飲、宣白承氣湯、黃連解毒湯、解毒活血湯等。下法是諸多熱病的祛邪途徑,判斷邪熱入胃與否的關鍵是苔色。吳又可基于“邪在胃家,舌上黃苔……黃苔宜下”,靈活應用三承氣湯通腑祛邪,屢見奇效,值得進一步研究。中期為治療COVID-19關鍵階段,邪去則體安,否則病情惡化極易導致臟器功能衰竭,其中尤以肺水腫、呼吸衰竭最為常見,也是導致患者死亡的最主要原因,吳鞠通所謂“肺之化源欲絕,乃溫病第一死法”。
中期治療不當,病情難以扭轉,則進入重癥期或極期,邪熱內閉、陽脫陰竭,患者表現為呼吸困難、動輒氣促,伴神昏,汗出肢冷,脈微欲絕或浮大無根。此時當以扶正為主,可借助參附湯、生脈散,酌加山萸肉、三七等補腎活血固脫。另外,安宮牛黃丸、參附注射液、生脈注射液、參麥注射液、血必凈注射液等中成藥可酌情應用。
患者病情若有逆轉,正氣恢復,邪退正傷,則進入恢復期。此時患者疲憊,體質虛弱,多見氣陰兩傷、肺脾氣虛證。治當以益氣養陰、調補肺脾為主,方選生脈散、黃芪六君子湯、沙參麥冬湯、參苓白術散等。若余邪未盡,可選竹葉石膏湯以防復發。在瘟疫治療過程中,吳又可尤其強調對胃陰的維護,所謂“留得一分陰液,便有一分生機”,另外,對于恢復期的患者飲食,吳又可提出“蓋客邪新去,胃口方開,幾微之氣,所以多與、早與、遲與皆不可也。宜先與粥飲,次糊飲,次糜粥,次軟飯,尤當循序漸進,毋先后其時”,值得重視。
2 關于膜原理論的幾個問題
2.1 邪伏膜原與伏毒學說不同,前者具有較為明確的瘟疫治療范圍
伏毒是外感溫病的主要致病因素,具有季節性、潛伏性。如晉代王叔和認為“寒邪藏于肌膚,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暑病”,清代雷少逸提出“溫毒者,由于冬令過暖,人感疫癘之氣,至春夏之交,更感溫熱,伏毒自內而出,表里皆熱”。伏毒致病具有隱伏、纏綿、暗耗、暴戾、雜合多變等特點。
就潛伏特點而言,伏毒與邪伏膜原有一定相似性。但從病因看,伏毒種類頗多,無論外感或內生,毒邪久藏體內均可形成伏毒。而膜原理論更側重于癘氣致病,病邪潛伏時間較短,其致病具有廣泛傳染性,病情進展迅速,一般不會形成反復發病態勢,較之伏毒更為嚴重。因此,膜原理論具有明確的應用范圍和對應治療方案,適用于瘟疫的治療,不可與普通溫病的診治相混淆。
2.2 膜原理論應用的局限性
因膜原解剖定位的模糊性,有學者將膜原學說作為吳又可之假設,用于區別傷寒的隨證施治,明確病位中心,以達原飲之用鋪路[1]。以膜原學說指導治療的疾病主要用于瘟疫。后世醫家在各科疾病的治療中鮮有將其廣泛應用的記載,以致在某個時期因傳染病的控制,膜原理論逐漸離開醫者視野。因此建議在COVID-19治療中通過借助各方資料,對該理論進行深入研究與完善;關于膜原位置,在現代醫學環境下,是否可借助COVID-19死亡病例解剖提供參考,值得探索。
2.3 現代醫學技術對膜原理論的影響
現代醫學對SARS、COVID-19等傳染病,主要采用抗病毒、減輕機體應激反應和支持治療,使機體已不單純隨邪毒病位的轉移而產生相應的變證。對此,需要明晰辨病治療與辨證治療的關系。在瘟疫治療中,以辨病祛邪為主,同時結合各個階段的辨證治療,緩解臨床癥狀。辨病與辨證相統一,二者相輔相成,才能達到邪去而體安的治療目的。
3 結語
上述對COVID-19的中醫診療相關文獻分析,顯示膜原理論在COVID-19治療中有較好的臨床意義。當然,膜原理論中癘氣致病、邪伏膜原、祛邪為要、病證結合及顧護胃陰為主的學術思想,還有待借助現代醫學技術探討其潛在的科學內涵,為病毒性傳染病的防治提供參考。
[1] 張霆.“戾氣為患,邪伏膜原”——試論傳染型非典性肺炎之病因病機及治療[J].天津中醫學院學報,2003,22(3):58-60.
[2] 蘇云放.非典的伏氣瘟疫-膜原說探討[J].浙江中醫學院學報,2003, 27(4):6-8.
[3] 楊道文,李得民,晁恩祥,等.關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中醫病因病機思考[J/OL].中醫雜志,2020[2020-02-17].http://kns.cnki.net/ kcms/detail/11.2166.R.20200217.0906.002.html.
[4] 王玉光,齊文升,馬家駒,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醫臨床特征與辨證治療初探[J].中醫雜志,2020,61(4):281-285.
[5] 馬家駒,陳明,王玉光.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綜合征中醫證治述要[J/OL].北京中醫藥,2020[2020-02-07].http://kns.cnki.net/ kcms/ detail/11.5635.R.20200207.1616.002.html.
[6] 董國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醫診治思路之我見[J/OL].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20[2002-02-03].http://kns.cnki.net/kcms/detail/ 11.3554.R.20200223.1425.002.html.
[7] 李衍達,張文晉,趙振宇,等.中醫診治SARS的經驗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啟示[J/OL].天津中醫藥,2020[2020-02-28].http://kns.cnki. net/kcms/detail/12.1349.R.20200227.0909.006.html.
[8] 范逸品,王燕平,張華敏,等.試析從寒疫論治新型冠狀病毒肺炎[J].中醫雜志,2020,61(5):369-374.
[9] 南征,王檀,仕麗,等.吉林省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醫診治思路與方法[J].吉林中醫藥,2020,40(2):141-144.
[10] 唐靜,姚思夢,褚慶民,等.《廣東省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中醫藥治療試行方案》解讀及專家案例分析[J/OL].廣州中醫藥大學學報, 2020[2020-02-24].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425.R.20200224.1540.002.html.
[11] 鄭文科,張俊華,楊豐文,等.中醫藥防治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各地診療方案綜合分析[J].中醫雜志,2020,61(4):277-280.
[12] 龐穩泰,金鑫瑤,龐博,等.中醫藥防治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方證規律分析[J/OL].中國中藥雜志,2020[2020-02-19].https://doi.org/10. 19540/j.cnki.cjcmm.20200218.502.
[13] 苗青,叢曉東,王冰,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的中醫認識與思考[J].中醫雜志,2020,61(4):286-288.
[14] 王剛,金勁松.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醫認識初探[J/OL].天津中醫藥, 2020[2020-02-18]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2.1349.R.20200214.1710.004.html.
[15] 李建生,李素云,謝洋.河南省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醫辨證治療思路與方法[J].中醫學報,2020,35(3):453-457.
[16] 薛艷,張煒,徐貴華,等.濕瘟為病,疏利透達——上海地區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醫臨床證治探析[J].上海中醫藥雜志,2020,54(3):16-20.
[17] 陳瑞,羅亞萍,徐勛華,等.基于武漢地區52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中醫證治初探及典型病案分析[J/OL].中醫雜志,2020[2020-02-2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2166.R.20200220.1443.002.html.
[18] 張巍嵐,王相東,王郁金,等.從國醫大師鄧鐵濤治非典經驗探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醫診療思路[J].中醫學報,2020,35(3):483-486.
[19] 王傳池,吳珊,江麗杰,等.全國各地區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醫藥診治方案綜合分析[J/OL].世界科學技術,2020[2020-02-26].http://kns. cnki.net/kcms/detail/11.5699.R.20200225.1702.006.html.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Moyuan Theory in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Based on Literature Reports
WANG Jinzhong, XIE Wenyuan, QIN Xiaolan, HOU Shizhao, LI Yuming,ZHENG Jiechao, ZHANG Xiaochun
Moyuan Theory believes that Li Qi (epidemic miasma) causes diseases, and it is lurking in Moyuan (interpleuro-diaphragmatic space). The main treatment method in clinic is to expel Li Qi. This theory has long been used to guide the treatment of plague. This article combined the literature reports published since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of Moyuan Theory in this disease,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treatment of viral infectious diseases.
Moyuan Theory;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TCM therapy

R259.631
A
1005-5304(2020)09-0021-04
10.3969/j.issn.1005-5304.202002354
廣東省中醫院譚爕堯、張浣天名中醫學術經驗傳承工作室項目(E48807);廣東省中醫院嶺南岑氏雜病流派傳承工作室項目(E43602)
覃小蘭,E-mail:lanxqin@126.com
(2020-02-21)
(2020-03-19;編輯:梅智勝)
——中醫藥科研創新成果豐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