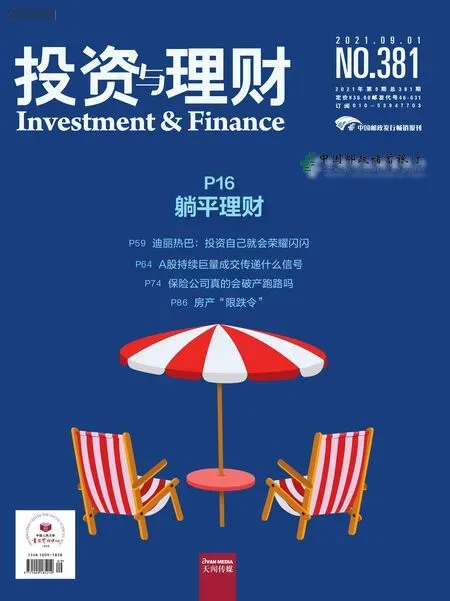試析中國畫虛境營造之留白

中國畫用生動變化的形跡,給人們展示出充滿奇幻之美的藝術空間。在眾多的國畫形式語言中,“留白”以虛實相間的手法,追求意象造型、強調主題、增強畫面縱深感,展現中國繪畫特有的意境。“留白”藝術看似一種構圖的技巧,實則是藝術家流露的感情與畫作有機的結合,給人距離很寬很廣的想象。
自東晉顧愷之提出“傳神論”后,就奠定了中國畫的最高標準。從南齊謝赫《古畫品錄》到晚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等都對“留白”賦于“傳神”的獨特魅力,進行生動的闡釋。從先秦時期的《錯彩鏤金》到六朝的《出水芙蓉》,從東晉顧愷之的《洛神賦圖》到明代徐渭的《墨葡萄圖》……“留白”更多是為了神似,寄寓了“殊殊各異”的氛圍。
“留白”給人提供無限的想象空間,表現畫面前后層次關系,營造了空曠深遠的情境。表現方式有兩種,其一主要利用觀者的心理因素引起無限的共鳴,并對畫家所傳達的意境感同身受。在這樣的意境引領下,觀者看到畫中空白之處,似乎變得有聲有色,由虛轉實。如元朝高克恭《云橫秀嶺圖》就是個中翹楚。畫中彌漫的云霧是“留白”,因為云霧本身就是白色,此處“留白”以虛轉實地體現變幻莫測之勢。其二是為了畫面形象與整個構圖達到交融和諧的境界。如元代吳鎮的《漁父圖》,利用大片“留白”水面,烘托出漁父駕一輕輕扁舟,逍遙于云水之間的“漁隱”意境,也讓畫面有虛實呼應的視覺體驗。

“留白”的藝術特征可以歸結為留白與虛實、留白與意境、留白與計白當黑……許多傳世精品可以作為例證。
南宋馬遠和夏圭的山水意趣更多追求“虛無的意境”。畫面留了大片空白,主體物象置于一邊,后人形容其“留白”藝術,就形象地稱作“馬一角,夏半邊”。二人傅色以濃墨為主,在畫面經營上加以淡淡的色彩或者淡墨,同時將暈染的層次疊加,意境深遠,以展現筆力的遒勁。表現山體則多用“斧劈皴”,以干脆利落的刷筆見長。線條剛勁、墨色淋漓的奇山怪石與流動舒緩、疏朗開闊的平灘曲水形成的“邊景山水”(或稱“殘山剩水”)就有“留白”的技巧,給觀者極大的想象空間。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的花鳥具有強烈感情色彩。造型非常簡潔,極少墨色表現“計白當黑”的開合之勢,更是“留白”的妙處。如其《河石水禽圖》,數叢荷葉、幾朵荷花用筆奔放,濃淡分明;池邊雙禽一只延頸一只縮脖,似乎翻著白眼。畫面其他位置均留有大片空白,卻讓觀者能感受畫家憤世嫉俗的情感。

近現代以來,受西方繪畫的沖擊,尤其是西方油畫全景式不留空白的整體觀念,讓傳統國畫“留白”藝術受到冷落。特別是許多人追逐時風,更愿意把畫面填滿,就像大呼隆“攤大餅”一樣,缺少蘊藉敦厚的感染力。在當下,唯有擴充知識,豐富底蘊,提升涵養,才能更多的認識和表現“留白”帶來的意境之美。
“留白”根本作用是讓畫面更有內涵,筆墨少而精當,意境隨之豐滿。當代中國畫向全篇幅構圖形式轉變,這是由于畫家們對傳統優秀文化的缺失造成的,沒有更多地體會古人那種空靈之美,而是把精力放在如何將紙面上“形而下”的東西鋪陳開來,因而也就沒有紙面背后的那種“形而上”的哲思意味。筆者認為,對于東西方繪畫藝術要有開放包容的態度,但更要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取舍。西方繪畫藝術只有和中國傳統藝術形式相結合,才能在世界美術之林占有一席之地,才能綻放出獨特的光芒。如果舍棄傳統,迷失自我,一味拾人牙慧,就只能是遮蔽在別人巨大的陰影之下。
對“留白”傳統技法的發揚光大是當代國畫創作者的重要任務。我們應該以中華傳統文化為根基,以國畫寫意精神為內核,以包括“留白”在內的虛境營造手法,探求“天地精神”和“人生境界”,藝術地表達中國特色、中國韻味和中國氣派。


朱卯
別名芃一,女,漢族,江蘇淮安人。
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女畫家協會會員。
作品入展全國第十三屆美展、全國第六屆青年美展等全國一類美術展覽,
在十余次中國美協舉辦的全國性美展中獲獎入展。
入選市委、市政府“名師帶徒”工程,拜師中國美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張谷旻教授,
2019-2020在中國美術學院訪學。
主要成就:版畫入展第十三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中國畫全國第六屆青年美術作品展覽。代表作品:中國畫《九曲天歌》、《秋意苗鄉》、《瑤寨物語》,版畫《新溪山·映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