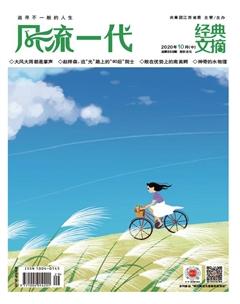草醫
劉群華
草醫在杏林中的地位很低,但常有一味單方氣死良醫的軼事。他們親近土地,對自己生活的地方長著什么藥了如指掌,比如屋頂杉皮上長的石葦,溪流邊的旱蓮草,路邊的車前草,田埂上的半邊蓮,高山上的七葉一枝花,等等;跟人說起來像在說菜園子里的蘿卜白菜豆角茄子,什么時候出苗,什么時候開花,什么時候結果,什么時候采摘最佳,滔滔不絕,如數家珍。甚至夜里碰到急診的病人,提燈出門,在房前屋后轉一圈,就把所需的鮮藥摸回來了。
這種摸藥的神奇,與草醫平常出門時的細心留意分不開,是草醫所說的“謀藥”,即平常觀察到某地有某種藥,一到用時馬上就能找到。
在我們村里,原來也有個草醫,六七十歲,是一個孤寡老頭子。他嗜酒,一日三餐總斟杯小酒,添一碗涼颼颼的菜兀自地蹲在板凳上喝。他似乎善治慢性病,嚼一大口黏稠的綠汁碎葉,敷在病人的小腹上,馬上暖暖的,如絲絲炭火熱,緩緩地溫熨著直達病所。
他是不講究報酬的,求診者知其好酒,就都帶壺酒去。他躺在竹椅上,求診的人喊他一句,他的眼睛倏地睜開了,瞟著桌子上的酒,不急也不慌,說:“拿么子酒哩!草藥又不值錢,來就是了。”然后又說:“既然拿來了,就喝兩口。”于是起身握盞,提起就喝。偶爾不小心倒在桌面上,就手慌腳亂了,忙俯身低頭貼面吸著喝,邊喝邊叫:“好酒!好酒!太可惜了啊!”
他的那幾口草藥治好了不少人,也賺了不少好酒。在他陳舊破爛的三只腳的柜子上,橫七豎八放了若干個酒瓶子。我有次去他家,他在旁防賊一樣盯著我,說:“別亂翻,這是我治好的醫案。”我順手拿出一個瓶子,考他,他想都沒想,隨口道:“某某,女,1998年某月某日入診,發病三年,夜口干舌燥,時有尿赤……”
我驚得目瞪口呆,暗暗感嘆一番,虛心地說:“要人背背簍(收徒弟)嗎?我閑散得身子沒勁了,想去山里轉一轉。”他看著我哈哈大笑。我狡黠地瞄了瞄他。許久,他大手終于一揮,像放下一百斤重的擔子,說:“帶到土里也可惜,就教給你吧。”
我們是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早上進山的。我跟在他的身后,他邊走邊說:“當陽坡地祛風多,利水草藥去水溝。”他還說了很多,簡單的順口溜一串串,把草藥的習性精準地概括、描繪了出來,也讓我記住了一些草藥的藥性特征。
那一次我們攀爬了七八座高峰,蹚過幾條清澈的小溪。走到一座山的坳口,有一棵古老遒勁的大樹下,他指著樹上寄生的一種盤曲如花的藤,說:“這藥止血。”我爬上去摘下一蔸,問:“它沒有根啊?”他笑了笑說:“這是一種鳥吃了籽,屙在樹上生的。寄生于此樹的粗干,沐日月星辰,飲曉風夜露,有點仙風道骨的意思了。”
哦,原來藥也修行啊,難怪如此慈眉善目,普度眾生。我聽著,近乎在聽一個流傳了很久的神話,勾起了我無窮的興趣和求知欲。
以后的日子,我一有空就去找他,漸漸地認識了不少草藥。有一次,他躺在那張舊椅子上說:“草醫不值錢,用鮮草鮮葉治病,在鄉村容易找,也不好收錢。草醫忙,忙的是人情世故,是鄰里之間的攜扶。”我點了點頭。然后他難過地長嘆:“識天地之藥,治人間之病,找延壽之方。可惜,草醫的經驗沒人學,快瀕臨失傳了。”他指著土坪邊培育的一株草藥,說:“牛苦膽,治腫瘤,散結活瘀,清火敗毒,現在山上極其稀少了,很難找到。”
他擔心草醫消失的時候,一些珍貴的草藥也隨之消失。這種因果或許不會存在,也或許真實存在,他的忐忑和恐慌,猶如那株牛苦膽一樣苦惱。
一種藥儼然是一個人,通了靈性的。故鄉的草醫,是一味平凡的草藥,在田野山岡搗鼓著七經八脈的仁愛,也感觸了五色五味的生命。
(亞白摘自2016年4月11日《人民日報》,西米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