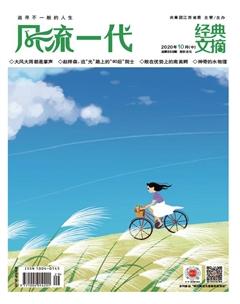腦海中的想象如何影響我們“看”世界
宇辰
當你專注于閱讀一本小說時,在你大腦的想象中都看到了些什么?對我們許多人來說,不管小說本身寫得有多么生動,在腦海中只不過形成一種模糊的、低對比度的場景。但對有些人來說,他們大腦中生成的圖像,卻可能如身臨其境一般逼真。
對于這種超想象能力的研究,揭示出了有關人類意識的一些奧秘,包括我們的想象力如何塑造我們所感知的世界,以及如何塑造了人類的意識本身。
超幻癥:想象力之極致
有些人擁有極其豐富的想象力,他們的心理意象就像電影一樣栩栩如生,這種超想象能力被稱為“超幻癥”。比如,當克萊爾·杜德尼看到一些小說中的場景描述,尤其是對血腥事物的描述時,她的大腦中所想象的場景如同身臨其境一般逼真——她曾在火車上讀到一篇文章,其中描述了一個人的腳被釘子卡住的情節,她竟然被腦海中所浮現的情景直接嚇暈了。
我們迄今還不清楚,人群中有多少人擁有這種超級豐富的想象力,但杜德尼正是其中之一。這種被稱為“超幻癥”的能力究竟有多非同尋常,科學家直到最近幾年才逐漸有所認識。
畢竟,要表達出自己腦海中看到的東西已經非常不容易,要了解其他人的心理意象就更難了。但我們現在知道,心理意象在個體之間的差異是很大的。對于有些人來說,甚至連想象自己臥室的樣子也做不到,而有些人卻能通過閱讀,在腦海中喚起電影般清晰的畫面。
這種極致想象力是一種十分有趣的現象。這個研究領域可能很有發展前景,研究此類大腦活動,會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心理意象對于人類情感和心理健康方面的作用,從而為各種心理障礙尋找更多治療方法,甚至有可能揭示“人類如何體驗世界”的奧秘。
“我有時候覺得,人類對外層空間的了解都比對自身要多。”瑞典烏普薩拉大學臨床神經學家艾米麗·霍姆斯說,“在心理意象這一前沿研究領域中進行探索的時機已然成熟”。
激發并構建實際上并不存在的圖景,是大腦的一種令人驚嘆的能力。如果說,我們對周圍世界的感知意識是科學研究中最令人驚訝的現象之一,那么我們在沒有任何外部刺激的情況下想象世界的能力更令人嘆為觀止。我們擁有的這種想象能力可能正是人類能夠成為地球主宰的原因之一。想象力是我們內在心理體驗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為我們提供了回憶過去、模擬未來的一種絕妙方式。
啟動效應:你有想象障礙嗎?
長久以來,由于缺乏客觀觀察工具等因素,科學家只對視覺想象有所研究。直到上世紀60年代,隨著腦成像技術的出現,研究人員才具備了對超想象力進行研究的條件。自那以后,各種研究表明,喚起心理影像與視覺感知的模糊印象在神經心理學上的意義是完全不同的,心理影像是可以通過檢測評估加以研究的。
最早進行這方面嘗試的是澳大利亞悉尼新南威爾士大學的喬爾·皮爾森。2008年,皮爾森和他的同事開發出了一種心理影像強度測試的方法。
這種技術利用了一種叫作“雙眼拮抗”的現象。盡管人們的左眼和右眼同時捕捉到的圖像并不相同,但人們實際看到的卻是一個圖像。用一個簡單的技巧,就能影響他們只看到其中之一:如果你在展示房子和汽車這兩幅圖片之前,先在受試者眼前閃過一幅房子的圖片,那么受試者眼中更有可能看到的是房子。
為什么會產生這種效應?皮爾森認為,這是因為人們會在腦海中根據最先閃現的圖像創建出一幅大腦圖像,因此在同時面對兩幅圖像時,大腦會優先感知已創建的圖像,“由此可見,想象確實改變著我們看世界的方式”。
皮爾森認為,一個人的心理意象越生動,受這種“啟動效應”的影響就越明顯,這就為他提供了一種客觀方法,來證實人們所報告的心理意象的生動程度。
2011年,他發現,那些想象障礙者(自稱沒有任何心理意象的人),幾乎不存在“啟動效應”。而那些訴稱自己經歷過極其生動的心理畫面的人,受這種“啟動效應”的影響則十分顯著。
那么,為何面對同樣的東西,我們腦海中會 “看到”不同的場景?2010年,英國埃克塞特大學神經學家亞當·澤曼公布了一個病例,這名男性患者稱,自己在心臟手術后失去了心理意象能力。此后,澤曼收到了幾千封來信,大多數人訴稱自己一直有想象障礙,更有小部分人訴稱自己患有嚴重的想象障礙癥。
皮爾森從來信者中邀請了部分志愿者參加神經影像的研究。澤曼和皮爾森的研究開始漸漸揭開人們心理意象能力差異背后的一些線索。
2016年,兩人的研究團隊獲得了最早的發現。皮爾森和他的同事對36名志愿者進行大腦掃描后發現,那些心理影像能力高于平均水平的人,他們的大腦視覺皮層(負責處理來自眼睛信息的大腦區域)比一般人小,該區域的神經活動也較弱。而那些心理影像能力較強的志愿者的大腦皮層活動也較強。大腦皮層好比是大腦的指揮中心,控制著其他大腦區域的活動。“就決定視覺形象強度的因素而言,似乎部分與神經結構有關,部分與神經活動的強弱有關。”皮爾森說。
澤曼的研究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他們讓志愿者看一些名人照片或有名建筑物的圖像,然后讓他們在大腦里想象之前看到的東西,同時觀察他們的大腦活動。通過“視覺形象生動度問卷”(VVIQ)測試,他們發現,那些對自己的心理意象評分較高的人,在回憶這些意象時,比那些在測試中得分較低的人激活的大腦區域更小,反之亦然。
“這與其他一些研究成果不謀而合,當你在做比較擅長的事情時,通常用到的腦力會少一些,這是大腦一種更為經濟的策略。”澤曼說。
雙刃劍:感知心中的“我”
需要說明的是,以上研究對象多為中等程度想象力者,而對于具有超強心理意象的人,至今所知甚少。不過,澤曼從他的研究中發現了一些有趣的聯系。例如,有著生動想象能力的人,通常自訴也有較強的自傳體記憶能力,同時記憶人臉沒有困難,這似乎與一種名為“聯覺”的現象有關。聯覺是神經系統的一種特殊能力,即不同的感官感覺發生重疊,比如有些人可以“聽見”顏色或“看見”聲音。
與大多數人相比,有著生動心理意象的人會做更多的白日夢。據推測,這可能是因為他們的大腦里有著更多生動的影像素材。同時,這些人也更容易被心理意象激發出各種情緒,如后悔、渴望和懷念等。
擁有超強意象能力的杜德尼是自愿加入超幻癥研究的人之一。這位來自倫敦的畫家在2007年的一次展覽會上認識了澤曼。她根據夢中見到的景象所創作的繪畫作品,以及她描述自己視覺想象力的能力,引起了澤曼很大的興趣。于是,澤曼邀請杜德尼參加VVIQ測試,并對她進行大腦掃描。
當聽到自己有超幻癥時,杜德尼并不感到特別驚訝,但當她了解到并不是每一個人都擁有像她這樣的視覺想象力時,她覺得十分驚訝,因為之前她一直以為大多數人都和她一樣。
“我小時候會通過在腦海中想象來學習閱讀,當老師阻止我閉上眼睛想象字母和單詞時,我有些不知所措。”杜德尼說,如今她才發現,這種超常的想象能力對她的藝術生涯非常重要,她把自己這種非凡的想象力看作是上天的一種恩賜,而不再是一種負擔。
然而,并非所有擁有生動想象力的人都會將這種能力看作是一種優勢。在過去十年里,一些研究人員發現,心理影像對我們的情緒和心理健康會產生很大影響。瑞典烏普薩拉大學臨床神經學家艾米麗·霍姆斯及其同事的研究顯示,當要求健康志愿者想象負面影像時,他們報告稱,與通過詞語描述同樣的場景相比,想象會令他們產生更強烈的焦慮感。
這可能與人們的直覺有關。如果想象某個圖像是看到真實事物的一種弱化形式,那么它必然會產生連鎖反應。例如,當你想象自己最喜愛的食物時,你會不由自主地流口水;當某個害怕社交場合的人想象自己身處派對之上時,他會感到焦慮。
事實上,英國倫敦國王學院的科萊特·赫希已經通過研究證明,負面的心理意象對引發焦慮、恐懼等負面情緒起著一定作用。赫希和她的同事讓有社交焦慮癥的志愿者一邊與陌生人聊天,一邊在腦海里想象負面畫面。此時,志愿者報告稱“感到更加焦慮”,并認為自己的表現不太好。
霍姆斯說:“這一研究表明,很多時候,重要的并不是你在別人眼中的真實形象是什么,而是你在自己的腦海中如何看待自己。”
(新芳摘自2020年4月4日《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