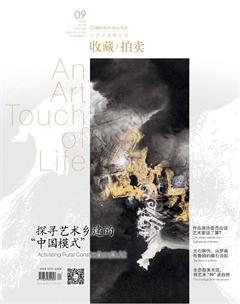彭勃,揮毫間點釉成彩
瓜子 雨田



頭一回見彭勃的作品,就被瓷器上充滿新鮮感的畫面吸引:靈動的線條,絲絲入扣的描繪,還有露珠般的釉滴點綴,極具裝飾感的畫面讓人驚艷,同時也欣慰于遇上一種“新瓷語”。他的“新”已無法沿用固有的思維,歸納到傳統的工藝或門類中去。只能姑且稱之為叫創新混合型彩繪,或許更為合適。
瓷上彩繪,前人已創造過太多經典。作為一名陶瓷藝術家,80后的彭勃毅然選擇做一些更特別的嘗試,不斷賦予彩繪新的可能。他善于進行工藝混搭,喜歡“點釉成彩”。雖然平時彩繪的技法與釉料都與前人無異,但經過他的演繹,總能讓人耳目一新,別具新意。
滲入到日常的熱愛,已無需“堅持”
彭勃把自己的工作室安置在景德鎮鄉郊的一棟民宅里,周圍都是空曠的綠野,更遠處便是綿延的群山。這樣能讓他遠離喧囂,靜下心來創作。
平日的生活也過得很樸素,工作室里除了實用的桌椅、工具,擺放最多的就是一件件素胚陶瓷,他喜歡在陶瓷上彩繪,熱衷于一點一點地把空白轉化為色彩斑斕的畫面,他享受裝飾帶來的快感。
即使從事多年陶瓷彩繪,擁有了扎實的功底,自我風格也日漸成熟,但彭勃對創新的熱情始終不減。他既能耐得住寂寞,也能在長年累月的累積中尋求突破。
可以說彭勃的創新更多時候是在日復一日、一個接一個的陶瓷彩繪中進發出來的。他有著驚人的耐力,即使描繪相同的畫面,面對成百上千件空白的陶瓷素坯,他也能氣定神閑地把一絲不茍貫徹到每件器物、每根線條上。也許有些偉大,總是在歷經十年磨一劍的修煉后方能成就。
不同于一般匠人的彩繪,彭勃并不認為在瓷面上反復描繪同一畫面是枯燥乏味的,相反,他樂在其中,每一回他都嘗試在構圖、局部的處理上作出微小的變化,但不經過仔細對比也無從辨認,只有他自己才能知曉個中隱藏的小心思。
尋常人會欽佩這種默默“堅持”,但對彭勃而言,每天執起畫筆,在陶瓷上不厭其煩地勾勒、平涂、點釉,從清晨描到日落,這早已是滲入日常的慣性動作,這種動作源于他對陶瓷彩繪執著的熱愛,已無需以“堅持”二字形容。
令人嘆為觀止的是,彭勃對待每一根線條都能處理得恰到好處,畫筆隨著平和的心境游走瓷上,畫出流暢的弧度,如同悅動的旋律,整齊、均勻但絕不呆板。也不會讓人感到“密集恐懼癥”,相反,這是一種“強迫癥治愈系”的視覺呈現,總能引起“極度舒適”。
把美好的暢想注入瓷中
彭勃的彩繪帶著鮮活的靈性。他喜歡畫鶴、畫魚、畫龍,這些優雅而祥瑞的動物,一直植根于中國的文化血脈,但他的演繹卻與傳統的大相徑庭。筆下的動物都長著水靈靈的大眼睛,活潑中帶著幾分憨厚,極具個性;他還別出心裁地選擇顏色釉的釉料在魚鱗、龍身、翎羽上直接進行點綴,燒成后便凝結其上,如一顆顆光潔的露珠,增添畫面的立體感;有時還會涂上一抹銀彩,進一步豐富了色彩層次,華美異常。
如果細細觀察可以發現,鶴、魚、龍的身子總被彭勃巧妙地“藏”了起來,讓人無法完整地一窺全貌,這樣細部的裝飾便可以最大程度地吸人眼球。每當轉動把玩時,器中的鶴、魚、龍也隨之游動起來,如在天上、水中遨游,給予觀者更廣闊的想象空間。
彭勃的內心也一定是天真爛漫的,他把這份美好傾注在筆下的每一處細節中。一件真正好物能激發人與人之間心理共鳴,引人遐想。使用者會想象畫者如何傾注心血在器物上,如伺從無到有地創造畫面;而創作者在每一次落筆時也會聯想器物日后擺設的場景,使用者如伺在掌上把玩、觀賞……也許,這種美好的暢想,讓彭勃耐住性子,精心打磨,讓筆下的每一處細節經得起觀者的推敲。
或者說真正讓人欽佩的是,彭勃把常人眼里的枯燥轉化為五彩斑斕的詩,不管走多遠,他的內心依舊是此間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