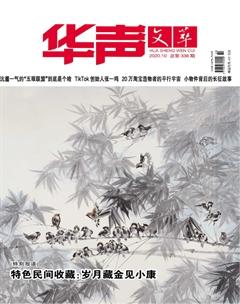91歲老人和他的“票證檔案館”
黃鶯
曾經,生活里,不是有錢就可以買到物品的。好吃的點心、實用的自行車,甚至燈泡、線、肉類、糧食這些生活必需品,都需要票據。
從1955年第一張糧票發行開始,到1993年糧票正式謝幕,中國曾經歷了近40年的“票證時代”。“憑票供應的日子好像過去很久很久了,其實也就不到30年的時間。”在杭州西溪街道下馬塍社區,年逾90的吳均林老人把家里剩余的和從市場購買的一些票證分為“票證種類”“糧票上的風景”“糧票歷史”“改革開放初期城鄉的糧證”“取消糧票后過渡期使用定量供應辦法”等八個類別,組成了一個“票據檔案館”,記錄了那一段歷史。
1928年出生的吳均林,當過兵,也在郵電系統工作過。上世紀末,離休后的吳均林閑了下來,對收藏歷史物件有了興趣,他把家里的老物件都整理起來,還寫了自傳。在他家里,日記、家信、工資單等等都已經裝訂整理好,一個家庭的歷史通過老物件得以定格。票證是他的收藏品之一,他最初的想法,就是希望通過這些票證能夠喚起那一代人的記憶,能加深當代年輕人對歷史的認識。如今,他手頭的票證比起專業的收藏家來說并不多。吳均林的女兒吳克蘭告訴記者:“我爸爸的收藏大部分都是當年家里的結余,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各種票都不夠用,哪里會有剩下,后來他去收藏品市場淘過,市場上也沒有多少剩下。”
在所藏的票據里,有鹽票、糖票、月餅票、肥皂票、香煙票、各種尺寸的布票、棉花票、棉胎票、工業品購貨券等等。煙票是儲存最多的票據,因為吳均林不抽煙,所以這些當年發下來的煙票都結余了下來。1988年開始,肉票、糧票、水產票、豆腐票、煤油票開始變多了,有時候還有整版的富余。
在吳均林的收藏里,零星有幾張1976年、1978年的肉票,看到這些肉票吳克蘭笑了,“按照我的記憶,70年代的肉票肯定是不夠用的,這幾張剩下的肉票,應該是當年藏來藏去藏過期的。”她說,那會兒肉票都是有時間的,一個月過期,就不能用了,“我記得家里的肉票只夠用來切切肉絲、肉片,難得吃一頓紅燒肉,那是一個月的肉票都要搭在里面了。”
不少副食品票上還有編號,從1號到30號,是一個整版,這是怎么用的?難道是一天用一張?
“不是一天用一張。應該是一個編號可以對應一種物品,具體對應什么物品,當時會發通知的。”吳克蘭回憶,“比如當時會出一個通知,從4月20日到5月20日,可以憑3號副食品票購買粽子,那么就要回家把3號票找出來,然后帶上錢趕緊去買粽子,如果去得晚了,已經賣完了,這個票就用不出去了,算是作廢了。”
細心的吳老先生,還留存了當年憑票供應商品的一則通知,“我家所有的肉票、豆腐票、糧票我是有權限管的,上學路上要買個油條打牙祭,也是又要糧票又要錢的,我們家條件還可以,小孩子身上也是有一些糧票的。”吳克蘭還記得當年買荷花糕,也是要憑糧票買的,“那會兒哪用哄孩子吃飯,說不乖不給飯吃,立馬孩子就乖乖的了。”
而對于吳均林來說,所有票據里,印象最深刻的要數一張自行車票,“我們家人口少,所以是輪不到發自行車票的。后來,70年代初,部門里有一張自行車票,我當時表現好,領導獎勵給我了。”
老人記得,那張票拿去買了一輛永久牌自行車,車子騎了很久很久。與糧票一同出現的,還有購糧證。吳均林記得,購糧證和糧票是配套使用的,居民要憑購糧證到糧食管理所取糧票,買糧也要憑購糧證,購糧證其實是每家的“命根子”。
在那個時期,居民搬遷,除了要到搬出地和搬進地的派出所辦理有關手續,另外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手續便是到兩地的糧管所辦理相應手續。“哪家要是遺失了購糧證,意味著這個家庭將無法買到糧食。是要餓肚子的。”
(摘編自《錢江晚報》2019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