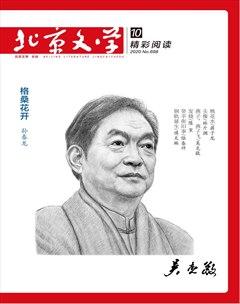烏鎮的船
楊俊文
到過烏鎮,看過小橋流水、傍河民居,便知道這是江南的風景。待幾年后再看這座古鎮,與西塘、周莊、同里相比,免不了有些色調雷同的感覺,所以景致一類則不在興趣之內。倒是墻上風蝕的青磚,水閣斑駁的浸漬,以及腳踏石街的聲響,還有那庭院和店鋪里端莊質古的堂號、字號,讓我沉思良久,覺得這其中似有沉厚悠遠的意蘊。
一月的烏鎮,飄著細雨,悠長的巷子氤氳著淡淡的水汽,讓人意識到盡管是江南的冬天,也少不了綿綿的雨水。午后時分,天雖未放晴,但云有了分明的層次,雨也隨之停歇下來,房舍和水岸的輪廓稍見清晰。無論如何,這個季節不招游人喜歡。正因為如此,烏鎮才褪去了惱人的喧囂和商業熱浪的襲擾,顯露出難得的安謐,使得這方水鎮更像是水鎮。
我漫無目的地走在西柵河岸古舊的石板上,恍惚間就到了一個叫安渡坊的地方。棧頭船(俗稱載客船)整齊劃一地泊于碼頭,顯然是專供游人“到此一游”的。然而,我的目光卻被岸邊的一排展板吸引。展板是竹制的,數十張相連一起,由水岸延至一條窄窄的柏油路,此后南折,足有四五十米的長度,上有陰雕的文字和樣式各異的船的圖案。從一端看起,才知道此乃“舟楫文化長廊”。
也許烏鎮的起落興衰,盡都承載在舟楫之上,所以駐足細觀,漸漸覺得長廊有了長河的寓意,繼而生出流動奔涌的氣象。
一一看過展板,沿著時光的水路走過來,再回首望去,烏鎮一帶所有的舟楫,幾乎都消逝在歷史的霧靄里。只有眼前用來載客的棧頭船,依然錯落有致地在水閣之間緩緩游走,像是完整的樂章演奏到最后,剩下單調而深沉的音符,不舍晝夜地飄蕩著。
烏鎮作為京杭大運河南端的一方水鎮,袂湖連江,衣帶吳越,使其有了獨特的水鄉韻致。盛唐時期,烏鎮就有十萬百姓在此居住。由于此地河網交織,舟船是人們唯一的交通工具,百舸千舟該是這一水域最為炫目的景觀。當然,在運河上最為氣勢浩大的,莫過于大業元年(公元605年)秋,隋煬帝乘船下揚州的一幕。唐朝的文學家皮日休稱其為“萬艘龍舸綠絲間”,這倒是夸張的筆意。但此次出游,隋煬帝確是奢華到了極點。據記載,他與皇后分乘龍舟和翔螭舟,隨行的公主、妃嬪、文武官員、宮娥侍女,以及御醫、僧尼、道士,分乘各式船只,計5191艘前后相接,長達二百余里。這蓋世無雙的帝王出行圖,委實令人唏噓不已。當年的江南民眾,如果真的看到這樣的場面,那感覺一定如夢如幻,而在目瞪口呆之后,必定有了一個經年不休的話題。
其實,中國的舟船并非獨屬于哪個朝代的發明。在浙江湘湖的跨湖橋遺址博物館里,有一艘由圓木鑿空后制作的船——享譽“華夏第一舟”的獨木舟。在現代化聚光燈的照射下,已經在時光中停泊了8000年的簡陋漂游工具,顯現出良渚文化清晰的紋理和早期人類的智慧之光。當時的人們還沒來得及意識到這艘原始“龍舟”的革命性意義,它就已經載著他們開始了文明進程中的靈巧劃行,以一種超越現實的速度,打通了水陸、地域和時代的阻隔。當三皇五帝在中原的黃土地上爭雄稱霸時,江南水鄉的獨木舟便自由穿梭于漁獵文明與農耕文明籠罩下的河網之間。
待到木板船一出現,一改獨木舟的簡陋,人們在水上穿行的速度和動力又前進了一步。后來江南的舟楫,在吳越爭霸時更是不可或缺,并成為彼此征戰的一大優勢。及至隋唐時期,舟船制造業已十分興盛,隋煬帝那次風光無限的出行雖顯驕奢淫逸,但也并非毫無積極意義,用現代理念的眼光看,也算是舟船的一次巡展吧!
舊時的官船一般不會輕易在普通的水鄉現身,但在烏鎮卻不罕見。據說,南朝梁尚書沈約、昭明太子蕭統、唐丞相裴休、清翰林夏同善等,都是乘坐官船來烏鎮掃墓、祭祖、省親和交游。明嘉靖年間刑部主事沈興龍的官船,顯然是寬大了許多,乘船回烏鎮故里擔心船身受阻,不得不派人在西柵開辟出一個“轉船灣”,迫使西市河在此處轉了個大灣兜,以便使船掉轉自如。主事的人真是獨具匠心,那灣兜的形狀酷似一頂碩大的官帽,不能不討來沈大人一份歡心。至于秦檜乘官船去北柵,到其妻王氏家省親,抬眼看見為取悅他而取名的那座“太師橋”,自然會滿心歡喜。只是后來的烏鎮人,對其人其橋卻自有一段嘲謔的評說。
歲月使用的魔法,讓身世不同的船只,在煙雨迷蒙的河面上變得模糊。而歲月也耗盡了氣力,同許許多多的船只一起老去。也許是卷帙里的文字和一代代人的講述,讓現在的烏鎮人始終站在歷史的岸邊,看帆影融入碧空,漁火閃于河網,或聽一曲漁舟唱晚,讓心靈與船同行,以慰藉一份鄉愁。他們像是閱盡了河上的過往,最終把那些承載生命的舟楫,從記憶的底片里顯影、放大,然后逐一打量它們的前世今生,如同端詳祖輩的容顏和自己曾經的模樣。他們很清楚,祖輩的身影就閃動在船頭,且在船頭隱沒。他們當中,也許就有曾伏在搖櫓的母親的后背,后來在船板上爬坐、玩耍的童年,再后來也開始了河上蕩槳搖櫓的生活。船,之于烏鎮人包括許許多多的江南人,是那么形影相隨而又不可舍棄。
我以為,這樣的凝視,無疑是選準了追懷的物象。
當我走完那段文化長廊時,再轉身,發現這原來是一部內容龐雜、豐富的大書,而我只瀏覽了書中的幾幅插圖。于是,我決定深究細問,千方百計找到長廊的創作者邵先生,通過他打開烏鎮船文化密閉的扉頁。邵先生早年在桐鄉報社和廣播站工作,平素鉆研烏鎮歷史,很是博學,人稱烏鎮的活字典。他說話聲音洪亮,笑聲爽朗,與水鄉的柔靜似不相合,講起烏鎮的船,很像是站在浪花濺起的船頭,迎著河上鼓蕩的陣風,在為你展示一幅幅流動的真切畫面——
烏鎮人很早就開始乘坐運河上的客船。明清時期,這里就有通往上海、蘇州和杭州的客運,每隔七天到十天一個班次,客船停靠的碼頭,就在西柵外的運河塘邊,烏鎮人就乘著這些船,跑蘇杭、闖天下。他們乘船不僅便利,而且那船也有一定的規模。后來,客船每天有對開的蘇杭班,交匯在西柵水域。這不免讓塞北的人有些嫉妒,雖有大河奔流,但用于載客的船只并不很多。在廣袤的土地上,會天天看到騾馬,鄉下人時常坐它們拉的車,去往田間或遠處的集市、城鎮。如果跑一次遠途,要么先坐馬車再坐汽車,要么干脆坐馬車跑上幾天幾夜,而坐一次火車便會成為值得炫耀的經歷。想來那時烏鎮人坐船出行,不會是一身塵土,且可看運河兩岸的風景,一定是很快樂的事。午夜十二點,汽笛聲在烏鎮的上空準時傳來,此時還在喝茶、打牌的烏鎮人便說,“蘇杭班”拉回聲(汽笛)了!于是,人盡散去,水鄉的夜才算沉寂下來。他們在附近一帶的出行,依然離不開船。那種船叫快班船,如陸地上的公交車,準時停靠在固定的水岸,為出行人提供便利。
過去,烏鎮商家大都有船,農村幾乎家家有船,手搖農船更是家中的必備,搖著它可以走親戚、外出辦事、購物。撒網打魚作為許多人家的主要收入來源,漁船則比比皆是。漁船的說法未免有些概括,若細分還可分為撒網船、拖網船、鸕鶿船、蝦籠船、耙螺螄船等。讓孩子們感興趣的還是鸕鶿船。鸕鶿(也叫魚鷹、水老鴉)們警惕地站在船邊,聽到主人一聲令下,便疾飛過去捉拿水中的魚。它們哪里懂得被主人戴上脖套的用意,只知道口中叼著魚卻無法吞咽下去,便只好迅速返回船上,乖乖地把魚獻給主人。遇到大一點的魚,它們配合默契,啄眼、咬尾、叼腮各有分工,很快會把魚拖至船頭。孩子們忍不住在岸上歡呼,漁夫急忙擺手,示意不要擾了他的好事,隨后會嫻熟地從竹簍里抓出一把小魚,一一放進魚鷹的嘴里,以獎賞它們的辛勞。
烏鎮附近也有田畝可供耕作,水上還可從事飼養業。有一種船叫黃鴨船,專門用來牧鴨,當年時常出現在這片水域。數不清的鴨子在水上鳴叫著,不時俯下身去,搶啄水中的食物,而主人一副悠閑的神態,緩緩撐船,哼著小曲,牧歸時的水面泛動著晚霞絢爛的光澤。這場景如今卻看不到了。烏鎮人深愛著身邊的河水,當他們懂得了水上牧鴨會給河水帶來污染,便毅然停止了這樣的營生。連同他們平常喜歡的經濟實用的水泥船,也因有害于對河水的環保,不多時日也在烏鎮銷聲匿跡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當年水鄉的娛樂活動竟也那般豐富,船便是不可或缺的依托。展示競技的踏白船,在烏鎮某個節日里最吸引人們的眼球。該船雙櫓八槳,十幾名壯漢按統一號令,在鑼鼓聲中合力爭先,使得船如疾箭,河面浪花翻飛。這場景很像賽龍舟的熱烈。專用于武術表演的拳船,每逢清明時節,當地人要請武師在船上表演拳術。烏鎮人最喜談論的還是高竿船,俗稱“蠶花船”。一條大船或兩條船相并一起,固定于河面,一根高竿豎立船上,表演者沿竿上下騰躍,并在竿頂展示蠶寶寶吐絲、作繭等高難動作。這些娛樂活動并非娛樂而已,其中都有吉祥的寓意。拳船和高竿船上的表演,則分別是為了祈求蠶繭豐收和蠶花繁茂。水鄉陸地狹小,看船上的表演,觀眾大都在乘坐的船上觀看。這讓我想到魯迅《社戲》里的趙莊,“近臺的河里一望烏黑的是看戲的人家的船篷”,也許與當年烏鎮人看船上表演的情形有幾分相似。若逢水上集市,也會有表演活動,那繁鬧便是不同平日的。人們紛紛搖著自家的船,早早地趕過來進行水上交易,船與船相連一片,可謂船的聚會。
雨時落時停,高竿船靜靜地停靠在一處水灣,沒有人登船表演。即使有演出,圍攏過來的已不是地道的烏鎮人,而是遠道來此的游客。高竿船表演的絕技,在給一代代烏鎮人帶來驚嘆和歡樂之后,最終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留下來。
保留下來的必是因為一種珍貴,讓人們常常想起并深愛不已,而那些消亡的東西卻也無法在記憶中徹底清空,有時恐怖與憂傷的水浪還會拍打心靈的堤壩。太湖水域當年并不太平,有一種船叫太湖船,水盜在船上晝伏夜出,四處搶掠百姓財物。太湖船分大小兩種,大船往往隱蔽于遠處,水盜乘小船快速出擊,把搶到的物資運至大船,大船便會迅速溜之大吉。官府對此無能為力或推卸責任,烏鎮人不得不自行設防,鎮的東南西北都有木制的柵門,白天打開以便出行通商,晚上關閉以防水盜之害。烏鎮里的柵,不過是防賊得來的稱謂。
在邵先生的講述中,我一直對“風子船”心生痛楚。那是怎樣的情形啊!幾只簡陋的小船,像是因失群而悲戚的殘雁,怯怯地停靠在離村莊很遠的河灘上或幽深的蘆葦中。面目丑陋的主人,隨船體的搖晃不住地呻吟,日漸潰爛的肢體再不顧忌烈日的烤灼和風雨的吹打。帶著心理和生理的雙重羞辱與痛苦,麻風病人在人們以自己疾病命名的船里,延續著最后一段生命。他們以討要食物為生,既要選準時間,又要方式恰當,所以,風子船的出行顯得格外審慎。討要者遮蓋著臉,在船頭向岸上伸出一根長長的竹竿,竿頂系著一個網兜或是可盛食物的器皿,施舍者把食物戰戰兢兢地放進去,便會馬上離開。
我總是擔心風子船與喜船(俗稱郎船)相遇。如果真的是這樣,那便成了悲與喜的沖撞。喜船是新郎去接新娘的船,船上放著屬當地習俗的“蠶花竹”,站在船頭的敲鑼人,不時地發出“捉蚌(當地人對女性的不雅稱謂)、捉蚌”的呼聲,引來民眾到岸上觀看。實際上,風子船最忌諱熱鬧的場景,絕不會沖了喜船的喜氣。在那條船上的麻風病人,當然不會看到喜船上的人,是怎樣在圍觀者的拍手祝福聲里,大把大把地向岸上撒去糖果。新中國成立以后,風子船的影子再也不見了。
雖是水上漂游工具的同類,大小快慢也不過是源于工具的形體與性能,但仔細觀之,你會發現那船與船之間形成諸多的對峙——高官與庶民的互斥,簡樸與豪奢的映襯、正義與邪惡的較力、文明與愚昧的相持、歡樂與悲苦的比照,都曾一一上演在舟楫之間了。似乎是所有的船,在歷史的長河上錯落著、揚棄著、推挽著,最后使烏鎮告別了往昔的悲苦,在今天的水岸展露出別樣的容顏。我忽然覺得,烏鎮就像是一條船,在歲月的波浪間一路顛簸著,而它的方向始終朝著遠離苦難的遠方,并滿滿地載負歷史的更迭與文化的繁衍,其中無盡的悲歡離合與愛恨情仇,讓這條船在盡經滄桑之后,開始變得如此的揚眉吐氣。時光老人盡管總是默不作聲,但種種對峙的結果最終告訴人們:昏暝和陳腐不再復返!只有那些生活與生命的記憶會頑強地存活與生長。
一陣叮咚的聲響從圍攏的展板后面傳出來。那是一處修船的水岸,工匠們正在修理船只。走進去看他們的動作和神態,是那么恭謹而專注,每條破舊的船,在他們看來都像是有生命的本體。一位工匠說,他早年造木船,后來修木船,近些年木船越修越少了,運河上跑的都是大型的機動鐵船。但看不出他有何抱怨,臉上一直堆滿笑容。是的,烏鎮河網之外,早已有了交織的公路、鐵路,各種車輛穿梭往來,自然使許多船只尷尬地隱去。其實,烏鎮人在乘坐高鐵和汽車時,早已消解了悵然若失的情緒,只是那些有心的參觀者,卻禁不住要順著時光的中軸,把那些曾經漂游于此的舟楫一一撫摸。
我還是忍不住要尋找什么,覺得這關于船的故事并未終了。從茅盾紀念堂走出后南行,便是茅盾陵園。在如一冊書狀似的墓碑之上,茅盾先生眺望遠方,恰如在船頭迎風而立,緊抱的雙臂仿佛擁抱一方山水。陽光透過云的縫隙,把塑像映照得光彩溢目。當看到元寶湖畔木心美術館方頭渡船似的組合建筑,禁不住又想到茅盾,想到與他同有一片故土的王會悟、孔另境、沈澤民……他們的生命之船,帶著劈波斬浪的驍勇,從苦難的遠方駛來,穿過歷史的風雨,最后靜靜地停泊在故鄉的水灣,再也不會離開。而他們精神的風帆,卻一直在為子孫后人高高揚起!
入夜,月光下的河水寧靜而明亮,運河上的行船間或鳴響的汽笛,在水面蕩起深沉悠遠的回聲,像是從歲月的深處響起,又似乎正向一個遠方傳去。我想起木心的一句名言——“我曾見過的生命,都只是行過,無所謂完成。”
烏鎮,依然行進在水上。
責任編輯 侯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