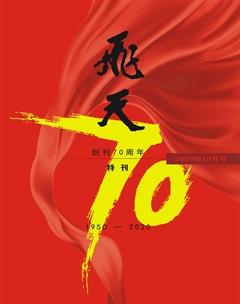《飛天》一直在我的身邊
最初知道《飛天》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內蒙古高原的一所三流本科院校里“放養”著——彼時剛恢復高考沒幾年,沒有師資,圖書館的書很少。我們像一群饑餓的羊,到處尋找青草。那時,《飛天》從天上掉下來,其中的“大學生詩苑”讓我們癲狂!詩歌是那么高貴的存在,“大學生詩苑”像一支箭射過來,插進了一棵樹,觸及到了蒼老的年輪和潔白的樹心,至今我都能回味到疼痛的歡欣。那時蘭州是一個遙遠的地方,那時我記得蘭州的一個詩人叫張子選。
做夢也想不到的是,幾年之后我嫁到了蘭州。從地圖上看,黃河上游,包蘭線,海拔1500米。我心里想著大漠孤煙、邊塞詩人、《讀者文摘》(《讀者》前身),還有《飛天》。我知道那是一些我與生俱來熱愛著的文字,我將把手伸過去,觸摸它的偏旁部首。
從河套到蘭州其實不遠,黃河幾字形的“一撇”,從上往下。綠皮火車,沿著黃河溯流而上。進了青白石,便看到皋蘭之州,兩山一河中端坐的美人。
用娜夜的詩說,從一個羊圈跳進了另一個羊圈,一切都是新的。在這個地方,我開始生兒育女。其間我知道,像黃河在我身邊羊皮筏子在我身邊牛肉面在我身邊一樣,《飛天》就在我身邊。我很稀罕蔣家坪的桃樹,河套沒有桃樹,我是在蘭州第一次看到桃子掛在枝頭。我把背上的娃兒往上面顛了顛,對桃農說,我想買幾只桃子。桃農把桃子裝進紙箱,頭都不抬說,不賣!我上前囁嘬著說,就一塊錢給我的娃兒買一只桃子。那人說,不夠潑煩的!天哪,我真的沒想到,后來我會愛上蘭州,愛上蘭州人,愛上他們的說話,我現在竟然離不開這個地方!我往返在包蘭線上,在河套想蘭州,在蘭州想河套,我像挑著一只扁擔。就這樣新一個世紀到了,不知道是讓誰耽擱了,在我年近不惑時,才拉開架式,準備寫了。那些虛度了的美好時光包括那些“不夠潑煩的”的生活,倒流進我的文字里,在《飛天》里,像一只只黃河里的魚跳躍起來。
我在《飛天》上發表的第一個小說《一打舊玫瑰》,責編張平。接著是中篇小說《我和兩個柿子樣的女人》。記得當時的主編陳德宏先生說,大概意思是,向春小說的氣質與本人給人的印象有一些不同。值得一提的是跟我同期發表的一個中篇小說《拯救》,作者孫頻。當時這個二十歲蘭大女生的作品讓我倒吸一口涼氣,我想,這個女孩子以后比我強。十幾年過去了,孫頻的發展路徑早已印證了我當初的判斷。回頭細數,在《飛天》共發表八九個中短篇,是我在同一刊物上發表作品最多的,并且無一退稿。本來也沒寫多少,我是起得遲走得慢睡得早,一直不成氣候,這就令人非常感動。《飛天》是寬厚的,容納了我的缺點,給予我鼓勵與寬容。
2003年上半年,魯迅文學院第二期高研班文學報刊社主編班因非典中止。下半年復課時,有些學員不能返校,這就騰出幾個名額,有幾個報刊的副刊編輯補充到這個班學習,我有幸和《飛天》副主編馬青山同窗。學員是全國各地文學期刊的掌門人,大多集編輯工作和作家身份為一身,縱論文學,橫談期刊,說著酒量與發行量,不亦樂乎。期間,舉班赴鄭州,參加由中國作協、國家新聞總署、中國期刊協會聯合主辦,魯迅文學院和《小小說選刊》《百花園》雜志社承辦的“全國文學報刊改革與發展研討會”。會議圍繞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加快文學報刊社改革步伐,推進體制機制創新,文學報刊如何更貼近生活、貼近讀者、走向市場,推進文化產業化進程等議題進行討論。總之,面臨著文學期刊何去何從的問題;我首先想到的當然是《飛天》。文學和文學期刊不是土豆和白菜,它的市場化確實面臨著諸多困難。我與馬青山一個是《飛天》副主編,一個是《飛天》作者,為著文學期刊的生存擔憂。把酒小酌,不免憂心,仿佛我們在一條船上。
十幾年過去了,《飛天》越來越好。除了各方面的支持,最重要的是有一支品學兼優、德才兼備的編輯隊伍,和對文學事業不懈堅持的寫作者。很多外省的作者也以在《飛天》上發表作品為榮,并且《飛天》刊發的作品大量地被國內的各種選刊選載。
再說《飛天》的人,基本都是一手編輯一手寫作,個個和這本雜志一樣,厚實、厚重、厚道。2016年,《飛天》第二個十年獎揭曉,在上面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包括我。其時我已有一段時間不在《飛天》上發表作品了,《飛天》還記得我!通知我去領獲獎證書的時候,我久久說不出話,當時的感覺是,慚愧大于感動,真的有點不好意思去飛天編輯部了。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第一次在《飛天》發表小說的情景——責任編輯張平老師說,這是咱們甘肅的作者,以前怎么沒有發現呢,她怎么現在才寫呢?其時我已年近四十歲。《我和兩個柿子樣的女人》是我初學時期的一個小說,嫩、本真,無論如何都沒有后來的小說好,但我對它的記憶是永久的。我現在還保留著樣刊,2005年4期,封面是桔黃色的底子上四枝蓮藕;同期發表的有方格子的《冥冥花正開》和孫頻的《拯救》,我們一起從《飛天》踏上了文學的第一個臺階。每每去文聯大樓,總要去《飛天》編輯部去看一眼,談笑風生之后會說,去農民巷吧——農民巷是文聯后面蘭州很著名的一條美食街。馬青山就從書架下面拽出了酒。
在我的書架上有一套從1949年到1999年的《甘肅文學作品》選。前言中說:“甘肅這塊厚重而又貧瘠的黃土地,幾十年來曾經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學作者,填補了自身一個又一個的空白。在中國浩蕩的文學長河中,甘肅文學也不時地躍起一朵朵閃亮的浪花,或多或少地增添著她的流速和色彩。”我覺得編者的話有點謙虛了,隴原大地,從來都是一片詩性與神性的土壤,古代邊塞詩照亮了整個中國歷史,到了近代就連客居甘肅的譚嗣同都寫出了不朽的詩篇。當代甘肅的傷痕文學,《當代文藝思潮》《飛天》的《大學生詩苑》都是攪動中國文壇甚至中國歷史的洪流。翻閱《甘肅文學作品選》,甘肅五十年的文學史撲面而來,里邊有很多震懾中國文壇的優秀篇章,再次閱讀,讓人淚目。而這五本裝的“甘肅50年的文學作品”,大部分都是從《飛天》刊發的!
70年,如果是一個人,已經飽經風霜,看淡身前身后,鶴發只是表象,最華麗的是骨頭。
從河套到蘭州,包蘭線,從黃河中游到上游,還是當初的綠皮火車。我想不通火車的顏色為什么一直沒有變,而我已早生華發。我22歲在內蒙古一所大專院校當老師,25歲在蘭州的一所中專學校當老師,30歲進一家報社做副刊編輯,之后報業整合,本世紀初我和我的同事們下崗了。生活始終不算難,也不算順,我遇到的所有的挫折,都是把我推向小說創作的無形的手。于是我走進小說,走進《飛天》,雖然遲到,但沒有缺席。后來我和我的同事們進了我們的主管單位,混進了省政協大院里。我拿著工資寫著小說,感謝上天對我的最好安排!
我經常想,包蘭線上的這一場畢生的奔赴,一定是為了一些什么。在蘭州出生的兒子楊桐與蘭州一同長大了,他竟然也是一個詩人,也在《飛天》發表作品。有一天他把發表他詩歌的《飛天》封面的照片發到了朋友圈,我這個《飛天》的老作者即刻熱淚盈眶。
責任編輯 郭曉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