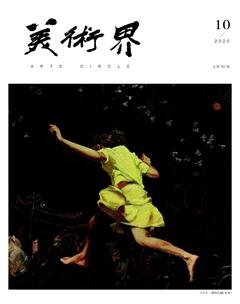梯山航海
黃光良
【摘要】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中國風景油畫承載了中國文化中的傳統精神和現代理想。時至今日,中國新時期風景油畫的內涵精神就是真善美的崇高思想意境,它的發展是對現實社會的審辯與反思,也是新時期藝術家追求理想社會的一面鏡子。
【關鍵詞】繪畫圖式;人文精神;中國風景油畫
19世紀末,油畫作為西學的一部分傳入中國。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迅速傳播開來,期間涌現了一些杰出的藝術家和一批精品佳作。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風景油畫向人們展示了新時期中國發展過程中的生存環境與社會變遷,在這里面有審辯也有反思,在這段過程中折射出的民族藝術情感和社會人文精神耐人尋味,直抵我們的心靈之境。
一、寫實主義風格下的蛻變和人文精神的缺失
(一)主題為先的寫實
油畫傳入中國,使得中國的寫實主義風格繪畫如同得到了滋養的甘露,其特有的具象、生動的寫實表現形式,深受國人的喜愛,并在中國畫壇迅速傳播開來。本著“成教化、助人倫”的畫訓以及社會文化的發展,再次喚起了國家對繪畫社會功能的重視,主題性寫實繪畫重新服務于社會,社會也需要繪畫去反映時代的特征和精神,而寫實主義風格的油畫在這個時期緊密結合社會和現實內容,承載了歷史和時代的重任。
這個時期的中國風景油畫主要承擔了社會的教育、認知、審美的功能。首先是20世紀早期受西歐寫實主義和蘇聯革命現實主義風格影響的中國風景油畫,因為時代的原因,許多中國的畫家都“鐘情”于寫實技法,在通過現實主義的表現方式借鑒西方的繪畫形式的同時,他們融入對中國社會發展主題的思考,鼓勵著一代國人珍惜大好河山、積極奮發向上。期間,盡管有李鐵夫、李叔同、潘玉良等前輩對寫實主義的民族化做出了種種努力,但終究未能影響開來,國家的動蕩、政治的影響、社會的現實無情地掩埋了他們竭力所要推廣的“油畫民族化”構想。
20世紀早期的中國風景油畫,其主要的表現風格就是沿襲曾經風靡多個世紀的寫實主義繪畫,特別是主題性的風景繪畫似乎已在風雨之中飄搖不定,似乎在表現的主題上還是那么單一和表面,似乎它只是政治性的繪畫工具,已無美學價值可言。然而,在回首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里,像陳抱一《蘇堤春曉》、劉海粟《北京雍和宮》、徐悲鴻《桂林山水》等風景系列的作品仍有很深的影響力,仍是難得的佳作,那是因為,我們所指的主題性的風景油畫并不泛指那些僵化的、一味追求抄寫對象的低俗作品,而那些具有獨特思維和表現力的寫實性繪畫才能如大浪淘沙,在歷史的長河演進中流傳下來,顏文梁、關良、吳冠中等前輩大師都是在寫實主義油畫的個性語言上有過多年的探索,并取得杰出成就。
(二)人文精神的缺失
現在所提出的人文精神的缺失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作為從西方引進的寫實主義觀念,在過去的一段時間或是一部分畫家中,在現實寫生與創作中形成了一種固定的構圖套路和表現模式,以至于養成一種先入為主的審美惰性。傳統風景繪畫的僵化模式和具有西方固有的理性精神符合社會對藝術的需要,從樸實的現實主義轉向了革命現實主義,革命的需要消解了現實主義畫家在藝術語言上的更多思考。蘇聯的“革命主義”為主旋律的現實主義繪畫被引入中國后,促進了中國油畫的理論化進程,也標志著中國風景油畫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然而,所面臨的時代與文化類別的差異,一味地強調作品的“大意義”“大場面”“形式感”,使得我們的繪畫只講表現范式,而不植根于藝術審美的土壤之中。這種用盲目地跟風即是低級的模仿,更是一種人文精神的缺失。
其次,是一種低級的模仿和虛情假意的抒情影響了繪畫精神的傳達。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期里面,中國風景油畫寫實主義的繪畫風格占據了中國油畫的主流地位,在借鑒西方傳統風景樣式的基礎上著力表現中國主要人文景觀及大好河山的場景。那個時期的風景繪畫是根據國家政體對傳統文化的理解而建立起來的傳統規范,是建立在一定歷史階段以經典傳統圖示為參照,借鑒西方寫實主義表現風格,再融合當代的中國視覺形象而建立起來的寫實主義的表現形式。這個時期大批的風景繪畫作品為了適應大型活動和社會需求,作品的創作大都建立在模仿與借鑒之上,在這個時期的作品中“媚俗”之風盛行。大眾文化的發展和社會活動的頻繁,使得很多藝術創作更趨向于通俗化、娛樂化。動蕩的國家狀況,也使得風景油畫缺乏深入高層次的藝術性和個性的審美的研究。
第三,是藝術個性的失落。藝術表達可貴之處,無外乎一個“真”字,“感人心者,莫顯乎情”(唐·白居易),唯有吐露真情才能體現繪畫的個性風采,風景油畫的表現形式及個性不僅各有不同,品味格調、雅俗層次也各有分別,但只有具備了較高的藝術素養及繪畫技能才能開掘作品的深度,才能真正體現藝術家的個性才華。追逐名利與盲目跟風的作品往往流于平庸,這種搖擺不定的繪畫心態不僅缺乏獨立的情感和個性,更是藝術創作路上的大敵。再則,許多畫家降低作品的品質去獲取短暫的利益,出現了很多劣質的作品摻雜其中,阻礙了中國現實主義風景油畫的發展。在這個階段,風景油畫作品更多是一種粉飾生活的商品,充當的是靡靡之音和視覺享樂的媒介,筆觸之下、圖式之間顯現的是藝術創作和人文精神迷茫。
中國風景油畫一路走來,經歷了“學習—融合—確立”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的中國風景油畫真實地反映了中國社會的歷史與發展,應該說這是中國風景油畫在每個時期都有它的文化選擇,風景油畫創作就是這樣帶有強烈的時代感,既使是在歷史上受西方藝術風格影響的時期,人們也有著普遍認同和熟識度,它已經成為中國美術一段時期內的文化主流藝術形式。
二、“消逝”的風景
(一)時代文化的需要
一個時期的風景繪畫反應了一個時期人的生活、人的精神狀態,以及關注這個社會的典型現象與問題,從另一個角度分析,可以體現為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人、自然、社會等多重關系的思考,是通過人在生活中的行為和經歷,引申到對社會現狀的關注和思考。
在社會的發展進程中,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不斷地在發生變化和演進。隨著中國社會的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從對自然的崇拜到相依共存,從獲取到破壞,再從破壞到保護,人與自然、社會的關系錯綜復雜……在風景圖式演進的背后,我們看到了前輩藝術家在自然中追求的軌跡。20世紀初期,作為向西方美術學習的范式,作為為主流社會而服務的“怡神之物”的風景圖式,中國風景油畫在這個時期的美學價值是作為一種文化行為而彰顯出來的。20世紀中期,呈現的是風景英雄史詩和田園牧歌式的風景圖式,這個時期,“物”的圖式化正在形成,主體的認同更加形而下。到了20世紀后半葉的新時代風景時期,可以看到自然秩序和社會秩序的和諧與統一,可以看出藝術家開始在對風景的審視中張揚“人”的主體性,因此,構建一種心靈體驗休憩之風景愈加迫切,且任重道遠。
人文風景圖式是畫家筆下一個重要的表現載體,“圖式”是人類認知世界過程中知識和經驗積累的一種形式,它具有原形的、大眾化的、概念的特性。對20世紀上半葉中國風景繪畫作品進行分析,從而了解圖式化演進在當時繪畫作品中的呈現,以及對中國風景繪畫創作帶來的影響和發生了怎么樣的變化。通過史實與繪畫作品我們可以看到,眾多從事風景油畫創作的畫家在創作與活動中呈現了極大的主動性,他們把自己的繪畫經驗融化到作品中,正是當時的社會發展所引起的文化進程將藝術家內心的特性化為了有強烈視覺效果的畫作。
20世紀初,中國風景油畫在實踐和觀念上開始關注中國社會問題和環境問題,繪畫內容和表現也由“傳統”轉向“現代”,畫家對傳統的現實主義繪畫風格進行了主動的變革和改良。在徐悲鴻早期的油畫《桂林風景》、關良的油畫《飛來峰》等作品中可以看到,我國早期的油畫家在油畫的傳播與發展中已經把具有中國代表性的風景圖式表現在畫作中,他們結合時代與社會的現實,努力挖掘中國的傳統文化的民族圖式。羅工柳、董希文、蘇天賜等一批藝術家主張從現實生活寫生入手,大力提倡戶外寫生活動。其中,鐘涵的《塞上秋野》《白鶴梁》等系列風景油畫作品體現了中國藝術家對油畫民族化的思考和實踐,作品中將黃土高原、麥田、黃河等具有中國風景元素的圖式導入了人性的關注,通過光影、色調、氣氛的營造使自然的景物轉化成精神的棲息之所,鐘涵的風景油畫作品有著明顯的民族精神的新圖式,有著深厚的文化養分,是一名有著民族責任心的藝術家。
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的本土畫家把目光轉向了地域風土人情和文化精神的內涵上來,在陳逸飛的油畫風景作品中,洋溢著濃濃的中國民俗、江南水鄉、民風民俗的中國地域特點,作品中有對風景靜物內在美的刻畫,有對民族傳統的文化追問和思考。在他的《江南水鄉系列》作品中,把江南的河道、民宅、拱橋做了古樸、靜怡、神秘的“東方化”處理,使得“江南水鄉”重現了中國傳統文化渲染下的浪漫情懷。吳冠中的《周莊》《水鄉》等系列作品,體現了他在油畫“民族化”“中國畫現代化”的探索與研究,他在色彩的概括處理以及抽象表現中,呈現了我們民族的水墨精神和黑白趣味,這些畫作并不是一山一景的真實記錄,而是哲學思考和象征手法的結合,是藝術家內在感受和理想信念轉化而成的“新”圖式。
(二)本土風景油畫人文意識的覺醒
所有的繪畫元素都承載著畫面結構與表現邏輯的思考,通過作品畫面呈現出藝術家的內心世界。風景繪畫從偏重于對光影的表現的荷蘭小風景畫派,到巴洛克對色彩的迷戀,再到古典主義強調畫面黑白關系和浪漫主義在色彩上夢幻般的呈現,風景油畫的寫實性已然可以再現自然。20世紀中葉,中國藝術家的作品已經開始指向實現所見之物向繪畫圖示語言的轉化,風景圖式的發展和演進也造就了人在風景繪畫中關注點的轉變,這種轉變的實質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它使得人們不滿足于所看到的風景中的一些簡單的山川、樹林和屋舍,而是這些風景的圖式符號給他們帶來的精神上的享受與愉悅。
西方的人文精神一直是與理性的科學精神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從文藝復興到工業革命,人文與科學、機械與反工業等交集在一起,形成了當今推崇個性發展、科學與哲學高度融合的人文精神社會。中國新文化運動,使得中國風景油畫從模仿西方圖式語言和形式上升到了主動追求東方文化神韻以及表現藝術家的精神面貌、個人情趣的新階段。它體現了新時期的藝術家以中國審美的態度有意識地去追尋繪畫作品的筆墨之韻律、山水之精神。到了20世紀的80、90年代,風景油畫作品比之前的作品在形式上更加的多樣化、涉及的內容更加的廣泛,不僅僅限于自然景觀題材和人文景觀題材,而且在作品的精神內質之中飽含了藝術家關注社會、關注生活的審美態度。中國本土的美學內涵和當代人文精神的發展也促使了中國的風景油畫創作對自身語言、審美、精神追求的思考。
美學評論家李澤厚先生說:“我曾把自然界本身的規律較之‘真,把人類實踐主體根本性質叫做‘善。當人們的主觀目的按照客觀規律去實踐得到預期效果的時刻,主體善的目的性與客觀事物真的規律性就交匯融合起來,真與善、合規律性和合目的性的這種統一,就是美的本質和根源。”①這種在自然本質中顯現出的“真”以及在人文精神理想中流露出來的“善”正是能創作出“美”的優秀風景繪畫作品的根基所在。建構在傳統人文精神之上的中國風景繪畫,讓我們清晰地看到這個時期的藝術家在風景繪畫的創作進程中刻苦鉆研、孜孜探索,取長補短、相互包容,使得中國的風景油畫的精神品格在新的時代中孕育出新的華彩。
注釋:
*本論文為:1.廣西藝術學院2016年科研項目重點項目“文化研究視野中的風景理論”(項目編號:ZD201604)階段性研究成果。2.廣西藝術學院2020年科研項目一般項目“地域文化背景下的風景繪畫圖式美學特征及傳承研究——以廣西風景油畫創作為例”(項目編號:YB202011)階段性研究成果。
①李澤厚:《美學四講》,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參考文獻:
[1]陳和西,吳忠光.中西語境結合下的中國風景油畫[J].裝飾,2006(08).
[2]王治平.中國風景油畫與人文精神[J].美術大觀,2011(02).
[3]胡沙金.中式風景或油畫山水——中國風景油畫的新探索[J].美術研究,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