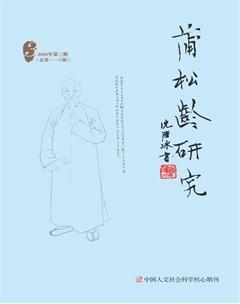《聊齋遺文》再版前言
馬振方
中圖分類號:G122? ? 文獻標識碼:A
路大荒先生整理的《蒲松齡集》和蒲松齡紀念館編輯的《聊齋佚文輯注》將國內所存蒲松齡的詩文、詞賦、戲曲和雜著收羅殆盡,為蒲學研究提供了較為完備的蒲著資料。而據刻于蒲氏碑陰的墓表附記,先生尚有《省身語錄》《懷刑錄》《歷字文》雜著三種;又據文集序跋,其所編著、輯錄之書還有《蒲氏族譜》《婚嫁全書》《觀象玩占》《小學節要》《莊列選略》《帝京景物略》等多種。其孫蒲立德在為《日用俗字》所撰的《跋》中寫道:“又有通俗勸世游戲詞,亦不下數十種,皆可以行世。”若然,柳泉先生的戲、曲類作品也當不止碑陰著錄的“戲三出”和“通俗俚曲十四種”。至于未見記載的蒲氏佚作,估計不會很多,卻也不會全無遺珠。上述種種散佚之作有的可能已不復存在,永無再現之日;有的則在國內失傳,而域外尚有存本。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聊齋文庫就是這類存本的集中所在。那是上世紀30年代日本醫生平井雅尾趁在蒲松齡家鄉的淄川醫院任職之便多方搜集的,后于50年代以百萬日元的重價出售,被一位當時在慶應大學就讀的企業家買下,捐贈給慶應大學圖書館。這批資料有抄本二百余種。其中多有偽作;但也確有一部分國內無存的蒲氏遺著。有的還是極可貴的作者手稿(如已在日本影印行世的《蒲氏族譜 聊齋草》)。1992年春,筆者應邀赴日本九州大學任教。其時一個重要愿望,就是盡力將這些抄本中為國內學人最關切者復制回來,經過考察,去偽存真,將其真品公諸于世。基于這一愿望,1998年便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筆者輯校的《聊齋遺文七種》。所收之文,就是從十六種慶應大學抄本復制件中芟夷偽作后整理付梓,除《琴瑟樂》,都是國內無存本的。
這些遺文,也只有《琴瑟樂》已被當時學界認定為蒲氏所作。《省身語錄》(抄本原題《聊齋編處世格言百全》)、《歷字文》(殘本)、《歷日文》《作文管見》《聊齋小曲》等在藤田佑賢、八木章好所編《慶應義塾所藏聊齋關系目錄》中都標有表示真偽待定的“*”號。筆者經過考察,以為前四種肯定為蒲氏編著。其中《省身語錄》不僅是蒲氏碑陰著錄者,且有序文存于《聊齋文集》,為蒲學家關注、尋索已久。但因題目已經更換,且另有一種六大冊偽作《省身語錄》混跡于平井氏搜集的抄本之中,這個題作《格言百全》的抄本便未引起人們的注意。筆者也是在慶應大學發現其善本室所藏《語錄》為贗品之后,才轉而關注這個名目相類的抄本,并將其復制帶回國內的。當時考察的結果,以為它是《語錄》的真本,收入前出遺文之首。惜其前無篇首,似非完璧。刊出后,經過學人和我個人再三考辨,本人最后的結論是:其部分條目尚有為蒲氏所編《省身語錄》殘稿之可能,但至少已被后人加入了相當數量晚出之《格言聯璧》等語錄,故此次修訂再版,只將它收入“附錄”,并改用抄本原題《聊齋編處世格言百全》,以備讀者繼續研究與察考。《歷字文》,也是蒲氏碑陰著錄之作,原為兩冊,僅存上冊前半或大半,殘缺多半。即此也頗可觀,是復制的諸種抄本中篇幅最長的一種。由于是在數年坐館畢家“茶余酒后”從四庫書摘錄、匯纂而成,內容龐雜,長短參差,間有圖表,或無標題,有些部分之間難于區分。前次付梓,除以校注訂正訛誤,一仍其舊,力求保持抄本的本來面目。本次校讎,特別關注開篇的《歷代帝王考》,上起夏、商,下至明末,與今之歷史年表及相關史書核對,又增加校注十多處;對前版本文其余校注也再次勘核,略有增減。《歷日文》和《作文管見》,都是前無記載之文,系為教授生徒而作,為了解先生的坐館生涯提供了新的資料。刊出后,二十余年未見異議。此次再版,訂正個別文字訛誤,依舊收入,讓它們繼續接受時間的考驗。
《琴瑟樂》,又名《閨艷秦聲》或《閨艷琴聲》,向被聊齋學界和我本人認為是蒲氏碑陰刻錄的同名曲作。經過近年幾位學人對其作者和產生年代的研究,已多有歧見。筆者經過比較,傾向于黃霖先生否定其為蒲氏所作或抄錄的見地,因而不再將它列入本次再版的《聊齋遺文》。
《聊齋小曲》,平井氏所編原為兩卷,七十余首,內有“附錄”十三首。前經筆者初步考辨,確定其中八首為柳泉公作。其余作者情況不明。由于筆者對小曲生疏,所見不廣,一時難于深入考辨,又恐舍去聊齋遺珠,索性將所剩幾十首全部編入新增的“附編”或“附錄”(為與原“附錄”區別,另題“附編”,實則同意,即其《前言》所說:“是為了便于研究者對它們進行更多的考辨與探討。”)。二十年來,既有友好點撥、見告,又有學者發文、賜教,開闊了筆者的眼界和思路,明確了其中大多數乃其所用曲調于乾隆以后旺盛興時期間的產物,非蒲松齡之筆;便是其間穿插抄寫的所謂聊齋詩之類也是贗品(筆者將其中三首錯認作蒲作,編入本書初版),此次修訂一并刪去。可喜的是山東大學馬瑞芳教授從偌多曲作中考出亦屬馬頭調的《豈有此理曲》乃柳泉公年輕時的戲作,戲仿比他年長許多的館主王永印背地與其某氏妻妾交談之語,從而為《聊齋小曲》也為再版的《聊齋遺文》增添一篇新的真品。我當初廣種薄收的愿望也因而小有所獲。本次再版,對小曲的“附錄”頗費考量,最后決定僅留兩首,即《李丑三吃狗肉曲》和《露水珠兒曲》。后者,作者于康熙十三年寫有“附后”之語,前面寫于康熙五年至十二年有此等附語的三首曲作均為蒲氏真品,故疑此曲亦有蒲作之可能。平井雅尾還將它譯成日文,于1954年與《五更合歡曲》等刊發于東京的《綜藝》。前者,據作品所寫,主人公家住淄川“城東十里”的大王莊,如果“說的實在話”,離城東只有幾里的蒲家莊應該更近;寫作時間是康熙“登基”的“壬寅”年(1662),蒲松齡時年二十三歲,尚居家中,近村有獵食狗肉的“奇事”,很容易得知,因而很有可能被愛好民間文藝的蒲松齡寫成這首類乎鼓詞的頗有意味之作。姑且將這兩首再次存入“附錄”,望行家繼續予以關注。
本書所收的聊齋遺文,《歷字文》前有耿世偉跋,《歷日文》后有張篤慶跋,平井雅尾還撰寫了《聊齋小曲編輯經過序》,為保留這些資料,便于研究、查考,分別附于各篇之后。《歷日文》前題“同邑孫樹百評閱”,但全文并無評語,而有夾注近百條,輯校分別標號,以“原注”列于篇末。
筆者考辨這批材料,始于從日本歸來的1994年夏,寫就“是否蒲松齡所作——慶應大學十五種抄本真偽考議”一文,后附于《聊齋遺文七種》之末。二十多年來,文集中收入此文有所修訂、補正,改題《是否蒲松齡著述》,附于再版本書之后亦略有增刪,以為參考。
(責任編輯:李漢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