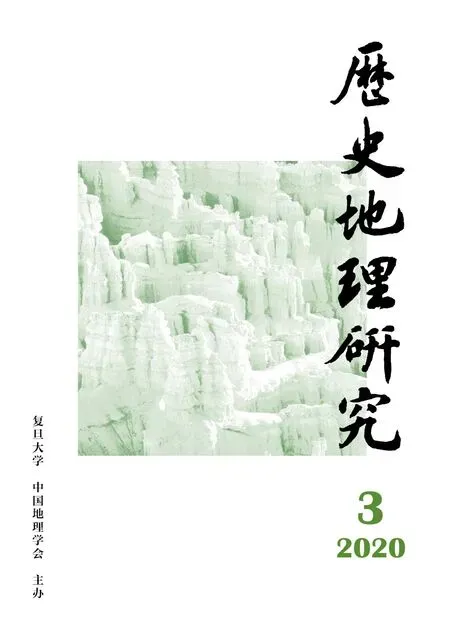“泥婆羅門”疏證
王 璞
(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云南昆明 650091)

關于器弩悉弄晏駕的經過,《新唐書》又道:“而虜南屬帳皆叛,贊普自討,死于軍。”(7)《新唐書》卷二一六上《列傳第一四一上·吐蕃上》,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6080頁。贊普去世的用字固然再度降級,相應的地理所指也變得模糊。藏史名著《西藏王統記》則說都松芒波杰“崩于六詔之地(Ljang-gi-yul)”(8)〔元〕 薩迦·索南堅贊: 《西藏王統記》(藏文),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頁。按: 當時南詔(蒙舍詔)尚未統一六詔,故Ljang-gi-yul在此不可循通例譯為“南詔”,下同是理。,《雅隆史》《漢藏史集》和《智者喜宴》同持此論,只是Ljang-gi-yul《漢藏史集》略作Ljang-yul(9)〔元〕 釋迦仁欽岱: 《雅隆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頁;〔明〕 班覺桑布: 《漢藏史集》(藏文),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頁;〔明〕 巴俄·祖拉陳瓦: 《智者喜宴》(藏文),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頁。。《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具言器弩悉弄于703年(長安三年)往六詔之地(’Jang-yul)(10)王堯、陳踐譯注: 《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第20頁。,次年“冬,贊普牙帳赴蠻地,薨”(11)王堯、陳踐譯注: 《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第149頁。。該書之《贊普傳記》補敘贊普曾行政令于六詔,“使白蠻來貢賦稅,收烏蠻歸于治下”(12)王堯、陳踐譯注: 《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第166頁。。“蠻地”藏語作Mywa,“白蠻”為Mywa-dkar-po,“烏蠻”乃Mywa-nag-po(13)王堯、陳踐譯注: 《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第20、53頁。,而西洱河諸蠻儀鳳中(676—679年)即被吐蕃兼并(14)《舊唐書》卷一九六上《列傳第一四六上·吐蕃上》,第5223—5224頁;《資治通鑒》卷二一四《唐紀三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55—1456頁。,可見“蠻地”指的是西洱河地區——藏文諸史所示器弩悉弄之升遐區域相互間并無抵牾。《舊唐書》還談到長安二年(702年)器弩悉弄率萬余人進犯悉州。(15)《舊唐書》卷一九六上《列傳第一四六上·吐蕃上》,第5226頁。按: 一說攻悉州東面的茂州,悉、茂二州所處中心區域今皆屬四川茂縣,參見《資治通鑒》卷二〇七《唐紀二三》,第1397頁。如此說來兩年后贊普亡于六詔之地或討逆之役均有可能,空間描述相異蓋因史料來源不同。再加思索,這難道不是吐蕃施放的疑兵煙幕?
《舊唐書·郭元振傳》確有“泥婆羅門等屬國”之語(16)《舊唐書》卷九七《列傳第四七·郭元振》,第3045頁。,但“泥婆羅門”不宜等同于至8世紀20年代仍為贊普夏牙的泥婆羅(Nepla(17)自唐至明還有“泥波羅”“尼波羅”“尼八剌”等譯法。廓爾喀崛起的18世紀60年代以前,清人多用藏語Bal-po(巴勒布)統稱加德滿都一域諸王權。)(18)王堯、陳踐譯注: 《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第15—25頁。,盡管前輩所言唐時天竺對應婆羅門的共識無有差錯。邊事顧問郭元振(656—713年)的“泥婆羅門”話語源出其《論闕啜忠節疏》中有關唐蕃形勢的剖析與忠告:“往者吐蕃所爭,唯論十姓、四鎮,國家不能舍與,所以不得通和。今吐蕃不相侵擾者,不是顧國家和信不來,直是其國中諸豪,及泥婆羅門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普躬往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屠滅。”郭氏隨即點出吐蕃之前倨后恭:“又其國中諸蠻,及婆羅門等國,見今攜背,忽請漢兵助其除討,亦不知欲以何詞拒之?”(19)〔唐〕 郭震: 《論闕啜忠節疏》,《全唐文》卷二〇五,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076—2077頁。“泥婆羅門”和“婆羅門”在同一文本中相繼出現,作者諒不致混淆二者。對于7世紀末8世紀初內外交困的吐蕃政局,呂思勉先生(1884—1957年)有一段抽絲剝繭的解析:“國中大亂,未必非贊普南征不反召之。贊普之南征不反,則國中諸豪及屬國之攜貳致之;國中諸豪及屬國之攜貳,恐亦用其力太過,有以召之也。”(20)呂思勉: 《呂思勉讀史札記》(增訂本)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8頁。此論不禁讓人想起贊普與噶爾家族(Mgar,唐譯“蒆氏”)的斗爭。再者,器弩悉弄承統后的相關疆域《新唐書》記為“南極婆羅門”(21)《新唐書》卷二一六上《列傳第一四一上·吐蕃上》,第6078頁。,實同《舊唐書》;對照之下,藏文史乘《拉達克王統記》卻說是時吐蕃之邊界“南至泥婆羅都城”(22)A. H. Francke,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Part (Volume) II: The Chronicles of Ladakh and Minor Chronicles,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India, 1926, p.32. 按: 原文是借“猴廟”(Bal-po’i-shing-khun /shing-kun)來代稱泥婆羅都城。。各史表述雖異,但從中仍可了知吐蕃的南向兵威已達“泥婆羅門”、婆羅門甚或泥婆羅地區,然其對當地的控馭并不穩固,離心反上事件時有發生。

藏族史學復興期的代表作《紅史》講到松贊干布在位時已將南方的珞(Blo)和門(Mon)納入治下。(28)〔元〕 蔡巴·貢嘎多吉著,東嘎·洛桑赤列校注: 《紅史》(藏文),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頁。《智者喜宴》亦說彼時吐蕃盡有南方珞(Klo)與門(Mon)之黔黎。(29)〔明〕 巴俄·祖拉陳瓦: 《智者喜宴》(藏文),第105頁。這兩個詞既可指具體的地區,又可稱當地的主體族群,“珞”意味著珞隅(Klo-yul,一作“珞瑜”)或珞巴(Klo-pa)(30)“珞瑜”一詞清代和民國史料常配以歧視性的反犬旁或豸字旁,與Klo-pa的本義“蠻貉”“野人”恰成一唱一和之勢,Kla-klo(蔑戾車)則是Klo-pa的同義詞。珞巴族藏語名稱現已改為Lho-pa(南方人)。,“門”則是門隅(Mon-yul)或門巴(Mon-pa)之簡稱,《唐蕃會盟碑》在頌揚贊普功績時同樣提到門巴:“南若門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蜜等雖均可爭勝于疆場,然對神圣贊普之強盛威勢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彼此歡忭而聽命差遣也。”(31)王堯編著: 《吐蕃金石錄》,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頁。松贊干布時代吐蕃還在邊陲各地設置了監稅官,隸于屬帳,負責向百姓征收貢賦,嵌有方物信息的官名分別為“那木巴寶王(Nam-pa-lde-rgyal)、泥婆羅銅王(Bal-po-li-rgyal)、蘇毗鐵王(Sum-pa-lcags-rgyal)、門隅竹王(Mon-rtse-rgyal)”(32)〔明〕 巴俄·祖拉陳瓦: 《智者喜宴》(藏文),第102頁。。Mon-pa在清代也漢譯作“穆安巴”,史述“其男子披發,頂覆紅牛毛,毿毿四垂,褐衣革鞮,肩披黃單;女披發,約以金篐,綴珠鈿,褐衣跣足,亦有著革鞮者”(33)〔清〕 傅恒等編: 《皇清職貢圖》卷二,《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第183冊,世界書局1988年版,第505頁。。相比之下,今天門巴族的服飾并無顯著變化,男性的帽檐配有紅色氆氌;女性披發、辮發或盤頭,金銀寶石的頭飾一仍舊俗;除炎徼族民布衣赤足外,男女多穿紅色長袍以及鞋底鞋幫皆用牛皮縫制的紅黑氆氌筒靴。綜上可以斷言,“泥婆羅”和“門”確然是兩個概念,《智者喜宴》的四王記敘尤為點睛之據。
清人所編《衛藏圖識》將珞巴描寫為愚昧獰厲的食人生番:“珞瑜野人國,在藏地之南數千里。其人名老卡止,荒野蠢頑,不知佛教。嘴剖數缺,涂以五色。性喜食鹽。不耕不織,穴處巢居。冬衣獸皮,夏衣木葉。獵牲并捕諸毒蟲以食。衛藏凡犯罪至死者,解送赴怒江,群老卡止分而啖之。”(34)〔清〕 馬少云、盛梅溪纂: 《衛藏圖識》下卷《圖考·番民種類圖》,沈云龍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編第57輯,第561冊,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221頁。“老卡止”當還原為Klo-kha-khra,《皇清職貢圖》別譯作“魯卡補札”。(35)〔清〕 傅恒等編: 《皇清職貢圖》卷二,第508頁。罪人流放之怒江在《西康圖經》中更正為雅魯藏布江下游。(36)任乃強: 《西康圖經(境域篇)》第62節《珞瑜》,新亞細亞學會1933年版,第166頁。《西藏全圖附說》繼述鹽利豐厚之博窩(Spo-bo),“一名波密,碩汎之南野番部落。博窩西通工布,南通珞瑜。每販珞瑜所產米谷來易,換三十九族鹽觔,常獲重息”(37)〔清〕 嵇志文: 《西藏全圖附說·陸路·博窩野番》,《西藏舊方志(增編)》第1冊,蝠池書院2016年版,第406頁。。碩汎即當今西藏昌都市洛隆縣(Lho-rong)的碩督鎮(Sho-pa-mdo),產糧的珞瑜無疑是波密土王(Ka-gnam-sde-pa)轄下的農業區,與拉薩東北夥爾三十九族易鹽之“博窩野番”可解作藏漢混血的波隅人(Spo-pa /Spo-ba),傅嵩炑(1869—1929年)就說:“波密部落界于康藏之間,與白馬崗野番毗連,自稱系漢人苗裔。土人相傳乃從前進藏之兵,因無餉而流落于此,與番女配,子生孫,而孫又生子,自成一部落焉。”(38)傅嵩炑: 《波密投誠記》,民國《西康建省記》,《中國方志叢書·西部地方》西康省第27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97頁。寧瑪派的最勝秘境白馬崗(Pad-ma-bkod)略當今墨脫(Me-tog),“白馬崗野番”應指18世紀末從主隅(’Brug-yul)(39)即不丹,佛教傳入前為古門隅之地,清代通謂“布嚕克巴”(’Brug-pa)。和門隅遷往墨脫的門巴后裔。19世紀末20世紀初,白馬崗及其以南的珞瑜各族群俱臣服于波密土王,珞巴與門巴更需向土王進貢或繳稅。波密既要派兵保護兼具伏藏圣地和勝樂金剛道場雙重角色之扎日神山(Tsa-ri /Rtsa-ri)的朝圣者不受珞巴襲擊——條件是交納酥油和皮子(40)捷克藏學家雷內·德內貝斯基-沃伊科維茨(René de Nebesky-Wojkowitz,1923—1959)的田野工作表明: 依藏人觀念,珞巴分生熟兩種,有別于漸已藏化的山區熟珞(Kha-klo),侵擾藏民的隊群(band)大半為盤踞壩區的生珞(Gting-klo)。參見René de Nebesky-Wojkowitz, Oracles and Demons of Tibet: The Cult and Iconography of the Tibetan Protective Deities, Graz: Akademische Druck-u. Verlagsanstalt, 1975, pp.406-407.,又要借西藏政府屢征珞巴之機向上下波密和白馬崗以外的南部擴張,局面十分微妙。(41)Santiago Lazcano, Ethnohistoric notes on the ancient Tibetan Kingdom of sPo bo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eastern Himalayas, trans. Rita Granda,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Number 7, 2005, pp.41-63; Hamid Sardar-Afkhami, An account of Padma-bkod: A hidden land in southeastern Tibet, Kailash, 1996, Volume 18, Number 3 and 4, pp.1-21.在法國藏學家石泰安(R.A.Stein)看來,野處工布(Kong-po)的珞巴見諸史冊的記載不多,最有名的莫過于直至15世紀,即被“鐵橋師尊”唐東杰布(Lcags-zam-pa Thang-stong-rgyal-po,1385—1464年 /1361—1485年)“點化”之前,他們還把持著前往扎日神山的道路以至珞隅的鐵礦。吐蕃南邊的另一群居民也僅是聚合在“門”之名下,遠未觸及立國的門檻。“門”包括喜馬拉雅林區的各土著部落,大概和漢語的“蠻”有關。一些門族人曾現身于偏東的漢藏交界地帶,而在西部,“門”是指拉達克的低種姓社群。(42)R. A. Stein, Tibetan Civilization, trans. J. E. Stapleton Driv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27, 34-35.
精研西藏上古史的美國學者約翰·文森特·貝萊扎(John Vincent Bellezza)在吸取先賢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認為,散居于西藏西陲乃至羌塘(Byang-thang)的門部落來自何方尚難確知,且這一史前族群的事跡學界多是霧里看花。不過根據口述資料,早在象雄(Zhang-zhung)(43)漢籍寫作“羊同”或“楊同”。時期勤勉的門族人就在此浩闊地域墾殖采礦,亦信仰本教(Bon),甚而建造過巍峨的城堡、要塞以及幽玄的陵寢和環壁神柱(walled-in pillars),部分遺址至今可尋。人口迅速增長的門部落或因致命性流行病的侵染而漸趨消亡,其后過了很長時間吐蕃人才領有門族故地。另有13世紀文獻談及門族十三支被突厥—蒙古系的霍爾人(Hor)驅至南方一事,權備一說。(44)John Vincent Bellezza, The Dawn of Tibet: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pp.24, 80-81, 98, 101-102, 128-130, 144-148.門族文化在共性之外因時空變易自也有個性的演繹,前者如耕種與本教的傳承,后者如象雄單部落和吐蕃多部落的差異。
至此筆者推定,“泥婆羅”和“門”不應合為一詞,標點時二者之間當用頓號隔開。“泥婆羅、門”是吐蕃南境屬國或虜南屬帳叛軍的先鋒,“泥婆羅、門等屬國”又為一地方勢力泛稱,其中至少還關涉六詔和珞隅,盡管門隅和珞隅并未建立政權。吐蕃王朝開疆拓土的行動不免引發藩屬的抵拒,《格薩爾王傳·門嶺之戰》(Mon-gling-g.yul-’gyed)便是這類邊患的文學影像。由曩時記錄不難想見,吐蕃對這些邊徼族群是當蠻夷(lho-bal)看待的。(45)Fang Kuei Li, W. South Coblin,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Special Publications No.91), Nankang,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87, pp.47-48, 106.不過基于以上論述和前輩的田野工作(46)李堅尚: 《喜馬拉雅尋覓》,山東畫報出版社1999年版;李堅尚: 《喜馬拉雅民族考察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從人類學角度觀察,吐蕃史上的珞巴當以漁獵采集為生,屬于覓食者(forager)。自錯那(Mtsho-sna)往南及迤西的門隅應是狩獵、牧業和鋤耕(horticulture)并存于世或次第行世。至于“泥婆羅銅王”居止的國度:“其俗翦發與眉齊,穿耳,揎以竹筒牛角,綴至肩者以為姣麗。食用手,無匕箸。其器皆銅。多商賈,少田作。以銅為錢,面文為人,背文為馬牛,不穿孔……每日清水浴神,烹羊而祭。”(47)《舊唐書》卷一九八《列傳第一四八·西戎》,第5289頁。《大唐西域記》更言該國:“出赤銅、牦牛、命命鳥。貨用赤銅錢。”(48)〔唐〕 玄奘、〔唐〕 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注: 《大唐西域記校注》卷七《尼波羅國》,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612頁。按: 谷地之國何以產牦牛?英國藏學家大衛·斯內爾格羅夫(David Snellgrove,1920—2016)推測鴦輸伐摩(Amshuverma /Amshu Varman)秉政之際(約605—621年)北進的泥婆羅人已占據高海拔地區。參見David Snellgrove, Indo-Tibetan Buddhism: Indian Buddhists and Their Tibetan Successors,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 2002, p.371.結合銘文所錄本土輸出天竺的麝香、雌黃、氈罽和熟紙(49)Rishikesh Shaha, Ancient and medieval Nepal, Kailash, 1988, Volume 14, Number 3 and 4, p.163.,工商礦冶與畜牧制度(pastoralism)誠可謂相得益彰。六詔社會則大抵推行后為南詔王國紹承的犁耕(plow agriculture):“犁田以一牛三夫,前挽、中壓、后驅。然專于農,無貴賤皆耕。不徭役,人歲輸米二斗。一藝者給田,二收乃稅。”(50)《新唐書》卷二二二上《列傳第一四七上·南蠻上》,第6270頁。按: 引文中最后一句尤中教授的闡釋較為細致:“具有一種手工業生產技藝的人,同樣分給一份土地,并不曾脫離農業生產。但因為他們在手工業生產中已提供了一部分稅收,所以農業稅便相對地減輕些,這就是‘二收乃稅’的意思。”參見尤中: 《中國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1頁。換句話說,南方“諸蠻”的適應策略(strategy of adaptation)實各得其所。(51)適應策略的相關理念參見Yehudi A. Cohen, Culture as adaptation, Yehudi A. Cohen ed., Man in Adaptation: The Cultural Present (2nd ed.), Chicago: Aldine Pub. Co., 1974, pp.45-68.《冊府元龜》嘗言吐蕃國“西南通泥婆羅、門國,卑實茲焉”(52)〔宋〕 王欽若等編: 《冊府元龜》卷九六一《外臣部六·土風第三》,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1308頁。。似此真有些“蕃夷之辨”的主觀意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