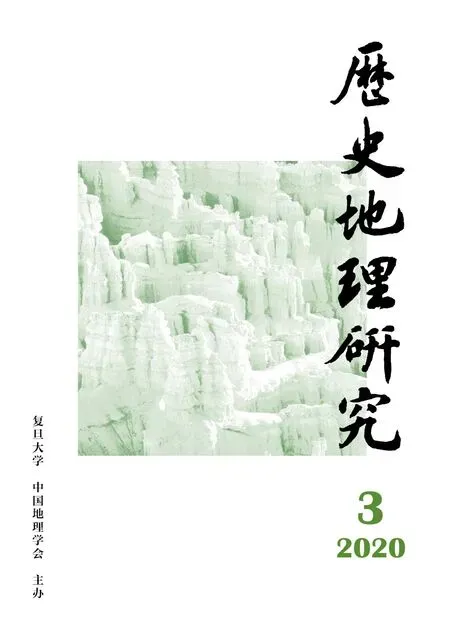嘉靖七年特別極端干旱對(duì)“嘉靖革新”的作用機(jī)制研究
韓健夫
(杭州電子科技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浙江杭州 310018)
一、 引 言
嘉靖初年的政策革新是明代中期重要的歷史事件,它不僅一定程度上清理了積弊,也為之后一系列改革打下了基礎(chǔ),史稱“嘉靖革新”(1)對(duì)“嘉靖革新”的相關(guān)研究可參見李洵: 《“大禮議”與明代政治》,《東北師大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1986年第5期;田澍: 《論明代大禮議中的革新思想》,《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研究生院學(xué)報(bào)》1999年第1期;田澍: 《嘉靖革新研究》,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02年版;馬靜: 《一道非同尋常的“即位詔”——明世宗“即位詔”與嘉靖初期改革》,《西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7年第5期;胡吉?jiǎng)祝?《“大禮議”與明廷人事變局》,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7年版;田澍: 《正德十六年——“大禮議”與嘉隆萬改革》,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這次“革新”涉及廣泛,包括關(guān)系到國(guó)計(jì)民生各個(gè)方面,諸如推行“余鹽制”、裁革冗員、清查勛戚莊田、革除鎮(zhèn)守中官、規(guī)范倉儲(chǔ)與漕運(yùn)以及調(diào)整太倉歲收結(jié)構(gòu)等,且延續(xù)時(shí)間較長(zhǎng)。關(guān)于革新中的各項(xiàng)措施及內(nèi)容前人研究已十分充分(2)鹽法與太倉改革可參見蘇新紅: 《明代太倉庫研究》,東北師范大學(xué)博士學(xué)位論文,2009年;蘇新紅: 《明代中后期的雙軌鹽法體制》,《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史研究》2012年第1期;蘇新紅: 《從太倉庫歲入類項(xiàng)看明代財(cái)政制度的變遷》,《東北師大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3年第1期。清查勛戚莊田可參見: 王毓銓: 《明代的王府莊田》,《王毓銓史論集》上冊(cè),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395—540頁。吏治改革可參見田澍: 《嘉靖前期內(nèi)閣改革述論》,《明史研究》1999年第6輯;田澍: 《雙向流動(dòng): 嘉靖前期的人事制度改革》,《社會(huì)科學(xué)戰(zhàn)線》2003年第3期;田澍: 《嘉靖前期裁革冗員述論》,《西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4年第4期;田澍: 《嘉靖前期監(jiān)察制度改革述論》,《蘭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8年第4期。,這里不再贅述。
近年來,有關(guān)歷史氣候事件與社會(huì)變革間關(guān)系的研究逐漸增多。氣候不僅是影響自然環(huán)境的重要因素,在社會(huì)經(jīng)濟(jì)變革中的作用機(jī)制亦日漸為人們所注意。其中,氣候要素變化及其影響下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變動(dòng)、國(guó)家政策調(diào)整,整個(gè)社會(huì)對(duì)氣候變動(dòng)的響應(yīng),各氣候要素的作用機(jī)制等,均是值得關(guān)注的課題。那么,從成化、弘治以降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變革到“嘉靖革新”,與氣候變化是否存在某種關(guān)聯(lián)?這個(gè)問題值得探討。
根據(jù)筆者等重建的過去千年北方地區(qū)極端干旱事件序列,嘉靖七年(1528年)是發(fā)生概率在2%的特別極端干旱年份(3)韓健夫、楊煜達(dá)、滿志敏: 《公元1000—2000年中國(guó)北方地區(qū)極端干旱事件序列重建與分析》,《古地理學(xué)報(bào)》2019年第4期。,而這一年也正是嘉靖革新大規(guī)模推行的起始之年。之所以關(guān)注此次北方地區(qū)的特別極端干旱事件,原因有二: 其一,北方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結(jié)構(gòu)使得其農(nóng)業(yè)產(chǎn)量深受降水量影響,“旱災(zāi)指數(shù)與歉收指數(shù)的相關(guān)系數(shù)達(dá)到0.71”(4)蕭凌波、閆軍輝: 《基于地方志的1736—1911年華北秋糧豐歉指數(shù)序列重建及其與氣候變化的關(guān)系》,《地理學(xué)報(bào)》2019年第9期,第1784頁。,即相較于澇災(zāi),旱災(zāi)尤其是極端旱災(zāi)對(duì)北方秋糧豐歉影響更巨;其二,明朝北方特別極端干旱事件共有五次,分別是成化二十年(1484年)、嘉靖七年、萬歷十年(1582年)和崇禎十三年(1640年)、十四年(1641年),崇禎年間接連兩年的特別極端干旱是導(dǎo)致明朝滅亡的直接原因之一,成化年間的大旱則被認(rèn)為開啟了之后的“災(zāi)害型社會(huì)”。(5)趙玉田: 《環(huán)境與民生: 明代災(zāi)區(qū)社會(huì)研究》,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6年版,第315—341頁。那么,在明朝社會(huì)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關(guān)鍵期的嘉靖初年,嘉靖革新開啟當(dāng)年爆發(fā)的特別極端干旱事件又扮演何種角色,引人深思。
前人曾從嘉靖皇帝的心理角度分析災(zāi)害與改革的關(guān)系,認(rèn)為此次大旱給當(dāng)時(shí)朝廷乃至嘉靖皇帝內(nèi)心帶來極大震動(dòng),從而推動(dòng)變革。(6)陳旭: 《因?yàn)?zāi)求言與嘉靖八年初明世宗的改革》,《西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3年第5期。另外,因大旱出現(xiàn)在“大禮議”之爭(zhēng)后不久,嘉靖皇帝此時(shí)正尋求地位的穩(wěn)固,而以“大禮議”進(jìn)階的朝中官員也對(duì)積弊存在不滿,因而借此大旱趁機(jī)攻擊異己,謀求變化。(7)鞠明庫: 《災(zāi)害與明代政治》,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184頁。上述研究更多將原因歸咎于嘉靖的個(gè)人因素和政治斗爭(zhēng),并未就干旱對(duì)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所造成的具體影響展開詳細(xì)分析,更未深入剖析這些影響對(duì)當(dāng)時(shí)既有政策運(yùn)作的作用過程和作用機(jī)制。但“嘉靖革新”的規(guī)模和范圍之廣,遠(yuǎn)超政治斗爭(zhēng)與心理因素可能造成的程度,若不從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政策運(yùn)作層面探討,恐不得其要。
本文以嘉靖七年的特別極端干旱事件為切入點(diǎn),通過分析災(zāi)區(qū)救濟(jì)、邊鎮(zhèn)糧餉供應(yīng)危機(jī)的過程,探討由事件發(fā)生到致使中央財(cái)政吃緊乃至開啟一系列革新的具體情況與作用機(jī)制,進(jìn)而解釋氣候?yàn)?zāi)害與國(guó)家響應(yīng)間的復(fù)雜關(guān)系,為研究氣候變化與社會(huì)發(fā)展的關(guān)系提供一個(gè)案例。
二、 極端干旱的爆發(fā)及對(duì)國(guó)家財(cái)政的沖擊
(一) 極端干旱的爆發(fā)
根據(jù)明代所存實(shí)錄、文集及地方志等資料,可以對(duì)嘉靖七年極端干旱事件進(jìn)行空間復(fù)原。《明實(shí)錄》載,當(dāng)年九月“各處地方多奏災(zāi)傷,朕訪得四川、陜西、湖廣、山西等處尤甚”(8)《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二“嘉靖七年九月甲申”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2119頁。,十月“各處災(zāi)傷,以陜西、四川為甚,湖廣、山西次之”(9)《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三“嘉靖七年十月辛丑”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134頁。,十二月災(zāi)情愈加嚴(yán)重,“河?xùn)|大饑,請(qǐng)得比河南、山東一切賑貸……又聞陜西、四川、湖廣及河南之南、山西之西,民皆救死不贍”(10)《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六“嘉靖七年十二月辛巳”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239頁。。楊一清奏對(duì)中對(duì)此災(zāi)情之嚴(yán)重程度有一宏觀描述,其曰:“去年(嘉靖七年),北直隸、山東、山西、陜西、四川、湖廣等處節(jié)報(bào)災(zāi)傷,南直隸、山東、淮、揚(yáng)、蘇、松等處亦多災(zāi)少熟。”(11)〔明〕 楊一清: 《楊一清集》卷三《論彌災(zāi)急務(wù)奏對(duì)》,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873頁。可見,當(dāng)年大旱不僅席卷了陜西、山西、河南、山東、北直隸整個(gè)北方地區(qū),在南方的四川、湖廣及南直隸也十分嚴(yán)重。
根據(jù)文獻(xiàn)資料的記載及語言描述,可以繪制出當(dāng)年北方各站點(diǎn)的災(zāi)害等級(jí)圖(圖1)。(12)韓健夫、楊煜達(dá): 《歷史時(shí)期極端氣候事件的甄別方法研究——以西北千年旱災(zāi)序列為例》,《歷史地理》第30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29頁;韓健夫、楊煜達(dá)、滿志敏: 《公元1000—2000年中國(guó)北方地區(qū)極端干旱事件序列重建與分析》,《古地理學(xué)報(bào)》2019年第4期。從圖1中可以看到西北、華北干旱尤為嚴(yán)重,山西、陜西兩省絕大部分地區(qū)受災(zāi)等級(jí)達(dá)到5級(jí);北直隸中南部、河南中西部及山東大部地區(qū)也達(dá)到5級(jí),可以說當(dāng)年整個(gè)北中國(guó)除個(gè)別府州和衛(wèi)所外,幾乎全為5級(jí)。受災(zāi)區(qū)域完全覆蓋了主要承擔(dān)向九邊輸送民運(yùn)糧的陜西、山西、河南、山東和北直隸諸省。當(dāng)年北方大旱對(duì)農(nóng)業(yè)產(chǎn)量的影響表現(xiàn)在各地從“春三月至秋八月,不雨”(13)康熙《平陸縣志》卷八《雜記》,《浙江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第3冊(cè),國(guó)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版,第552頁。,跨越三個(gè)季度的降水稀缺造成禾苗盡數(shù)枯槁。更為嚴(yán)重的是旱災(zāi)引發(fā)蝗災(zāi)肆虐,蝗蟲遮天蔽日,“蝗蝻食二麥絕……盡傷禾稼”(14)康熙《費(fèi)縣志》卷五《災(zāi)異》,哈佛大學(xué)圖書館藏,第96頁,https://id.lib.harvard.edu/curiosity/chinese-rare-books/49-990086428110203941。,“嚙禾稼為赤地”(15)萬歷《稷山縣志》卷七《祥異》,《中國(guó)地方志集成·善本方志輯·第一編》第23冊(cè),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276頁。,“飛蝗自東南來,群飛蔽空,不辨天日,每止處,平地厚二三寸,禾稼盡為所食”(16)嘉靖《通許縣志》卷上《祥異》,《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xù)編》第58冊(cè),上海書店1990年版,第116頁。,多地因此顆粒無收。糧食的歉收、絕收造成多地出現(xiàn)“人相食”的慘劇,僅當(dāng)年見于山東、河南、陜西、甘肅方志記載的“人相食”便有42條之多。(17)張德二: 《中國(guó)三千年氣象記錄總集(增訂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5—1070頁。此次特別極端大旱及蝗災(zāi)對(duì)北方社會(huì)造成了巨大沖擊。

圖1 1528年中國(guó)北方干旱等級(jí)圖
(二) 極端干旱對(duì)財(cái)政的沖擊
此次特別極端干旱殃及范圍巨大,對(duì)國(guó)家財(cái)政沖擊嚴(yán)重,國(guó)家收入大幅減少而開支大幅上漲。兩湖和江南等主要產(chǎn)糧地區(qū)和西北、華北等主要承擔(dān)和運(yùn)送民運(yùn)糧的省份均是此次旱災(zāi)的重災(zāi)區(qū)。這對(duì)明廷當(dāng)年漕運(yùn)、田賦的收入以及九邊糧草的供應(yīng)造成極大影響。尤其兩湖和江南受災(zāi),使往年北方遇災(zāi)時(shí)改調(diào)運(yùn)南方糧草濟(jì)邊的舉措難以實(shí)現(xiàn),由此引起了一系列連鎖反應(yīng)。
糧食產(chǎn)量銳減是最直接的影響。從圖1來看,重災(zāi)區(qū)在陜西、山西、北直隸、山東、河南幾省,比較嚴(yán)重的地區(qū)還有四川、湖廣、南直隸和廣東數(shù)省。以嘉靖初年上述諸省在全國(guó)夏稅秋糧征收中所占比重為參照,可從一定程度上看出該次特別極端干旱對(duì)糧食產(chǎn)量影響的程度。表1利用梁方仲先生所引嘉靖八年(1529年)桂萼在《各直隸府州布政司圖敘》中對(duì)嘉靖初年各省戶口、錢糧數(shù)的記錄進(jìn)行簡(jiǎn)單估算。

表1 明嘉靖初年分區(qū)戶、口、錢糧數(shù)

續(xù)表
從表1中可以看出,受災(zāi)嚴(yán)重的9個(gè)省份在籍戶數(shù)占全國(guó)總戶數(shù)的62.8%,在籍口數(shù)占總口數(shù)的72.8%,往年夏稅秋糧米麥?zhǔn)杖胝伎偸杖氲?5.2%,足見這些省份在全國(guó)經(jīng)濟(jì)中的重要性。因?yàn)?zāi)情對(duì)以上諸省田賦部分的蠲免及緩征勢(shì)必造成當(dāng)年田賦收入的大為減少。蠲免的政策在當(dāng)年九月下達(dá)。明世宗敕諭戶部、都察院對(duì)蠲免給予了詳細(xì)說明,并下令及時(shí)差人投送至受災(zāi)地方以便在全國(guó)施行。內(nèi)容如下:
戶部便道行查,議將各奏報(bào)災(zāi)傷十分重大者今年起存錢糧盡行蠲免,稍輕者照依分?jǐn)?shù)勘實(shí),即便停征,或量為折征輸納……其充軍起邊不可缺者,將兩淮等運(yùn)司鹽價(jià)銀兩及各處先因別項(xiàng)征納、今未用者酌量派補(bǔ)運(yùn)納,如有不敷,仍將太倉收貯官銀動(dòng)支百余萬兩,派發(fā)送去,以備代補(bǔ)。起運(yùn)及賑濟(jì)二項(xiàng),支用事完,造冊(cè)奏繳……竊恐貪暴官吏糧里人等聞之,即肆行催征,以圖侵尅。請(qǐng)多用黃紙備抄圣旨,馬上差人分投齊去被災(zāi)地方,交與撫按,遍貼鄉(xiāng)村,明白開載。應(yīng)全免者,不分起存一體全免;原勘被災(zāi)九分免九分,上征一分;八分以下俱照此例。(18)《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二“嘉靖七年九月甲申”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120—2121頁。
至嘉靖七年十月,各處災(zāi)傷“以陜西、四川為甚,湖廣、山西次之。議將各省夏稅秋糧照被災(zāi)分?jǐn)?shù)停征……因言天下歲征稅糧,因?yàn)?zāi)蠲免大約過半”(19)《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三“嘉靖七年十月辛丑”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134頁。。可見,因大旱而蠲免之田賦至十月已減過半,若加上隨后的蠲免數(shù)額,當(dāng)年所收田賦則更少。田賦蠲免最直接的影響是邊鎮(zhèn)的供給。在田賦的征收中,北方諸省每年有很大一部分稅糧征收后起運(yùn)各邊,即所謂“民運(yùn)糧”。民運(yùn)糧在嘉靖初年九邊總收入中占比最高,這筆向邊鎮(zhèn)輸出的物資與錢糧數(shù)額巨大,是九邊所需開銷的重要來源之一。然而承擔(dān)這些稅糧的北方省份偏在當(dāng)年受災(zāi)最為嚴(yán)重。據(jù)嘉靖初年《戶部題稿》所記載嘉靖十年(1531年)前后各邊鎮(zhèn)的收入來源細(xì)目可以看出,當(dāng)年各邊鎮(zhèn)對(duì)內(nèi)地諸省的需求涵蓋折銀、折布、草料、絹、綿等數(shù)項(xiàng),且所需巨大。其中,宣府和延綏所需民運(yùn)糧比重最大,達(dá)到80%以上;甘肅、寧夏、大同三鎮(zhèn)比重也超過70%,最少的遼東也占到將近四成。(20)〔明〕 佚名: 《戶部題稿》,《明抄本奏議十種》第5冊(cè),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359—381頁。因此,大旱下對(duì)北方各省稅糧的蠲免,無疑對(duì)九邊軍鎮(zhèn)的供給造成嚴(yán)重的影響。
然而,作為邊防前線,九邊對(duì)供給的需求極為剛性,如此只能將負(fù)擔(dān)轉(zhuǎn)移到中央財(cái)政之上,使當(dāng)年財(cái)政不僅要大規(guī)模投入賑濟(jì)當(dāng)中,還要應(yīng)付邊鎮(zhèn)的巨大需求,壓力劇增。這從嘉靖八年正月時(shí)任戶部尚書梁材的上奏中可窺探一二,其曰:“查嘉靖七年太倉所入止一百三十萬金,而費(fèi)出之?dāng)?shù)乃至二百四十一萬有余。”(21)《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七“嘉靖八年正月壬戌”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280頁。可見此時(shí)太倉已經(jīng)嚴(yán)重入不敷出。隨后戶部在復(fù)楊一清所奏恤民窮事中說道:“今天下被災(zāi)地方四川、陜西為甚,湖廣、山西、南北直隸、河南、江浙、山東、廣東、大同次之。自蠲免停征及動(dòng)支倉庫糧銀之外,計(jì)所發(fā)內(nèi)帑銀一百六十三萬二千三百有奇,鹽一百五十一萬八千五百引有奇。”(22)《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七“嘉靖八年正月壬戌”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280—2281頁。在嘉靖七年太倉銀糧收支赤字達(dá)91萬兩的不利局面下,不得不通過內(nèi)帑及鹽銀補(bǔ)助,以滿足支出241萬余兩、151萬余鹽引的需求,足見大旱對(duì)國(guó)家財(cái)政沖擊之嚴(yán)重。以下從災(zāi)害賑濟(jì)和邊鎮(zhèn)支出兩方面進(jìn)行爬梳,力求還原本次大旱造成財(cái)政赤字的具體過程。
在嘉靖七年十月前,各地仍主要按災(zāi)分?jǐn)?shù)停征并利用各布政司庫銀、預(yù)備倉賑濟(jì)支撐,并未大規(guī)模的動(dòng)用太倉庫銀及鹽引折銀。十月戶部所奏災(zāi)荒詳情載:“議將各省夏秋稅糧照被災(zāi)分?jǐn)?shù)停征;其應(yīng)賑給者,查各布政司貯庫銀兩及見在倉糧動(dòng)用;不足則發(fā)太倉銀給之;仍議發(fā)鹽引及蠲免兌軍等糧各有差。”(23)《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三“嘉靖七年十月辛丑”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134頁。可見此時(shí)朝廷對(duì)被災(zāi)各省夏秋稅糧給予停征,并調(diào)動(dòng)地方糧倉之儲(chǔ)糧用于賑濟(jì),災(zāi)情尚可維持。
但隨著之后邊鎮(zhèn)因?yàn)?zāi)乞賑的陡增,內(nèi)地賑濟(jì)開支大幅上漲,便亟須中央從太倉及鹽引中大量調(diào)銀以應(yīng)對(duì)。(24)當(dāng)然,運(yùn)用充軍糧、預(yù)備倉儲(chǔ)糧賑濟(jì)內(nèi)地的情況在十月之后也普遍存在。如嘉靖七年閏十月,陜西靖虜衛(wèi)、固原州饑民入寧夏,撥發(fā)陜西預(yù)備倉糧以賑濟(jì)(《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四“嘉靖七年閏十月戊子”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191頁);十一月底,嘉靖皇帝聽聞河南陜州災(zāi)荒甚重,人相殘食之情,下令戶部在原來留下充軍糧五萬石的基礎(chǔ)上,再留五萬石充軍糧賑濟(jì)之。(《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五“嘉靖七年十一月癸亥”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229頁)從閏十月開始,除戊子日因固原、靖邊等地饑民流入寧夏界,戶部命陜西以當(dāng)?shù)仡A(yù)備倉糧救濟(jì)外(25)《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四“嘉靖七年閏十月戊子”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191頁。,賑濟(jì)已更多要靠太倉銀庫等的供應(yīng)。戶部給事中夏言奏請(qǐng)“量發(fā)官銀二萬兩賑濟(jì)山西、河南近日被掠貧民”。(26)《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四“嘉靖七年閏十月己丑”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193頁。十一月,又從大同都御史蔡天祐之奏,“以大同災(zāi)傷,糧草缺乏,詔戶部發(fā)銀二十萬兩給之,令趁時(shí)糴買”(27)《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五“嘉靖七年十一月乙巳”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204頁。。同時(shí)寧夏巡撫都御史翟鵬又以旱災(zāi)請(qǐng):“免寧夏鎮(zhèn)所屬地方秋糧馬草,仍發(fā)銀賑濟(jì)。”(28)《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五“嘉靖七年十一月庚戌”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210頁。巡撫山西都御史王應(yīng)鵬等上疏言山西連年災(zāi)荒,戶部又“急發(fā)太倉銀數(shù)十萬及他有司銀以補(bǔ)蠲免”,并用“庫銀及引鹽合銀六十七萬四千九百有奇給之”。(29)⑩ 《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六“嘉靖七年十二月己卯”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237頁。山西巡鹽御史蔣賜“請(qǐng)戶部發(fā)京庫及有司倉庫之蓄以賑濟(jì),上納其言,下戶部議處”。⑩同月,“詔發(fā)太倉銀十萬兩于延綏鎮(zhèn)預(yù)備芻糧”。(30)《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六“嘉靖七年十二月甲午”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258頁。到嘉靖八年正月,又以“山西旱災(zāi)詔發(fā)太倉銀七萬兩給賑”(31)《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七“嘉靖八年正月己亥”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261頁。,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與大規(guī)模蠲免與賑濟(jì)一同出現(xiàn)的是諸多腐敗現(xiàn)象,如:“今有司一奉詔旨,往往虛報(bào)災(zāi)傷,覬覦蠲免,而都察院亦不俟本部議奏,輒與題覆。夫蠲免益數(shù)則歲用益拙,今免之一年尚難補(bǔ),若年復(fù)一年,國(guó)用何由而給?”(32)《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三“嘉靖七年十月辛丑”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134頁。這無疑令本已十分拮據(jù)的財(cái)政狀況雪上加霜。因而不久之后,嘉靖皇帝便令戶部及各地巡撫“查(邊鎮(zhèn))倉場(chǎng)實(shí)在之?dāng)?shù),具聞?dòng)懈鎱T者,即為議補(bǔ),軍士月糧,盡為給之。若視常延調(diào),致人心嗟怨、邊備廢弛,責(zé)有所歸”(33)《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五“嘉靖七年十一月丙午”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205頁。,并開始對(duì)邊鎮(zhèn)應(yīng)有銀糧及所存銀糧進(jìn)行統(tǒng)計(jì),以防邊鎮(zhèn)虛報(bào)錢糧以乞銀于中央。
綜上所述,統(tǒng)計(jì)災(zāi)起至嘉靖八年正月,全國(guó)各項(xiàng)賑濟(jì)支出細(xì)目如表2所示:

表2 全國(guó)賑濟(jì)開支明細(xì)
再看供邊情況。因邊鎮(zhèn)旱災(zāi)嚴(yán)重,原本各省輸邊的民運(yùn)錢糧因蠲免而無法運(yùn)達(dá),充軍糧又屢次被改折用以賑濟(jì)內(nèi)地災(zāi)區(qū),致使此時(shí)邊鎮(zhèn)面臨“各衛(wèi)所軍士月糧多有經(jīng)年累月不得關(guān)支”(34)《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〇“嘉靖七年七月丁亥”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066頁。的局面。加之每年防秋的軍事壓力在入秋后逐漸加大,以陜西三邊、遼東為主的九邊紛紛上疏乞中央撥銀備邊,以解救災(zāi)和防秋的雙重壓力。
嘉靖七年八月,提督三邊軍務(wù)尚書王瓊以陜西三邊邊防吃緊為由,上奏邊防前線的甘肅鎮(zhèn)士馬俱困,請(qǐng)求“加添糧銀養(yǎng)其銳氣,買補(bǔ)馬匹給付騎征,俱請(qǐng)以便宜行事”,得“兵部議覆,如瓊言,詔從之”(35)《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一“嘉靖七年八月癸丑”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091—2092頁。。但隨后不久,遼東巡撫都御史潘珍又以歲饑請(qǐng)求增加年例銀,并要求倍加折色,以待秋成糴糧備用時(shí),這引起了戶部的強(qiáng)烈不滿。戶部認(rèn)為“歲派年例已有定額,輒難輕議其折色,豐年既不扣除,過歉亦難增加”。(36)《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一“嘉靖七年八月丙辰”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093頁。但隨即考慮到邊鎮(zhèn)急需趁此秋成糴買糧草以備邊防,以及遼東邊軍因?yàn)?zāi)之故確實(shí)缺支糧餉,又只好“請(qǐng)發(fā)太倉銀十萬兩,內(nèi)七萬補(bǔ)明年之年例,余三萬為例外接濟(jì),聽其從長(zhǎng)議處,或收候秋成糴買糧料,或支給官軍月糧”(37)② 《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一“嘉靖七年八月丙辰”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094頁。。不僅如此,還將“淮、浙、山東、長(zhǎng)蘆引鹽銀七萬三千五百兩有奇,定擬斗頭斤重,分發(fā)各緊要城堡,上納本色糧草以備緩急支用”。②
但面對(duì)防秋任務(wù)的日漸嚴(yán)重及北方邊患時(shí)常發(fā)生的不利局面,所發(fā)銀兩可謂杯水車薪,原本因“民運(yùn)糧”缺口所致的供應(yīng)不足問題更顯緊迫。時(shí)任宣府巡撫都御史的劉源清就因北方邊患、糧草缺乏、直隸各省因?yàn)?zāi)起運(yùn)錢糧久久不至等原因,乞求戶部于庫中“別項(xiàng)銀兩借補(bǔ),并將嘉靖八年年例銀兩預(yù)乞移借”;“戶部議發(fā)銀十二萬兩給之,以八萬兩抵明年年例”。(38)《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三“嘉靖七年十月己未”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155頁。八年正月,戶部又分發(fā)銀兩以供西北邊防糧草之需,用于彌補(bǔ)前一年民運(yùn)糧等虧欠,“以太倉庫銀十萬,淮、浙等運(yùn)司鹽價(jià)三十三萬有奇,分給延綏、寧夏、甘肅、固原,先補(bǔ)起運(yùn)及存留俸米之?dāng)?shù),令其召買芻餉,中納本色,分貯要害備用。其寧夏一鎮(zhèn)則以織造余銀及布政司在庫官銀接濟(jì)”(39)《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七“嘉靖八年正月戊午”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274頁。。
不僅如此,嘉靖七年明廷為彌補(bǔ)民運(yùn)糧不足導(dǎo)致的邊鎮(zhèn)糧餉虧空,還前后兩次將鹽引折銀供邊。即以“淮浙山東長(zhǎng)蘆貳拾貳萬壹仟陸佰壹拾肆引,共銀拾萬兩……兩浙山東長(zhǎng)蘆肆拾肆萬叁仟貳佰叁拾貳引,共銀貳拾萬兩”,分別補(bǔ)足山西原派宣府鎮(zhèn)與大同鎮(zhèn)的民運(yùn)稅糧馬草價(jià)銀不足之?dāng)?shù)。(40)《萬歷會(huì)計(jì)錄》卷二三《額餉·宣府鎮(zhèn)》、卷二四《額餉·大同鎮(zhèn)》,《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53冊(c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版,第813、856頁。另外,八年正月開始,明廷為籌措邊鎮(zhèn)所需錢糧,不得不開啟武官開納制度,“兵部以陜西三邊軍餉不充,奏開武職援納之例。上以鬻爵非善法,第邊事方急,姑暫一行,歲終即止”(41)《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七“嘉靖八年正月己亥”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261頁。。同時(shí),還下令各地?fù)岚垂賳T在不加征稅糧的前提下,通過催征往年拖欠以補(bǔ)邊鎮(zhèn)之不足:“今歲歉民窮,既不當(dāng)額外加征,即發(fā)帑開鹽,又不可繼,宜令撫按官督所屬征還積逋,仍以近日補(bǔ)各邊起存銀鹽積余者稍濟(jì)之。”(42)《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七“嘉靖八年正月丙寅”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283頁。
上述多項(xiàng)舉措并行折射出嘉靖八年國(guó)庫匱乏的事實(shí)。但原有開源手段全部利用后,仍不足以應(yīng)對(duì)同時(shí)來自邊鎮(zhèn)與內(nèi)地的錢糧需求。此時(shí),只能乞求來年風(fēng)調(diào)雨順和催征往年拖欠以補(bǔ)缺額。表3統(tǒng)計(jì)了災(zāi)起至嘉靖八年正月,用于邊防軍事的開支細(xì)目,詳細(xì)如下:

表3 邊防軍事開支細(xì)目
至嘉靖八年四月,時(shí)任戶部尚書梁材上疏談及上年至今戶部開支情況時(shí)說道:“各該省鎮(zhèn)抵補(bǔ)、賑濟(jì),并備邊銀兩,總計(jì)一歲之間,共解銀三百四十七萬三千三百余兩……今倉在庫銀兩止有二百一十八萬七千六百三十余兩。”(43)〔明〕 佚名: 《戶部題稿》,《明抄本奏議十種》第5冊(cè),第214頁。由此可見,從嘉靖七年夏秋爆發(fā)特別極端干旱災(zāi)害至嘉靖八年上半年,戶部赤字達(dá)130余萬兩。另外,當(dāng)年大旱對(duì)于中央財(cái)政的沖擊還反映在宗室開支問題和工部工料、銀料是否蠲免的爭(zhēng)論之上。嘉靖七年八月,內(nèi)官太監(jiān)張敬奏請(qǐng),要求戶部批金四千五百一十余兩為各王府造金冊(cè)金帶等用品。戶部對(duì)此無理要求十分不滿,要求從嚴(yán)使用經(jīng)費(fèi):“歲例買金多不過二千,今驟加一倍,其中有無實(shí)數(shù),及應(yīng)否支用,本部無從稽考,且冊(cè)封歲行,官帑有限。今天下災(zāi)傷,理當(dāng)節(jié)省,姑出本部所貯贖金及發(fā)榷關(guān)銀,收買以足其數(shù),請(qǐng)敕司禮監(jiān)督同該局,歲終一勘冊(cè)封,用金幾何,年例外應(yīng)添買幾何,扣數(shù)題請(qǐng),勿致浪費(fèi)。”(44)《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一“嘉靖七年八月丁卯”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104頁。
在財(cái)政緊張局面陡增的七年十月,工部尚書劉麟與工科左給事中張潤(rùn)身就工部工料、銀料是否應(yīng)予蠲免問題出現(xiàn)爭(zhēng)論。此事是因劉麟提出依舊征收工部工料、銀料用來供給宮殿、陵寢的修建而起,給事中張潤(rùn)身對(duì)此表示不滿,進(jìn)而提出反對(duì)意見,雙方由此發(fā)生爭(zhēng)執(zhí)。最后,皇帝批準(zhǔn)了劉麟的上疏,沒有蠲免當(dāng)年工料、銀料的征收。而在此討論前不久,戶部已發(fā)出感慨稱:“天下歲征稅糧,因?yàn)?zāi)蠲免大約過半,而太倉銀請(qǐng)發(fā)借補(bǔ)者,亦已過半。”(45)《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三“嘉靖七年十月辛丑”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134頁。當(dāng)年工料銀供應(yīng)捉襟見肘,甚至不得不預(yù)支來年款項(xiàng):“己卯時(shí),陵工方興,計(jì)所費(fèi)以巨萬數(shù),工部尚書劉麟稱藏錢少,十不能給一,請(qǐng)借支天下明年工價(jià)之半及原修清寧宮、世廟余銀十萬余兩以濟(jì)急用,待后征補(bǔ)。”(46)《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四“嘉靖七年閏十月己卯”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179頁。故此,在這一局面下,皇帝已經(jīng)沒有魄力和途徑再對(duì)工料、銀料給予蠲免。
綜上,因嘉靖七年夏秋爆發(fā)波及九省的特別極端干旱,致使當(dāng)年夏稅秋糧蠲免、停征過半,供邊民運(yùn)錢糧銳減,太倉收入額度也減少到只有130萬兩。面對(duì)大范圍的救濟(jì)及邊鎮(zhèn)開支,明廷先后動(dòng)用各省倉庫儲(chǔ)糧及太倉庫銀、鹽引銀乃至內(nèi)帑之銀,前后共支出241萬兩有余。到嘉靖七年年底,太倉、內(nèi)帑均已告罄。及至嘉靖八年四月,戶部累計(jì)赤字一百余萬兩,面對(duì)接下來內(nèi)地賑濟(jì)和邊鎮(zhèn)軍事的持續(xù)需求,中央財(cái)政已無銀可用。在此局勢(shì)下,通過一系列具體的機(jī)制與過程,觸發(fā)了“嘉靖革新”。
三、 觸發(fā)革新的機(jī)制與過程
(一) 觸發(fā)革新的機(jī)制
嘉靖七年的大旱是整個(gè)明朝北方最嚴(yán)重的五次旱災(zāi)之一,造成北方糧食減產(chǎn)、絕收進(jìn)而引發(fā)財(cái)政危機(jī)的同時(shí),更是對(duì)明朝已有財(cái)政制度和運(yùn)作情況的考驗(yàn)。正德朝的積弊,使明朝到嘉靖初年已面臨極為嚴(yán)重的統(tǒng)治危機(jī),致使國(guó)家“國(guó)柄潛移,權(quán)幸用事,祖宗之制度,朝廷之綱紀(jì),蕩廢殆盡”(47)〔明〕 張?jiān)?《論王邦奇等七次奏辯疏》,《明臣奏議》卷一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445冊(cè),臺(tái)灣商務(wù)印書館1986年版,第314頁。。嘉靖的即位詔書中委婉表達(dá)了對(duì)武宗的批評(píng):“惟我皇兄大行皇帝運(yùn)撫盈成,業(yè)承煦洽,勵(lì)精雖切,化理未孚,中遭權(quán)奸,曲為蒙蔽,潛弄政柄,大播兇威。”(48)《明世宗實(shí)錄》卷一“正德十六年四月壬寅”條,《明實(shí)錄》第38冊(cè),第10頁。所有弊端中,尤以鹽政、宗藩及屯田、邊防供給等問題最為嚴(yán)重,加之干旱災(zāi)情的沖擊,這些積弊悉數(shù)暴露出來。
嘉靖初年鹽政大壞,時(shí)人深知。正德年間,宗室被大肆授權(quán)購買鹽引,致使鹽政混亂,支鹽困難,官鹽壅塞,私鹽大行,國(guó)家鹽政收入遭極大損害。如霍韜所奏:“正德年間,或權(quán)奸奏討,或勛戚恩賜,皆給引目,自買余鹽。故法遂大壞,而鹽亦平賤。復(fù)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秤摯余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quán)要報(bào)中,借影私鹽以雍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jià)雖平,而正課日損。”(49)〔明〕 霍韜: 《鹽政疏》,《明經(jīng)世文編》卷一八七,《續(xù)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657冊(c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00頁。同時(shí),明廷還面臨著宗室占據(jù)大量民間田產(chǎn)、宗室人員滋生每歲祿米所費(fèi)巨大等困局。霍韜奉命編纂《大明會(huì)典》時(shí),曾翻閱典籍考察宗室之膨脹,上疏:“洪武初年,山西惟封晉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郡王鎮(zhèn)輔奉國(guó)將軍,中尉而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位矣,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50)〔明〕 霍韜: 《修書陳言疏》,《明經(jīng)世文編》卷一八七,《續(xù)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657冊(cè),第598頁。故此,霍韜以災(zāi)變應(yīng)詔陳言時(shí)不無感慨:“夫土地稅入不能加多,宗藩子孫日益繁衍,祿糧所由不給也……昔也以一郡而供一王,今以一郡而供數(shù)千百人矣,祿糧所由不給也。”(51)《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八“嘉靖八年二月庚午”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290頁。宗室對(duì)民田的侵占更使得民眾逃亡、田地荒蕪。劉麟在嘉靖初年奏議中稱:“土地之在小民者,日侵月削,有司莫敢誰何。小民日見逃亡,畿內(nèi)凋零,亦已太甚。”(52)〔明〕 劉麟: 《乞免查撥莊田疏》,《明臣奏議》卷一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445冊(cè),第307頁。正如王毓銓先生所總結(jié)的:“孝宗武宗兩朝時(shí)期親王、勛臣、貴戚奏討莊田過多且日甚一日。”(53)王毓銓: 《明代的王府莊田》,《王毓銓史論集》,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421頁。民生本已多艱,致使其對(duì)干旱的沖擊異常敏感,這也是旱災(zāi)發(fā)生后北方諸省有如此多“人相食”慘劇的原因之一。
此外,嘉靖所面臨的還有冗官的泛濫、奸佞的專權(quán)、土地的兼并、屯田的頹敝、邊儲(chǔ)的不足等問題。(54)參見嘉靖即位詔書,《明世宗實(shí)錄》卷一“正德十六年四月壬寅”條,《明實(shí)錄》第38冊(cè),第10—37頁。如此種種,又因干旱而激化。面對(duì)由此觸發(fā)的巨大財(cái)政危機(jī),戶部尚書梁材認(rèn)為:“在京及各省各邊錢糧所以不足者,大端有五,一曰宗室,二曰武職,三曰冗食,四曰冗費(fèi),五曰逋欠。”(55)〔明〕 佚名: 《戶部題稿》,《明抄本奏議十種》第5冊(cè),第216頁。所有上述積弊,在災(zāi)害的介入下,集中表現(xiàn)在供邊問題上,最終釀成財(cái)政危機(jī)。
該次大旱觸發(fā)改革的內(nèi)在機(jī)制,從供邊體制的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可以有所反映。首先,邊鎮(zhèn)需求不斷增大。北方邊鎮(zhèn)的軍屯數(shù)額增減直接關(guān)系到其對(duì)內(nèi)地需求的強(qiáng)弱。隨著軍屯兼并不斷加劇及制度本身的腐壞,軍屯所出糧額不斷減少。從正統(tǒng)二年(1437年)屯田子粒征收改革后算起,直到正德末年,屯田子粒額明顯下降,如圖2所示。

圖2 邊鎮(zhèn)屯田子粒歲額統(tǒng)計(jì)
正德后期屯田子粒出現(xiàn)大幅下降,從300萬—400萬石降為100萬石,出現(xiàn)了200萬石的巨大缺口。正德三年(1438年),巡按山東監(jiān)察御史周熊在上疏中描述了永樂朝遼東鎮(zhèn)的屯田情況:“永樂十七年(1419年),遼東定遼左等二十五衛(wèi)原額屯田共二萬一千一百七十一頃五十畝,該糧六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五石;至是田止一萬二千七十三頃,該糧二十四萬一千四百六十石。”(56)《明武宗實(shí)錄》卷三九“正德三年六月己卯”條,《明實(shí)錄》第34冊(cè),第915頁。可見正德初年邊鎮(zhèn)屯田已屬缺失之狀,便需要從內(nèi)地供給獲得更多的錢糧以彌補(bǔ)因屯田失額所帶來的虧空,來滿足邊鎮(zhèn)每年開支的剛性需求。
其次,邊鎮(zhèn)供給不穩(wěn)定。供邊主要靠民運(yùn)糧、鹽法開中和年例銀發(fā)放,偶爾也依靠漕糧的撥發(fā)補(bǔ)給。隨著邊鎮(zhèn)屯田產(chǎn)量不斷下降,民運(yùn)糧逐漸成為彌補(bǔ)屯田產(chǎn)量不足的關(guān)鍵角色,擔(dān)負(fù)起供邊的主要責(zé)任。從梁材記錄下的邊防諸鎮(zhèn)財(cái)政來源可看出民運(yùn)糧對(duì)于邊防的重要性,將其所述列表4如下。

表4 嘉靖初年邊鎮(zhèn)收入來源細(xì)目
從表4可見,五鎮(zhèn)糧食來源中民運(yùn)糧占?jí)旱剐缘匚唬潜镜赝图Z的3倍有余,馬草數(shù)額也占據(jù)總額的接近一半。正如戶部官員在正德初年所分析的那樣:“各邊初皆取給屯糧,后以屯田漸弛,屯軍亦多掣回守城,邊儲(chǔ)始唯民運(yùn)是賴矣。而其派運(yùn)之?dāng)?shù)又多逋負(fù),故歲用往往不敷,乃以銀鹽濟(jì)之,舍此似無長(zhǎng)策。”(57)《明武宗實(shí)錄》卷三七“正德三年四月甲戌”條,《明實(shí)錄》第34冊(cè),第876頁。
另外,到嘉靖初年“銀鹽”補(bǔ)濟(jì)未有顯著增長(zhǎng),起伏也較大。如年例銀的開支,從《萬歷會(huì)計(jì)錄》的記載來看,在弘治、正德年間,供給北邊軍鎮(zhèn)的數(shù)額在40萬兩上下,只占邊鎮(zhèn)每年收入的10%左右。《明實(shí)錄》中對(duì)弘治末年供邊年例銀支出額的記載為“各邊先年除原派料草外,歲該送銀四十八萬兩”(58)《明孝宗實(shí)錄》卷一九二“弘治十五年十月辛酉”條,《明實(shí)錄》第32冊(cè),第3552頁。。到正德末年這一數(shù)額基本不變,“直至正德末年,通計(jì)各邊年例,亦止銀四十三萬兩,內(nèi)宣府十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十五萬兩,延綏三萬兩,寧夏四萬兩,甘肅六萬兩”(59)〔明〕 潘潢: 《會(huì)議第一疏》,《明經(jīng)世文編》卷一九八,《續(xù)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658冊(cè),第29頁。。嘉靖初年雖有所增加,但“猶止五十九萬”(60)〔明〕 陳于陛: 《披陳時(shí)政之要乞采納以光治理疏》,《明經(jīng)世文編》卷四二六,《續(xù)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661冊(cè),第498頁。。據(jù)《萬歷會(huì)計(jì)錄》對(duì)各邊鎮(zhèn)年例銀的發(fā)放記載進(jìn)行統(tǒng)計(jì),結(jié)果如圖3所示。

圖3 年例銀數(shù)量統(tǒng)計(jì)
由圖3可以觀察到,雖然年例銀的供給呈現(xiàn)逐漸上升的趨勢(shì),但在弘治、正德及嘉靖初年基本穩(wěn)定在40萬兩上下,并沒有顯著的提升。同樣,鹽法供邊數(shù)額亦未見上升,反而成化、弘治之際的納銀送司政策導(dǎo)致商屯逐漸消失。這使得在日漸形成以銀供邊政策的主導(dǎo)下,邊鎮(zhèn)米價(jià)逐漸走高,且波動(dòng)幅度日漸增大(圖4)。然而,邊鎮(zhèn)士兵所開糧餉卻并未隨之提升,反而所開月糧的折銀發(fā)放變成對(duì)官軍的再一次剝削。如弘治九年(1496年)時(shí),甘肅地方士兵月糧中一石糧折銀二錢五分發(fā)放,但隨著米價(jià)的上漲,每石糧食需六錢以上,這無形中增加了邊鎮(zhèn)士兵的生活壓力;又如弘治十六年(1503年)時(shí),遼東邊鎮(zhèn)米價(jià)平時(shí)銀一錢可換五至六斗糧,但遇到災(zāi)荒年份即漲至一錢僅換一斗的高物價(jià),而遼東將士的月糧折銀依然按照一石給二錢五分的標(biāo)準(zhǔn)發(fā)放,此中困苦可想而知。

圖4 邊鎮(zhèn)米價(jià)統(tǒng)計(jì)
漕糧的供邊也時(shí)有時(shí)無,并未形成制度規(guī)范。在旱災(zāi)之前,較大的漕糧輸邊有成化十年(1474年)浙江、江西漕折銀38萬兩運(yùn)邊供應(yīng)軍餉,成化二十年(1484年)將通州倉粟米30余萬石運(yùn)至大同,其余年份輸邊之?dāng)?shù)在20萬石左右,相較于另外三者供邊數(shù)額而言最低。
邊防開支的主要來源由邊鎮(zhèn)屯田向民運(yùn)糧轉(zhuǎn)變的同時(shí),因弘治末年明蒙貿(mào)易的中斷,雙方關(guān)系開始持續(xù)惡化,北方邊境軍事壓力上升,邊鎮(zhèn)的支出需求變得更加剛性。面對(duì)并不穩(wěn)定的民運(yùn)糧供應(yīng),弘治末年韓文就曾表達(dá)過深深的擔(dān)憂:
今太倉無數(shù)年之積,而冗食者加于前,內(nèi)帑缺現(xiàn)年之用,而給費(fèi)者日伺其后。征需已極而郡縣旱澇之不時(shí),輸送已窮而邊方請(qǐng)給之不已。顧后瞻前,朝不謀夕,萬一他日河流少止,漕運(yùn)遲誤,邊郡有警,軍餉空虛,則京儲(chǔ)求歲入三百七十萬之?dāng)?shù),固難猝至。邊餉須四百萬兩之銀,亦難遽集,不幸復(fù)加數(shù)千里之水旱通行賑貸,連十?dāng)?shù)萬之軍旅皆欲餉給,是時(shí)欲賦之民而民困已極,欲借之官而官帑已虛,不知又將何所取給哉。所謂又有可憂者,正以此也。(61)〔明〕 韓文: 《會(huì)計(jì)天下錢糧奏》,《明臣奏議》卷一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445冊(cè),第169頁。
正如韓文所擔(dān)憂的那樣,中國(guó)東部的季風(fēng)氣候?qū)е潞禎碁?zāi)害頻發(fā),這令以內(nèi)地民運(yùn)糧為主的供邊體系長(zhǎng)期處于一種不穩(wěn)定的狀態(tài)。為緩解此種不穩(wěn)定性,一方面明廷通過增加供給制度的彈性來予以應(yīng)對(duì),主要表現(xiàn)在鹽法的開中及之后的納銀、年例銀發(fā)放等措施上,配合民運(yùn)糧一起構(gòu)成供邊體系;另一方面明廷不斷維持軍鎮(zhèn)屯田生產(chǎn)以增加需求彈性。這種邊鎮(zhèn)供給體制的建立與運(yùn)轉(zhuǎn)涉及明代軍屯、鹽法、太倉收入及內(nèi)地民運(yùn)糧等多個(gè)方面。當(dāng)這些方面處于正常狀態(tài)時(shí),即便民運(yùn)糧因旱澇災(zāi)害而出現(xiàn)供應(yīng)不足的情況,其他幾項(xiàng)措施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給予彌補(bǔ)。但如前所述,到嘉靖初年整個(gè)體制內(nèi)各個(gè)環(huán)節(jié)均已存在極大隱患,在剛性需求增大而供給極不穩(wěn)定的情況下,對(duì)旱澇災(zāi)害等突發(fā)狀況非常敏感。當(dāng)嘉靖七年主要產(chǎn)糧區(qū)的江南地區(qū)和民運(yùn)糧供給區(qū)的北方諸省發(fā)生極端干旱時(shí),弊端叢生的供邊體系面臨崩潰,巨額負(fù)擔(dān)不得不轉(zhuǎn)嫁到中央財(cái)政之上,不得不尋求改變和革新。
革新追求的開源與政策調(diào)整能發(fā)揮作用的前提,是明朝此時(shí)國(guó)內(nèi)市場(chǎng)已逐漸發(fā)育,白銀日趨貨幣化、生產(chǎn)流通量變大。至嘉靖年間,全國(guó)性的徽商、晉商已開始嶄露頭角,商業(yè)的發(fā)展與國(guó)內(nèi)市場(chǎng)的發(fā)育為糧食等產(chǎn)品的商品性流通提供了條件。這期間白銀的逐步貨幣化,便是當(dāng)時(shí)商業(yè)高速發(fā)展的標(biāo)志之一。從征收金花銀開始,白銀隨著賦稅制度和鹽法的調(diào)整,在貨幣中的地位愈發(fā)鞏固。如萬志英所言:“1430年代中葉,當(dāng)政府表明它實(shí)際上接受白銀,白銀很快排擠其他貨幣,至1450年,白銀經(jīng)濟(jì)牢固確立起來……我們可以開始將其視為‘白銀經(jīng)濟(jì)’了。”(62)Richard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6, pp.76-79.到正德年間,太倉所儲(chǔ)已是錢一銀九,白銀成為明朝賦役征收和國(guó)家壟斷經(jīng)營(yíng)中重要的收入形式。(63)邱永志: 《“白銀時(shí)代”的落地: 明代貨幣白銀化與銀錢并行格局的形成》,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9年版。且當(dāng)時(shí)未納入官方統(tǒng)計(jì)的國(guó)內(nèi)白銀產(chǎn)量較官方統(tǒng)計(jì)數(shù)額為多,基本在民間市場(chǎng)流通。(64)楊煜達(dá)、[德] 金蘭中: 《明代云南銀礦生產(chǎn)的空間格局研究》,《歷史地理》第38輯,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9年版,第107—124頁。上述種種為革新提供了充分的實(shí)施條件。另外,嘉靖初年“大禮議”的結(jié)束,以及前述提及的極端干旱對(duì)嘉靖皇帝內(nèi)心的震動(dòng)也為革新創(chuàng)造了條件。
因此,為應(yīng)對(duì)嘉靖七年特別極端干旱所帶來的危機(jī),明廷必須且有條件做出相應(yīng)的改革措施,以增加國(guó)家所能掌控的錢糧數(shù)額,并通過市場(chǎng)的作用來緩解此次大旱引發(fā)的嚴(yán)重危機(jī)。在這樣一種作用機(jī)制下,嘉靖七年的大旱直接觸發(fā)了嘉靖革新大規(guī)模開啟。那么,過程又如何呢?
(二) 觸發(fā)革新的過程
具體觸發(fā)革新的仍是由旱災(zāi)導(dǎo)致的切實(shí)的財(cái)政危機(jī)。明廷必須且有條件做出相應(yīng)的改革措施,以增加國(guó)家所能掌控的錢糧數(shù)額,并通過市場(chǎng)作用來緩解此次嚴(yán)重危機(jī)。嘉靖七年十一月,明廷財(cái)政已面臨嚴(yán)重入不敷出的局面。也是從此時(shí)開始,時(shí)任工部尚書劉麟首先上奏要求駁回侍衛(wèi)軍旗官軍討要軍需的乞求,以節(jié)流財(cái)源。隨后負(fù)責(zé)鹽政的胡世寧、汪鋐、李佶及魏有本等與時(shí)任禮部尚書霍韜紛紛上疏,要求改革鹽法,以增加財(cái)政收入,達(dá)到開源目的。不久后,朝廷終于罷去乞求致仕多次的鄒文盛,任命更善理財(cái)?shù)牧翰臑閼舨可袝_革新的大幕。
隨著嘉靖八年正月的兩筆開支,太倉庫銀及內(nèi)帑存銀已所剩無幾,此后一整年極少再出現(xiàn)如上年那樣大規(guī)模的銀、鹽支出。而對(duì)于旱災(zāi)影響的持續(xù)及邊防軍事壓力的不斷加劇,戶部只能依靠拖延答復(fù)時(shí)間,乃至開具空頭支票,具體銀兩常以拖延數(shù)月亦不見到賬等方式進(jìn)行處理,甚至在直接關(guān)系王朝安危的邊防軍事需求上也如此行事。
以當(dāng)年軍事壓力最重的西北邊防為例。嘉靖八年初王瓊上奏稱:“虜眾駐套,勢(shì)必入寇,備御之策,理宜早定,集兵非難而饋餉為難。今陜西兇荒,斗米三錢,人不聊生,起運(yùn)稅糧盡行蠲免,沿邊倉庫空虛,官軍饑餒,又欲調(diào)集,饋餉缺乏,必致臨敵失事。”(65)⑤ 〔明〕 王瓊: 《北虜事跡》,《四庫存目叢書》子部第31冊(cè),齊魯書社1995年版,第13頁。請(qǐng)求“整理甘肅邊儲(chǔ)都御史劉天和前來陜西總督軍餉,令戶部發(fā)運(yùn)太倉庫銀并開中鹽課”⑤。但該上奏直到半年后才得到朝廷批復(fù)。面對(duì)緊迫的邊防巨額軍備需求,朝內(nèi)改革的呼聲再起,時(shí)任詹事府詹事霍韜、總督漕運(yùn)都督楊宏等紛紛歷陳積弊,乞求改革。這促使朝廷將改革伸向了久有積弊的漕運(yùn)、馬政等領(lǐng)域,并進(jìn)一步開始清查六部,想方設(shè)法擴(kuò)大財(cái)源,以補(bǔ)缺額。(66)參見《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八“嘉靖八年二月戊辰”“嘉靖八年二月庚午”“嘉靖八年二月壬申”“嘉靖八年二月壬午”“嘉靖八年二月丙戌”“嘉靖八年二月癸巳”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288—2292、2295、2312—2313、2320—2323頁。此次清查也頗有成效,僅工部便羅列出可節(jié)銀兩達(dá)數(shù)萬兩之多。(67)《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八“嘉靖八年二月甲午”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325—2327頁。所以到三月,當(dāng)總制三邊尚書的王瓊攜甘肅撫按官再次上疏言及軍餉匱乏,饑而不支的時(shí)候,上述改革舉措所得收入便被及時(shí)用于西北的邊防開支,準(zhǔn)發(fā)“太倉銀一十萬兩輸送陜西巡撫,并前所發(fā)備虜銀二十萬兩”(68)《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九“嘉靖八年三月壬子”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346頁。。但這其中的十一萬兩還有一部分源自“太倉收貯鹽價(jià),并折糧草等銀”(69)《明世宗實(shí)錄》卷九九“嘉靖八年三月壬子”條,《明實(shí)錄》第40冊(cè),第2346頁,又見〔明〕 梁材: 《發(fā)補(bǔ)河西災(zāi)免稅糧銀兩》,〔明〕 范欽等編: 《嘉靖事例》,《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51冊(cè),書目文獻(xiàn)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頁。,太倉庫銀隨即告竭。四月,巡撫都御史劉天和以調(diào)兵馬九千,駐防六月為因,再向戶部請(qǐng)求糧料草束共計(jì)折銀九萬九千二百二十五兩,戶部旋即以之前三月由王瓊奏討的一十萬兩中,除發(fā)給寧夏三萬兩、榆林二萬兩外,固原還少銀四萬九千二百二十五兩為由拒絕支付。后為籌措這筆款項(xiàng),戶部不得已只能東拼西湊,將上年(嘉靖七年)發(fā)給延安府屬所剩賑濟(jì)銀二萬五千兩充補(bǔ)軍費(fèi);又在布政司開納銀中,將除賑濟(jì)寧夏的五千兩外所余見在銀兩酌量動(dòng)用,以補(bǔ)軍費(fèi)。以上兩筆開支均是從之前賑濟(jì)開支之中擠出,戶部已無銀可出。正如梁材所言,此時(shí)“太倉銀庫所積有限,而內(nèi)外支用為費(fèi)不貲”(70)〔明〕 梁材: 《議覆陜西事宜疏》,《明經(jīng)世文編》卷一〇五,《續(xù)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656冊(cè),第336頁。。
面對(duì)再一次的財(cái)政枯竭,改革的觸角伸向清查勛戚莊田之上。(71)《明世宗實(shí)錄》卷一〇〇“嘉靖八年四月甲戌”條,《明實(shí)錄》第41冊(cè),第2369—2370頁。隨后又將清查范圍擴(kuò)大到御馬監(jiān),以增財(cái)源。(72)《明世宗實(shí)錄》卷一〇一“嘉靖八年五月己酉”條,《明實(shí)錄》第41冊(cè),第2393頁。同時(shí),梁材集中上奏表彰湖廣地區(qū)的積極義賑行為,以此鼓勵(lì)民間義賑,來彌補(bǔ)政府在賑濟(jì)上的力不從心。(73)〔明〕 梁材: 《褒勵(lì)義民》《議處荊襄荒政》,〔明〕 范欽等編: 《嘉靖事例》,《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51冊(cè),第179、182頁。這一系列舉措為之后在延綏、大同的軍事活動(dòng)提供了一部分應(yīng)對(duì)的錢糧。所以待到五月,延綏、寧夏兩鎮(zhèn)大兵“共三萬之?dāng)?shù)”(74)〔明〕 王瓊: 《北虜事跡》,《四庫存目叢書》子部第31冊(cè),第14頁。,在陸續(xù)開拔至定邊營(yíng)—花馬池一帶集結(jié)的前幾天,戶部從巡撫都御史翟鵬之奏,以大虜在套與花馬池等處調(diào)集兵馬為由,又“發(fā)太倉銀四萬兩于寧夏鎮(zhèn)預(yù)備軍餉”(75)《明世宗實(shí)錄》卷一〇一“嘉靖八年五月壬子”條,《明實(shí)錄》第41冊(cè),第2394頁。,兩天之后又“發(fā)太倉銀五萬兩于大同鎮(zhèn)接濟(jì)邊餉”(76)《明世宗實(shí)錄》卷一〇一“嘉靖八年五月甲寅”條,《明實(shí)錄》第41冊(cè),第2394頁。。七月戶部又撥“五萬付都御史劉天和,于要害城堡糴買本色,專備動(dòng)調(diào)人馬”(77)《明世宗實(shí)錄》卷一〇三“嘉靖八年七月丙午”條,《明實(shí)錄》第41冊(cè),第2426頁。。然而戶部經(jīng)過此次撥銀后,太倉庫銀兩又所剩無幾,先前王瓊等人在正月所奏乞銀兩一事只能靠?jī)?nèi)帑“發(fā)銀十萬兩”給予解決。(78)〔明〕 王瓊: 《北虜事跡》,《四庫存目叢書》子部第31冊(cè),第13頁。發(fā)銀十萬兩之事,參見《明世宗實(shí)錄》卷一〇三“嘉靖八年七月丙午”條,《明實(shí)錄》第41冊(cè),第2426頁,“以大虜在套,姑準(zhǔn)發(fā)帑銀十萬兩給之”。
從梁材七月十一日指責(zé)邊將所需無度的題本中,可看出此時(shí)戶部確已無銀的窘?jīng)r:“今歲撥去官銀二十五兩,計(jì)其到鎮(zhèn)不過兩三個(gè)月,縱使動(dòng)調(diào)三萬人馬,計(jì)其行糧草料所支亦有常數(shù),豈得遽至缺乏?正該悉聽都御史劉天和便宜區(qū)處,以備御虜支用,豈知還撫官不遵本部題奉明旨,擅以折放官軍月糧。以此觀之,歲用之?dāng)?shù)通不追征,而每年惟以虜賊在套,請(qǐng)乞內(nèi)帑為詞,再使發(fā)去銀鹽,又將以充歲用,年復(fù)一年,豈有以有限之財(cái)填無窮之壑……內(nèi)帑所發(fā)為一時(shí)應(yīng)變之宜,邊儲(chǔ)國(guó)計(jì)責(zé)在兩全,非本部出納之太吝也。”(79)〔明〕 梁材: 《議給陜西邊餉》,〔明〕 范欽等編: 《嘉靖事例》,《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51冊(cè),第132頁。此后,面對(duì)錢糧已罄的危局,朝廷的改革方向開始從應(yīng)急性、臨時(shí)性向長(zhǎng)期性、穩(wěn)定性方面轉(zhuǎn)移。在節(jié)流方面,暫停蘇松杭織造開支(80)《明世宗實(shí)錄》卷一〇三“嘉靖八年七月丁巳”條,《明實(shí)錄》第41冊(cè),第2431頁。,并進(jìn)行大范圍裁員(81)《明世宗實(shí)錄》卷一〇四“嘉靖八年八月丁丑”條,《明實(shí)錄》第41冊(cè),第2446頁。,以求減少開支。開源方面,重新開啟了召商納糧輸邊之法以充邊備(82)萬歷《大明會(huì)典》卷三二《鹽法》,廣陵書社2007年版,第563頁。,同時(shí)推行余鹽制度以擴(kuò)大白銀收入,并下令增加靈州大小鹽池的開采額度以供王府開支。(83)《明世宗實(shí)錄》卷一〇七“嘉靖八年十一月乙卯”條,《明實(shí)錄》第41冊(cè),第2537頁。
綜上所述,在嘉靖七年年底財(cái)政已經(jīng)出現(xiàn)透支,而隨著嘉靖八年干旱的持續(xù),九邊不斷遭遇騷擾,致使整個(gè)邊防供應(yīng)體系面臨崩潰,明廷面對(duì)著巨大的財(cái)政赤字壓力和邊防危機(jī)。這種內(nèi)外交困的局面,促使明廷從嘉靖七年十一月開始,逐步討論改革的相關(guān)事宜,而變革的內(nèi)容也從臨時(shí)性轉(zhuǎn)向長(zhǎng)期性的制度層面,從而將數(shù)年來艱難推行的改革一舉進(jìn)行。可以說,嘉靖七年的特別極端干旱是促成革新加速進(jìn)行的一個(gè)重要因素,不可忽視。
四、 總 結(jié)
對(duì)歷史時(shí)期氣候變化及其影響的研究需要關(guān)注自然與社會(huì)系統(tǒng)間的作用機(jī)制。這要求在論述過去氣候變化的社會(huì)影響時(shí),先還原氣候變化,再以此為基礎(chǔ)分析其影響過程、途徑和機(jī)制。氣候變化對(duì)于整個(gè)社會(huì)的影響一方面取決于其本身劇烈程度,另一方面取決于當(dāng)時(shí)的具體社會(huì)情況。其中,歷史時(shí)期極端氣候事件作為氣候變化中的一部分,因其要素量值或統(tǒng)計(jì)量顯著偏離平均態(tài)且超出觀測(cè)或統(tǒng)計(jì)量特定閾值,對(duì)社會(huì)的影響更為劇烈。
嘉靖七年的特別極端干旱事件是明朝北方地區(qū)最為嚴(yán)重的五次大旱之一,席卷當(dāng)時(shí)幾乎整個(gè)北方地區(qū),并波及湖廣、南直隸及兩廣地區(qū),受災(zāi)面積達(dá)9省,以山東、山西、陜西、河南等地尤其嚴(yán)重。大旱所引起的蝗災(zāi)更是令北方各省歉收、絕收,人相食的慘劇在多地發(fā)生。而此次大旱又發(fā)生在諸多制度弊端沉積已久,制度彈性極差的嘉靖初年。社會(huì)對(duì)大旱的應(yīng)對(duì)力異常之弱,使災(zāi)害的破壞力顯得格外強(qiáng)大。首當(dāng)其沖的便是財(cái)政體制,并集中表現(xiàn)在供邊問題上。邊防對(duì)稅糧的剛性需求本就很大,為應(yīng)對(duì)嘉靖七年的大旱而蠲免的稅糧超過全年稅糧總額的一半,其中民運(yùn)糧占了很大比例,使本就脆弱且不穩(wěn)定的供邊體系隨即崩潰。財(cái)政因賑濟(jì)與邊防兩項(xiàng)巨額開支出現(xiàn)嚴(yán)重赤字,使嘉靖七年年底已至無銀可用的境地。明廷不得不采取緊急措施。
另外,伴隨著嘉靖初年國(guó)內(nèi)市場(chǎng)的發(fā)育和白銀貨幣化的趨勢(shì),前期的社會(huì)狀況已使此時(shí)明廷通過革新開源白銀、滿足國(guó)家需求變得順理成章。再加上“大禮議”的結(jié)束和嘉靖皇帝自己的心理作用,革新由此出現(xiàn)。因此,嘉靖七年大旱通過觸發(fā)財(cái)政危機(jī),使嘉靖八年出現(xiàn)了“危機(jī)—改革—短期收益—開支—危機(jī)—再改革”的數(shù)次循環(huán),由此在開啟革新方面扮演了催化劑的角色。
嘉靖初年的革新在一定程度上清理了長(zhǎng)久以來的弊端陋規(guī),其中更具長(zhǎng)遠(yuǎn)影響意義的是進(jìn)一步推動(dòng)了貨幣白銀化且鞏固了白銀在國(guó)家供需中的地位。然而,在國(guó)家無法有效控制白銀數(shù)額且供邊愈發(fā)依賴市場(chǎng)的情況下,此舉雖暫時(shí)緩解了危機(jī),但無疑為之后應(yīng)對(duì)同等級(jí)別的干旱事件埋下了深深的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