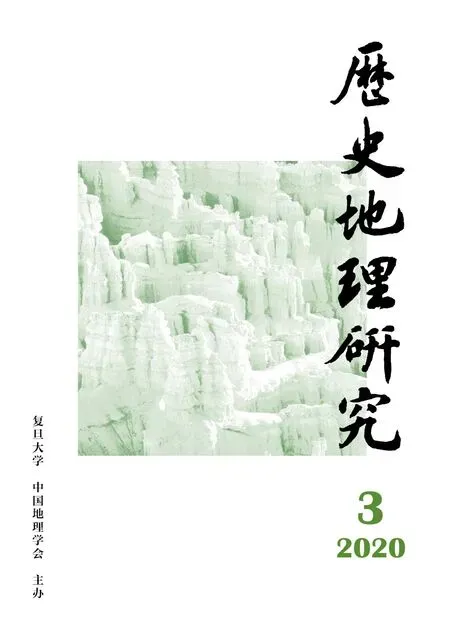南京博物院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藏本之詮注
闕維民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北京 100871)
1949年以來,有關利瑪竇世界地圖的已有研究成果,尚無探討南京博物院利氏《坤輿萬國全圖》藏本(以下簡稱“南博本”)(圖1)的專文。本文從8個方面略述“南博本”的公展記錄、摹本比較、現有刊版、圖幅尺寸、成圖形式、成圖底版、摹繪底本、獨特價值。
一、 公 展 記 錄
“南博本”于1922年入藏北京歷史博物館,1933年尚存于北平歷史博物館(1)《北平歷史博物館藏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1933年第45期第1版(前2幅)、2版(中2幅)、第46期第2版(后2幅)。,1936年前(2)洪煨蓮: 《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禹貢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1—50頁。移藏至南京中央博物院,即今南京博物院。
1923年4月13—15日,“南博本”公展于北京故宮午門大殿,這是該圖首次公布并展出。此消息最先由中文刊物《時報》(3)《利瑪竇所繪地圖之陳列》,《時報》1923年4月14日,第4版。報道,其后《圣教雜志》(4)《利瑪竇在華所撰繪之地圖》,《圣教雜志》1923年第12卷第6期,第277—278頁。《青年友》(5)《三百年前之古地圖: 明萬歷年間舊物,利瑪竇在華所撰繪》,《青年友》1923年第3卷第5期,第11頁。《史地學報》(6)《三百年前之古地圖利瑪竇在華所撰繪》,《史地學報》1923年第2卷第5期,第14—15頁。按: 該刊轉載時將“十三、四、五等日”誤為“十三、四、五等月”。相繼轉載(文字略有出入)。這份報道在有關利氏世界地圖的所有研究成果中迄今未被引述,故錄《時報》載《利瑪竇所繪地圖之陳列》全文如下:
近世天文大家利瑪竇氏于明萬歷年間,由歐來華,現在極負盛譽之上海徐家匯天文臺,即為該氏及徐光啟諸人所手創遺留迄今者。聞日昨午間歷史博物館(7)“查《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十八度工作報告》,謂舊藏本系于民國十二年訪獲入藏”。參見曹婉如、薄樹人、鄭錫煌等: 《中國現存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文物》1983年第12期。得該氏摹繪“世界坤輿全圖”六幀,一幅長七尺寬三尺,圖作球形,經緯度數俱全,各地均附注解,五色絢爛,古雅可愛。第一幅及第五幅有該氏題句,款(8)“款”,《圣教雜志》與《青年友》誤為“欵”。用大明萬歷壬寅年(距今三百余年),他幅復有李之藻祁光宗等跋語。李等與氏為摯友,亦科學界著名之士也。圖中南北亞墨利加洲已標出,而所述則為印地安土人之生活,蓋氏作圖時,約后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八九十年,而距合眾建國時期,固甚遠也,其他歐洲諸國譯名,均與今大異,中國幅員亦不相同,如滿洲東三省之地,統標名女直(9)圖上標為“女直”,《時報》原錄,但《史地學報》《圣教雜志》與《青年友》均稱“女真”。,黃海稱為大明海,此其尤顯著者,圖內海洋空隙,繪有怪異魚類多種,陸地則加繪猛禽厲獸若干,狀貌悉猙獰可畏,大抵現時滅種者居多,大洋中復間繪十六世紀船只十余艘,作乘風掛帆之狀,形式雖不一,均奇特出人意表。此圖原在廠肆某古玩鋪(10)經查,“民國十一年悅古齋鋪主韓德盛收購一利瑪竇繪制的《坤輿萬國全圖》,旋經人介紹賣給了北平歷史博物館。‘九一八’事變后,此圖運往南京”。參見曹婉如、薄樹人、鄭錫煌等: 《中國現存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文物》1983年第12期。,為某外人所見,將購送海外,有成議矣,該館據北京教育會會員孫君報告,急俛(11)按: 《圣教雜志》作“挽”,《青年友》作“浼”。人向某鋪磋商,以重值購得。現定于十三、四、五等日河南賑災會(12)檢索民國期刊,1923年中國的賑災省份有山西、廣東(汕頭)、陜南而無河南,故此處“河南賑災會”疑為“陜南賑災會”。期內,懸掛午門大殿,供人觀覽。并函商前意大利公使錢念劬君,請將其舊(13)原文為“售”,據《史地學報》《圣教雜志》與《青年友》更正為“舊”,即“舊”。藏利瑪竇氏繪像,暫借該館,與地圖一同張掛,以引起參觀人興趣,且寓表揚前賢之意。錢君已函復照辦。想屆期前往參觀者,必不在少數也。
自1924年首次公展以來,“南博本”曾多次在國內外展出。據檢索,國外展出記錄有: 1988年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史博物館的“中國五千年的發明與發現”(Chine Ciel et Terre 5 000 Ans d’inventions et de decouvertes)(14)John D. Day,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 of Matteo Ricci’s Maps, Imago Mundi, 1995, Volume 47, Issue 1, pp.94-117, Note 16.展、2014年6月27日—10月19日英國愛丁堡蘇格蘭國家博物館的“明朝: 黃金帝國”(Ming: The Golden Empire)展、2014年9月18日—2015年1月5日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的“明: 盛世皇朝50年”(Ming: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展(15)秦川: 《英國兩大博物館舉辦明代文物展》,《中國日報》中文網[2014-8-12], http: / /language.chinadaily.com.cn /bbc /ent /2014-08 /12 /content_18293618.htm。(該展主要闡述1400—1450年改變中國的50年歷史(16)郭婷、徐立恒: 《反思燦爛和多元的時代——回顧大英博物館明代大展“1400-1450: 改變中國的50年”》,《書城》2015年第4期。按: 成圖于1608年的《坤輿萬國全圖》何以隨展不詳。)。國內展出記錄有: 2019年4月16日—6月16日浙江美術館館慶10周年的“心相·萬象——大航海時代的浙江精神”(17)《“心相·萬象”大航海時代的浙江精神群展》,雅昌展覽[2020-05-01],https://exhibit.artron.net/exhibition-63279.html。特展。2020年6月19日—8月23日中國絲綢博物館“一花一世界: 絲綢之路上的互學互鑒”(18)本文即應中國絲綢博物館為此展之約而撰。展。
二、 摹 本 比 較
現存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藏本有刻印本與摹繪本(包括“刻印+摹繪本”),迄今已知世界各地所藏摹繪本共有9份:“南博本”,南京博物院藏本(彩繪,1—6幅);“首大本”,韓國首爾大學藏本(彩繪,1—8幅)(19)《〈坤輿萬國全圖〉(彩繪)韓國漢城大學藏本》,黃時鑒、龔纓晏: 《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頁。;“大阪本”,日本大阪北村芳郎藏本(彩繪,1—8幅)(20)《〈坤輿萬國全圖〉(彩繪)日本大阪北村芳郎藏本》,黃時鑒、龔纓晏: 《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第151頁。;“凱達爾本”,美國凱達爾捕鯨博物館藏本(Kendall Whaling Museum)(彩繪,僅第3幅)(21)John D. Day,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 of Matteo Ricci’s Maps, Imago Mundi, 1995, Volume 47, Issue 1, p.95.;“理格本”,法國人理格(G. Nicolas)藏本(彩繪,1—6幅)(22)此圖現只轉載于德禮賢《利瑪竇神父的中文世界地圖》一著所附黑白照片,《〈坤輿萬國全圖〉(彩繪)理格藏本》,黃時鑒、龔纓晏: 《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第153頁。;“國圖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彩繪,僅第4幅)(23)《坤輿萬國全圖局部(中國部分)》《坤輿萬國全圖局部(東亞部分)》,曹婉如、鄭錫煌、黃盛璋等編: 《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頁。注: 該圖集未標注為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通常被誤導為南京博物院藏本,如《南京版坤圖上的船》(黃時鑒、龔纓晏: 《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第154頁),實際為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龔纓晏也已指出了這一問題(龔纓晏: 《關于彩繪本〈坤輿萬國全圖〉的幾個問題》,張曙光、戴龍基主編: 《駛向東方》,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223—239頁)。;“奉先寺本”,韓國奉先寺藏本(彩繪,1—8幅;已毀,首爾大學奎章閣存有黑白照片(24)楊雨蕾: 《〈坤輿萬國全圖〉朝鮮彩色摹繪本及相關問題》,《歷史地理》第29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36—343頁。,韓國實學博物館藏有復原圖(25)趙敏住: 《明清西方天文學對朝鮮時期地球研究的影響及其視覺表達: 以韓國所藏〈坤輿萬國全圖〉為中心》,《中國美術研究》2019年第4期。);“魯德曼本”,美國魯德曼古地圖商店49843號(彩繪,僅第1、6兩幅)(26)龔纓晏、梁杰龍: 《新發現的〈坤輿萬國全圖〉及其學術價值》,《海交史研究》2017年第1期。按: 據魯德曼商店網站顯示該地圖目前已售出。;“歷博本”,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本(墨線仿繪,1—6幅)(27)《〈坤輿萬國全圖〉(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墨線仿繪本)》,曹婉如、薄樹人、鄭錫煌等: 《中國現存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文物》1983年第12期。。比較分析9份藏本,可獲以下幾點結論:
(1) 所有摹繪本均有不同程度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圖版拼幅(6幅與8幅之異)、圖識圖說(圖面布局之異)、圖面文字(缺漏變更之異)、圖本內容(陸域或島嶼的大小缺漏之異)等幾個方面。
洪煨蓮認為“意大利人理格君所存之繪本和歷史博物館原藏之本盡相同”(28)“北平交民巷臺吉廠理格洋行之主人,意大利理格先生(G. Nicolas)亦藏有彩色舊繪本一圖。承他示我以十分清晰的照片。我見得原圖第四幅的上端紙頗殘缺,然其圖中所寫的文字,所繪的地形,和船,魚,禽,獸,等等,全與歷史博物館之原圖一致。理格君且告我: 他的原圖之尺寸,設色,盡與博物館本相同。因此,我姑定: 這兩圖同屬一個時代,且同出于一源,不必請他費神去取原圖相示,亦未嘗向他借照片來研究。”洪煨蓮: 《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禹貢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3、27頁。,即指“南博本”與“理格本”完全相同,但比較兩圖還是可以分辨出差異。主要差異之處是第4條幅“地南極線”上方圓圈內“看北極法”的文字排列形狀,“南博本”呈近正四方形,而理格本呈矩形。事實上由于摹繪本是手工摹繪,摹繪本與被摹繪之本、各摹繪本之間多少都會出現差異之處,當屬正常現象。
(2) 除“歷博本”為墨線仿繪本外,其余8份均為彩繪本。
(3) 除“凱達爾本”與“國圖本”兩藏本外,其余7份均為完整藏本。
(4) 所有藏本中,“南博本”保存最善、品相最佳,地理內容及圖題圖識與1602年李之藻的刻印本最為接近。
(5) 在7份完整藏本中,除“南博本”與“歷博本”(墨線仿繪“南博本”)兩藏本外,其余5份藏本均有版識:“錢塘張文燾過紙 萬歷壬寅孟秋日”,相當于今天正式出版書籍版權頁標明的出版印刷單位與出版日期。“過紙”,是木刻印刷過程中一道重要技術工序的術語,包括把握刻版的上墨深淺、調試印紙與刻版的吻合程度等,在裱畫、繪畫與拓碑前對紙張也有類似的整理工序(29)闕維民: 《倫敦本利氏世界地圖略論》,北京大學歷史地理中心編: 《侯仁之師九十壽辰紀念文集》,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325頁。,可以解釋為今天的“刊印”。“南博本”不用1602年的“過紙”版識,正說明其版是1608年呈貢萬歷皇帝的原圖。
三、 現 有 刊 版
“南博本”1923年首次展出后不久《東方雜志》即以三整頁的篇幅刊載了全圖(30)《利瑪竇之坤輿全圖》,《東方雜志》1923年第20卷第9期。,對此圖的各種學術研究也由此開啟,尤其激發了中國學術界對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熱情。
《東方雜志》刊載之后,隨著對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逐步開展,“南博本”又被多次刊載引用,分別為: 1928年,法國傳教士裴治堂的研究小冊《北京歷史博物館所藏利瑪竇之世界地圖》附圖(31)[法] 裴治堂(化行 Henri Bernard): 《北京歷史博物館所藏利瑪竇之世界地圖(法文)》,北京政聞報出版社1928年版(Augustin Bernard, La Mappemon de Ricci au Musée Historique de Pékin, Collection de la Politique de Pékin, 1928)。“冊子內附有一小張縮影歷史博物館藏圖”,參見洪煨蓮: 《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禹貢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5頁,尾注17。;1933年,《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的分幅刊載(32)《北平歷史博物館藏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1933年第45期第1版(前2幅)、2版(中2幅)、第46期第2版(后2幅);分幅刊載。;1938年,德禮賢著《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之附圖(33)Pasquale M. d’Elia, Il Mappamondo di Cinese dell P. Matteo Ricci, S. J., Rome: Vatican Library, 1938, Fig.29 (Copied by John D. Day,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 of Matteo Ricci’s Maps, Imago Mundi, 1995, Volume 47, Issue 1, pp.94-117. Fig.3).;1940年,《東方畫刊》刊圖(34)《中國第一部世界地圖: 坤輿萬國全圖》,《東方畫刊》1940年第3卷第8期,第6頁。;1983年,研究論文附圖(35)《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南京博物院藏彩色摹本)》,曹婉如、薄樹人、鄭錫煌等: 《中國現存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文物》1983年第12期。;1995年,《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刊圖77(36)曹婉如、鄭錫煌、黃盛璋等編: 《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第77頁。;1988年,《中華古地圖珍品選集》圖92(37)中國測繪科學研究院編纂: 《中華古地圖珍品選集》,哈爾濱地圖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127頁。;2004年,《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圖版四(38)黃時鑒、龔纓晏: 《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圖版四。。
上述所有“南博本”的刊載本,以1988年《中華古地圖珍品選集》的刊載圖最為清晰,色彩度最接近于原圖。
四、 圖 幅 尺 寸
關于“南博本”的圖幅尺寸,據筆者檢索,共有五種記錄(縱×橫,厘米): ① 192×675; ② 168.7×380.2(39)“縱168.7厘米,通幅橫380.2厘米”,見曹婉如、薄樹人、鄭錫煌等: 《中國現存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文物》1983年第12期;“高168.7厘米,通件長380.2厘米”,見黃時鑒、龔纓晏: 《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第147頁;“高168.7厘米,通幅長380.2厘米”,見龔纓晏、梁杰龍: 《新發現的〈坤輿萬國全圖〉及其學術價值》,《海交史研究》2017年第1期。; ③ 168×382(40)“縱168厘米,橫382厘米”,見《九大博物館入選〈國家寶藏〉的27件國寶》,搜狐網[2017-12-04],https://www.sohu.com/a/208257382_488370。; ④ 192×380.2(41)“縱192厘米、橫380.2厘米”,見龐鷗: 《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中國測繪》2002年第5期;“縱一百九十二厘米、橫三百八十點二厘米的整幅”,見萬方、周宏偉: 《中國古地圖——坤輿萬國全圖》,《書屋》2006年第12期。; ⑤ 192×346(42)“縱橫192厘米×346厘米”,見孫果清: 《利瑪竇在中國編制的“世界地圖”》,《地圖》2008年第5期;“縱192厘米,橫346厘米”,見《〈坤輿萬國全圖〉說明》,中國測繪科學研究院編纂: 《中華古地圖珍品選集》,第126—127頁。。
記錄①為1923年中文《時報》記錄:“……六幀,一幅長七尺寬三尺”(43)《利瑪竇所繪地圖之陳列》,《時報》1923年4月14日,第4版;《利瑪竇在華所撰繪之地圖》,《圣教雜志》1923年第12卷第6期,第277—278頁;《三百年前之古地圖: 明萬歷年間舊物,利瑪竇在華所撰繪》,《青年友》1923年第3卷第5期,第11頁;《三百年前之古地圖利瑪竇在華所撰繪》,《史地學報》1923年第2卷第5期,第14—15頁;《利瑪竇之坤輿全圖》,《東方雜志》1923年第20卷第9期。,洪煨蓮解釋:“可惜我未得繪本之尺寸。據《東方雜志》影圖后之說明云:‘寬三尺,高六尺’。此尺如為營造尺則是192×96 cm。不知這是如何量的。我疑繪本和李之藻刻本大小相同。”(44)洪煨蓮: 《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禹貢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1—50頁,尾注146。
筆者認為“……六幀,一幅長七尺寬三尺”,當作“……六幅,每幅長七尺、寬三尺”解,這樣整幅地圖的尺寸即為: 縱7尺、橫6×3尺,即: 縱192厘米、橫675厘米。
由于原圖有裱襯底紙,而裱襯底紙的寬度往往大于原圖,因此,原圖尺寸與裱襯底紙尺寸的量算結果,往往存在差異。記錄①中的橫675厘米遠大于后4種記錄的原因,應當是量算6幅裱襯底紙寬度之和的結果。
以《時報》“……六幀,一幅長七尺寬三尺”為據推測:“南博本”在1922年入藏北京歷史博物館是6分幅,1923年4月在午門展出時,將6分幅裱合成完整一幅。而墨線仿繪“南博本”的“歷博本”,分為6幅收藏(45)《〈坤輿萬國全圖〉(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墨線仿繪本)》,曹婉如、薄樹人、鄭錫煌等: 《中國現存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文物》1983年第12期,第61頁。,可作旁證。
在未實際量算的情況下,筆者傾向于出自南京博物院管理人員(46)在《中國現存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文物》1983年第12期)一文的作者中,有曹者祉,時為南京博物院副院長。約翰·D·戴在其文(John D. Day,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 of Matteo Ricci’s Maps, Imago Mundi, 1995, Volume 47, Issue 1, pp.94-117)尾注20、22、23中的“Cao Zhefu (Nanjing Museum)”,當為“Cao Zhezhi曹者祉”之誤。的記錄(記錄②),縱168.7厘米、橫380.2厘米。
五、 成 圖 形 式
在有關利瑪竇世界地圖的已有研究成果中,多少都涉及利氏世界地圖的成圖刻板、成圖顏色、成圖材質、成圖方式。具體如下:
1. 成圖刻版
成圖刻版主要分為石刻底版與木刻底板,未發現金屬刻板。石刻底版有1598—1598年間趙可懷在蘇州的石刻《山海輿地圖》,既是石質地圖,也是拓圖的底版。木刻底版共有5版: 第一版為《輿地山海全圖》(肇慶,1584年,王泮刻板);第二版為《山海輿地全圖》(南京,1598年(47)湯開建、周孝雷: 《明代利瑪竇世界地圖傳播史四題》,《自然科學史研究》2015年第3期。按: 普遍認為是1600年,湯開建、周孝雷經考證認為是1598年。,吳中明刻板);第三版為《坤輿萬國全圖》(北京,1602年,李之藻刻板);第四版為《兩儀玄覽圖》(北京,1603年,李應試刻板)(48)Pasquale M. d’Elia, Recent discoveries and new studies (1938-1960) on the World Map in Chinese of Father Matteo Ricci S.J., Monuments Serica, 1961, Volume 20, Issue 1, pp.82-164.注: d’Elia僅列前四版。;第五版為《坤輿萬國全圖》(北京,1608年,梓人秘造本(49)張宗芳: 《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考》,《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1933年第46期第2版;第47、48期第2版、第50、51、52、53、54期第2版。)。
2. 成圖顏色
成圖顏色主要分墨色和彩色。墨色,包括2種形式: 木刻版墨印(如梵蒂岡教廷圖書館的1602年李之藻刻印藏本)與墨色摹繪(如“歷博本”即為墨線仿繪藏本)。彩色,包括3種形式: 木刻版彩印(尚無實例)、“木刻版墨印+彩繪”(如遼寧省博物館《兩儀玄覽圖》藏本)與彩色摹繪(如“大阪本”)。
3. 成圖材質
成圖材質主要有三種。紙質: 凡用紙張進行墨(彩)色木刻版印、石版拓印或摹繪而成的圖,其材質均為紙質(絕大多數利氏世界地圖現存藏本的材質為紙質)。絹質: 凡用絹進行墨(彩)色木刻版印、石版拓印或摹繪而成的圖,其材質均為絹質(絹質利氏世界地圖尚無實例,但有史料記載證明其或曾存在(50)利瑪竇《入華記錄》:“皇帝自內廷下諭,令備六幅世界地圖絹本十二付”,轉引自洪煨蓮: 《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禹貢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25頁。)。石質: 凡用石進行刻繪而成的圖,其材質即為石質(如前述蘇州的石刻《山海輿地圖》)。
4. 成圖方式
成圖方式主要是三種形式。刻印,即用紙或絹,在木刻或石刻版上墨(彩)印或拓印而直接成圖的方式;摹繪,即在紙或絹上,進行墨(彩)色摹繪而直接成圖的方式;“刻印+摹繪”,即先刻印成墨色底圖,再墨色或彩色添繪而分步驟成圖的方式。
“南博本”為利氏世界地圖的木刻第五版,即該圖以殘留的刻工私刻底版為主體并加補刻而墨色印刷成底圖,再在底圖上彩繪圖像而成圖(詳見下節)。即: 該圖中的線條與墨色文字均為刻版墨色印刷而成,然后在需要的部分渲染設色,書繪彩色文字;圖中的繪畫圖像(10艘海船、8頭陸生動物與15條海洋動物)其顏色當由制圖者挑選,但據構成圖像輪廓的、粗細均勻且清晰明辨的線條,可以推測該圖是在木刻版墨色印制的基礎上再經彩色描繪而成的。倫敦英國地理學會的《坤輿萬國全圖》藏本雖然沒有彩繪圖像,但圖上的彩色部分也是在木刻版墨色印制的基礎上再經彩描而成(51)闕維民: 《倫敦本利氏世界地圖略論》,北京大學歷史地理中心編: 《侯仁之師九十壽辰紀念文集》,第314—325頁。。確切地講,“南博本”不是純粹的摹繪本或“彩色繪本”(52)洪煨蓮: 《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禹貢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3頁。,不是彩繪絹本(53)鄒振環: 《神和乃囮: 利瑪竇世界地圖的在華傳播及其本土化》,《安徽史學》2016年第5期。注: 感謝鄒先生相告:“我把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與南懷仁《坤輿全圖》兩者的彩繪本混淆了,后者有彩繪絹本。”或彩色絹本(54)鄒振環: 《殊方異獸與中西對話——〈坤輿萬國全圖〉中的海陸動物》,《海洋史研究》2015年第1期。,也不是純粹的木刻印本,而是木刻墨印+彩色摹繪的紙質本。
六、 成 圖 底 版
關于“南博本”的成圖底版,有利瑪竇本人的兩份史料可資考證。一份是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七月十三日利氏寄羅馬耶穌會總監信(55)“今年年初,有以世界大地圖獻皇帝者。皇帝欲印多本。然原板已不在京,而副版已毀。于是有旨召竇,命竇印若干本。諸太監既知竇無版可印,則大懼,恐皇帝不肯信也,竇告以如得一月期限,愿別刻一更佳之本以應。諸太監具以覆奏。然皇帝不欲使竇破費,乃命彼等依照原樣,在宮中刻版。既就,印本遂滿全宮”。洪煨蓮: 《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禹貢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期,第24頁。;另一份是利氏《入華記錄》的記事之一(56)利瑪竇的《入華記錄》:“一日皇帝有旨召吾等,其急。利瑪竇及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二神甫既至靈臺諸太監住所,見掌印太監及其他近侍等,頗甚張皇。皇帝自內廷下諭,令備六幅世界地圖絹本十二付,蓋指昔李我存在京所印之本。此圖利神甫所制,每付共六幅,幅寬如肘之長,高過其倍,印就,裝裱之如紙窗,系其邊以帶,使可舒合,置于室中。圖中有利瑪竇神甫之名,太監之給役內廷者,或指以示皇帝,故命就利神甫取圖也。諸神甫曾以世界地圖多付贈太監若干人。此中不知何人竟以一付添繪彩色,而獻之于皇帝。皇帝見此佳制,繁列眾國,廣載異俗,中國人前此所未見者也,則大悅;故欲多圖,殆擬以分賜皇太子及其他親族者也。諸神甫未曾以此圖獻皇帝,且亦未嘗欲他人為之,蓋深恐皇帝或將誤會圖中中國所占地位之小,而以為吾等有意侮辱中國也。中國人素以為中國占天下之大半,中國士人且多謂吾等縮中國,伸外邦,而引以為憾者矣。然皇帝固自聰明,彼知此圖所繪者實得世界名地大小之真,非有意輕視中國也。此本地圖曾兩度刻于北京,二本盡相同。一本為李我存所刻,李回籍時已將版片帶去。又一本乃刻工等所刻,印之以求售,所賣印本頗多,且得善價。然北京大雨之年此本版片適在一舊屋中,夜中屋塌,壓斃工人二,且毀其板焉。諸太監聞此,知不能應皇帝命,則又疑吾等言妄,既遣四人至吾等住所再詢,復派人至刻工處取零碎版片之尚存留者,以為證。吾人之天主教徒李保祿曾刻八幅而更大之地圖。吾等亦遣取此版至。然諸太監不敢以此本獻皇帝。皇帝所指索者非此本,而兩本中之注釋亦間有不同也。彼等不知所為,躊躇不決者兩三日。吾等乃告以愿得一月期限,自費別刻一更佳之地圖,吾等意欲于圖中多加若干更有益于天主教之宣傳也。諸太監聞此,甚喜,即具以所聞奏復。然皇帝雅不欲多擾吾等,遂命就舊有之板,補刻以成六幅之世界地圖,此事旋即辦妥;其后宮內所需之地圖,即在宮內印之”。洪煨蓮: 《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禹貢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期,第25頁。。兩份史料均收錄在《利瑪竇全集》(57)Opere stortche del P. Matteo Ricci, S. I., edite a cura del Comitato per le Ouorauze Naziouali, cou prolegomeui, note a tavole dal P. Pietro Tacchi Venturi S. I.; Volume I, I Commentars della Cina (Macerata, 1911); Volume II, Le Lettere dalla Cina (Macerata, 1913).洪煨蓮: 《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禹貢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42頁尾注11。中,細讀這兩份漢譯史料,可總結如下:
(1) 利瑪竇及其他神甫曾向多位太監贈送過1602年李之藻的木刻墨印版《坤輿萬國全圖》。說明在未進獻皇帝之前,1602年版《坤輿萬國全圖》已在宮內流傳。
(2) 收贈地圖的太監之一將墨印版《坤輿萬國全圖》添繪彩色后獻于皇帝。是僅添繪了色彩還是添繪了彩色圖像未詳,但無論是添色還是添圖都說明: 一、 在1608年刻印彩繪《坤輿萬國全圖》之前,利瑪竇本人刻印的世界地圖以墨色素圖為主,沒有彩繪,也未繪圖像;二、 1608年版的添彩繪圖是被動而為。
(3) 皇帝見此繁列眾國、廣載異俗、前所未見之圖后大悅,令索更多份以分享皇族。說明《坤輿萬國全圖》所展示的地理新知識,已撼動了中國皇帝頭腦中固有的地理觀念。
(4) 因圖中有利瑪竇之序,故指名要利瑪竇提供。1602年版圖中有多人的題識序跋而皇帝唯獨指名利瑪竇,說明皇帝(或太監稟告皇帝)知道此圖“版權”屬利瑪竇,最佳被索人選非利瑪竇莫屬。
(5) 1602年版圖的原刻底版已被李之藻帶回杭州,刻工私刻底版雖被大雨塌屋毀壞,但仍有部分留存,說明此版的《坤輿萬國全圖》私刻底版并未完全毀滅。
(6) 利瑪竇建議以《兩儀玄覽圖》的8幅木刻底版作為取代版,印刷進獻。但因其版非皇帝索要版本,太監不敢。
(7) 利瑪竇再建議以一月期限自費另刻一版,皇帝不允。利瑪竇能夠保證在30天內完成《坤輿萬國全圖》的刻版印刷任務,說明他必定嫻熟于地圖底版的刻制與圖中圖像的摹繪。有學者也傾向于這一認識(58)鄒振環傾向于“彩繪本上的動物形象之設計者應該是利瑪竇”,參見鄒振環: 《殊方異獸與中西對話——〈坤輿萬國全圖〉中的海陸動物》,《海洋史研究》2015年第1期。。
(8) 皇帝“遂命就舊有之板,補刻以成六幅之世界地圖”,此事旋即辦妥。說明1608年版《坤輿萬國全圖》是以1602年版私刻底版殘留部分為主體加以“補刻”而成。且從補刻到完成制印的過程,時間很短。再次說明利瑪竇在刻印地圖與摹繪圖像方面的嫻熟程度。
(9) “其后宮內所需之地圖,即在宮內印之”。說明利氏《坤輿萬國全圖》1608年版(即為前述的木刻第五版)的木刻底版保存在宮中,還可根據宮內對該圖的需求量而添印之。
(10) 皇帝諭索絹本世界地圖(“令備六幅世界地圖絹本十二付”),但“南博本”為紙本而非絹本,這是一個遺留問題。有三種假設: 一是當時印制的進獻圖實際是紙本;二是當時在印制絹本進獻圖的同時,添印了紙本;三是在進獻“絹本十二付”之后,添印了紙本。無論何種假設,“南博本”的底版都是1608年版,即木刻第五版。
洪煨蓮考證認為:“我更疑宮中并無刊刻此圖之事”故將“南博本”視為“諸太監摹繪李之藻本”(59)洪煨蓮: 《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禹貢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26、28頁。按: 洪氏述及7刻板,但未述此版為刻板,僅述為“摹繪李之藻本”。。筆者認為: 完整刻制新版,與在殘留版基礎上補刻,是兩個概念。“南博本”的木刻底版顯然不是完整刻制新版,但據利氏記載分析,當為在1602年私刻版殘留部分的基礎上補刻之拼版。
洪煨蓮又認為:“歷史博物館舊藏的那本(即“南博本”)也許即是這樣的摹繪本之一,該本的內容與李之藻本,除了幾點外,完全相同。”(60)洪煨蓮: 《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禹貢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26—27頁。但對照梵蒂岡藏本(1602年李之藻原刻木版墨印)與“南博本”(1608年據補刻1602年刻工偷刻私版“墨印+彩繪”),去除后者圖中的繪畫圖像,僅就圖面大洲島嶼的封閉線形狀與題識序跋的文字布局而言比較兩者: 粗看,極其形似;細究,多有差異。故兩版之間非洪氏所述的“完全相同”或“二本盡相同”(61)“此本地圖曾兩度刻于北京,二本盡相同。一本為李我存所刻,李回籍時已將版片帶去。又一本乃刻工等所刻,印之以求售,所賣印本頗多,且得善價。然北京大雨之年此本版片適在一舊屋中,夜中屋塌,壓斃工人二,且毀其板焉。諸太監聞此,知不能應皇帝命,則又疑吾等言妄,既遣四人至吾等住所再詢,復派人至刻工處取零碎版片之尚存留者,以為證”。洪煨蓮: 《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禹貢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25頁。,而是利氏所述的版幅尺寸“大小盡同”(62)“此圖之刻工又私梓一版,大小盡同”。洪煨蓮: 《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禹貢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16頁。。
七、 摹 繪 底 本
利瑪竇在編制世界地圖暨《坤輿萬國全圖》所依據的地圖參考資料,是利氏世界地圖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洪煨蓮認為: 利瑪竇獻于皇帝的貢品之一《萬國圖志》就是《坤輿萬國全圖》所據底本,并據金尼各《中華傳教記》(DeChristianaExpeditione)考證為亞伯拉罕·奧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年)(63)亞伯拉罕·奧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有多種漢譯: 奧提力阿斯(洪煨蓮譯)、奧代理(方豪譯)、奧特里烏斯(黃時鑒譯)、阿伯拉罕·奧特呂(李旭旦譯: 《地理學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528頁)。本文譯據: 新華通訊室譯名室編: 《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064頁。的《地球大觀》(TheatrumOrgisTerrarum)(64)《地球大觀》(Theatrum Orgis Terrarum)為方豪所譯,他認為:“洪氏譯奧代理所著書名為《輿圖匯編》,完全不合原義,Theatrum本作舞臺解,故譯為‘大觀’。”(方豪: 《書評: 梵蒂岡出版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讀后記》,《上智編譯館館刊》1947年第2卷第2期,第170—173頁)若譯《寰宇概觀》更雅,但為了不引起混亂,本文沿用方豪譯名。。從百科全書的介紹中可知,該著有各家所繪地圖五十三幅。他還利用利瑪竇全集的記載,證明利氏還參照了意大利地圖學家魯瑟利(Girolamo Ruscelli, 1500—1566年)編制的地圖。限于各種原因,他自嘆:“關于十六世紀意大利派或比利時派的地圖,可惜我現今都未能得而將與利氏的地圖細校”(65)“萬歷二十八年十二月利氏所獻與皇帝的貢品內有《萬國圖志》一冊。據金尼各的《中華傳教記》,這即是奧提力阿斯的《輿圖匯編》;其中有各家所繪的地圖五十三圖。至于意大利地圖家法,則利氏本是意大利人,況他亦得用魯瑟利Ruscelli(卒1566)的地圖。關于十六世紀意大利派或比利時派的地圖,可惜我現今都未能得而將與利氏的地圖細校。”洪煨蓮: 《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禹貢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18頁。。
洪煨蓮考證但未親睹的著作《地球大觀》就藏于北京西什庫天主堂圖書館(方豪稱“北堂圖書館”),且有1570年與1595年兩版藏本,由于利氏1578年即啟程赴印度,1582年抵達中國澳門,因此利氏制作世界地圖所參照依據的當為1570年版。美國漢學家德禮賢在其著《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出版(66)寵光: 《利瑪竇地圖在羅馬影印出版》,《天主公教白話報》1939年第22卷第3期,第44頁;《利瑪竇地圖在羅馬影印出版》,《公教進行》1939年第11卷第4、5期,第130—131頁;《利瑪竇地圖在羅馬影印出版》,《圖書季刊》1939年第1卷第1期,第99頁。前五年的1933年曾赴北堂圖書館翻攝了《地球大觀》全著。1946年,方豪也赴北堂圖書館調閱了該館珍藏的“利瑪竇《萬國輿圖》所依原書”(67)《北平西什庫天主堂內發現珍本古物,有利瑪竇萬國輿圖原書》,《新聞報》1946年7月22日,第2版。,并于次年撰文評述道:“利瑪竇繪《坤輿萬國全圖》,必有所本;十余年前,外國學者早就注意這一點,并認為利氏必本于”奧特柳斯的《地球大觀》。并考證出如下事實: 德禮賢翻拍的《地球大觀》,錯將1595年版認作1570年版(68)方豪: 《書評: 梵蒂岡出版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讀后記》,《上智編譯館館刊》1947年第2卷第2期,第170—173頁。。
有關彩繪摹本《坤輿萬國全圖》(包括“南博本”)中的繪畫圖像,洪煨蓮未考證其摹繪來源。他嘆述:“這殆是從他處摹抄來的,西人舊圖往往有這些玩意兒,可惜我現今不能證明其從何書,或何圖中搬來的。”(69)“歷史博物館舊藏的那本也許即是這樣的摹繪本之一,該本的內容與李之藻本,除了幾點之外,完全相同。在其相同中,如名稱之同為《坤輿萬國全圖》,各序跋之完全相同,地形及注釋之相同,皆足以證: 繪本乃以李之藻本為藍本,而摹寫的。至其不同之最顯著者,則繪本中獨有船只,奇魚,異獸之圖。這殆是從他處摹抄來的,西人舊圖往往有這些玩意兒,可惜我現今不能證明其從何書,或何圖中搬來的。”洪煨蓮: 《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禹貢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26—27頁。真是一大遺憾!如果他看過了北堂圖書館所藏《地球大觀》中的地圖,就知道《坤輿萬國全圖》中的繪畫圖像即直接仿摹于《地球大觀》中的多幅地圖。
比利時制圖學家、地理學家亞伯拉罕·奧特柳斯于1570年出版了《地球大觀》第1版,共輯地圖70幅(歐洲56幅、亞洲與非洲10幅、四大洲各1幅),堪稱世界第一部完整的構想地圖集,被一再重印再版至1612年止,并被翻譯成歐洲各主要語種。(70)“Abraham Ortelius 1570”, in Phillip Allen, The Atlas of Atlas: The Map Maker’s Vision of the World, London: Marshall Editions, 1997, p.36.注: 洪煨蓮稱《地球大觀》載“各家所繪的地圖五十三圖”,則一定不是第一版。僅筆者所閱就有1570年、1573年、1584年、1585年、1587年、1589年、1590年、1595年、1598年、1606年版中的被轉載圖,這些圖幾乎多少都繪有海陸動物與海船圖像。但在已有研究中很少引載《地球大觀》所輯地圖,就筆者所閱僅有展示偽圓柱投影的橢圓形世界地圖(1570年、1587年版)(71)黃時鑒、龔纓晏: 《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圖版十一、圖版十二。、展示繪畫圖像的冰島圖(1590年版)(72)Map of Iceland from Abraham Ortelius’s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1590, Map 8), in John D. Day,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 of Matteo Ricci’s Maps, Imago Mundi, 1995, Volume 47, Issue 1, pp.94-117.與中國地圖(1584年版)(73)黃時鑒、龔纓晏: 《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圖版十三。數幅。
除奧特柳斯的《地球大觀》所刊地圖外,為了說明“南博本”的地圖偽圓柱投影及在地圖上描繪圖像的現象在16世紀的西方十分普及,再展示4幅世界地圖: 西蒙·格里諾伊斯(Simon Grynaeus)的世界地圖(1532年,木版刻印)(74)Simon Grynaeus, Typus Cosmographicus Universalis. Woodcut. An elegant world map first published in 1532 in a collection of voyages by John Huttich edited by Grynaeus, in Carl Moreland and David Bannister, Antique Maps, London: Phaidon Press Limited, 1989, p.15.(圖2)、賈科莫·加斯塔爾迪(Giacomo Gastaldi)的世界地圖(1546年,刻板)(75)World map by Giacomo Gastaldi, 1546, the progenitor of a sequence of maps continuing through the end of the century, in Thomas Suarez, Early Mapping of the Pacific, Singapore: Petiplus Editions, 2004, pp.42-43.(圖3)、保羅·福拉尼的(Paolo Forlani)世界地圖(1565年,銅版刻印)(76)World map on an oval projection. Universale descritione di tutta la terra conosciuta fin qui, by Paolo Forlani, copper engraving, Venice, 1565. A close copy of Giacomo Gastaldi’s map of 1546, in John Goss, The Mapmaker’s Art: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artography, Skokie, IL: Rand McNally, 1993, pp.11,132.(圖4)、安東尼奧·拉弗雷里(Antonio Lafreri)的世界地圖(1580年,木版刻印)(77)Antonio Lafreri 1580, in Phillip Allen, The Atlas of Atlases: The Map Maker’s Vision of the World, London: A Marshall Edition, 1997, p.50.(圖5)。

圖2 西蒙·格里諾伊斯(Simon Grynaeus)的世界地圖(1532年,木版刻印)

圖3 賈科莫·加斯塔爾迪(Giacomo Gastaldi)的世界地圖(1546年,刻板)

圖4 保羅·福拉尼的(Paolo Forlani)世界地圖(1565年,銅版刻印)
這4幅世界地圖都是西方15—16世紀地理大發現成就的地圖再現,它們具有以下共性: 第一,地圖投影均為呈橢圓形的偽圓柱投影;第二,地圖內容均有繪畫圖像;第三,出版年份均在1582年利瑪竇入明之前;第四,地圖投影與地圖內容均與“南博本”形似。可以認為有繪畫圖像的橢圓形世界地圖在16世紀西方地理大發現時期十分流行。生長于那個時代的學者型耶穌會士利瑪竇,對于這些地圖必然爛熟于心。
利瑪竇編制《坤輿萬國全圖》(包括“南博本”)時,雖然國內外學術界都認為他利用了奧特柳斯的世界地圖,但并不意味他只利用了奧特柳斯的某一幅世界地圖(78)龔纓晏: 《〈坤輿萬國全圖〉與“鄭和發現美洲”——駁李兆良的相關觀點兼論歷史研究的科學性》,《歷史研究》2019年第5期。,更不意味他沒有參照與奧特柳斯同時代的其他世界地圖的編制成果,尤其是有繪畫圖像的橢圓形世界地圖。
八、 獨 特 價 值
“南博本”除具有利瑪竇中文世界地圖暨摹繪本《坤輿萬國全圖》的共性價值與意義(79)《利氏世界地圖共有的學術價值》,闕維民: 《倫敦本利氏世界地圖略論》,北京大學歷史地理中心編: 《侯仁之師九十壽辰紀念文集》,學苑出版社2020年版,第314—325頁。外,還另具獨特性。
中國學術界對于利氏世界地圖的研究,可分為4個階段:
(1) 明末清初漢文化圈的吸收學習階段。代表研究者分兩類: 一類是參與利氏世界地圖刻版印制的學者,如《坤輿萬國全圖》中題識序跋的作者吳中明、李之藻、陳民志、楊景淳、祁光宗等;另一類是編錄利氏世界地圖及其序跋的學者如章潢(著有《圖書編》,收錄《輿地山海圖》與《輿地圖》,1613年)(80)④ 轉引自黃時鑒、龔纓晏: 《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第20頁。、周于漆(著有《三才實義》,收錄《輿地圖》,康熙、乾隆年間)④、馮應京(著有《月令廣義》,收錄《山海輿地全圖》,1602年)(81)⑥⑦ 轉引自黃時鑒、龔纓晏: 《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第29頁。、王圻(著有《三才圖會》,收錄《山海輿地全圖》,1609年)⑥、游藝(著有《天經或問》,收錄《大地圓球諸國全圖》,1675年)⑦、程百二(著有《方輿勝略》,收錄《山海輿地圖》,1610年)(82)轉引自黃時鑒、龔纓晏: 《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第46頁。、徐敬儀(著有《天象儀全圖》,收錄利氏部分地圖,明末)(83)⑩ 轉引自黃時鑒、龔纓晏: 《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第47頁。、潘光祖(著有《匯輯輿圖備考全書》,收錄東西兩半球圖《纏度圖》,1633年)⑩、熊明遇(著有《格致草》,收錄《坤輿萬國全圖》,1634年)(84)轉引自黃時鑒、龔纓晏: 《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第59頁。、熊人霖(著有《地緯》,收錄《輿地全圖》,1638年)等。
(2) 20世紀上半葉歷史基礎研究階段。代表研究者有陳觀勝(85)陳觀勝: 《論利瑪竇之萬國全圖》,《禹貢半月刊》1934年第1卷第7期,第19—24頁;陳觀勝: 《利瑪竇對中國地理學之貢獻及其影響》,《禹貢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31—72頁;Kenneth Ch’en and Matteo Ricci, Metteo Ricci’s contribution to, and influence on, geographical knowledge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39, Volume 59, Issue 3, pp.325-359.、洪煨蓮(86)洪煨蓮: 《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禹貢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合期,第1—50頁。、方豪(87)方豪: 《書評: 梵蒂岡出版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讀后記》,《上智編譯館館刊》1947年第2卷第2期,第170—173頁。、王庸(88)王庸: 《中國地理學史》,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第107—109頁。等。
(3) 20世紀下半葉的中外地圖研究階段。代表研究者有曹婉如等(89)曹婉如、薄樹人、鄭錫煌等: 《中國現存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文物》1983年第12期。、金應春與丘富科(90)金應春、丘富科: 《中國地圖史話》,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120頁。、盧志良(91)盧志良: 《中國地圖學史》,測繪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177頁。、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地學史組(92)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地學史組主編: 《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331—332頁。等。
(4) 21世紀以來的東西文化交流研究階段。代表研究者有黃時鑒、龔纓晏(93)黃時鑒、龔纓晏: 《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等。
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時間間隔近300年,意味著利氏世界地圖曾帶給明代中國的世界地理新知識沒有得到傳承,而是中斷了近三個世紀。正是1922年被發現、1923年公開展出的“南博本”,開啟了中國學術界對利氏世界地圖研究的現代新篇章。在目前各地現存的所有利氏世界地圖藏本中,這一特殊意義唯“南博本”獨有。
綜上所述,本文有以下五個要點:
(1) “南博本”的價值:“南博本”的被發現與公展,開啟了中國學術界對利氏世界地圖研究的現代新篇章。
(2) 新發掘兩類相關史料: 一是有關“南博本”1923年第一次公展的4份史料;二是可證明“南博本”編制摹繪的參照底本,即4幅16世紀歐洲編制的、圖中有繪畫圖像的橢圓形世界地圖。
(3) “南博本”的成圖形式: 已有研究基本公認“南博本”是非刻印的摹繪本,即無刻印底版;但本文認為“南博本”的成圖形式是: 木刻墨印+彩色摹繪的紙質本,其刻印底版是在1602年私刻版殘留部分的基礎上補刻之拼版。
(4) “南博本”與“理格本”之異: 洪煨蓮認為“南博本”與“理格本”兩者“盡相同”;本文認為仔細比對兩圖仍然存在差異,即不盡相同。
(5) 李之藻刻版與刻工私刻版之異: 洪煨蓮認為1602年李之藻刻版與同年刻工私刻之版(即1608年補刻拼版之主體)“二本盡相同”;但據1602年刻版墨印的“梵蒂岡本”與據1608年補刻拼版墨印+彩繪的“南博本”相比較,1602年的李之藻刻版與同年刻工私刻之版兩者僅尺寸“大小相同”,內容則相似而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