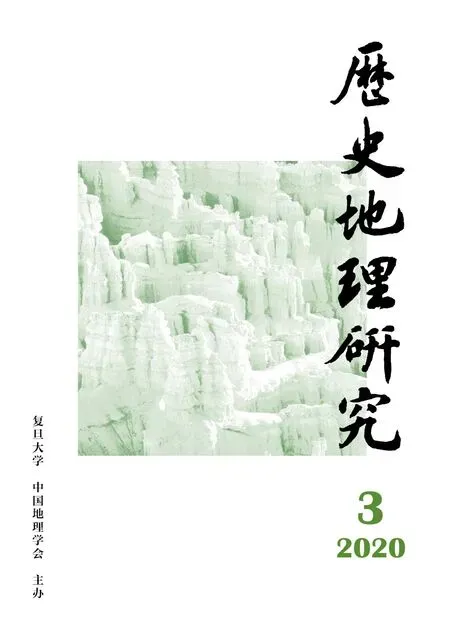基于地圖數字化的民國政區復原
——以1934年版《中華民國新地圖》為例
徐建平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一、 引 言
自秦一統以來,因地域遼闊、人口眾多,中央要對整個疆域進行有效控制與管理往往需要通過設立不同的行政區域來實現。因此,歷代中央政府對地方行政區劃都給予高度重視,且保留有大量文獻記載。同時,為加強對地方的控制,中央政府還形成了各種以政區為單位記錄各種社會現象的歷史傳統。這樣的政治結構和歷史傳統使得歷史上的政區變遷成為了解歷代中央與地方關系的窗口。因此,研究歷史上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變遷過程,必須建立在準確而翔實的歷代政區變遷基礎上。
行政區劃變遷研究的成果形式主要有史、志、圖、表等形式,史指政區沿革史,志指政區沿革志,圖指歷史地圖,表指政區沿革表。從編纂形式上又可以分為通代和斷代形式。由于政區設置及其變遷的重要性,歷代均有學者致力于對政區信息的記錄和研究,至清代乾嘉時期達到頂峰。梳理已有的歷代政區變遷研究的相關成果,可以發現大多研究將時段限定在傳統王朝時期,很少及于民國,更遑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周振鶴主編,周振鶴、李曉杰著: 《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總論 先秦卷》(第2版),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5—46頁。由復旦大學與哈佛大學等單位合作開發的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GIS),即以政區為綱,基于地理信息系統(GIS),將歷史上的政區沿革數據建成時間序列,提供以年為最小單位的連續變化政區數據庫,為歷史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但是該系統的時間下限僅到1911年。(2)葛劍雄: 《中國歷史地圖: 從傳統到現代》,《歷史地理》第18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頁;滿志敏: 《走進數字化: 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的一些概念和方法》,《歷史地理》第18輯,第12—22頁。
民國時期全國性的政區沿革史研究成果,屬傅林祥、鄭寶恒的《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中華民國卷》最為重要。(3)周振鶴主編,傅林祥、鄭寶恒著: 《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中華民國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該書分為三編: 緒編簡述民國時期對行政區劃變化產生過影響的各個政權從產生至消亡的過程;上編闡述民國時期各種政權的地方行政制度的變化過程及特點;下編分述各個行政區劃個體,包括由國民政府劃定的各省、直轄市、地區從清末到民國末年的具體變遷過程,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與日本扶持的偽政權統治地區的政區變化。該書集史、志、圖、表于一體,是迄今有關民國地方行政和政區變遷最為詳盡的研究成果。可惜該書以文字考訂為主,雖有數幅地圖,但皆屬于示意圖性質,無法直觀展示民國時期的政區面貌。
疆域政區圖是行政區劃最為直觀的展示方式,可以展現政區各要素在某一時間斷面上的空間分布。地圖又可以分為歷史地圖(集)和古舊地圖。歷史地圖集以《中國歷史地圖集》最為重要,而近三十年來區域性的歷史地圖集也層出不窮。區域性的歷史地圖集大多以省級政區為單位,也有以地級市甚至還有縣級政區為單位的歷史地圖集,例如《上海歷史地圖集》《北京歷史地圖集》《西安歷史地圖集》《福建省歷史地圖集》《重慶歷史地圖集》《濰坊市歷史地圖集》《萊陽縣歷史地圖集》(4)周振鶴主編: 《上海歷史地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侯仁之主編: 《北京歷史地圖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史念海主編: 《西安歷史地圖集》,西安地圖出版社1996年版;盧美松主編: 《福建省歷史地圖集》,福建省地圖出版社2004年版;藍勇等主編: 《重慶歷史地圖集》,星球地圖出版社2017年版;濰坊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地名委員會辦公室編輯: 《濰坊市歷史地圖集》,中國航海圖書出版社1988年版;萊陽縣人民政府地名辦公室編: 《萊陽縣歷史地圖集》,萊陽縣人民政府地名辦公室1986年刊印。等。這些地圖集繪制了相應區域歷史上各個時期的政區設置面貌并展示了其發展歷程。但是,單獨展示民國時期行政區劃變遷的,尤其是范圍覆蓋全國的歷史地圖集還未曾有過。
民國時期出版的普通地圖集,從時間段上看,基本涵蓋了整個民國時段,其中以20世紀30—40年代的最為豐富;從類型上看,既有全國性的地圖集,也有以省區為單位的地圖集,而單幅行世的更是數不勝數;從專題上看,民間出版的地圖,以表現政區、交通、聚落為主,其他專題地圖為輔。全國性地圖集大多比例尺過小,且只繪出省界;省區地圖集雖然繪出了縣界,但并非所有省份都有出版,很難湊齊同一時間斷面的各省縣級政區圖。
由上文可以看出,民國歷史地圖集以及合適的民國普通地圖集的缺乏對民國史研究造成許多不便。受此諸多限制,又能否利用地圖資料將CHGIS的工作延續到民國甚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呢?
目前關于政區沿革數據庫的建設一般有兩種方法: 時間截面描述法和生存期記錄描述法。應用生存期記錄描述法建設現當代政區沿革數據的案例筆者已有專文論述(5)徐建平: 《GIS支撐下的中國縣級政區沿革基礎數據(1912—2015)——以甘肅省為例》,《歷史地理》第38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57—268頁。,運用該方法建設的數據庫精度較高,又可以接續CHGIS,是比較完美的現當代政區沿革可視化展示的解決方案,缺點是工作量和技術難度較大,需要一定的技術保障以及大量人力保障。而時間截面描述法的工作量和技術難度相對較小,但其要點是必須以精度較高的地圖為工作基礎。這方面,韓昭慶對于《皇輿全覽圖》的數字化研究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相關研究方法值得借鑒。(6)韓昭慶: 《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數字化及意義》,《清史研究》2016年第4期;韓昭慶、李樂樂: 《康熙〈皇輿全覽圖〉與〈乾隆十三排圖〉中廣西地區測繪內容的比較研究》,《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
由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主編的《中華民國新地圖》(俗稱“申報地圖”,1934年上海申報館為紀念《申報》創刊六十周年編制出版),被評價為“唯一能代表舊中國地圖制圖水平”(7)廖克: 《中國古代地圖的歷史與近現代地圖學的發展》,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編: 《科學技術史研究六十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論文選》第2卷《地學史·生物學史·醫學史·農學史》,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8年版,第38頁。的地圖。其優點是編制精度高,覆蓋全國所有地區,比例尺較大(二百萬分之一),且不僅繪出了省界和省治,還繪出了縣界和縣治。如果以該圖為基礎進行數字化,提取相應的政區要素,建立20世紀30年代初的全國政區數據庫,似乎是一個可行的方案。因此,本文即以《中華民國新地圖》為例,運用GIS進行配準,提取政區要素建立數據庫,以此探討通過舊地圖建設時間斷面政區數據庫的可行性以及可能存在的問題。
二、 《中華民國新地圖》的數字化
《中華民國新地圖》作為《申報》創刊60周年最為重要的紀念作品之一,其最初緣起于1929年秋丁文江的建議:
誠欲從事邊疆調查乎?一、圖;二、籍,斯為主要。籍無論已,顧安所得精且確之地圖者?權輕重,較緩急,盍先事制圖乎?吾國自清康乾后,局部測繪,有之,匯合以成全國精圖,殆猶未也。其先事制圖便。(8)史量才: 《中華民國新地圖序》,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主編: 《中華民國新地圖》,上海申報館1934年版,第1—2頁。
《中華民國新地圖》正式出版于1934年4月,在此圖的編纂的過程中,于1933年先出版了縮編本的《中華民國分省新圖》。這兩種圖在當時被稱為“申報地圖”。《中華民國新地圖》在中國近現代地圖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盧良志將其重要意義總結為以下五點: 一是資料引用廣博;二是在地形表示上采用等高線分層設色法;三是創立了國家地圖集編制的新體例;四是促進了中國地圖印刷技術的發展;五是影響深遠,實用價值大。(9)盧良志: 《中國地圖發展史》,星球地圖出版社2012年版,第240—241頁。楊浪在其科普性的著作中介紹了申報地圖的編制過程,給予“中國地圖出版的里程碑”的評價,并且從四個方面指出了申報地圖的重大意義,這四方面的內容與盧良志書中所提到的五點內容基本相同。從兩書出版的時間看,似乎是盧良志沿用了楊浪的說法。見楊浪: 《地圖的發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08—116頁。持相似評價的還有徐紅燕、段怡春、馬伯永: 《地質調查所在中國地圖學史上的重要貢獻——以〈申報〉地圖為例》,《國土資源科技管理》2008年第6期。從歷史政區地理的角度來說,這部地圖提供了20世紀30年代初期全國范圍的政區分布狀況,包括省、縣兩級政區邊界以及省、縣、市鎮三級聚落的空間分布。如此重要的一部地圖,相關研究信息甚少,大多限于外圍研究(即編圖過程、技術、價值、地圖史上的意義等),至今未見針對圖上信息的本體研究。為了更好發掘該地圖所載的時空信息,需要從歷史政區地理的角度對圖上所載的政區信息作一個校對分析,以便提高以之建構的相應政區數據庫的精度,同時也為從事民國史研究的學者更準確地利用這套地圖提供便利。
《中華民國新地圖》分為總圖和分區圖,“總圖用亞爾勃斯投影法,其主要優點在各部分方向不失(經緯線常正交),故形勢逼真,面積不變,故圖上面積相等者,其所代表之實際面積亦等,而且所用標準緯度,系就中國疆域之位置自行創制者,故比例所差為數減至極小。分圖用多圓錐投影,此法各地可以通用”(10)翁文灝: 《中華民國新地圖序》,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主編: 《中華民國新地圖》,第2頁。。分區圖又分為自然圖組和人文圖組,因本文主旨只涉及圖集中的人文圖組,因此下文討論全部基于人文圖組,即從第8圖至第50圖的偶數圖幅,加上全國總圖一幅,共計23幅地圖。
由于已知地圖的投影方式且圖上標注有經緯度,因此將23幅地圖掃描后借助Arcgis軟件配準,便可得到配準后的全國總圖以及由22幅分區圖相互拼合的全國圖。因為投影方式的不同,以及分區圖各圖結合部的誤差,因此,全國總圖與分區圖之間的疊加會有一定的誤差。為了保證數據的準確性,采用以下方式提取政區數據: 從全國總圖上提取省級邊界多邊形數據;從分區圖上提取縣級政區邊界和省、縣兩級治所點數據。(11)縣級政區多邊形數據提取有相當大的難度,主要是圖上標注得不是很清晰,很多地方與道路、河流混雜,難以區分。至于縣以下市鎮點數據的提取,根據圖集所附地名索引,有35 000條左右,這批地名非常重要,可以做成帶有時空信息的民國時期地名數據庫,由于此項工作與本文主旨關系不大,因此留待后續研究。
由于《中華民國新地圖》分區圖沒有圖例,作為縮編本的《中華民國分省新圖》則每一幅分省圖都有圖例,因此可以參考后者來確定前者圖上幾種符號的具體指代,如表1所示:

續表
基于此,在Arcgis軟件中建立4個圖層,分別為“省級政區”“縣級政區”兩個面狀數據圖層以及“省級治所”“縣級治所”兩個點狀數據圖層。面狀數據圖層的數據表中有ID、名稱、省份、備注等字段;點狀數據圖層的數據表中有ID、名稱、級別、省份、備注等字段,其中級別字段對應表1中的前4種圖例符號,分別以羅馬數字Ⅰ—Ⅳ標識。(12)大多數省會城市也是附郭縣的縣城,因此在縣級治所圖層中仍需采集省會數據。將拼合之后的地圖上的政區邊界和治所數據全部采集建庫,下文對《中華民國新地圖》的具體分析即以此為基礎。
三、 《中華民國新地圖》政區信息統計
數字化完成之后,必須對數據進行考訂,以保證數據庫的精度。這里的精度是指時空兩個維度,由于政區本身就帶有時空特征,所以只需確保圖上政區信息是同一年份且在空間上覆蓋全部民國疆域。為此,必須尋找一份可靠的時間明確的政區信息表作為參照。
從歷史政區地理的角度來說,衡量一套普通地圖集質量高下最為重要的一條指標即圖上所載政區信息是否為同一個時間截面。宏觀來說,行政區劃從古至今都無時無刻不在變化。就全國范圍來講,國民政府內政部幾乎每個月都會在《內政公報》上公布一次行政區劃調整數據。《中華民國新地圖》從1929年底開始到1933年3月編繪完成,兩年多的時間里全國范圍內政區變動十分頻繁,那么該圖集所載政區是否有一個統一的時間截面呢?圖集的編纂者早就明白使用最新的行政區劃來制圖的重要性:
本圖雖迭經校閱,然吾國幅員寬廣,編者見聞有限,難免仍有訛誤脫漏。且以雕刻銅板,工作遲緩,故于經緯定點搜集完備后,不得不隨編隨印,計首批原稿于二十年五月付梓,末批亦于二十二年三月完成。以此最近建設,如縣治之更改,道路之建筑,間有未及一一編入,頗為遺憾,除已于再版中國分省新圖中更正外,尚祈閱者隨時賜示指正,以便于再版時更正。(13)曾世英: 《中華民國新地圖編纂例言》,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主編: 《中華民國新地圖》,第6頁。
可見該圖集并非一次性編成,而是分區域編成一批即雕刻銅板印刷: 1931年5月第一批圖稿印刷,1933年3月最后一批圖稿完成,當年年底全部殺青,1934年4月正式出版上市銷售。因此,理論上該圖集各省地圖政區斷限并非在同一年,應該是1931年5月至1933年3月間。由于編者并未明確交代各區域地圖的印刷順序,因此并不清楚各分區圖確切的時間斷限。雖然只是兩年的時間差,但是1930年前后恰恰是南京國民政府整頓地方行政較為高效的時期,地方行政區劃變動頻繁。加上目前史學研究越來越講究精細化,尤其是政區數據庫建設必須精確到以年為單位,這就客觀上要求將各分區圖做進一步的校準,明確其時間斷限,然后在數據庫中將不同年份的政區信息修改至同一年份。
國民政府內政部是主管全國行政區域的機構,由其發布的“全國行政區域統計”“全國行政區域簡表”之類的信息應該是最為權威的資料。(14)內政部的全國政區信息來自各省的上報以及本部門的調查統計,所以也會出現信息更新不及時甚至錯漏的情況,見周振鶴主編,傅林祥、鄭寶恒著: 《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中華民國卷》,第78頁。找到1931—1933年間的全國行政區域表,即可作為校訂“申報圖”政區信息的參照。筆者找到了一份1933年的全國行政區域統計表(表2),這份統計并未羅列出各省轄縣,因此只能比對統計數量,而無法比對所有的政區名稱。

表2 1933年全國行政區域統計
在這份統計資料中,依然未列出各省所轄縣及設治局的名目,只有總數。另一份國民政府內政部1934年公布的《全國行政區域簡表》中,列出了截至1934年6月全國各省區所轄縣級政區的名錄,全國共計:
省28,縣1 934,設治局29;院轄市5: 南京、上海、北平、青島、西京;省轄市13: 天津、杭州、漢口、長沙、成都、廈門、廣州、汕頭、貴陽、昆明、濟南、包頭、蘭州;行政區2: 威海衛行政區,東省特別行政區;地方2: 蒙古、西藏。(15)內政部編印: 《全國行政區域簡表》,1934年6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 一二(2),案卷號: 2622。
在這份統計資料中,依然未列出各省所轄縣及設治局的名目,只有總數。還有一份可供參照的政區資料從《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中華民國卷》所附《中華民國時期省級政區變遷表》中獲得,即1933年全國的政區設置如下:
省28,縣1 926,設治局43;院轄市5: 南京、上海、北平、青島、西京;省轄市9(16)《中華民國時期省級政區變遷表》1933年的數據中,河北省遺漏天津市,湖北省遺漏漢口市,福建省遺漏廈門市,四川省多重慶市。故而實際省轄市應為11個。: 杭州、長沙、成都、重慶、萬縣、廣州、汕頭、濟南、包頭;行政區1: 威海衛行政區;特別區1: 東省特別區;地方2: 蒙古、西藏。
將已完成數字化的《中華民國新地圖》治所數據表導出得到全部治所信息的表格,根據治所級別按省分類統計后得到表3。

表3 《中華民國新地圖》政區信息統計
由表3可知,《中華民國新地圖》一共繪出28個省、2個地方、2個院轄市,以及1 927個縣和35個準縣級政區(設治局、行政區、對汛督辦)。對照上述三份統計,除了個別省份縣級政區數量一致外,其余省份包括院轄市和行政區都有差異。其中最大的差異在“市”這類政區,原因是《中華民國新地圖》除了北京、南京和汕頭外,其余城市型政區均未繪出或注明。
除了城市型政區外,《中華民國新地圖》在行政區劃信息的表達上還有如下特點:
(1) 所有地名標注無通名,蒙古和西藏聚落符號與其他省份并無二致;
(2) 未繪出威海衛行政區和東省特別區;
(3) 內政部的統計中未計入云南省沿邊地區的行政區和對汛督辦,而《中華民國新地圖》將之視為與設治局同等性質處理。
由于《全國行政區域統計》以及《全國行政區域簡表》并未列出各省所轄縣級政區的名目,因此無法找出具體差異的是哪些縣級政區。
四、 《中華民國新地圖》各省政區斷限辨析
除上文提到的院轄市、省轄市、行政區等失載之外,具體到各個省份的縣級政區名稱以及時間斷限是否準確?這就需要以省為單位,根據史料以及已有研究成果進行比對。由于涉及全國范圍將近兩千縣級單位的校對,以國民政府內政部1935年6月公布的《全國行政區域簡表》(以下簡稱《簡表》)(17)由于該工作必須有完整的縣級政區名錄做參照,而內政部定期公布的《全國行政區域簡表》并非每期都列出各省所轄縣級政區名目,故而只能以搜集到的年代最為接近的1935年的《全國行政區域簡表》作為參照,見內政部總務司編: 《內政公報》1935年第18卷第17期。作為參照,首先找出《中華民國新地圖》和《簡表》所列縣名的不同之處,然后依據《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中華民國卷》(以下簡稱《通史·民國卷》)(18)以下各省區政區詳細斷限中,沿革論據依《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中華民國卷》者不一一出注,僅將頁碼括于其后。并配合其他文獻,分析兩者差異的原因并考證《中華民國新地圖》所載縣級政區斷限。這一工作可以達到兩個效果: 一是通過縣之置廢、縣名更改、治所遷移等信息盡量縮小圖載信息的時間斷限范圍;二是通過比對找出圖上失載、誤載、錯繪的縣級政區信息。
1. 安徽省
《中華民國新地圖》載有“秋浦、婺源”,《簡表》載有“嘉山、立煌、臨泉、至德”。
1932年10月,秋浦縣改名至德縣。1932年12月,析滁縣、來安、定遠、盱眙4縣交界地置嘉山縣。1933年置立煌縣。1934年置臨泉縣,婺源改隸江西省。(《通史·民國卷》第179—183頁)
圖上有秋浦縣,無嘉山縣,因此,安徽省圖所反映的政區下限為1932年10月。
2. 察哈爾省
《簡表》載有“崇禮設治局、尚義設治局、化德設治局”。
1934年9月置化德設治局,12月置崇禮設治局,1935年置尚義設治局。(《通史·民國卷》第441—444頁)《中華民國新地圖》并無上述三設治局,因此,察哈爾省圖所反映的政區時間下限與《中華民國新地圖》的完成時間并無沖突,可定為1933年3月。
3. 福建省
《中華民國新地圖》載有“光澤、歸化、思明”,《簡表》載有“廈門市、明溪”。
1932年12月,歸化縣改名明溪縣。1933年5月,析思明縣置廈門市,1935年2月,廢思明縣。1934年7月,光澤縣劃歸江西省。(《通史·民國卷》第255—260頁)
圖上歸化縣尚未改名明溪縣,故此判定福建省圖所反映的政區下限為1932年12月。
4. 甘肅省
《中華民國新地圖》載有“紅水、東樂”,《簡表》載有“民樂、康樂設治局、景泰”。
甘肅省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行政區劃多有調整。
1930年,正寧縣治所由羅川遷駐山河鎮,即今治所。1932年6月,設洮西設治局,1933年2月更名康樂設治局。1933年4月,紅水縣遷治一條山鎮,并改名景泰縣。1933年6月,民樂縣治所由東樂遷治洪水堡,即今治所,并改東樂縣為民樂縣。重劃東樂、山丹兩縣縣界,以山丹縣屬童子壩、沐化壩屬民樂縣,以舊東樂縣城屬山丹縣。(《通史·民國卷》第410—416頁)
由圖觀之,正寧縣治標注在縣域南部羅水之上,可知縣治尚未遷移至縣域西北部的山河鎮。另外,圖上無洮西(康樂)設治局,紅水縣尚未更名。故而,根據正寧縣治的遷移時間判定甘肅省圖所反映的政區下限為1930年之前。
5. 廣東省
從廣東省的縣級政區名稱上看,雖然《中華民國新地圖》和《簡表》并無二致,但是通過治所變遷的信息依然可以找出若干政區斷限信息。
1930年6月,中山縣治所由石岐鎮遷移至唐家鎮;1931年3月,新會縣治所由會城鎮遷移至江門。(《通史·民國卷》第270—277頁)
由圖可知,中山縣治已遷移至唐家鎮,新會縣治尚未遷移至江門。圖上并未標注梅菉市。因此,廣東省圖所反映的政區斷限為1930年底至1931年3月。
6. 廣西省
《中華民國新地圖》載有“古化、西延”(19)1929年,由全縣西延區、長萬區析置,治西延鎮(今廣西資源縣駐地大合鎮)。1936年撤銷,與興安縣北部的車田、尋源兩鄉合置資源縣,以地處資江上源得名,駐地未變。因此,《簡表》缺載西延縣。,《簡表》載有“百壽”。
1929年8月,以萬承土州置萬承縣。1930年1月,改馬平縣為柳州縣。(20)《簡表》中有馬平縣而無柳州縣,誤。1933年2月,古化縣改名百壽縣。(《通史·民國卷》第286—297頁)
圖上載有萬承縣,有馬平縣而無柳州縣,故廣西省圖所反映的政區斷限為1929年8月之后1930年1月之前。
7. 貴州省
《簡表》載有“貴陽市、道真、金沙、納雍”。
1930年4月,改開縣為開陽縣,改鳳泉縣為鳳岡縣,改羅斛縣為羅甸縣,改麻哈縣為麻江縣,改思縣為岑鞏縣。1926年9月,省政府批準改南籠縣為安龍縣,1931年10月國民政府批準。1928年4月,省政府批準改靈山縣為三穗縣,1931年10月,國民政府批準。1932年9月,國民政府令準析黔西縣置金沙縣,析正安縣置道真縣,析大定縣置納雍縣。(《通史·民國卷》第323—334頁)(21)道真、金山、納雍三縣雖批準設縣,但限于政局實際并未成立,直到1941年7月才正式成立。《內政年鑒》所載應是以國民政府的批準為準。
貴州省圖載有開陽、鳳岡、羅甸、麻江等縣,而無金沙、道真、納雍三縣,因此貴州省圖所反映的政區斷限為1930年4月之后,1932年9月之前。(22)安龍和三穗兩縣,屬于省政府先批準,地方實際已改名,國民政府后追認。故而,無法判定《中華民國新地圖》是據實際繪圖還是國民政府批準為準。同樣,因《中華民國新地圖》未繪制省轄市,故貴陽市無法作為判定依據。
8. 河北省
《中華民國新地圖》載有“定都”,《簡表》載有“都山設治局”。
1930年12月,分遵化縣置興隆縣。1931年2月,析遷安、撫寧兩縣置都山設治局。(《通史·民國卷》第350頁)(23)《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中華民國卷》認為都山設治局成立于1933年8月。據縣志,都山設治局成立于1931年2月13日,參見《青龍滿族自治縣志》,中國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據1931年1月12日遼寧省政府訓令中已確載成立設治局以及設治委員等信息,參見《遼寧省政府公報》1931年第12期。此處設治日期據縣志所載。
河北省圖上已繪出興隆縣,定都標注為縣治,疑為都山之誤,治所圖標應改為設治局符號。因此河北省圖所反映的政區時間上限為都山設治局設立的1931年2月之后,下限則為圖集完成的1933年3月之前。
9. 河南省
《中華民國新地圖》載有“自由、平等”,《簡表》載有“伊川、經扶”。
1928年析登封、禹縣置民治縣,1931年裁撤。1931年6月,合并滎澤、河陰兩縣為廣武縣。1927年12月析洛陽、登封、臨汝、伊陽4縣地置自由縣;析嵩縣、洛陽、宜陽、伊陽4縣地置平等縣;1931年10月裁撤平等縣(實際裁撤于1933年10月),1932年10月自由縣改名伊川縣。1933年9月析光山縣置經扶縣。(《通史·民國卷》第374—381頁)
圖上無民治縣,有廣武縣,自由縣尚未更名為伊川縣,據此可判定河南省圖所反映的政區斷限為1931年6月之后,1932年10月之前。
10. 黑龍江省
《中華民國新地圖》載有“鳳山縣、依安設治局、綏棱設治局、明水設治局、奇克設治局、佛山設治局、景星設治局、雅魯設治局”,《簡表》載有“綏棱縣、明水縣、依安縣、奇克縣、佛山縣、景星縣、雅魯縣、鳳山設治局”。
綏楞設治局1915年置,1917年升縣,1921年改綏棱。鳳山設治局1929年11月置,民國時期并未改縣。明水設治局、奇克設治局、景星設治局、依山設治局、雅魯設治局、佛山設治局,1929年11月改縣。1930年5月,室韋縣治遷移至蘇沁。(《通史·民國卷》第476—485頁)
圖上室韋縣治標注在吉拉林,并未移駐蘇沁。明水等設治局尚未改縣,但是鳳山和綏棱兩縣的政區信息與其他文獻有沖突,因此黑龍江省圖政區斷限并不清晰,大致可以定為1929年11月左右。鳳山初置時為設治局,治所圖標誤為縣,另外綏棱此時已改為縣,圖上仍標注為設治局。
11. 湖北省
《中華民國新地圖》載有“蘄水”,《簡表》載有“浠水、禮山”。
1932年6月松滋縣治所遷移至新江口。1932年12月,黃岡縣治所由團風鎮遷移至黃州。1933年1月,以河南省羅山、湖北省黃陂、黃安、孝感4縣地置禮山縣,1933年5月6日國民政府批準。1933年5月,改蘄水縣為浠水縣。(《通史·民國卷》第201—206頁)
由圖可知,松滋縣治尚未遷移至新江口,黃岡縣治所依然在團風鎮。禮山縣并未標注。蘄水尚未改稱浠水。故此,湖北省圖所反映的政區時間下限為1932年6月。
12. 湖南省
《中華民國新地圖》載有“陽明”。
1929年12月,析零陵、寧遠、祁陽、新田、常寧6縣置陽明縣。1931年7月撤銷。(《通史·民國卷》第214頁)
因此,湖南省圖所反映的政區斷限為1929年12月之后,1931年7月之前。
13. 吉林省
1929年9月,吉林縣改名永吉縣、同賓縣改名延壽縣、綏遠縣改名撫遠縣。(《通史·民國卷》第468—464頁)
圖上有永吉、延壽和撫遠,因此,吉林省圖所反映的政區斷限為1929年9月之后,1933年3月之前。
14. 江蘇省
1928年11月置蘇州市,1930年4月23日,撤銷蘇州市并入吳縣。1931年6月,上海縣治所遷移至北橋鎮。(《通史·民國卷》第159—160頁)
圖上并無標注蘇州市,但《中華民國新地圖》不載省轄市,因此無法以此作為判定依據。圖上上海縣治所尚未遷移至北橋鎮,據此判定江蘇省圖所反映的政區時間下限為1931年6月。
15. 江西省
《簡表》載有“婺源、光澤”(24)1934年7月,安徽省婺源縣改隸江西省,福建省光澤縣改隸江西省。。
1928年8月,定南縣治所遷移至下歷。(《通史·民國卷》第193頁)
由圖可知,定南縣治所并未標注在下歷,由此判定江西省圖所反映的政區時間下限應為1928年8月。
16. 遼寧省
1929年6月,改興京縣為新賓縣。1929年7月,國民政府批準將清源縣改為清原縣。1929年7月,改金川設治局為金川縣。(《通史·民國卷》第454—459頁)
圖上載有新賓、清原和金川三縣,因此遼寧省圖所反映的政區斷限為1929年7月之后,1933年3月之前。
17. 寧夏省
《中華民國新地圖》載有“定遠營、陶樂、紫湖、居延”,《簡表》載有“中寧、陶樂設治局、紫湖設治局、居延設治局”。
1932年寧朔縣治所遷移至王洪堡。1933年12月,分中衛縣置中寧縣。(《通史·民國卷》第420—422頁)
由圖可知,寧朔縣治已從寧夏省城遷出,中衛縣尚未分置中寧縣。故寧夏省圖所反映的政區斷限為1932年之后,1933年3月之前。定遠營為阿拉善厄魯特旗旗府駐地,在民國時期并非作為縣治,圖上誤載。紫湖設治局、居延設治局內政部雖已批準設置,但實際可能并未設治(《通史·民國卷》第422頁),故而圖上在注記上加了“?”,但治所符號用的是普通縣治,誤。關于陶樂設治局,寧夏、綏遠兩省有爭議(《通史·民國卷》第422頁),但治所符號用的是普通縣治,誤。
18. 青海省
《中華民國新地圖》載有“巴燕”,《簡表》載有“化隆、囊謙、同德、共和”。
自1928年青海設省之后,縣級政區多有變動。1928年2月,置玉樹縣;1928年3月,改巴戎縣為巴燕縣,1931年6月改名為化隆縣;1929年7月置亹源縣、共和縣;1929年8月置同仁縣;1930年4月置民和縣(治上川口,同年12月移治古鄯驛,1933年12月,移治上川口);1930年8月置互助縣;1930年11月置都蘭縣(1931年10月遷治希里溝)。(25)1931年3月國民政府正式批準上述置縣申請。1933年12月置囊謙縣;1935年5月置同德縣。(《通史·民國卷》第424—429頁)
首先,由巴燕縣的政區名稱變更可知,青海省圖政區斷限為1928年3月之后,1931年6月之前。其次,圖上民和縣治所標注在古鄯堡,則時間應在1930年12月之后,1933年12月之前。綜上,青海省圖所反映的政區斷限應為1930年12月之后,1931年6月之前。另,共和縣與亹源縣、同仁縣同為1929年置,1931年3月國民政府批準,然圖上有亹源縣、同仁縣而無共和縣,應判定為失載。
19. 熱河省
《中華民國新地圖》載有“天山、凌南、寧城、天寶山設治局、林東設治局”,《簡表》載有“林東、天山設治局”。
1928年9月熱河設省,1933年2月熱河淪陷。這期間縣級政區多有調整,主要有: 1930年,綏東縣治所由庫倫街遷移至八仙筒。1931年,析赤峰縣置全寧設治局,同年改縣,次年裁。1931年9月,圍場縣治所由克勒溝遷移至錐子山鎮。1931年,析平泉縣置大寧設治局,同年12月改為寧城設治局。1931年,析朝陽、凌源兩縣置凌南設治局。寧城、凌南兩設治局遲至1947年才改縣,而圖上治所符號標注為縣,誤。1931年,天山設治局治所由昆都遷移至查布桿廟,1947年改縣,圖上治所符號標注為縣,誤。1932年8月,林東設治局改為林東縣。(《通史·民國卷》第447—449頁)
根據圖面信息,綏東縣治所還在庫倫街;無全寧;有寧城縣及凌南縣;天山縣治所尚未遷移至查布桿廟;根據治所圖例,林東標注為設治局。圍場縣內標注了兩個治所,即圍場和天寶山(26)《中華民國新地圖》第16圖(主體表現熱河省政區)天寶山標注方式不同于普通縣治。然而第48圖(主體表現蒙古區域)天寶山標注為普通地名,因此天寶山治所符號有誤。。綜上所述,由寧城的標注可知圖上信息不得早于1931年12月,由林東未稱縣可知圖上信息不得晚于1932年8月。然圖上綏東和天山的治所遷移信息與實際不符。故而,熱河省圖政區信息并不嚴謹,如以縣級政區名稱斷限,則為1931年12月之后,1932年8月之前。
20. 山東省
《簡表》載有“濟南市”。
1931年3月,析濮縣地置鄄城縣。(《通史·民國卷》第365頁)
圖上已繪出鄄城縣,由此可知,山東省圖所反映的政區斷限為1931年3月之后,1933年3月之前。
21. 山西省
民國前期,山西省縣級政區幾乎無大變動,因此,山西省圖所反映的政區時間下限為1933年3月。
22. 陜西省
1929年2月,析朝邑、華陰兩縣地置平民縣。1930年,永壽縣治所遷移至監軍鎮。(《通史·民國卷》第399—400頁)
由圖觀之,平民縣已設治,永壽縣治所并未標注在監軍鎮。由于無其他重要的政區變動信息可資參照,因此,陜西省圖所反映的政區斷限為1929年2月之后,1930年永壽縣治所遷移之前。(27)永壽縣治所遷移的具體日期待考。
23. 四川省
《簡表》載有“成都市、金湯設治局”。
1932年6月,析寶興縣置金湯設治局。(《通史·民國卷》第251頁)
圖上并未標注金湯設治局,因此,四川省圖所反映的政區時間下限應為1932年6月之前。
24. 綏遠省
《簡表》載有“包頭市”。
1925年7月置大佘太設治局,1931年6月改名為安北設治局。1933年4月,國民政府核準設立包頭市。(《通史·民國卷》第434頁)
圖上載有安北設治局,因此綏遠省圖所反映的政區斷限為1931年6月之后,1933年3月之前。
25. 西康省
《中華民國新地圖》載有“貢噶”。
據《川邊各縣輿地圖·西康各縣總圖》有縣治貢噶,然《川邊各縣輿地圖·稻城全圖》則貢噶屬于稻城縣,并非縣治。且分圖中并無單獨的貢噶縣全圖。(28)川康邊政訓練所制: 《川邊各縣輿地圖》,1928年3月。1935年出版之《西康省分縣新圖》上貢噶并非縣治,為稻城縣境內一地名。(29)《西康省分縣新圖》,武昌亞新地學社,1935年8月。《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中華民國卷》認為有兩說,一是1913年3月置貢噶縣,然旋置旋廢。二是貢噶并未置縣。(《通史·民國卷》第246頁)(30)今《稻城縣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對于貢噶設縣一事亦無記載。
綜合判斷,西康省圖所反映的政區時間下限為1933年3月,貢噶并非縣治。
26. 新疆省
《中華民國新地圖》載有“庫爾勒、烏魯克恰提、七角井、托克遜、魯克沁、耳里匱”,《簡表》載有“鞏留、托克蘇、和什托洛蓋設治局、賽圖拉設治局、庫爾勒設治局、七角井設治局、烏魯克恰提設治局、托克遜設治局”。
1930年10月新疆增設柯坪、阿瓦提、哈巴河、吉木乃、托克蘇5縣以及七角井、托克遜、烏魯克恰提、和什托洛蓋、賽圖拉5設治局。1932年3月,析伊寧縣置鞏留縣。(《通史·民國卷》第491—503頁)1930年新設5縣5設治局中,新疆省圖失載托克蘇縣、和什托洛蓋設治局和賽圖拉設治局,1932年新設之鞏留縣未載。故而,新疆省圖政區斷限應為1930年10月之后,1932年3月之前。庫爾勒、烏魯克恰提、七角井、托克遜四設治局治所誤標為縣。托克蘇縣、和什托洛蓋設治局和賽圖拉設治局失載。魯克沁為清代額敏和卓王府所在地,并非縣治。耳里匱實際并未設立。(31)《測量公報》1931年第14期。
27. 云南省
《中華民國新地圖》載有“普文、阿迷、苴卻(32)1929年11月,析大姚縣之苴卻地方置永仁縣,縣治駐仁和街(《通史·民國卷》第315頁)。云南省圖上已標注永仁縣,但是縣境之內仍然標注苴卻為縣治,疑誤載。、黎、永北(33)1934年2月改名永勝縣(《通史·民國卷》第312頁)。、永寧(34)1936年9月,撤銷永北縣寧蒗縣佐改設寧蒗設治局,之前該區域屬清代永寧土知府和蒗蕖土知州(凌永忠: 《民國時期云南邊疆地區特殊過渡型政區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98頁)。因此,云南省圖之永寧縣治應為誤載。、五福、威信(35)1932年由威信行政區改設威信設治局,1934年改威信縣(凌永忠: 《民國時期云南邊疆地區特殊過渡型政區研究》,第198頁)。照理,此時威信治所圖例應標注為行政區,然由圖上標注為普通縣圖例,疑有誤。、猛丁行政區(36)據凌永忠的研究,猛丁行政區1932年改為平河設治局,1936年7月,與金河設治局合并改置金平縣(凌永忠: 《民國時期云南邊疆地區特殊過渡型政區研究》,第200頁)。因此,此設治局《全國行政區域簡表》失載。、金河行政區(37)1936年7月,金河設治局與平河設治局合并改置金平縣(凌永忠: 《民國時期云南邊疆地區特殊過渡型政區研究》,第200頁)。因此,此設治局《全國行政區域簡表》失載。、芒遮板行政區、猛卯行政區、盞達行政區、知子羅行政區、上帕行政區、菖蒲桶行政區、臨江行政區、隴川行政區、瀘水行政區、干崖行政區、阿墩子行政區、靖邊行政區、河口(38)此處河口應為對汛督辦特別區,且圖上麻栗坡對汛督辦特別區失載(凌永忠: 《民國時期云南邊疆地區特殊過渡型政區研究》,第111—122頁)。”,《簡表》載有“昆明市、永勝、屏邊、華寧、開遠、蒙化、南嶠、碧江設治局、德欽設治局、福貢設治局、貢山設治局、蓮山設治局、梁河設治局、龍武設治局、潞西設治局、寧江設治局、瑞麗設治局、硯山設治局、盈江設治局、隴川設治局、瀘水設治局”。
云南省縣級政區在1930年前后變動劇烈,主要分為兩類,一是新置縣或設治局,二是縣改名。主要變動記錄如下: 1929年11月,置永仁、曲溪、雙江、西疇4縣,東川縣改名會澤縣,云南縣改祥云縣,廣西縣改名瀘西縣,改嶍蛾縣為峨山縣。1929年12月,置普文(1932年9月撤銷)、佛海、車里、鎮越、江城、五福(1934年2月改名南嶠縣)6縣。1931年12月,改阿迷縣為開遠縣,改黎縣為華寧縣。1932年,以瀘水行政區置瀘水設治局、以隴川行政區置隴川設治局、以猛卯行政區置瑞麗設治局,以菖蒲桶行政區之貢山設治局、以盞達行政區置蓮山設治局,以干崖行政區置盈江設治局,以芒遮板行政區置潞西縣,以知子羅行政區置碧江設治局,以上帕行政區置福貢設治局,以阿墩子行政區置德欽設治局,以臨江行政區置寧江設治局,分石屏縣置龍武設治局,分騰沖縣置梁河設治局。1933年2月,改靖邊行政區為屏邊縣。1933年6月,置硯山設治局。(《通史·民國卷》第303—318頁)
根據阿迷、黎兩縣名稱的變化,可以確定政區時限不晚于1931年12月,由普文、佛海、車里、鎮越、江城、五福5新縣可知政區時限不早于1929年12月。基于此,云南省圖所反映的政區斷限為1929年12月之后,1931年12月之前。圖上標繪河口對汛督辦而未標麻栗坡對汛督辦,判斷為失載。
28. 浙江省
《簡表》載有“杭州市”。
1930年前后浙江省縣級政區無大變化,唯1927年分杭縣置杭州市,分鄞縣置寧波市。(《通史·民國卷》第169—174頁)對于市,《中華民國新地圖》并未有特別的標注,故而不足以作為判定依據。因此,浙江省圖所反映的政區時間下限為1933年3月。
29. 蒙古地方
《中華民國新地圖》載有“加達、科布多、庫倫、烏蘭固木、烏里雅蘇臺”。
《簡表》并未載蒙古地方的行政區域狀況。從圖例符號看,庫倫以省會符號標注,其余四處以縣治符號標注。
由于無其他可資參照的政區設置信息,故蒙古地方圖所反映的政區時間下限為1933年3月。
30. 西藏地方
《中華民國新地圖》載有“碟穆綽克、定結、定日、噶大克、岡馬、吉隆、江孜、拉薩、羅多克、日喀則、榮哈、薩噶、薩迦、善和、特拉多穆、西泥沙、協噶爾、亞東、札倫、札錫岡”。
《簡表》并未載西藏地方的行政區域狀況。從圖例符號看,拉薩以省會符號標注,其余宗駐地以縣治符號標注。
由于無其他可資參照的政區設置信息,故西藏地方圖所反映的政區時間下限為1933年3月。
五、 時間截面政區數據庫的修正
將上一節各省區圖所反映的政區斷限信息進行匯總,即可得到表4和表5。

表4 《中華民國新地圖》各省區圖所反映的政區斷限

表5 《中華民國新地圖》政區信息錯漏一覽表
由表4可以看出,這套地圖在時間斷限方面基本做到了編者“反映現行行政區劃”的目標,各省圖所體現的政區斷限基本與圖集的出版過程相一致,整個圖集政區時間斷限都集中在1928—1933年。
進一步檢討《中華民國新地圖》在政區信息繪制上的錯漏之處。在省級行政單位的標注方面,存在四個問題: 一是在內政部對蒙古地方的正式名稱為蒙古,而圖上標注為外蒙古;二是漏繪上海、青島和西京三個院轄市,尤其是漏繪上海特別市可謂較大失誤;三是漏繪威海衛行政區和東省特別行政區,誤標瓊崖特別行政區;四是未標示廣西省省會(39)民國時期廣西省會在邕寧(南寧)和桂林之間搖擺不定,這可能也是《中華民國新地圖》未明確標示省會的原因。根據內政部公布的《簡表》,廣西省會為邕寧。。所以在省級政區層面,這套地圖錯漏較為嚴重。在縣級行政單位的標注方面,也存在四個問題: 一是漏載10個省轄市;二是漏載2縣、2設治局、1對汛督辦;三是誤載7個縣級行政單位;四是10個縣級治所符號繪制有誤,將設治局標注成正式的縣。
將上述省縣兩級行政單位的錯漏信息在Arcgis系統中進行修正,便得到了信息準確的《中華民國新地圖》政區數據庫,但是該數據庫有一個缺點,就是時間斷限并非是同一年,而是一個時間段,即1928—1933年間。為此還需更進一步將該數據庫修訂至同一個年份。
根據表4各省區政區信息的時間斷限,最優方案是選擇1931年底作為政區數據庫的時間截面。在該方案下,只需將廣東、廣西、黑龍江、湖南、江蘇、江西、青海、陜西8個省份1931年之前的政區變動信息補充進數據庫即可,相比其他年份工作量最小(表6)。

表6 各省增補政區信息匯總表
結 論
通過本文的研究可以發現,只要以高質量的舊地圖為基礎,完全可以用數字化的方式來構建時間截面描述法的政區數據庫。
李孝聰先生曾指出:“關于古地圖的研究,應該加強對現存古地圖的分類整理與研究,將古地圖運用于歷史研究的工作,更需要加強和深入。利用古地圖研究中國行政區劃的演變,中國的邊疆問題,中國的海疆問題,復原中國歷代道路和城市結構,特別是有關中國國家核心利益和政治、經濟、文化的內容,亟待分析闡述。……此外,近年來地理信息系統(GIS)的應用逐漸廣泛,如何利用GIS推進古地圖的整理與研究,需要地理學者和歷史地理學者進一步做細致踏實的工作,期待這項工作取得進展。”(40)李孝聰: 《文以載道圖以明志——古地圖研究隨筆》,《中國史研究動態》2018年第4期。
利用古舊地圖來建構政區數據庫是一項跨學科的綜合性工作,這一工作可以分解為幾個步驟。首先是地圖學,即將地圖上的各項信息研究透徹,包括地圖的繪制時間(既要搞清楚地圖繪制的時間,也要搞清楚圖上信息所表達的時間),地圖的作者,繪制的背景、目的、用途,地圖繪制的技術標準(投影、坐標系、經緯度)等。其次是利用GIS建立數據庫,對地圖掃描、配準之后提取相關信息,如邊界、治所、聚落、河流、交通等。再次是歷史政區地理研究,也就是一旦發現地圖上的地理信息并非同一個時間截面,就需要利用歷史政區地理的理論和方法,對相關信息進行查漏補缺,使其統一到同一個時間截面。通過以上三個步驟之后建成的政區地理數據庫便構成了某個時間截面的時空框架,成為下一步研究的基礎性數據。
由于民國時期中國的疆域廣大,各個省區發展又極不平衡,客觀上造成了各省的測繪數據積累也相差很大。體現在地圖上,就是各省的地理信息在地圖上的展現質量良莠不齊。《中華民國新地圖》已經是民國時期國人編繪的最高質量的民用地圖,但依然不能保證時間斷限一致,也無法避免錯繪、漏繪的情況發生。但是以省為單位或者其他小區域,則很有可能依靠高質量的地圖直接建構時間截面數據庫,比如東部幾個省份,無論是政府層面的軍用地形圖測繪還是民營地圖出版機構的民用圖繪制都有非常深厚的傳統,地理信息數據積累豐富、準確且更新迅速,完全可以以之為基礎構建起多個時間截面的政區數據,為將來以生存期記錄描述法建設時間序列政區數據提供堅實的資料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