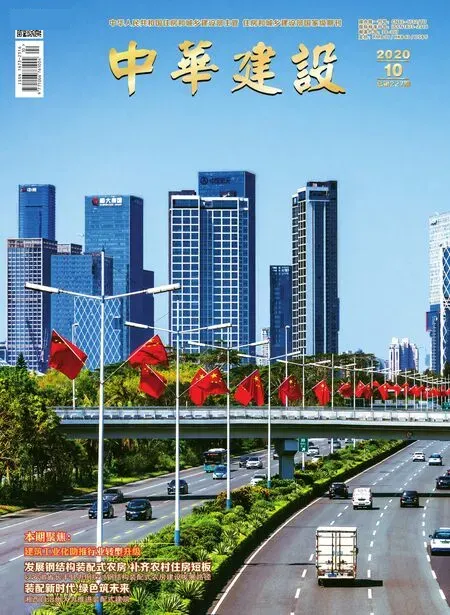花澗堂
——物體中的城市,城市中的物體
魏清橋
人是家的主人
在自然中靜下心來
回歸自然
回歸自然的同時
全方位地敞開心扉
家是向藍天、白云敞開的
或者是向滿天星云敞開的帶屋頂的建筑
——勒·柯布西耶 《直角詩》,1955
在勒·柯布西耶著名的直角詩的第一節中,這位或許是二十世紀以來最偉大的建筑師用一種極其富有詩意的方式為讀者渲染了“居住”的場景。從建筑學的角度解讀,《直角詩》也許已經為我們勾勒出了建筑的本質——其所在的環境、建筑本身以及建筑對環境的回應。
相較于1955年,人類社會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劇變,柯布西耶的宣言卻仍然適用,建筑依然在探討社會要素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以及作為建筑師如何回應這種復雜關系的物化體現。在當今社會中,我們如何定義并理解人與環境就變得尤為重要。花澗堂是我對這一問題做出的探討與回應——隨著社會的發展,城市早已蔓延至每個角落,建筑在這一語境中,應同時作為“城市中的物體”與“物體中的城市”而存在。
一、物體
我們需首先對“物體”與“城市”這兩個概念進行明確與定義。
物體從可以代指一切——它可以是一棵樹一支筆乃至一滴水,它看似模糊,但當深入理解時,我們可以認為它普遍代指一個存在于具體現實中的、并具有身份特征的有意義的“事物”。 它的意義不需要被構建,就如當看到諸如杯子之類的物體時,人們可以立即識別它。此外,一個物體除其自身特性之外,還應能夠對周圍的世界產生影響。正如舒爾茲所說,一個物體能夠通過其形態揭示其意義。
由翁貝托·薄邱尼創作的雕塑《瓶子在空間中的發展》可能是對物體這一概念做出的最明確的解析之一。作為一個物體,一個瓶子具有內在的特性,并時刻在表達自己,但這個表達并非立即可以被理解。在瓶子站在那里呈現出本身的同時,其意義仍然被隱藏著。瓶子里裝有液體,同時它封閉且透明。即使瓶子是有色的,我們也會通過玻璃察覺到液體的波動性,潛在的運動使物體變得更加活躍。瓶子存在于空間中,并具有其獨特的身份與特征,同時其材料特性也對空間產生了影響。
二、城市
從本質上來講,城市是物體的集合,也是物體的載體。由于城市化進程城市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密集,一個城市需要承載越來越多的物體、敘事或空間,以滿足各種需求。那么我們可以將城市視為不同活動的空間的容器。
通過將城市定義為“集體住宅”,舒爾茲清楚地表達了他對城市的理解——“當定居完成時,其他涉及人類群體結構的基本形式的住宅就會逐漸形成。定居點是一個相遇的地方,居民可以在那里交換產品、想法和感情”。自古以來城市空間就是人類聚會的舞臺。聚集并不意味著達成妥協,人類因需求的多樣性而走到了一起。城市空間本質上是一個發現的地方,一個“可能性的空間”。在城市空間中,人類居住在體驗世界豐富的意義上。
城市與交換、談判和多樣性有關,城市是載體。在雷姆·庫哈斯的“俘虜地球之城”中,城市的這一特性得到了概念性的描繪,不同街區的各種活動和空間得以被組織,聯系與加強。
總之,“城市”可以被定義為構建、包含并加強這種人類交往、活動及不確定性的外向性容器,與之相反,“物體”則是確定的、現實存在的、能夠揭示其內在含義并影響周遭世界的內向性實體。
三、物體中的城市
在現代城市中,酒店一直是一種獨特的、內向的且功能單一的場所。花澗堂所希望拆改釀造的,則是“物體中的城市”——一個加強、組織并激發活動與交流的場所。
花澗堂坐落于龍隱湖畔,由數個單體建筑組成,并由一條主要軸線加以連接。酒店的入口位于場地的西端,進入大門后,是開放的涼亭(圖1)。涼亭以一種謙卑的姿態將湖面風景加以強調與展示。穿過涼亭就是接待中心,一棟的小尺度建筑,為住客提供入住等服務,也綜合了洽談、展示等多種功能。通過一條長長的連廊,接待中心與住宿區(圖2)域相連通。餐廳位于北面,與住宿區一起構建了最主要的室外公共空間。公共廣場穿插于居住區與餐廳之間,打破了室內外邊界。清樾堂(圖3)位于場地東端,承載著主要的公共娛樂空間--咖啡館、電影院、棋牌室、閱覽室等多樣化的公共空間,是花澗堂空間序列末端的“終點”。通過體量的堆疊與空間邊界的模糊,整棟建筑的尺度被消解,并有機地與其它建筑融合在一起。餐廳、休憩空間、茶室等小尺度公共空間分散在建筑群各處,不僅服務于功能需求,更重要的是,同時打破了規整的布局。

圖1 花澗堂入口涼亭

圖2 花楹樓

圖3 清樾堂
在花澗堂里,就如同博爾赫斯所描述的,有無數序列,背離的、匯合的和平行的時間織成一張不斷增長、錯綜復雜的網。由互相靠攏、分歧、交錯,或者永遠互不干擾的時間織成的網絡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
這與城市又有什么不同呢?與城市一樣,花澗堂致力于構建并加強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活動、多樣性與不確定性。室內外空間的穿插、公共與私密空間的整合、多樣的空間體驗與特性,輔以不斷變化的自然景觀,花澗堂所創造的也許正是一個“物體中的城市”,一系列曖昧的、不確定的、不明確的空間關系,以及一個連其創造者也無法完全預知的空間網絡。
在著名的“廣普城市中”,庫哈斯曾這樣形容酒店——“酒店是一般性城市最為常見的建筑類型,它是一般性城市的代表性場所。過去,寫字樓中盡管人來人往,但是它至少還表明在寫字樓之外還有其他重要的場所存在。現在,酒店就像集裝箱一樣包羅萬象,令其他建筑顯得多余。就其數量而言,酒店是購物商場的兩倍,它是我們城市生活最親密的伴侶。酒店如同監獄,入住酒店就如同自我拘留;沒有其他與之匹敵的場所可以光顧,既來之則安之。日積月累,酒店演變成一個將千萬人口鎖在他們各自房間的城市。一種反向的活力,一種內向爆炸的密度。”
花澗堂所希望打破的,正是這種內向型的空間模式以及相互分割的隱形邊界。通過在物體中構建城市,酒店的復雜性得以進一步加強,每個房間封閉的“牢籠”得以打開,而建筑,則僅僅是它們的容器罷了。
四、城市中的物體
城市環——自上而下的大尺度城市交通系統將自然與地面切分為互不相連的碎片,坐落于城市以外的村落也早已自下而上地自我更新,成為了看似毫無特色的水泥盒的堆疊。村落這種傳統聚落類型,在現代城市的沖擊下,逐漸演變成了單一文化性、單一功能性及特定社會階級所組成的區塊,逐漸切斷了歷史與現在的關系。
坐落于鄉村中的花澗堂的策略是作為一個“物體”,在揭示其自身特點與含義的同時,以開放的姿態影響著其周邊關系并重構著當地斷裂的歷史文脈。花澗堂的周邊地區,村與城之間的二元對立關系尤為明顯。直覺上村是落后的、小尺度的且碎片化的景象。但由于其整體結構的密集與有機的發展模式,在大尺度上村落內部的復雜性往往可以被忽略,并可被看作是有著單一身份認知的“物體”。相反,以公路與鐵路為基礎的城市則呈現一種對周邊環境漠不關心的姿態。在大尺度交通基礎設施構建的城市結構中,村的概念可以成為對城市過度單一性的補充。除了提出自上而下城市發展的對立面外,“村落”這一空間構成概念也是當地自古以來城市發展的主要方式。在如此定義周邊城市背景的情況下,花澗堂旨在通過構建村落的概念,將小型且碎片化的建筑進行整合成為“物體”,以對周邊環境提出根本性的批判思考。
在花澗堂的設計中,我們嘗試著將傳統酒店的功能拆散并重構,通過體量堆疊與材料拼貼的方式構筑村落式的空間結構與視覺效果(圖4)。通過這一策略,花澗堂的結構形態得到了明確的揭示——即使是從高速公路飛馳的汽車上,其小尺度體量與空間的錯落以及碎片化的村落式空間特性也極為明顯。

圖4 花澗堂軸測圖
花澗堂在通過其結構形態表達自己特性的同時,其內在含義也得到了相對隱晦的表達——建筑,同我們每個人一樣,與其出生、成長的地點保持著緊密的聯系和深厚的感情。通過將紅磚——當地盛產與普遍被利用的材料與白色保溫板——簡單且極具現代性的材料的結合;通過對民居小尺度院落空間與現代建筑“普世空間”的結合,建筑希望尋找“少”與“多”、歷史與現在的平衡,也希望對“少就是多”這一現代主義教義提出質疑與思考。這種以“少就是多”為核心的現代主義設計手法雖對建筑具有極高的價值,但它們選擇的內容和表達所用的語言雖強而有力,仍不免有其局限性。花澗堂表現的則是另一種可能性——建筑設計并非對單一問題的選擇與主觀的回應,不是“純白”地排斥其他文脈關系的統一,也不是單純的對歷史的再造,而是構建兼容的困難的統一,“多”并不是“少”。意義的簡明不如意義的豐富,功能既要含蓄也要明確。我喜歡“兩者兼顧”勝過“非此即彼”,我喜歡黑白的或者灰的而不喜歡非黑即白。一座出色的建筑應有多層含義和組合焦點:它的空間及其建筑要素會一箭雙雕地既實用又有趣。在花澗堂中,紅磚與白墻的結合創造了意想不到的多樣空間體驗,小尺度碎片化的院落與現代簡潔的普世空間的連接也構建了極具不確定性的“灰空間”(圖5)。

圖5 紅磚與白墻
五、跋
不定性凝聚著達到最富有詩意的效果,并發現它產生一種他稱為“對立”的品質,即我們所稱的詩歌自身的沖突。在我看來,居住建筑所追尋的,正是這種對立的富有詩意的品質。它既是物體也是城市,它充斥著不確定性,卻也真實存在著并揭示著其內在的含義。在很多情況下,建筑師往往忽視建筑內在的真正復雜性和矛盾性,即使像住宅這樣規模簡單的項目,如果表現現代生活的不定性,其目的也是很復雜的。例如火箭的飛向月球計劃,其方法極為復雜,但其目的卻簡單明了。雖然建筑的設計在技術上簡單,但其目的卻復雜且捉摸不透。
復雜性與不確定性,在這個城市主導的時代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會是建筑師必須面對的話題。花澗堂,這“城市中的物體”與“物體中的城市”,看似矛盾,實則相互補充與支撐,而這也是我對現代城市復雜性與不確定性所提出的回應策略。最后,請允許我用勒·柯布西耶《直角詩》的另一段作為結尾:
我是房子和宮殿的
建筑師
我在錯綜復雜的
人們之間生活
做建筑就是去創造
變得、充盈、充實自己
充實自己,去狂喜
使復雜性中的冰冷爆裂,變成一只快樂的小狗。
去變成秩序
——勒·柯布西耶 《直角詩》,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