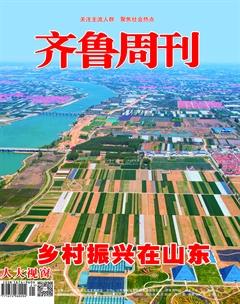鄉村振興的文化“夢工廠”
顧盼
鄉村振興,既要塑形,也要鑄魂。
文化是軟實力,也像一把鑰匙,之于鄉村振興的重要意義在于追溯鄉村的價值,通過對鄉村傳統價值的轉化,以此來激活鄉村。
藝術價值的鄉村實踐:先行者不再孤獨
藝術家蔡玉水,十幾年前隱居在濟南市長清區雙泉鎮,在雙泉鎮的村落中每天穿行,經常會遇到一些村里的老人。“在一個荒廢的老戲臺對面的院落,我看到一位老人在5點多鐘的夕陽下曬著太陽,破敗凄涼的院落與安詳平靜的面孔扎的我心疼。”
蔡玉水記得他當時對老人的承諾:“老爺子,很快有一天我會讓你在家門口,倚著門框就能再看到《四郎探母》《穆桂英掛帥》。”

董方軍投資興建的沂河源田園綜合體是山東省首批鄉村振興齊魯樣板省級示范區。
后來,從雙泉鎮萬畝油菜花田的大地藝術到講述雙泉故事的電影《藝術也瘋狂》,蔡玉水在藝術改變鄉村的愿景里,完成了對老人的承諾,也為文化產業的鄉村路徑豎立一面別樣鏡鑒。
山東工藝美術學院院長潘魯生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曾指出,“鄉村振興要培育鄉土情懷,培養扎根鄉村、與鄉村生死與共、有思想、有意愿、有情懷、有能力的鄉村人才隊伍,鼓勵文化精英等回歸鄉村。”
鄉村文化振興成為鄉村振興戰略內容的應有之意,首先應是“人”的振興。
濰坊市牟家院村,牟昌非發起的鄉村戲劇節在2020年10月迎來第九屆,此次的主題為“生活在真實中”。在他的構想中,鄉村戲劇節一年一屆,一屆兩季,梨花開放時為花季鄉村戲劇節,等到果實成熟,再做一季。
在鄉村戲劇節之前,牟家院村幾乎沒有任何文娛活動。2016年第一屆鄉村戲劇節時,第一次觀看戲劇演出就把村民“震驚”了。除了各類地方戲曲的演出,牟昌非還邀請了全國各地的戲劇團體,其中不乏凌云焰肢體游擊隊(濟南)、江湖戲班(武漢)、肢覺劇場(廣州)等知名劇團。
在“互聯網+”的時代背景下,牟昌非為自己生于斯長于斯的鄉村構建了一個戲劇的“詩和遠方”,改變了生活在那里的人們。
它注入了新鮮血液,搭建起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橋梁,提高了村莊的知名度。
由于影響力的提升和媒體的持續關注,鄉村戲劇節逐漸演變為代表本地區特色的名片。這種轉變使基層政府由原來的不知情轉變為認可和大力支持,成為落實鄉村振興戰略“最后一公里”的關鍵一環——
通過戲劇節帶動村莊發展和吸引農村青年回村創業,完善村級基本設施,吸引資本下鄉……牟家院村的鄉村戲劇節提供了一條獨特的探索鄉村振興的路徑。
沂河源,是另一個“藝術活化鄉村”的高地。
2019年,山東省首屆文化創意與鄉村振興高端論壇第四場研討會主題為“世界藝術與沂河源田園綜合體的融合發展”。
曾因戴高樂機場、北京國家大劇院等經典設計作品而名揚國際的法國著名建筑設計師保羅·安德魯,自愿無償來到這里做景觀設計;
李心田、劉玉堂等國內知名作家的文學館,就坐落在村民的房前屋后;
青山綠水、果樹草坪、石板翠竹,形成一道道鄉村振興的亮麗風景線……
在位于沂源縣魯村鎮的沂河源田園綜合體,讓人感受最深的是這里中西方文化藝術的有機融合。
負責人董方軍是東方匯泉金融控股集團公司董事局主席,作為土生土長的當地人,他將集團公司業務交由職業經理人打理,常駐“沂河源”,憑借自己多年積累的資本、資源和見識,不遺余力回鄉投身鄉村振興。
用藝術活化鄉村,他是受日本慈善家福武總一郎的啟發。福武總一郎通過藝術、自然與建筑融合,將日本直島、豐島、犬島等幾乎被世人遺忘的荒島,變成了在日本排名第六的旅游景點。目前,中日雙方就“藝術活化鄉村”落地中國達成了全面合作,并以沂河源田園綜合體項目為基地,帶動周邊7個鄉村全面推進“藝術活化鄉村”項目落地中國。
“打造沂河源田園綜合體,我們以慈善感召天下英才下鄉,以資本吸引優質產業進村,以藝術活化美麗鄉村,立志打造‘藝術振興鄉村的標桿,成為世界農村、農民、農業融合發展的典范。”
為了提高當地村民乃至全國有關鄉村振興的各界人士的認識和素養,董方軍正在創辦一所鄉村振興學院,深入廣泛地傳播世界各地鄉村振興的深刻內涵和成功經驗。
鄉愁“變現”與文化自信
剛剛過去的“十一”黃金周,鄉村旅游成為消費主流。據不完全統計,8天假期,全省鄉村旅游接待游客3141萬人次,實現鄉村旅游消費113億元。
走進鄉村,人們不僅尋得見鄉愁,還能把載有家鄉記憶的物產買回去,一買一賣間,釋放了鄉愁“變現”的市場潛力。
在蘭陵縣壓油溝景區的傳統記憶街區,一個個手工作坊,呈現出魯南地區傳統的手工技藝。“游客多的時候,我一天能賣6000多元,疫情期間,通過‘直播帶貨賣咸菜,我已經圈粉6000多人了。”咸菜坊負責人海燕坦言,村里原來一窮二白,年輕人都走光了,但自從發展鄉村旅游,自己把咸菜店開進景區后,日子越過越好。如今一年下來,能贏利10多萬元。
據統計,全省400個旅游扶貧村中,有77個已經進入鄉村景區化評估名單,占參與評估鄉村總數的三成左右。其中,8個貧困村躋身全國鄉村旅游重點村,旅游人次和消費水平節節攀升,成為引領齊魯鄉村游的新標桿。
鄉村振興,需要文化的內生力量。
近期,山東著力推動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建設,激發打造鄉村振興齊魯樣板的內生動力。目前,全省建成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176個、實踐所1749個、實踐站4.7萬余個,設立鄉村儒學講堂2.2萬個。
漫步在“中國美麗休閑鄉村”淄博市博山區池上鎮聶家峪村,景致怡人,兒童嬉戲,村民健身,一幅鄉村美景圖徐徐展開。
這幾年,聶家峪村充分挖掘特色鄉村文化,講好文化故事,整合了10多個部門的涉農資金1600多萬元,用于櫻桃冷棚、餐飲住宿、蔬菜暖棚、農家樂民宿改造等鄉村旅游項目建設,截至2019年底,共為村民分紅約27萬元。村民脫了貧,村集體也增加了收入。
兩年前,聶家峪村村民黃元禮放棄在青島的工作,回到家鄉,從事文化旅游開發。“原來我們這里叫寶泉村,至今在村里還有這么一眼泉水,從沒枯竭過,村里的這些傳說故事,我們年輕一代要講起來,讓更多人知道。”
十里不同鄉,百里不同俗,參差百態方能體現文化之美。
山東行政村數量達6.95萬個,村居數量多、規模小、布局散、密度高,如何讓鄉村文化各具特色、代代傳承?
山東將具有重要價值的古遺址、古民居納入文物保護范圍,加強傳統村落保護,2018年以來省級以上投入2.7億元,保護項目215個,建成鄉村記憶博物館210多個。
保留鄉村記憶,其中不僅承托著美好深刻的文化基因,更有可能蝶變新生,創造無盡的物質財富。
讓“指尖技藝”成為“指尖經濟”,近兩年來,我省培育了一批木雕、木版年畫、剪紙、刺繡、草編等專業鄉、專業村;建成國家級和省級非遺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71個,帶動23萬人就業。
正如潘魯生所說,只有融入農民的生產生活,讓農民腰包鼓起來,具有可持續性,才能真正讓鄉土文化在齊魯大地汩汩流淌、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