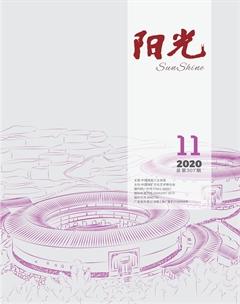起瞻壯睹卻金碑
李公小試其道,而化及夷邦,今茲天曹又登庸俊良,俾宇內陰受其賜,階是而宰均持衡,則幹旋之速,又何如哉?若夫崇坊之舉,所以峻其防也。
——《卻金坊記》(1514年)
這是一個初夏。四百八十年前的東莞海關。陽光從海岸線上躍起,一絲海風連著片片蕉葉的清香撲到窗外。
李愷深深地吸了一口蕉葉清香的空氣,小聲地哼著:“天烏烏,要落雨,阿公呀舉鋤頭要掘芋。掘啊掘,掘啊掘,掘著一尾旋鰡鼓。依喲嗄都真正趣味,阿公要煮咸,阿媽要煮淡,倆人相打弄破鼎。”
離開泉州已有幾載,李愷每每心里頭掛著喜事,就會情不自禁地哼起姥姥教給他的這首兒歌。嘉靖戊子(嘉靖七年,1528),在老家惠安鄉薦獲得第二的成績時,姥姥便拉著他的手,唱的就是這首歌。壬辰(嘉靖十一年,1532),考取進士,授廣州番禺令,也是哼著這首兒歌奔赴嶺南的,惹得隨從也學著他唱歌。
“叫天子”貼在大榕樹上,一個勁兒地唱著。
門崗來報,暹羅(今泰國)商人柰治鴉看來訪。
李愷連忙整了整臺上的文件,恭請柰治鴉看落座,并拿出從廣州帶來的一撮“小茶”。
打開茶杯蓋,一片清茗飄在水里,柰治鴉看將嘴輕輕地咬住杯邊,長長地吸了一口氣。他是一個中國通,他知道這是一杯好茶,情不自禁地吟起大唐詩人白居易的詩來:“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塵。無由持一碗,寄與愛茶人。”
“‘人間風日不到處,天上玉堂森寶書。想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斛瀉明珠。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硙霏霏雪不如。為公喚起黃州夢,獨載扁舟向五湖。這是宋代文學家黃庭堅將詩與茶送給蘇軾的,那才是一個味道。”李愷回敬一杯說,“看來,先生對中國茶道頗有研究。”
“不敢說有研究,來貴地多次,得到兄弟等人關愛,學得一二,見笑,見笑。”柰治鴉看指著李愷的茶壺說,“李進士這茶名叫鐵觀音,屬進士老家閩南烏龍茶,原產福建安溪縣,素有‘觀音韻之稱,其入口微苦,回味甘香,清郁雋永,韻味無窮。曾有詩贊道:‘青水高峰,出云吐霧,寺僧植茶,飽山嵐之氣,沐日月之精,得煙霞之靄,食之能療百病。”傳說安溪松林頭茶農魏飲信佛,每晨必奉清茶一杯于觀音大士像前,十分虔誠。一日,他上山砍柴,偶見巖石間有一株茶樹,在陽光照耀下,閃光奪目,異于分樹,便挖了回來精心培育,并采摘試制。其茶沉重似鐵,香味極佳,疑為觀音所賜,即名為“鐵觀音”。鐵觀音傳統的沖飲方法非常講究。茶具要小巧精致,水最好用山巖泉水。將水燒沸,先把茶壺燙熱,裝上約占壺容量十分之六七的茶葉,沖入沸水,用壺蓋刮去浮上來的泡沫,蓋好壺蓋,此時便有一股殊香撲鼻而來。隔兩三分鐘,再緩緩倒入茶杯,每人各持一杯,先聞香,再品味,慢慢啜飲,便滿口生香,回味甘美。
幾杯清香,柰治鴉看便進入主題。他受暹羅國商會全體同仁的委托,感恩李愷幾年來對暹國及周邊船商的關照,“乃以百金”獻給李愷。
“是贈給先生,并無賄賂之意。”
李愷站了起來,笑了笑:“這是一個大明人應該做的,至于你們要以金相送,豈不是侮我一生清名?”
說罷,揮了揮手,送客。
一個被傳頌千年的故事,就在這揮手之間進入了人們的記憶。久戰商場的柰治鴉看,走過多少條水路,看過多少個英雄豪杰,聽過多少次豪言壯語,卻未看到過有這樣一個東莞官員,面對百金無半點兒貪色。在這溫暖的南國里,陽光更加炫目,他已對東莞有了全新的認識。
李愷還是那樣淡淡地一笑,把柰治鴉看送出大門。
陽光從門口的荔枝樹葉間打了進來,一路晶瑩剔透。
“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禹貢·疏》)朝貢,古代的一個名詞。古代藩屬國或外國的使臣朝見宗主國或所在國的君主并敬獻禮品。凡來朝的國家,只要承認自己是“附庸國”就行。東亞朝貢體系乃是以中國中原帝國為核心的等級制網狀政治秩序體系,中原王朝以天朝自居,透過冊封,結合儒家思想體系,層層往外推拓。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唯一出身赤貧的皇帝。面對錯綜復雜的經濟結構,他沒有半點兒興趣,他時刻想著他那“雞犬之聲相聞”的農業社會生活,幾欲要將大帝國建筑在小農經濟之上。對宋代工商業經濟發展、王安石的變法,朱元璋從沒有肯定過,甚至不無貶損:“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他還不惜打擊工商業和航海業,下令禁止民間入海“通番”,把對外限制在海禁政策范圍以內的“朝貢”貿易,由市舶司主管,對外貿易以進貢名目由禮部掌管。
“夫以貢來,而實以私附”。為顯示大國風范,對來“朝貢”者以“加倍賞賚”進行優厚回贈。允許附帶貨物和開市貿易,商人亦隨便一同來華貿易。各國使節來華進行所謂“稱臣納貢”,而絡繹不絕。
這樣一個占據重要位置的對外貿易,擁有再強大的“國體”,也會日益削弱。尤其到了明代中葉以后,官場腐敗,政以賄成。在南海的廣州市舶司,“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官吏們,面對過往的商船,更是封船抽分,施以重稅。面對如此境況,正德四年(1059),廣東都御史陳金向朝廷建議,“將暹羅、滿剌加并吉蘭丹國夷國貨物,俱以十分抽三。”這是好事呀,朝廷當然應允,并馬上下令執行。繼后,又規定“抽其十二”,也就是按百分之二十的稅率征收進口稅,由廣東省市舶司執行之。
“抽分執委,世所染指”。不少官吏視主管市舶貿易為肥缺,常借抽分、盤驗番舶之機向外商敲詐勒索,中飽私囊。他們或插手市舶事務,“以黷貨殃民為常事”,或橫豎一竹竿敲得叮當作響,不得不讓外商們“以賄賂而速官謗,則又妄益番人之稅,以掩其跡。”說到底,為了個人利益,讓外商少報或不報關稅,貪小利而損國威。有的將權力無限放大,百般刁難,以“侵漁亦商”。一時間,外商怨聲載道。朝廷不得不采取“易官互詰”的辦法,“遣知縣有廉干者往舶抽盤”,以互相監督制約。
就這樣,李愷登場了。這位在廣東番禺令任上以“廉干有才名”受命督辦東莞進出船只的關稅。
東莞,瀕臨南中國海。作為“廣州通海夷道”的必經之地,東莞上通省會,下接香山,外有大洋,廣及萬頃,儼然是“番東之要津”。潮汐出入,內外往來,都以此為咽喉。“其利不貲,榷金山珠海,天子南庫也”,憑著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逐漸成為對外貿易極其重要的交易地。明時,來華外國商船停泊的碼頭在東莞雞棲(今香港九龍東南)、屯門(今香港)、虎門頭(即虎門)等。地處海濱,時轄今天的香港和深圳。東莞南部地區成為西方商人在東南沿海最重要的貿易區域之一。在澳門開埠前,東莞就這樣起著廣州外港的作用。東莞的莞香、莞席、莞鹽,亦借此便利行銷海外。商船到了外埠,進口外國的懷表、五金等,再回到東莞販售。
在這樣一個地方督辦關稅,那真是一個難得的肥缺。
縱觀古代,有三個崗位最容易產生貪官,即鹽政、河道和漕運。而專門面對外商的舶司,更是肥缺中的肥缺。從番禺起程赴東莞的前一夜,有鄉黨來到李府,幾杯茶下肚,便語重心長地說:“粵地別燕丹,壯士待沖冠。進士此去東莞,要一路慎行。”
李愷知道鄉黨借用了唐朝駱賓王的詩來為自己送行,仰慕古人也寓意他在新的崗位上要謹言慎行。
鄉黨指著書架上的一本書說:“兄,你還記得唐代詩人王勃寫的《滕王閣序》嗎?”
“當然記得。這篇駢文,從洪州的地勢、人才寫到宴會;寫滕王閣的壯麗,眺望的廣遠,緊扣秋日,景色鮮明;再從宴會娛游寫到人生遇合,抒發身世之感;接著寫作者的遭遇并表白要自勵志節,最后以應命賦詩和自謙之辭作結。‘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采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
望了望窗外的月光,鄉黨說:“文中好幾個用典都是寫廣東的。你看,‘酌貪泉而覺爽講的就是廣州刺史吳隱之的故事。離廣州二十里一個叫石門的地方,有一口泉叫‘貪泉,據說不管誰喝了這泉水,都會變得貪得無厭。吳隱之到廣州后,不相信這個謠言,為了表明立志清廉,他特意來到貪泉,掬水而飲,并賦詩為志:‘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意思是:人們都說喝了這泉水,就會貪財愛寶,假若讓伯夷叔齊那樣品行高潔的人喝了,我想終究不會改變那顆廉潔的本心。”
李愷嘆道:“是呀,‘直脂膏中,亦不能潤。大千世界,地有貧富;州縣省部,官有肥瘦。人心皆嫌貧愛富,但君子愛財,得取之有道。小弟謹記兄的教誨,誓做一個劉刺史一樣的清官。”
時間是嘉靖十七年(1538年)。
李愷上任伊始,便鉆進了鄉間、海邊、船上,深入到一線調查研究,然后燒了兩把大火。
第一把大火,就是簡化手續,實行自報制。由夷商自報貨物數量,再由中方抽查核實,依額征稅,不妄增益。
第二把大火,就是依法征稅,不得剝盤外商,做到“不封舶,不抽盤,責令自報其數而驗之,無額取,嚴禁人役,毋得騷擾”。
按照要求,外國商船入港后,先要由地方官吏加以封倉,以避免走私漏稅,然后再對貨物逐一檢驗并抽分。這些手續全部完成之后,才能進行正常交易。李愷為杜絕各級官員借封倉清貨之機勒索外商,并試圖解決動用大量人力逐一查驗而“費浩獲微”的問題,故決定不封船、不抽盤,改由番商自行報稅,同時宣布“敢有詐匿者,抵法則常”。這樣一來既縮短了外國商船在港口停泊的時間,又大大減少了外商的額外負擔,便利了他們的自由貿易。這一提議獲準后,李愷秉公執法,親自到港口查驗外商的船舶貨物。
這兩把大火確實燒到了“雁過拔毛”者的身上,大家見李愷敢動真格、不徇私情,貪婪的手不得不收斂起來。這兩把大火,燒出了東莞政界政通人和,令政治生態清朗起來,令外商耳目一新。
暹羅與明朝關系源遠流長。可以考證的是在洪武三年(1370),明廷設廣州三市舶司,即規定“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今越南南部)、暹羅、西洋諸國”。洪武七年(1374),廢除市舶司,只允許琉球、占城、真臘(今柬埔寨)、暹羅等少數國家進貢。
說到底,暹羅與明廷是友好鄰邦。明廷對朝貢的國家、船、期限、人數等都有具體規定,不符合規定不許入貢。貢期有一年一次,或三年、五年、十年一次,視其與中國關系而定,明廷往往用停貢來懲戒那些不聽話的蕃國。據《明史》記載:“琉球、占城諸國皆恭順,任其時至入京。唯日本叛服無常,故獨限期為十年。”
李愷的稅務改制,為當時的明廷帶來一縷春風,也將大明的官員們引向誠信。“不拒其來,以示廣也;令其自核,以導忠也;不再稽疑,以懷信也。”這在其時,要有何等大的胸懷?李愷做到了,東莞的舶司做到了。
而這些最大利益者,當屬與明廷合作較多的暹羅海商們。暹羅是“恭順”之國。明廷的“物合”也最早發給暹羅國,而且其附貢舶而來的商舶,一律免征關稅。其貢使行商不僅允許在指定的到達口岸和京城進行買賣,也可在上京的途中出售所攜貨物,并享受有“俱免抽分”的免稅優待。這對暹羅國來說,是十分有利可圖的事。所以,盡管明廷早在1375年(洪武八年)通知暹羅國“入貢既頻,耗費太甚,令不必復之”,但暹羅“貢船”仍絡繹于途。從1370年至1398年的二十九年中,暹羅的“朝貢”達三十五次之多,平均每年一次以上。1403年(永樂元年)和1423年明廷一再重申“三年一貢”的限制,但仍不能抑制暹羅頻繁的“朝貢”。
柰治鴉看作為暹羅商會的負責人,他看在眼里,喜在心頭。多年的營商,讓他對古老的中華文化有了較深的認識,尤其是對李愷“廉干”欽佩有加,他多次召開會議,對李愷予以金錢獎勵。這是外商自發的褒獎官員的事,在當時也見怪不怪。在他的動議下,暹羅商人共拿出百兩黃金托柰治鴉看送給李愷。
“彼誠夷哉!吾儒有席上之聘,大夫無境外之交,王人恥邊氓之德,茲奚其至我?”他指著柰治鴉看遞來的銀票說。
“這是暹羅商人的一片熱心,是感恩您的,您還是收下吧。”柰治鴉看一再獻金。
“你們的情義我收到了,但錢鈔我是絕對不收的。你應該讀過唐代詩人白居易《三年為刺史》的詩:三年為刺使,飲水復食葉。唯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白。希望你們尊重我,讓我留個清白在東莞。”李愷一再推卻。
在人治社會,這種屢試不爽、行之有效的方式,卻在東莞的一個舶司手中揮然而去。
百金,這不僅是一筆大資金,更是暹羅商人的一片心意。按照暹羅的風俗,禮品是不可能再退回去的。對于周旋于暹羅與明廷之間的柰治鴉看,這筆錢同樣成了燙手山芋——即便退給暹羅商人,在過去交通極不發達的時代,是何等之難呀!
“我不能不從他鐵面的神態中感動,中國好官,就在東莞。”百般無奈又無比欣喜的柰治鴉看找到暹羅使者柰巴,他們要將這份感動留在中國,讓廣東東莞為官者的美德在這片大地上弘揚,讓這筆錢生長成一株株蓬勃的細葉榕,使兩國情誼與中國廉政故事枝繁葉茂。
他們匆匆地趕到廣東省府,兩個人將李愷再三拒百金的事向廣東通判御王十竹通報,并希望用李愷婉拒的百金來修建一座卻金亭,表彰像李愷一樣的廉政官員。
“忠信可以行于蠻貊,而良心之在諸夷,未嘗泯也。”王十竹同樣被李愷感動了。暹羅商人看似一個個人感恩的建議,在明代或者以后,都會成為官場道德的弘揚。他當即行文命署東莞令選址建亭和坊。
時任東莞縣令呂瓊奉命,在東莞海關所在地莞城北門外演武場(即教場)南擇地,修建卻金亭和卻金流芳坊。
嘉靖二十年(1541),東莞縣丞李楣,有一次與嘉靖十三年(1534)棄官回家的南京刑科給事中城外圓沙坊(今莞城王屋街)人王希文聚會,聊到東莞官員李愷的廉政事跡:“有坊而無碑,豈能表彰李愷之功德?”倆人一拍即合,王希文當即表示,自己寫一碑文,以昭天下廉政官員之心。
這個王希文是何許人也?
弱冠之年就入儒學為生員。明嘉靖七年(1528年)得鄉試第一(即解元),次年聯捷成進士,授刑科給事中。當時監守太監暴斂不法,以廣東市舶、珠池為甚,王希文疏奏革總鎮太監,罷粵東珠池、市舶,又奏減蕪湖、南贛、梅關八省商稅。其彈劾不避權貴,得罪輔臣夏言,改南京刑科給事中。
縣令李楣的話,攪起一潭春水。李公拒百金于千里之外不正是自己當年不懼生色之寫照嗎?想到這里,王希文已心潮賁張,連夜將宣紙鋪開,一個讓后人傳誦的故事躍然紙上:
皇明御宇,萬邦攸同,重譯頌圣,島夷獻資。然來之不拒,則偽者日趨,遂窺壟斷。爰有榷征,舶志量衡,易官互詰,課三之一,余許貿遷。叢委兌交,供億頓煩,利害均焉。嘉靖戊戌,患安李柳齋公前宰番禺,俯臨稽舶,譯究夷狀,察其費浩獲微,而吾之得不償失,咸匪永圖。乃更制設規,聽其自核,敢有詐匿者抵法。甫旬日而竣事,又旬日而化居,犬羊有知,從臾忻戴,且致私覿,以圖報稱。公麾之曰:“彼誠夷哉,吾儒有席上之聘,大夫無境外之交,王人恥邊氓之徳,茲奚其至我?”夷首柰治鴉看者再懇,再卻,乃以百金偕其使柰巴的叩之蕃司,欲崇坊以樹觀。
洋洋千言,將李公不畏浮云障眼、再三推卻百金的事跡娓娓道來。寫到這里,他又筆鋒一轉,似乎正在鍛煉東莞兒女的盛世口碑:
若夫崇坊之舉,所以峻其防也,防夷以杜漸,防民以止趨,防奸以禁匿,使庶僚知所勸且做焉。
碑文撰寫畢,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郎中番禺勞紹科用純正的楷體謄寫,奉政大夫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進階朝列大夫五羊畢廷拱篆額。
合作者三人,都是賜進士。
縣令李楣捧著三位進士的精心之作,心花怒放,當即謹立。碑高一點五七米,寬零點七四米,青色大理石質,弧首方座,四周刻飾云海紋。以此“立德立公,紀言紀事,可以備野史矣”。
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對于可以表彰的,每每都會在人們的贊嘆聲中傳誦。在卻金流芳碑建立后的第二年,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姚虞來粵視政。剛剛赴任的東莞知縣蔡存微就李愷當年卻金之事向姚虞進行了匯報。他說:“匾以族廉,盛事也,不有碑之,吾懼其猥焉圮也。”
姚虞聽罷,欣喜若狂。“唐人陳子昂說得好‘從官重恭慎,立身貴廉明。時下,官場風氣不正,李公之事,皆可樹碑宣揚以示正氣。”用碑文的形式將李愷卻金之事“以貽不朽”。
當天夜里,他奮筆疾書,撰寫了《卻金亭碑記》。
“余按南粵之境,蓋數聞卻金事。及歷東莞,又見卻金扁(匾),于心實慕焉。駐馬遲回久之,蓋重感李子之政,良心之在諸夷,未嘗泯也。”
故事從南中國海躍起,船舶、商賈,那張清瘦的面孔,串連成李愷卻金講不完的故事。姚虞巡按仿佛鋪張著早已感動自己的敘事,一點點向外延伸,他要感動一切讀者,將那一個舉動隨著時光的流失而固化起來,鑲嵌在石碑之上。“雖然,天下者,一邑之積也;一邑者,天下之推也。政有大小,而道無二致,倘臻其極,則此舉權輿之也,豈唯李子哉?維彼碑亭,起瞻壯睹,望之巋如,枚枚渠渠。賢者過之,詢之足以興;不肖者聞之,則有泚顙而赧面者也。”
書畢,又請鄭一統篆額,林應亮書丹,三個人也同樣都是進士。
卻金碑比卻金流芳碑略高大,這是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冬至日。在東莞,有著“冬至大過年”的說法。這一天,東莞人真正地過年了,這個過年,高一米八四、寬一米零二,青色大理石質、弧形方座的卻金碑,就在這個大過年的冬至日里聳立在教場路口。
二○一六年一月,距李愷上任東莞四百七十八年,離李愷任上的“東莞海關”不到五公里的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某處級官員涉嫌受賄一案。
在辯護收受某公司好處費四百四十六萬元時,這個飽讀史書的官員竟然發出“雷語”:“該公司給的錢主要是給我一個壓力,也算是一個獎勵”,“設置獎勵是希望我有積極性盡快去解決問題。”受賄成了“獎勵”,將手中的權力作為奸商賺取最大利益的工具和“投資”。
“有兩樣東西一直讓我心醉神迷,越琢磨就越是贊嘆不已,那就是——頭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這段話,刻在德國哲學家康德的墓碑上。哲學家告訴我們,面對種種誘惑,面對社會中的道德法則,我們要做的,是時時刻刻的自省和自律。
“自省”和“自律”,看似簡單的四個漢字,卻蘊含著極重的道德定律。這個處級官員也飽讀過史書,一定到過位于莞城的卻金亭,據說他還在一次會上大談李愷卻金的故事。
歷經五百年風雨,卻金坊如何設置已找不到記載,卻金坊也早已不存,曾立于莞城外演武場(今光明路教場口一帶)的卻金坊記碑,現存在東莞市博物館內,碑刻完整,字跡清晰,讓人耳目一新。
大浪淘沙,時光的洪流給東莞留下的不僅僅是河道與沖積平原,前所未有的財富、人口和貨物都因為貿易與交通匯聚在這里。而兩塊石碑,給一代又一代后人講述著東莞故事。
在恒久的時間里,或許東莞官員李愷的一個舉動算不了什么,甚至可以說是微不足道。但是,聳立的兩塊富有生命力的石碑,因為生動在文字里的故事,讓我們的血脈賁張起來,讓民族的血脈賁張起來,充滿活力地綿延開來,成為一本厚重的廉政學辭典。
林漢筠: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文學創作二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