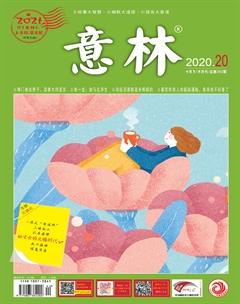宋代舌尖上的節儉之風
戴永夏
古人的節儉之風體現在各個方面,而舌尖上的節儉尤為突出。這方面,普通百姓自不待言,多數士大夫也以儉為美。特別在餐飲文化比較發達的宋代,許多名士大家都以儉樸引領時尚,成為后世的楷模。
蘇軾:粟飯藜羹間養神
北宋元豐三年(1080),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到黃州任團練副使(相當于縣武裝部副部長),一家人的吃用只靠他微薄的收入來維持。

為此,他絞盡腦汁,精打細算:每月初一這天他便從積蓄中取4500錢等分為30串,掛在屋梁上,每天用畫叉挑下一串來做飯錢,這樣每天的用度不得超過150錢,剩下的就放進一個大竹筒里,用來招待客人。就是這樣儉樸度日,蘇軾依然過得有滋有味。
平時,他在生活上也嚴格要求自己,堅決反對大吃大喝。他曾寫過一篇《節飲食說》的小文,貼在自家墻上,讓家人監督執行。他告訴家里人,從今以后,我每頓飯只飲一杯酒,吃一個葷菜。若有貴客來訪,設盛宴招待,也不超過3個葷菜,而且只能少不能多。如果別人請我吃飯,也先告訴人家,不要超過這個標準。若人家不答應,就干脆不去赴宴。他認為這樣做一可安分養福氣,二可寬胃養神氣,三可省錢養財氣。一次,一位久別重逢的老友請他吃飯,他囑咐朋友千萬不可大操大辦。幾天后,他應約去老友家赴宴時,見酒席異常豐盛,便婉言謝絕入席,拂袖大步而去。他走后,老友感慨說:“當年東坡遭難時,生活很節儉。沒想到如今身居高位,依舊本色不變。”
蘇軾還提倡蔬食養生的理論,并身體力行之。
他在各地做官,都常去挖野菜吃。他在《宋喬全寄賀君》一詩中寫道:“狂吟醉舞知無益,粟飯藜羹間養神。”以自己的經驗勸別人不要醉生夢死,而要粗茶淡飯養生。
司馬光:隨家所有自可樂
作為一名政治家,司馬光似乎比蘇軾更加成熟、老練,官也做得更大。但在生活節儉上,二人卻如出一轍。
司馬光在宋哲宗當政時,就已擢升為宰相。這以前,他曾辭掉官職,在洛陽居住15年,專門編寫《資治通鑒》。在洛陽期間,他同文彥博、范純仁等后來都身居相位的同道,相約組成“真率會”,每日往來,不過脫粟一飯、清酒數行。
相互唱和,亦以儉樸為榮。文彥博有詩曰:“啜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范郎貧。”范純仁和之曰:“盍簪既屢宜從簡,為具雖疏不愧貧。”司馬光又和道:“隨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微誰笑貧?”寥寥數句,充分表達了他們興儉救弊的大志。
司馬光居家講學,也是力行節儉,不求奢靡。“公每五日作一暖講,一杯、一飯、一面、一肉、一菜而已。”(《懶真子》卷第十)這就是他講學接受的招待。他回故鄉山西夏縣祭掃祖墳時,父老鄉親前來迎候獻禮,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他“享之如太牢”,覺得味道勝過魚肉。
陸游:從來簡儉是家風
陸游是宋代著名的愛國詩人。在文學上,他與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齊名,并稱“宋代四大詩人”;在仕途上,他始終堅持抗金,屢遭當權派打擊,遭遇比較坎坷;而在生活上,他力戒豪奢,一直以節儉為榮。
陸游對飲食講求“粗足”,力求清淡。他主張多吃蔬菜,如白菜、芥菜、芹菜、香蕇、竹筍、枸杞葉、菰、茄子、薺菜等,都是他喜愛和常食的蔬菜,而葷菜少之又少。他說,之所以這樣節約,不只是為了省錢,“不為休官須惜費”,這還是一種良好的家風,“從來簡儉是家風”。更何況,“鄰家稗飯亦常無”,自己吃粗茶淡飯,心中更坦然一些:“但使胸中無愧怍,一餐美敵紫駝峰。”
陸游不但自己生活儉樸,還要把這種儉樸家風傳之后世。他讓后代子孫務必引以為戒,不為所動,將節儉家風世世代代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