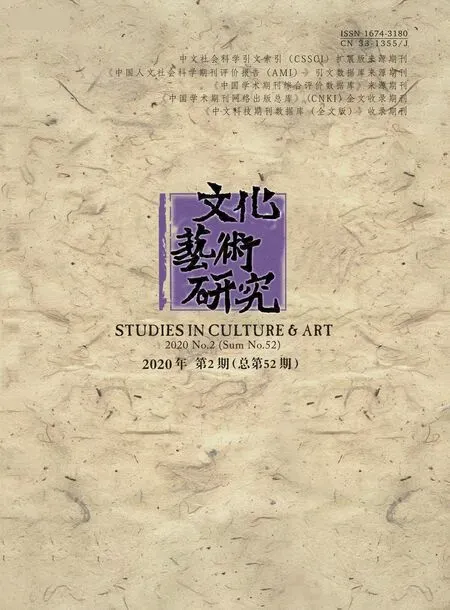畫框的“劃界”功能及其認識論意義*
湯克兵
(重慶師范大學 文學院,重慶 401331)
畫框或框架,英文中寫作“frame”,法文中寫作為“cadre”。根據法國拉魯斯出版公司出版的《西方美術大辭典》,“框架”的本義是繪畫中的畫框,是用于展示和保護二維藝術品(油畫、素描、版畫、刺繡)或浮雕的可拆卸的部分。這個詞是從意大利語中的“quadro”派生而來的,最早用來指呈正方或長方形的木質邊框,后來不再限于其外觀形制,含義更廣。框架回應的是將有形空間進行限定的需求,這種需要具有普遍性,體現在古代及中世紀壁畫中使用的簡單封閉線中,也見于手稿畫的鑲飾和17世紀版畫肖像的邊框。不過,嚴格意義上的畫框僅用于可移動的藝術作品,這種藝術作品是堅硬的(因此不包括書籍和遠東地區的卷軸),而且獨立于它所處其內的建筑。[1]《西方美術大辭典》實際上從廣義和狹義兩個層面對繪畫邊框的功能變化進行了概括,而且主要將畫框的概念限定于其物理層面的形制變化。因此,畫框通常被看作是藝術作品的一個外在物理框架,藝術史學界對畫框的意義往往缺乏充分的認識,即使偶爾提及,也只是當作一種趣味,視之為藝術作品的外在裝飾物,并沒有揭示出畫框的根本要義。本文主要從藝術史和哲學意義上來考察“畫框”的雙重內涵,即作為物理層面的“畫框”與觀念上的“框架”(也譯為“框子”),試圖揭橥畫框之于藝術圖像意義表達和美學話語建構的重要性。
一、畫框、邊界意識與繪畫空間
從大多數史前洞窟藝術(cave art)的圖像特點來看,遠古人類并沒意識到圖像與現實之間存在著某種明確的界線。繪畫者一般在墻壁或巖頂上的表面涂畫,也想不到將圖像物置于某個特殊的邊框,所以基本上不會考慮工作面的任何情況,他繼續在原畫之上畫他的獵物,也不需要把載面擦洗干凈,人們似乎看不到舊畫。與后世藝術家們對作畫場地態度明顯不同,遠古人類并不認為他畫的圖像必須與背景形成對照。[2]進一步來講,史前的繪畫者并不認為自己在巖壁上繪制圖像就是在創作“藝術”,更不會把圖畫空間看作是與現實空間不同的東西。研究表明,當他們在作畫的時候,很可能是因為內心的律動和為了領受神秘的意旨而創造了這些“作品”,“當他們在不規則的巖壁表面繪制出各種動物的圖像時,這些圖像就等同于動物在場。這些動物的圖像沒有邊框圍繞,說明這些圖像不屬于一種藝術世界中的繪畫,而是對這些鮮活牲畜的準巫術式呈現,是一種虛似的現實”[3]。或許在原始人類的心智中,圖像的在場就意味著真實性。目前人類學家也普遍認為,他們畫動物是為了打獵時能夠準確識別它們,同時也是為了保證打獵成功而進行的巫術儀式,因而沒有意識到圖像本身的造型和組合秩序問題,當然也就不會考慮圖像的邊界問題。這意味著,在沒有人造邊框、畫地平線和背景的情況下,仍需要確定這些圖像對于早期社會來說是否代表著一種神秘的真實。[4]

圖1 瑞典希維克(Kivik)石板畫,約公元前3000年
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附有邊框的圖像出現在了瑞典希維克(Kivik)石板畫上:兩邊各有一條豎線,兩條橫線上下平行分布(圖1)。當人們刻意地采用邊框線將圖像區域與載面區分開來的時候,畫框的原型出現了。在公元前2900年左右,毛伊島(Mari)宮殿和克諾索斯(Cnossus)城堡墻上,統一的色調或簡易圖案裝飾著不同的場景,墻上的空間劃分出不同的主題。多年以后,羅馬地下墓室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5]種種跡象表明,為了著重強調所描繪的事物,圖畫必須與外在環境區隔開來;與對現實中環境的一般認知不同,人們開始將某個圖像置于一個虛擬的空間內部。這樣,圖像的邊框就起到了物理和視覺層面的限制作用。由于明確了繪畫的區域和邊界,藝術家就只能在有限的空間內選擇恰當的造型要素來再現圖像主題或內容。由此看來,隨后陸續出現的教堂壁畫的建筑邊飾、祭壇裝飾畫的邊框以及架上畫的畫框,雖然在形制和材質上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差別,但從總體上來看都是作為一種物理和觀念上的邊界標記,強化了繪畫的再現空間與現實的物理空間之間的區隔。而且,從慣例上來說,自繪畫附帶一個邊框開始,圖畫空間就開始受制于邊框及其載體。
從表達宗教意義的藝術圖像來看,不管其載體是壁畫、手稿還是祭壇畫,畫家或工匠們如何在有限的載面繪制符合文本(委托合同與《圣經》故事)要求的圖像成了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因而,“在此之前的整個中世紀期,繪畫藝術不是獨立的,而是作為某個完成物的裝飾而存在。不管這件東西是一個盒子、一座大教堂、一頁手抄書籍,還是一塊城堡內室的墻面,它都完成于繪制裝飾之前,它不是根據裝飾設計的——那是以后布面繪畫或板壁畫的情形——而是根據人們所規定的用途設計的。裝飾者只是在結構留下的空白中——如果可以這么說的話——作畫,因此,被裝飾的東西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邊框強加給圖像”[6]1-2。
圖畫空間的再現往往受制于邊框及其載體特征,最為明顯的是歌特式繪畫。中世紀晚期,意大利教堂寬大的墻面和平滑的拱頂,為表現圣跡或逸事的圖像制作提供了條件,喬托式的大型敘事性壁畫出現了。但在歐洲北部地區,歌特式大教堂建筑的尖頂結構和繁復交錯的拱肋構造擠占了墻面面積,墻體因此被分割成許多同豎跨相適應的縱向間隔。這樣,過于零碎的“空白”已經不再適合于敘事性大壁畫,工匠和藝術家們只能勉強從尖拱拱肋組成的圖案上取得造型效果。由于需要繪圖的墻面逐漸減少,他們開始在有限的邊框里爭取更多的繪畫空間。盡管早期基督教藝術將這類框邊改造為象牙書籍封面和雙連畫的雕飾邊框,但在這樣的邊框內,圖畫只能以圖案的方式表達宗教主題,卻無法充分再現圣經故事。而彩色玻璃窗空間位置較高,看起來不方便,出錢建造的捐贈人的面目又遙遠難辨,而他們總是希望把自己的肖像放在顯眼位置上,于是祭壇畫應運而生。[6]5祭壇畫誕生于14世紀。它的出現證明了繪畫開始拒絕淪為建筑的從屬物。特別是小型祭壇畫,其最為顯著的優勢是它可以搬動,不再處于一個固定的地點。多明我派神父喬萬尼·多米尼奇(Giovanni Dominici)就曾大力提倡,每個家庭都要采用小型的床頭祭壇畫,以便家庭中的進行禮拜和慶典活動。[6]6祭壇與建筑的聯系雖然不再那么緊密,但并沒有像架上畫那樣擺脫一切束縛,祭壇畫作為圣像畫,被限制在固定的地點,主要起宣傳教義的作用。為了強化圖像的宗教意義,作為祭壇裝飾的框架通常仿效教堂的剖面、“中殿”“走廊”和“地下墓室”等結構,因此這類“畫框”就不僅具備了形制上的裝飾功能,而且具有了圖像學主題的內涵,即象征著教堂之門為我們打開了精神上的世界(圖2)。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盡管祭壇畫的邊框沒有完全獨立于它所處的(物質層面或象征層面的)建筑,但一般來說,祭壇式畫框的制作先于圖像繪制,畫框事先決定了繪畫內容的安排。[7]而且在當時,制作畫框的經濟價值要遠遠高于制作圖像。

圖2 《圣母領報》,西莫尼·馬爾蒂尼,1333年
直到15世紀,伴隨著“繪畫”概念自身的發展,出現了嚴格意義上的“畫框”。根據牛津英語詞典的記載,首次在藝術層面上使用“畫框”這個詞,大約是在1600年。[8]所謂“繪畫”概念自身的發展,實際上暗指架上畫的出現,標志著“繪畫”開始擺脫宗教語境(教堂),作為藝術作品掛在中產階級的墻壁上供人觀賞。關于這點,維克多·斯托伊奇塔(Victor I.Stoichta)從宗教改革與藝術觀念的關系角度給出了自己的解釋。根據他在《圖像的自我意識》一書中的考證,架上畫誕生于1522年德國的魏登伯格第一次圣像破壞運動之時。在此之前,壁畫與祭壇畫等繪畫中的圖像常常擁有這樣的功能,而被新教徒指責為褻瀆上帝:圖像聯系著基督教義,被置于界限清楚的語境(教堂)中,而且應該被膜拜。然而在當時的神學家卡爾施塔特看來,制作圖像并放在教堂里供人跪拜,顯然違背了《圣經》中“不可雕刻圣像”的第一戒律,尤其是將圖像置于祭壇之上為最甚。[9]正因如此,在三次階段性的、最具影響力的偶像破壞運動過程中,許多教堂的壁畫不斷被白墻覆蓋,祭壇畫也多次被燒毀。繪畫因此脫離了作為教堂裝飾的語境,從圣像時代走向物的時代。畫框使其自身獲得獨立物的身份,成為架上畫不可分割的部分,甚至成為繪畫的代名詞。
二、作為審美界限的畫框
不管是具有鮮明宗教背景的壁畫和祭壇畫,還是表現世俗生活的架上畫,繪畫都可以被指稱為邁耶·夏皮羅與托馬斯·普特法肯所說的“有邊界的圖像”(bounded image)。在夏皮羅看來,歐洲傳統有邊界的圖像具備三個基本特征:畫框或邊界、平滑的表面、通過畫框或邊界隱藏其后的繪畫空間的呈現。①“有邊界的圖像”這個術語,源自托馬斯·普特法肯對藝術史家邁耶·夏皮羅的借用。托馬斯·普特法肯認為,“有邊界的圖像”不僅和“架上畫”有同樣含義,還包括了大部分文藝復興藝術中的架上畫或舞臺畫不能涵蓋的祭壇畫以及很多壁畫。早期圣像、傳統的透視畫和錯視畫的平滑表面的“正面性”優先于邊界內的空間圖像,具有引導我們關注、聚焦和瞄準的圖畫意圖,并賦予朝向觀者的專屬感。托馬斯·普特法肯拓展了“有邊界的圖像”的現代內涵,暗示可以解釋伯林伯格所認為的現代主義繪畫。參見Thomas Puttfarken: The Discovery of Pictorial Composition: Theories of Visual Order in Painting 1400-1800,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age 20-30。平滑的表面與繪畫空間這兩個特征總是伴隨畫框或邊界的預先設定而存在。正因如此,作為邊界的畫框看似是繪畫的一個外在附屬物,卻又為繪畫提供了一個“內部”空間,畫框總是需要一幅畫來充當其“內部”,即使在其內部缺席的情況下,畫框將寓于其間的任何可見之物都轉化為一幅“畫”,并使畫面得以確定自身的規定性。這意味著,畫框作為一種原初中介,總是先在地標劃“界線”,經由“邊界”的介入,事物才得以相互區分,事物才得以取其形態。[10]畫框將“圖像”從“非圖像化”的事物中分離出來,它賦予所框之物一個意義世界,并與框外世界相對立。這個被分離出來的世界,在蘇珊·朗格看來,是一個獨立自主的繪畫世界,“它受到畫框、邊緣的空白或其他將其割斷的不相關的事物的限制”,因而“被創造的視覺空間是完全自足的、獨立的”[11]。
阿恩海姆從美學的角度明確地提出了畫框的這種區隔性。畫框并不只是限定圖像的范圍,它更將日常生活環境與圖畫內容區分開來。在這里,畫框就充當了一種原初的界線,使得作品能夠陳述自身,而不再被視為現實環境中的一個有機部分,“當藝術品成為一個陳述時,它變化了的現實地位是通過與周圍環境的明顯分離表現出來的”[12]。我們需要現實的墻面迅速而突然地隱退,這樣我們才能處于圖畫的非現實領域。所以,隔離是需要的,而畫框就是這種隔離裝置。作為一種隔離裝置,宗白華將之視為“間隔化”:“美的形式的組織,使一片自然或人生的內容自成一獨立的有機體的形象,引動我們對它能有集中的注意、深入的體驗……美的對象之第一步需要間隔。”[13]類似于繪畫的畫框、雕像的基座和建筑的欄桿臺階等外圍構件,都能夠發揮各種間隔作用,進而展開對視線和注意力的重新組織。齊美爾認為,對藝術作品來說,畫框的邊界功能體現在通過中立和抵制外部,達成關涉內部的統一整合。畫框將所有圍繞它的事物以及觀看者從藝術作品中區分開來,由此有助于將作品單獨置于那種帶來審美愉悅的距離中。[14]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畫框的隔離作用起到了一種審美靜觀效果:促使我們在將視線從日常生活世界移到圖畫世界里的同時,也連帶地轉變了觀看事物時的心理狀態。當我們看著家里的墻壁時,采用的必然是一種實用性的眼光;當我們觀看繪畫的時候,我們進入了想象的空間,那是一種純粹的注視的態度。這就好比從窗戶內朝外看,盡管從畫框里看到的并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但是,這是一個由僅次于上帝的藝術家創造的世界,一個虛構的、僅次于現實的幻覺世界。藝術家精通透視技巧,好讓我們從二維平面看到三維的畫面。畫家的作品懸置了我們的疑惑。要達成與藝術家的合作,需要我們脫離現實場景,忽略作品邊界之外的東西。由此,畫框在邊界之處豎立審美屏障——畫家創造的虛假世界不受外部現實的干擾,進而保持我們與藝術家的虛假協作關系。這樣,我們就不會過多地專注于畫框。我們關注的是畫面,要看透畫框,穿過畫框,進入畫面。然而,倘若畫框讓我們專注于畫面,那么也應讓我們意識到圖像世界的虛假性,認識到畫面與真實世界的距離。畫框在再現框中之物的同時,又讓我們駐足思量,讓我們擺脫一般的功利性關注,轉而觀照再現對象。實際上,畫框的這種裝置功能,有助于確立布洛所說的“心理距離”。所謂的“心理距離”并不是指實際空間和時間意義上的“距離”,而是指介于我們自身與我們的感受之間的距離,而我們的感受是指“一切在身體上或精神上對我們發生影響的事物,它們使我們形成感覺、知覺、感情狀態或觀念”[15]。例如面對海上起霧,如果船員能夠超越個人利害關系(如擔心、恐懼、緊張、焦慮等),而在自己與海霧之間建立一種心理距離的話,就不會注意到海霧可能帶來災難,相反,能夠欣賞到海霧的奇妙景致。概而言之,“心理距離”猶如建立了一道無關自身利害的安全屏障,不僅摒棄了事物的實際的一面,而且在距離的抑制中,肯定了感知對象在日常中意想不到的一面。因此,在布洛看來,心理距離是我們的這些感受的源泉或媒介,是一切藝術的共同因素,也是一種審美原則。
由于畫框起著原初中介或劃界的作用,因此,作為第三方,畫框在分割“內”與“外”的同時,實際上又縫合著兩方。也就是說,為了區分藝術空間與現實空間,也應承認“邊界”的人為制造性或虛構性,使得作品能夠擁有那種帶來審美愉悅的距離。畫框既不歸屬于圖像的內在結構,也不能被視為繪畫外在環境的物件;畫框既不能等同于繪畫空間,也不能等同于觀者的現實空間。畫框的邊界效應正是其魅力之所在,它是審美感知得以發生的前提條件。
三、畫框的“框架過程”
在《判斷力批判》中,康德回應了作為附屬物的畫框與審美知覺問題。康德從形式與美的關系這一角度討論了“裝飾”的功能。在眾多裝飾物中,他列舉了宮殿周圍的柱廊、雕像的衣著和畫框。提及畫框,康德稱之為外在的附屬物和點綴,“只不過是由于它們使這種形式在直觀上更精確、更確定和更完全了而已,此外還通過它們的魅力,通過它們喚起并保持著對對象本身的注意力而使表象生動起來”[16]。康德強調了注意力的審美轉換問題,但又區分了裝飾和藝術作品自身的構成物。一般說來,鍍金邊框只是為繪畫增添魅力的一種裝飾,它自身并不具有美的形式,如果一定要安裝在繪畫之上,反而對繪畫內在的美造成了破壞,那就成了一種惡意的修飾了。在康德看來,畫框之類的外在裝飾或附屬物,旨在服務于美的內在形式,但并不是美的內在秩序的構成部分。畫框如果過分引起觀賞者的注意,就是喧賓奪主,也就破壞了美本身。顯然,康德關于內在于和外在于某個趣味判斷的裝飾物的理解,已經超出了知覺層面的解釋,其間隱含了人為的理性區隔,例如,“內在形式”與“外在裝飾”的區分。康德關于“美的分析”,好比判斷一件藝術作品是“美”的時候,就必須給這件作品配置一個“畫框”。在《繪畫中的真理》一書中,德里達批評了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涉及的“畫框”概念。康德認為美不在對象本身,而在對象的形式中。美學判斷之所以不同于認識論,是因為它超越知識經驗,是無功利的,它只服從自身的內在邏輯,即所謂的“自我界定”(selfgrounding)。然而在德里達看來,康德的這個“自我界定”其實源自《純粹理性批判》,是從他之前的認識論框架發展出來的美學邏輯。[17]這意味著,康德對美的分析總是需要以認知判斷作為框架。因此,“畫框”或“框架”并非與作品無關,正是這個來自外部的附屬物,使得內部的作品成為內部,正如羅德維克所說:“正是堅決主張給畫作裝框——一方面明確了藝術自我身份的性質和范圍,另一方面也精確地解釋了審美判斷的特異性——事實上,它是致使主體與客體、畫內與畫外、心智與自然產生各種分裂的因素,它們是第三批評宣稱要超載的內容。”[18]
一般來說,為了把一個事物與另一事物隔離開來,我們需要一個既不是首要的也不是次要的第三方,即一種劃界的中介之物。在這里,畫框既不是現實世界中墻壁的附屬物,也不是那極具魅力的繪畫表面。作為界線的劃分,畫框有助于短暫剝離墻的功能。對康德而言,畫框(裝飾)的介入,其目的是實現審美態度的客體化,繪畫之所以要配置畫框,是因為畫框有助于繪畫呈現審美存在;但根據“美的無目的合目的性”原則,畫框或裝飾本身又并不具有美的形式。事實上,畫框在圍構圖像的內部同時,也產生了一個需要交流的外部因素,也就是說,它必須也把自己視為另一種情形下的“內部”,才能作為“外部”圍構之前的“內部”。因此,畫框在產生新的外部環境的同時,實際上又在不斷地制造“內部”與“外部”互相嵌套的邏輯。克里斯托弗·諾利斯(Christopher Norris)把畫框的這種悖論性存在稱為“界線的標志”(the marker of limits),他說:“在藝術作品(本體)與歸屬于背景、語境,展覽空間,舞臺設置或者諸如此類的事物之間,畫框建立了一個無法滲透的邊界。”更重要的是,諾利斯也提醒我們,制造邊界的畫框“或者只是我們的一種假設”。[19]言外之意,我們不能孤立地從一方的所框之物或從另一方的框外之物中,去確證某種界線的存在。藝術作品與畫框之間的對立假設,只是為了掩蓋(一件藝術作品、一個文本或一種話語的)內與外之間的隱喻關系。當敘事與框架之間、作品的“內部”與“外部”之間的對立因質疑而失效時,人為制造的框架(邊界)會跟著坍塌消失,從而破壞了探尋真理的美學觀念,這也意味著框架過程的重啟。實際上,并不存在某個實質意義上的框架,所以德里達說:“確有框架過程,但框架并不存在。”[20]畫框或框架只是使某種內在機制得以運作的外部力量,作為一種原初陳述,它是藝術成為藝術的一種替補邏輯。它總是處于我們觀看的規則之外,卻又制造了規則本身,類似幽靈之物,框架存在(being),但并不實在(existence)。
畫框的這種框架過程實際上涉及朗西埃所說的“可感性分布”(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這種可感性分布就是廣義上的美學或政治,朗西埃將之定義為是對“可感知、可見和可說事物”[21]的劃分,它決定了行動、生產、感知與思想形式之間的聯結模式,也預設了可感性的邊界。在某個特定的共同體中,可感即可分享,它決定了何種聲音能被聽見,何種東西能被看見,故而“可感性”分配機制實際上也是一種納入和排除機制。畫框的“框架過程” 與“可感性分配”秩序一樣,也服從于納入和排除機制,它決定了何者可見,何者不可見,何者是藝術,何者不是藝術。如此看來,畫框遵循的是一種倫理和實踐原則,它將認同與分化原則聯結起來,其間可以抽繹為一種等級秩序:“人們所能感知的和他們能理解的,是他們所作所為的嚴格表達;他們的所作所為由他們是什么所決定;他們是什么由他們的位置(place)所決定,反過來,他們的位置又為他們是什么所決定。因此,支撐框架過程背后的倫理秩序不僅是一個共同體諸種位置、職業和能力的井然有序的等級性體系,它也是對可視性、可想性、可能性的全面組織。”[22]藝術史學家杜羅(Paul Duro)指出,作為話語構成的“畫框”同樣遵循內化的實踐原則,它使藝術作品在可見空間內獲得自立,使再現成為排他性的在場。畫框如實地界定視覺感知的條件,也同樣界定了再現的意圖……經由畫框,圖像決不只是看到的一個事物:它變成了沉思的對象。[23]這意味著,畫框(基座)作為繪畫(雕塑)的一個歷史慣例和本質規范,已然不是藝術作品的某個外在附屬物,也并非如康德所說的僅僅是繪畫的金色邊框、雕像的基座和建筑的柱廊之類的外圍構件,它本質上是藝術本體的“蹤跡”,是繪畫之為繪畫的規定性,是使建筑最終完工的“腳手架”。畫框并不只是將作品從外部分割出來,更重要的是,畫框將“作品與“作品的外部”縫合在一起,提供了某種意識形態的語境,使得作為“內部”的“作品”成為可見與可說的對象。
小 結
通過上述對畫框“劃界”功能的闡釋,我們希望打破一種習見,即認為畫框就是一個裝飾物,主要作用是展覽時便于將圖畫掛在墻上供人欣賞。不可否認,觀看繪畫作品的時候,觀者希望通過有限的圖像再現捕捉到圖像之外的豐富意涵,因此,圖像仍然是我們討論藝術作品的重心。然而,圖像觀看與解讀過程中,實際上有一套隱含的觀看機制。畫框作為一種歷史慣例,深深地影響了我們觀看或者理解圖像本身的過程。觀畫過程中,圖像的再現、審美的發生,以及對構圖的解釋,都繞不開畫框。但為何我們不去關注畫框本身呢?可見,正是其邊緣性、不被看見等特點,決定了畫框往往以一種“反客為主”的方式,構建了整個觀看機制。對畫框的本體論思考,有助于我們反思藝術作品的制作和接受過程,進而審視藝術觀念等更具本質性的問題。現代藝術對畫框的破壞與摒棄,實際上也是想打破我們將畫面視為窗口的習見。繪畫不再受制于邊框內的圖像展示,而是破框而出,成為實際生活中的真實展演。這也啟發了諸如極簡藝術、偶發藝術、大地藝術等各種后現代藝術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