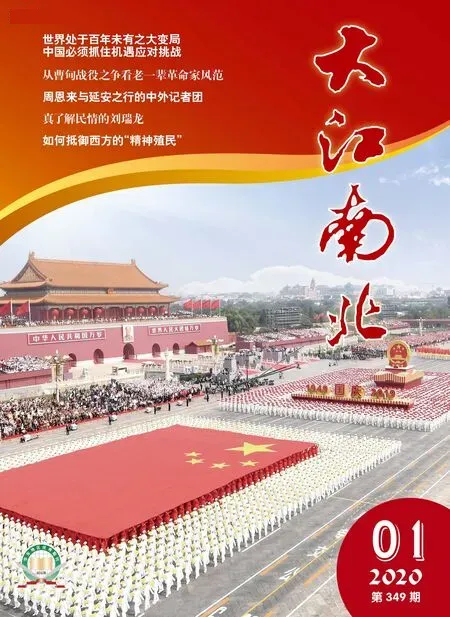從曹甸戰役之爭看老一輩革命家風范
□ 韓立堅
曹甸是蘇北寶應縣東北的一個集鎮,當年,這里曾經爆發了八路軍、新四軍與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部之間一場戰役。曹甸戰役從謀劃到激戰,乃至結束,我軍指揮部內部有過多次爭論。
1940年下半年黃橋決戰勝利,八路軍與新四軍勝利會師,使華中敵后形勢有了好轉,但兵敗黃橋的國民黨頑固派韓德勤退至興化、曹甸、東橋地區后,反共之心不死,積極構筑層層防線,企圖截斷蘇北和皖東新四軍、八路軍聯系;東北軍霍守義部112師共4000多人,以“武力調停蘇北摩擦”為由,從山東南下蘇北,并已進至淮陰以東蘇家咀一帶,即將同韓德勤部會合。在這種情況下,我軍要想在蘇北立足并開創抗戰局面,勢必要與韓德勤部再決一戰。
對此,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領導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究竟是先鞏固根據地,發動群眾,把腳跟立穩,再去攻韓,還是先打掉韓德勤部,徹底解決蘇北問題,領導人之間存在不同意見。時任中原局書記的劉少奇希望徹底驅逐韓德勤,建立抗日民主的新江蘇;總指揮部代總指揮陳毅也想挾黃橋決戰勝利之師的余威,一舉殲滅韓德勤余部。劉少奇、陳毅想到了一起,決心發起曹甸戰役,但沒有想到召集華中新四軍、八路軍各路將領開會研究部署時,八路軍第五縱隊司令員、政治委員黃克誠卻堅決反對倉促攻打曹甸。
黃克誠認為,曹甸雖然遲早必須攻打,但目前不宜。第一,政治條件不成熟。現在在搞統一戰線,黃橋決戰是韓德勤主動犯我,而現在則是我方攻韓,政治上被動。第二,我們剛剛占領淮海、鹽城地區,還沒有站穩腳跟,當務之急應是發動群眾,消滅蘇北偽頑殘部、土匪、特務、反動地主武裝,鞏固根據地,再打韓德勤也不遲。第三,曹甸是韓德勤苦心經營多年的老巢,防御體系堅固,又是水網地帶,易守難攻,而我軍缺少攻堅武器,軍事上并無把握,故暫時不打為上策。
黃克誠的意見未被采納,劉少奇、陳毅上報曹甸戰役計劃,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有條件地批復了作戰計劃(不得攻擊興化,保留韓德勤以利統戰大局)。黃克誠雖不同意發起此次戰役,但上級既然決定了他就堅決服從,命令八路軍第五縱隊中戰斗力最強的第一支隊和第二支隊第687團投入戰斗。
11月29日夜,曹甸戰役打響。曹甸是通過運河與皖東聯系的戰略要地,韓軍工事堅固,駐有5000多兵力,在北邊還駐有韓部23師和東北軍霍守義部,隨時可以策應曹甸,結果果如黃克誠所料,曹甸久攻不克,敵我雙方僵持不下。目睹我軍受到嚴重挫折,黃克誠心急如焚,感到這樣死打硬拼絕非良策,就發電報給華中局(原中原局)并報中央,提出了改變曹甸戰役打法,具體建議:一、在敵據點間構筑據點,截斷敵聯系和增援;二、把外圍敵人全部逼入敵據點內;三、逐步筑壘掘溝推進;四、運用小部隊接近,耗敵彈藥,增其疲勞;五、派小組潛入,放火燒其房屋;六、猛擊敵弱點,強攻則集中全部迫擊炮、小炮轟擊之。
黃克誠的建議再次被否決,華中指揮部遂于12月12日下達總攻命令,但我軍最終未能突破頑軍陣地,參戰部隊遭受重大損失,劉少奇于19日命令參戰部隊撤出戰斗,歷時18個晝夜的曹甸戰役結束了。
但是曹甸戰役之爭并未結束。戰役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華中局認為主要原因是黃克誠右傾保守,攻擊時不夠堅決,造成曹甸久攻不下。因此,撤了他第五縱隊司令員一職,保留政治委員職務。后來華中局在阜寧召開領導干部會議,陳毅又批評了黃克誠。開始黃克誠覺得委屈,據理力爭,最后他委曲求全,違心地作了檢查。
曹甸戰役之爭算是作了結論,但曹甸戰役之爭引起的反思仍在繼續。1942年,陳毅痛定思痛,在《曹甸戰斗總結》一文中坦承:“曹甸戰役是我去攻擊人家,缺少理的。”“我很輕敵,倉促作戰,準備不夠,變成浪戰。”“我們的戰斗手段是攻堅,這就要有很好的準備和按攻堅戰原則作戰才行。”“當時我們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攻是解決不了問題的。”1945年10月,陳毅在山東臨沂歡送黃克誠出征東北時,當著政委羅榮桓的面,對黃克誠說:“過去我也有批評錯的地方,請你多加原諒。例如曹甸戰役,我和少奇沒有聽取你的意見,堅持要打,結果沒有打下,我軍傷亡很大。最后批評你三師(八路軍第五縱隊以后改編為新四軍第三師)配合不力,撤了你的職,其實責任在我……不看你的功勞,指責你態度不好,指責你把問題直捅延安。”“是我有錯,向你道個歉。”
劉少奇也曾作過不同程度的自我批評。1944年7月10日,劉少奇在給黃克誠的信中寫道:“至于曹甸戰役,本來是可以不舉行的……我沒有細心考慮,急促下決心向頑軍進攻,這是我負責任的。后來強攻曹甸,也是不應該的。”“當時你反對強攻是對的。至于曹甸戰役未能完成任務,當然不能由你負主要責任。”
曹甸戰役已過去80個年頭,當年的硝煙不但早已換來了“紅旗十月滿天飛”的壯美世界,而且也留給我們無盡的思考,帶給我們無盡的感動和精神力量。
著眼大局、直言敢諫的忠誠品格。
當劉少奇、陳毅攻擊曹甸決心已下,召開會議部署時,黃克誠不是揣摩領導意圖,唯唯諾諾,隨聲附和;也不是緘口不言,留有余地,明哲保身,而是堅持從實際出發,提出了緩攻曹甸的建議,并分析了緩攻的理由,實際上是唱了反調。當他的建議遭否決后,見攻擊部隊傷亡過大、久攻不下時,他又建議停止強攻,并舉出了六條理由。黃克誠不會不懂得軍隊下級服從上級的道理,不會不知道一味違悖領導意圖,可能對自己產生不利的后果。實際上他就是因為直言敢諫,多次被批評為“右傾保守”,常常降職使用,長征時曾被撤銷所有領導職務,擔任偵察員,但他仍然不計個人得失,總是從大局出發,敢于犯顏直諫,在黃克誠身上,完美體現了“在諍諫不計個人得失、征戰不避自身兇險”的優秀品質。服從真理、勇于認錯的民主作風。
黃克誠承擔了主要責任,受到撤職的處分,曹甸戰役有了上可對中央交待、下可對部隊證明甚至可以對歷史負責的結論。但劉、陳并不因為這場充滿爭議的戰役性質有了定論、責任有人承擔而心安理得,也不是時過境遷而選擇淡忘,更不是為了維護個人威信而一意護短、諱疾忌醫,而是痛定思痛,深入反思,通過撰文、寫信、談話,多次承認錯誤,承擔責任,向他們的下級黃克誠當面道歉。在他們的心目中,不是計較領導權威,而是真理為尊;不是自視特殊,而是上下級平等;不是一味獨斷專行,而是尊重下屬意見;不是唯個人好惡、個人意志,而是以革命事業為重。實踐證明,老一輩革命家這種民主作風,不僅沒有影響他們的形象,反而得到人們由衷的敬佩。豁達大度、不計毀譽的坦蕩胸懷。
在曹甸戰役之爭中,黃克誠受到了上級并不正確的批評和指責,受到了組織上并不公正的對待,但黃克誠卻表現出堅強的黨性,不但從無怨言,從不計較個人恩怨,而且從不消極,從不改變獨立思考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品格。當劉少奇、陳毅主動向他承認錯誤時,他反而寬慰領導。值得注意的是,對于可以證明他見解正確的曹甸戰役,他在《黃克誠自述》一書中只字未提,這不是一般的遺漏,而是不愿顯露自己而已。其實,胸無芥蒂,胸懷坦蕩,是他一貫的品格。在工作上,他常與一些領導、同事爭論得面紅耳赤,有時乃至爭吵,但事后從不計嫌,仍然親密無間。1959年廬山會議,他被打入“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受到了殘酷迫害。“文革”后復出,面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評價問題上的“凡是派”和以“解放思想”為名的曲解派,被趕下政壇達18年之久的黃克誠不是乘機泄私憤、倒苦水、算舊賬,而是憂心忡忡,仗義直言,力挽狂瀾。年近八旬的黃克誠身體很差,雙目已失明,但他還是堅持在中紀委召開的會議上,發表長達1.3萬字的講話,在充分肯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同時,也實事求是地指出毛澤東晚年犯下的嚴重錯誤。講話于1981年公開發表后,引起了國內外廣泛關注和震動,深受極左路線迫害的黃克誠仍能著眼大局,積極維護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主動分擔毛澤東晚年犯錯誤的責任,促使人們重新認識黃克誠,更加欽佩他的高風亮節。實事求是、從嚴要求的擔當精神。
通過曹甸戰役,我軍雖然未能拔除韓頑據點,但也殲滅了韓德勤部主力8000多人,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東西夾擊八路軍、新四軍的陰謀,給予韓頑又一次沉重打擊,使其從此一蹶不振,為開辟和發展蘇北抗日新局面打下了較好的基礎。所以,換個角度,也可以說這場戰役是一次成功的戰役,評功擺好搞獎勵,弄得皆大歡喜。但劉少奇、陳毅、黃克誠等對于這場戰役的評價不是講成績如花似玉,滔滔不絕,講問題蜻蜓點水,強調客觀,甚至把問題說成是成績,說成是必要代價,而是敢于負責,勇于擔當,堅持反復檢討,反思存在問題,總結經驗教訓,不斷深化認識,自覺糾正失誤、錯誤。這種從實從嚴的擔當精神,不僅是革命戰爭年代我軍由弱變強、克敵制勝的法寶,也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進一步弘揚的優良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