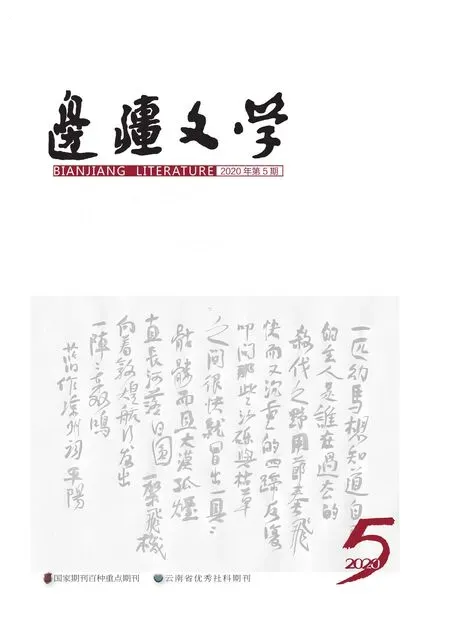去華北
2020-11-12 02:29:46
邊疆文學 2020年5期
過衢州
必然有一種微妙的震顫暗藏于
黃昏。大巴車壓過叢竹的浪頭行駛
軟椅使人遲鈍,天空在余光之余
絲綢般慢吞吞結出銹痕
小河隨著公路轉彎?蘆葦叢中鳧出野泳少年
雙臂夾著浪花。有人一邊擲牌,一邊
嬉笑,泛濫在車廂里,“仿佛回到了1998”
車廂外,白鷺是山體最幽深的裂隙
抵達之前,不要隔窗揣度夕陽的尺度
閉上眼,一個晉朝的夢正在逼近我
胸腔里 砰砰作響 如晚鐘填滿松林
一聲比一聲清晰
去華北
在途中,難免想著抵達
想著鐵軌存在交點,是一聲汽笛
可以劃破此刻,車窗外,白日下
單調如稿紙的華北平原。田壟縱橫
打就的格子里,麥子和豆類
是筆劃最端正的漢字
一座座墳冢散落其間
略去所有勞跡和汗水,草率地
成為句點。在世上,難免想起歸宿
去天上,去地下,都一樣
無非是把一個人體型相當的空
還給這熙熙攘攘的人間
在博物館,看佛造像
我看到你們是殘缺的。
斷臂,碎肩,失卻的手掌
這些人世的病痛與遺憾
正被你們在玻璃櫥中承受。
你們垂眉,閉目,微笑
合十。慈悲之外,還有
一條裂紋從眼角延伸到
下頜,像新鮮而滾燙的淚
多么可恥和庸俗!
我看到我們仿佛是一致的
竟然在木雕石鑿的身體里
偷偷藏了顆肉長的
想流淚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