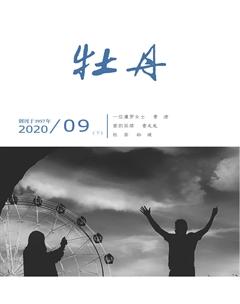淺析日本動(dòng)漫中的死亡美學(xué)意味
王怡純
20世紀(jì)中后期以來(lái),日本動(dòng)漫在世界范圍內(nèi)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日本動(dòng)漫業(yè)堪稱世界領(lǐng)先。其獨(dú)具民族特色的陰翳畫風(fēng)和對(duì)死亡意象的癡迷刻畫,與其傳統(tǒng)宗教及地理環(huán)境息息相關(guān)。死亡在日本動(dòng)漫中的體現(xiàn)主要集中于題材和形式上。本文將立足于死亡美學(xué)來(lái)剖析日本動(dòng)漫的美學(xué)價(jià)值,并從部分動(dòng)漫作品的內(nèi)容與形式探究死亡意象營(yíng)造,分析該類型作品帶來(lái)的審美感受和審美價(jià)值。
日本動(dòng)漫作為日本文藝發(fā)展的主要形式之一,由于其鮮明的作畫風(fēng)格、豐富的劇情、精致的制作,自1917年萌芽期起便風(fēng)靡全球,成為日本娛樂(lè)產(chǎn)業(yè)的主要支柱之一。1974-1989年,日本動(dòng)漫逐漸進(jìn)入成熟期,出現(xiàn)了大批科幻題材作品,今敏、宮崎駿等動(dòng)畫大師紛紛涌現(xiàn)。這一時(shí)期創(chuàng)作的動(dòng)漫作品審美取向深刻,完整地體現(xiàn)了日本民族的“無(wú)常”感和向死而生的陰翳美學(xué)。
一、題材
(一)中性主義——性別模糊的自我毀滅
20世紀(jì)80年代至90年代,日本動(dòng)漫乙女風(fēng)格發(fā)展至黃金階段。其間以clamp為代表的漫畫家團(tuán)體創(chuàng)作出一大批優(yōu)秀的動(dòng)畫及漫畫作品。這些作品的男性角色明顯具有女性化傾向特征,如纖細(xì)瘦長(zhǎng)的軀干、精致的面容、長(zhǎng)發(fā)或妖冶的打扮;個(gè)別女性角色也具有中性化傾向,如極短發(fā)、第二性征不明顯、聲線低沉等。同時(shí),創(chuàng)作者會(huì)有意隱瞞或回避坦白人物的準(zhǔn)確性別。
內(nèi)容上,除同性題材大量涌現(xiàn)外,雌雄同體、性別模糊、性別倒置的人物設(shè)定及故事情節(jié)也大范圍出現(xiàn)。例如,高橋留美子原作漫畫《亂馬1/2》后被改編為同名動(dòng)畫,講述了一個(gè)修武少年在修行時(shí)不慎落于女溺泉,遇到冷水就會(huì)變成女孩,遇到熱水又會(huì)恢復(fù)成男孩的一系列故事。車田由美創(chuàng)作的《圣斗士星矢》中,男性角色多擁有顏色鮮艷的中長(zhǎng)發(fā),身著配色大膽的鎧甲。
由于前輩畫師的影響和該類角色的大獲好評(píng),這種去性別化的特質(zhì)普遍且高頻地出現(xiàn)在21世紀(jì)后的各種題材的動(dòng)漫作品里,令人不得不思考其背后的創(chuàng)作動(dòng)機(jī)和審美影響。首先,在這類作品中,角色可男可女,同時(shí)擁有兩種性別特質(zhì),甚至產(chǎn)生一種融合的第三性性別特質(zhì),此時(shí)審美想象空間就會(huì)被擴(kuò)大,欣賞者可以得到不同且廣闊的想象空間。其次,這種去性別特質(zhì)由一開始的性別任意轉(zhuǎn)換到后期的無(wú)性別,將性別帶來(lái)的刻板印象直接打破,體現(xiàn)為一種對(duì)于人物內(nèi)在的破壞與解構(gòu)。這里的無(wú)性別化是對(duì)第二性征的不在乎和放棄,是對(duì)自我性認(rèn)知的一種否定與超脫,這與日本美學(xué)中的“無(wú)常”感不謀而合,即正如他們所認(rèn)為的沒(méi)有什么物質(zhì)可以永恒,所以生有何喜,死亦無(wú)懼,索性就從自身開始打破,所以這種消極解構(gòu)的第三性也帶來(lái)一種接近自我毀滅的別樣美感。
(二)機(jī)甲題材的超現(xiàn)實(shí)與肉體毀滅
日本動(dòng)漫創(chuàng)作者對(duì)于新世界的幻想,除了擁有高精尖的技術(shù)外,還將科技與人體結(jié)合,對(duì)人體進(jìn)行科技化改造。譬如,龍池敏文的《七武士》中將自己改造為力量型生物機(jī)械的菊千代、《午夜之眼》中風(fēng)林寺悟空的智能眼球、《新世紀(jì)福音戰(zhàn)士》中的EVA全體機(jī)等,都將人體生物器官與機(jī)械相結(jié)合。值得注意的是,創(chuàng)作者并未將人整體“機(jī)器化”,而是選擇改造部分生物器官,客觀上延伸了人的某部分能力來(lái)進(jìn)行進(jìn)化。與卡夫卡筆下的機(jī)器吞噬人的異化世界不同,在這里,人戰(zhàn)勝了工具并善于利用工具,將生存意志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但這種生存終究是要付出代價(jià)的,即必須讓部分身體“死掉”。甚至在部分動(dòng)畫作品中,主角不僅一個(gè)眼球或一條胳膊被改造,有可能全身都被鋼鐵重塑,但仍要保持一顆人類的心臟。這是將肉體的死與精神的生緊緊結(jié)合。
從性格的破壞與解構(gòu)到肉體的重塑與再生,科技的進(jìn)步不只是為了超越當(dāng)下,在日本動(dòng)漫中更投射出一種類似耶穌三死三生的舍生求死的超脫精神。生物學(xué)上的死亡就是肉體的毀滅,機(jī)甲題材動(dòng)漫對(duì)肉體進(jìn)行放棄和升華,這種立足于死亡的求生正是死亡美學(xué)的真正藝術(shù)價(jià)值內(nèi)涵。
(三)末日題材——世界毀滅
新千年的來(lái)臨于其他國(guó)家是無(wú)限的期望與暢想,但民族印記中刻著“物哀”與“無(wú)常”的日本民族情不自禁地聯(lián)想到了末日。“末日情結(jié)”仿佛是日本文化的胎記一般,這背后成因不得不結(jié)合其地域環(huán)境進(jìn)行考量。狹長(zhǎng)的島國(guó)風(fēng)貌,四周無(wú)任何接壤國(guó)家,左右環(huán)顧都是茫茫大海,常年受到海嘯地震等自然災(zāi)害的侵?jǐn)_,導(dǎo)致日本民族性中不得不帶有一種悲觀的、自毀的傾向。凡事都有盡頭,外部世界的災(zāi)厄又如此之多,不如將世間萬(wàn)物都看作是一場(chǎng)虛妄。
在此種末日情結(jié)上,日本動(dòng)漫創(chuàng)作者不僅創(chuàng)作了常規(guī)自然災(zāi)難題材作品,如講述東京大地震的《東京震級(jí)8.0》,還創(chuàng)作了反映戰(zhàn)爭(zhēng)災(zāi)難題材的《核爆默示錄》。除開這兩大類題材外,其中生物變異題材更值得人們注意。1988年開始連載的漫畫《寄生獸》講述了在地球上突然出現(xiàn)的某種孢子,以寄生人類腦部為目標(biāo),繼而控制人類“死掉的身體”,寄生孢子們殘忍殺人分尸并學(xué)習(xí)人類世界規(guī)則,從而掌控人類世界,使世界陷入一片恐慌之中。類似的末日災(zāi)難還出現(xiàn)在《進(jìn)擊的巨人》中,神秘巨型類人怪物肆虐吃人,造成人類滅亡的災(zāi)難;《東京喰種》中,喰種使人失去理智變異成食尸鬼,導(dǎo)致人類互相殘殺走向終結(jié)。
在這類作品中,人類成批地死掉,城市接二連三地被毀滅和吞沒(méi)。日本動(dòng)漫創(chuàng)作者樂(lè)于表現(xiàn)這種大場(chǎng)景的恢弘死亡意象,但僅此而已還不夠,如果說(shuō)地震海嘯是日本作為島國(guó)逃不掉的終結(jié)命運(yùn),那么幻想自己孤立無(wú)援被核彈攻擊是基于廣島的歷史創(chuàng)傷,這種僅限于外部世界的毀滅對(duì)于日本民族來(lái)說(shuō)是可預(yù)見的,所以創(chuàng)作者將目光移向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人的異化”的末日題材創(chuàng)作上,讓人類在必死的災(zāi)難環(huán)境中,身處與世界同況同構(gòu)的處境,給主角以命運(yùn)悲劇的設(shè)定,讓其在命運(yùn)中反復(fù)掙扎,最終為了人類大義選擇犧牲。這種歌頌死亡并反復(fù)美化的內(nèi)容便是日本文化中贊揚(yáng)的舍生求死的精神。
二、形式
日本動(dòng)漫能與本國(guó)的其他藝術(shù)形式相提并論,占到日本娛樂(lè)產(chǎn)業(yè)總產(chǎn)值的六成。其與影視作品都是綜合藝術(shù),不僅作為一種娛樂(lè)形式服務(wù)低齡人,還用繪畫手段擴(kuò)張了人作為主人公的各種可能性,譬如擁有不可思議的能力、新奇的經(jīng)歷、多層次的感官體驗(yàn),成為依托于現(xiàn)實(shí)的“繪畫白日夢(mèng)”。這種夢(mèng)幻感極大地體現(xiàn)在日本動(dòng)漫的色彩特色與作畫風(fēng)格上,其中的邪典動(dòng)畫類更是鮮明地體現(xiàn)出日式陰翳審美的死亡意味。
《未麻的部屋》是今敏創(chuàng)作的動(dòng)漫作品,全片采用較為昏黃的膠片色調(diào),色彩對(duì)比強(qiáng)烈且飽和度較高,使整部動(dòng)畫看上去像是被包裹在黏稠的海藻中,再加上其血腥懸疑的劇情,令觀眾從感官上全情沉浸在緊張的窒息感中。這種高飽和的色彩和昏暗的光影是為死亡意象營(yíng)造凝重神秘氣氛的最佳搭檔,與之相對(duì)的“生意象”大師宮崎駿則常用一些低飽和度的色彩、明亮且清新的光影。
川尻善昭監(jiān)制的《午夜之眼》全片采用昏暗陰冷的藍(lán)色濾鏡,使得人物的皮膚近乎于發(fā)藍(lán),增強(qiáng)了科幻感,也冷冰冰地接近于無(wú)生命的死亡狀態(tài)的人。在這兩部作品中,人物都接二連三地死亡,創(chuàng)作者熱衷于刻畫每一次的死亡現(xiàn)場(chǎng)并將血肉與傷口清晰地展現(xiàn)在鏡頭前,給人以直觀慘烈的沖擊。大量的暴力色情裸露鏡頭展示,在展示過(guò)后,人物大多被殘忍地殺害。這種凌厲無(wú)比的“川尻風(fēng)格”在海內(nèi)外好評(píng)如潮,風(fēng)格“冷硬”,人物華麗陰郁,將死亡意味極盡描摹。
三、結(jié)語(yǔ)
日本人既有對(duì)美的敏感,也有追求極致之美的偏執(zhí),以色彩和構(gòu)圖為基礎(chǔ)的動(dòng)漫則最能體現(xiàn)出日本人的這種對(duì)美的追求和實(shí)踐美的能力。日本動(dòng)漫中對(duì)死亡意象的反復(fù)描摹與追求,其表面?zhèn)鬟_(dá)了對(duì)死亡的某種贊頌與向往,但隱藏在血腥暴力與色情的意象背后的是對(duì)生的肯定,對(duì)勇氣的肯定,對(duì)舍生求死的精神的肯定,這種“生之肯定”消解了生死兩極的尖銳對(duì)立。
(長(zhǎng)安大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