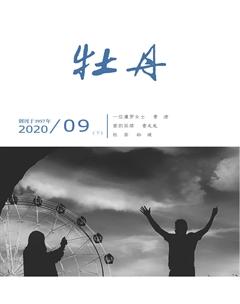北宋“知荊南府”現象研究
荊州地區地處江漢平原,西接天府之地川蜀,北通軍事要塞襄陽,順長江而下可達中國經濟重心地區,在趙宋一朝平定武平、后蜀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荊湖北路是兩宋時期重要的財政軍資供源地之一,而在該地發揮指導作用的官員就顯得尤為重要。筆者在對北宋時期荊州地區知府的研究整理過程中發現“知江陵府”和“知荊南府”并存或者交替出現的現象。“府”產生于唐代,發展至兩宋時期,其不僅是一個政區地名稱呼,也代表中央政府對當地的重視和美好期許,如嘉興府、瑞安府等,這也說明府名的選定和更改具有一定講究。北宋九朝史書文獻沒有明確記載府名更換的內容,合理解釋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也就成了研究荊州地區官員群體的重要前提。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對北宋荊州地區的研究主要包括詩歌官學等文化方面、荊州官員個體、軍事地理、江漢平原水域和特產、兩宋時期府名和地方行政區劃的研究。對于江陵府和荊南府二者關系沒有詳細的辨析,只簡單闡釋或直接引用《宋史》等相關文獻。因此,本文重點論述二者的關系及其影響。
荊州地區為趙宋一朝南下統一和北防御敵發揮了巨大作用,其間,該地區的地方政府官員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整理發現,對于北宋荊州地區的知府,官員任職記錄多為荊南府而不是江陵府。兩宋時期,有明確文獻記載的“荊南府”出現在宋高宗時期。出現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江陵知府需要兼任荊湖北路的軍事長官,即兵馬鈐轄,掌握本路最高兵權,江陵府也就成為荊南軍府,知府亦可稱為知荊南府。這種形式既有利于及時鎮壓少數民族叛亂,也有利于防止地方權勢壯大,威脅中央。
一、北宋“知荊南府”的現象
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荊南節度使高繼沖歸朝,北宋政府也就相應統轄了荊南政權下的“州、府三(江陵府,歸州、峽州),縣一十七,戶一十四萬二千三百”。當時,荊南是指五代十國之一的荊南國,江陵府只是其統府之一。統一南方以后,為更好地統轄各地,避免出現五代十國時期地方割據的情況,北宋于至道三年(997年)開始在全國劃分“路”,至宋神宗年間,全國共有二十三路,其中荊湖北路的范圍主要包括:
“北路。府二:江陵,德安……江陵府,次府,江陵郡,荊南節度。舊領荊湖北路兵馬鈐轄,兼提舉本路及施、夔州兵馬巡檢事。建炎二年,升帥府。四年,置荊南府、歸、峽州、荊門、公安軍鎮撫使,紹興五年罷。始制安撫使兼營田使,六年,為經略安撫使;七年,罷經略,止除安撫使。淳熙元年,還為荊南府。未幾,復為江陵府制。”
由此可知,北宋荊州地區隸屬于江陵府,而且整個北宋九朝沒有設置荊南府。直到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荊南府才開始設置。根據《宋兩湖大郡守臣易替考》中對任職江陵府、荊南府的官員統計,從乾德元年到靖康元年(1126年),有文獻記載的在荊州地區任職的知府共計102任、96位,包括知江陵(府)19任,知荊州府1任以及知荊南(府)76任。“(呂余慶)建隆三年,遷戶部侍郎。丁母憂……知江陵府”,“(郭贄)七年,以本官參知政事……知荊南府”,“(許仲宣)雍熙四年……移知江陵府”,朱巽知荊南府,李若谷知荊南,梅詢知荊南府,郭贄尋知荊南府等。《夢溪筆談》載:“荊南府片散茶共八十七萬五千三百五十七斤。”《歐陽修集》載:“荊南府紫府觀并潭州南岳真君觀開啟皇帝本命道場青詞。”《王安石集》載:“慶歷五年,天子以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荊南府王公為侍御史。”《曾鞏集》載:“知荊南府荊湖北路兵馬鈐轄,浚渠為水利。”以上多條文獻記載說明不僅官員職務有“知荊南(府)”的現象,其他涉及荊州地區的文獻記載中也出現荊南府。而北宋現存的歷史文獻并沒有具體記載“荊南府”或“知荊南”的原因,對“府名”十分重視的北宋出現這種現象,其背后原因值得深究。
二、北宋軍政合一與“知荊南府”
北宋時期,地方官員的設置經歷過幾次改革,軍政與民政大權逐漸統一。宋仁宗實施慶歷新政之前,地方各路的軍政與行政各有官員執掌,全國各地執掌兵權的官員主要為都部署路、兵馬鈐轄以及提舉兵甲司三種不同類型。慶歷新政以后,為更好地治理各路,行政與軍事大權集中于各路安撫使或經略安撫使。文獻中,“知荊南”現象的出現與這類官員有關。主要原因就是江陵知府兼任荊湖北路最高軍事長官。
北宋初期,朝廷在全國軍事重鎮或有軍事危機的地方設置安撫使。荊湖北路在宋仁宗時期設置過安撫使,事態平息后,就立即撤銷,因而荊湖北路主要實行兵馬鈐轄司和提舉兵甲司制度。兩司率臣掌控本路軍權,主要職責是職掌總管軍旅屯戍、營防、守御之政令及兵將屬官的訓練、教閱、賞罰等事。《宋史·地理志》記載,“江陵府,次府,江陵郡,荊南節度。舊領荊湖北路兵馬鈐轄”,說明江陵府知府在早期兼任荊湖北路的兵馬鈐轄,是荊湖北路的軍事最高長官。這在文獻中有大量相關記載,比如,《容齋隨筆》記載“荊州,軍額曰荊南,府曰江陵,而守臣則曰‘知荊南,通判曰‘通判荊南,自余掾幕縣官則曰‘江陵府”,郭贄“知荊南府。府俗尚淫祀,屬久旱,盛陳禱雨之具。贄始至,命悉撤去,投之江,不數日大雨”。文獻中的郭贄是“知荊南府”,是軍事官員,任職期間,他也參與治理當地的文教祭祀。這也側面說明這一時期本路的軍事長官兼理當地的民政。《宋史·李若谷傳》曰:“王蒙正為駐泊都監,挾太后姻橫肆,知府李若谷繩以法。”其中,駐泊都監隸屬軍額,荊南知府李若谷對其繩之以法是知府掌兵權的體現。除此之外,還有“高溪州蠻田彥伊入寇……與轉運使張素、荊南劉昌言計事。允則以蠻徼不足加兵,悉招輯之”(《宋史·李允則傳》)、“知荊南府朱巽罰銅二十斤”(《續資治通鑒長編》)、“詔知荊南馬亮發潭州虎翼軍五百人屯鼎州”(《續資治通鑒長編》)、“龍圖閣直學士、新知荊南、提舉本路兵馬巡檢等事吳中復言”(《續資治通鑒長編》)等。因此,在荊湖北路,如果從軍府的角度來看,兼任兵馬鈐轄或是提舉兵馬巡檢的江陵知府也可以稱為知荊南府,這時的知府具有江陵府的行政權以及本路的兵權,在不常設安撫使的情況下,其地位相當于本路的帥司安撫使。這也合理解釋了在《北宋經撫年表》和《宋代安撫使考》中荊湖北路的安撫使基本與江陵府知府重合。
由于以上原因,江陵府也被稱為荊南軍府。北宋初期,荊南節度使高繼沖入朝后,中央直接任命朝臣王仁贍管理荊南地區,“高繼沖請命,以仁贍為荊南巡檢使。繼沖入朝,命知軍府”。《湖北通志》記載,“治平二年,予(鄭獬)佩荊州印……治平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右司諫、知荊南軍府事安陸鄭獬記”,《宋史》記載鄭獬“出知荊南”。雖然沒有明確的文獻記載荊南軍府,但是從《宋史》《續資治通鑒長編》以及北宋文集中也可以看出江陵府也是荊南軍府的事實。
三、江陵府“軍政合一”的意義
北宋時期,在安撫使或經略安撫使成為定制之前,州府兼領本路兵權是常態,這種形式給了地方更大的便利,同時也存在一定的隱患。荊湖北路江陵知府掌本路兵權產生的意義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一)有利于鎮壓少數民族叛亂,維護治安
荊湖北路統轄二府十州二軍五十六縣,范圍包括今天湖北省大部分,在西南與四川省、湖南省接壤,民族問題突出。宋神宗任用王安石進行改革,其中拓邊政策激化了民族矛盾,再加上平時漢人百姓與官員的侵擾,五溪地區少數民族反抗頻繁。《宋史》中存在大量相關記載,如“五溪蠻擾邊”“五溪蠻叛……鼓行度險,賊七遇七敗,斬首數千級,蠻遂降”“章惇興南、北江蠻事……得其下溪州地,五溪皆平”“蠻復大入鈔略,覆官軍,荊土為大擾”“五溪都統向通漢,約以入貢”等。五溪蠻時叛時降,而荊湖北路的駐軍在西北和東北部,距離較遠,由本路知府直接調遣駐軍鎮壓叛亂更加及時和便利。到北宋后期,為了迅速鎮壓五溪蠻的叛亂,“克服帥司在荊南,去邊既遠,又隔大江,難以支援的困難”,方便調集軍隊,將“荊湖北路荊南,歸峽安復州、荊門漢陽為荊南路,帶都鈐轄,治荊南”,將荊湖北路西部以及兩軍全部劃入荊南路,以更好解決西南少數民族問題。
(二)避免地方權勢過大,威脅中央
北宋時期的安撫使“先后設置于三路、京東西及廣南、湖南等地,東南其它路分及川陜地區則因社會矛盾相對緩和及其他種種考慮沒有設置,依舊行用鈐轄司和提舉兵甲司制度”。關于安撫使,《宋史·志·卷一百二十》記載:
“經略安撫使一人,以直秘閣以上充,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帥其屬而聽其獄訟,頒其禁令,定其賞罰,稽其錢谷、甲械出納之名籍而行以法。若事難專決,則具可否具奏。即干機速、邊防及士卒抵罪者,聽以便宜裁斷。”
由此可見,安撫使權力較大,同時擁有一定的獨立自主性。荊湖北路位于中部地區,社會矛盾相較于邊界地區緩和,主要集中表現為內部的少數民族叛亂,相對于北方游牧民族來說,五溪蠻問題比較容易通過羈縻政策和武力鎮壓等方式解決。除此之外,荊湖北路帥司距離東京開封府比較近。所以,荊湖北路的安撫使不需要也不能常置,以防止地方權勢壯大,威脅中央。
荊州因為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一直活躍在歷史舞臺中,荊南一詞自先秦發展到兩宋時期乃至明清,其歷史意義愈加深刻和豐富。總體而言,從地理區域范圍看,江陵府與荊南府是一樣的。區別在于二者的職權范圍不同,江陵知府按制應該掌握本地的軍政權,統轄本府一切事務。而荊南府更多地突出軍事職能,其知府由江陵知府兼任,除了江陵府的事務,更重要的是掌握荊湖北路的兵權,地位相當于安撫使。安撫使是一個地區軍事戰略地位的體現,其在荊湖北路不常設置,說明北宋時期荊州地區雖不如廣南、湖南等地形勢嚴峻,荊南府的特殊性也說明當時荊湖北路主要的軍事重心在西南部,而到南宋時期安撫使成為定制,軍事重心也開始轉移。荊南府也就為南宋荊湖北路安撫使的出現奠定基礎。
(長江大學文學院)
作者簡介:胡玲(1995-),女,湖北大冶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荊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