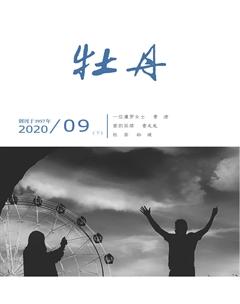暴力美學中的心理現實主義
付筱娜 馬荻夢
在如今的美國文壇,喬伊斯·卡羅爾·歐茨的小說可謂是獨樹一幟。作為美國當代大師級作家,她擅長運用獨特的視角和女性特有的敏銳情感挖掘社會諸相,其作品以性與暴力著稱,但并沒有停留在一味揭露政治腐敗和社會黑暗的層面,諷刺與批判的同時也存在著對于人性復歸的期盼。由于夾雜著哥特式的元素,歐茨作品往往帶有空靈、神秘的氣息,她所描繪的人物也或多或少地透露出虛無主義,但在這種后現代的表象下隱含著她對于人性的關懷。本文將以歐茨的代表作品《黑水》作為切入點,分析歐茨筆下暴力美學中的心理現實主義。
暴力與現實的描寫在文學作品中屢見不鮮,許多作家用暴力鏡頭來描繪現實、挖掘現實、闡釋現實。因此,暴力美學已然成為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國當代女作家喬伊斯·卡羅爾·歐茨是暴力美學的書寫者,她作品中的性與暴力帶給讀者感官刺激的同時,也隱藏著心理現實主義,表現出作品中人物的細膩心思和微妙情緒。與此同時,更進一步揭露現實的虛偽和殘酷,剛柔并濟,直擊主題。
一、《黑水》中的軟暴力
《黑水》以瀕臨溺死的女主人公凱莉·凱萊赫生命最后幾個小時的心理活動為主線,運用倒敘和插敘的手法,以閃回的方式描寫了凱莉·凱萊赫這個僅有二十六歲的年輕女子的不幸遭遇。凱莉是美國布朗大學的高材生,對于美國的歷史與政治有著獨特的見解和向往。男主人公沒有具體的名字,被稱為“參議員”。他是一名頗有聲望的政治家,年過五十依然風度翩翩,富有魅力。兩人相識于七月四日國慶節的宴會上,并彼此產生了好感,凱莉決定跟隨“參議員”私奔,不想車子在開往碼頭的路上跌入河中,“參議員”踩著凱莉的身體成功逃生,而凱莉不幸溺死。
凱莉回憶的不斷閃現表現出她從小到大都生活在看不見的暴力之中。父親不準她隨意動車里的儀表盤,耳背的伯父卻反感她大聲說話。她曾在總統競選中與父親唱反調,結果卻以失敗告終,最后彷徨在街頭只能求助于母親接自己回家。這些稀松平常的回憶無不展現出在男權至上的社會背景下,女性獲得獨立的艱難。凱莉曾勇敢地追求自我,卻始終無法實現精神上的自由與獨立。
凱莉與“參議員”的孩子年紀相仿暗示了——在社會現實中,在男性強權面前,她永遠只是一個孩子。作者不斷描寫凱莉小時候穿著帶花邊的白色棉襪在屋子里跑跳被爺爺抱起來的畫面也證明了這一點。她坐在“參議員”又黑又亮的豐田車里,空調發出的噪聲和并不好聽的歌曲混雜在一起,“參議員”不停地喝酒,還把酒灑在她裙子上,她都一聲不吭。她懷疑他們迷路了,卻一直不敢說出來。小說中一直反復出現“乘客”這個詞,在這輛車上,甚至在他們突如其來的感情中,凱莉一直以“乘客”自居。她認為車是“參議員”的,這段感情也是“參議員”主動才得以生發的,“參議員”決定著方向,掌握著主動權,而她只是一個乘客,只能跟之隨之。而當他們的車子失去控制,掉入漆黑的水中,“參議員”不斷甩開她求救的手,踩著她的身子逃出車外,她都叫不出他的名字;當她離死亡越來越近,腦海中的記憶不斷浮現的同時,她仍天真地幻想“參議員”會回來救她。但是,當她面前浮現“參議員”的幻象時,她叫不出他的名字。在凱莉與“參議員”短暫的愛情里,凱莉一次也沒叫過“參議員”的名字,只用尊稱而不能直呼其名,等級高下立判。
凱莉是一位有才、有貌、有夢想的知識女性,對美國的歷史和政治頗有研究,她有自己的“美國夢”,那就是走上政壇。但從與“參議員”的多次交談和互動可以看出,她希望通過依靠有聲望的男性權貴對自己的愛慕與追求來實現自己的“美國夢”。盡管在之前失敗的感情經歷中,曾經的男朋友給她留下了痛苦的回憶,使得她不愿意再去觸碰男性,但是對于“參議員”的親吻以及表現出的赤裸裸的欲望,她只表現出忐忑。伴隨這種忐忑而生的不是反感,而是欣喜。凱莉一方面不敢相信“參議員”真的會愛上自己,另一方面又對自己的“美國夢”可能有了依托而竊喜。凱莉把自己的一切都“豪賭”在了“參議員”身上,最終只落得個夢未成、身先死的悲慘結局。
在歐茨的作品中,暴力的描寫是多種多樣的。有的是硬暴力,鮮血淋漓;《黑水》則是軟暴力,也可以說是心理暴力,傷人于無形。
二、暴力美學中的心理現實主義
歐茨小說中所描寫的暴力均有其現實原型,《黑水》就取材于1969年轟動一時的“肯尼迪-查帕奎迪克丑聞”。那一年,愛德華·肯尼迪當選為參議員民主黨副領袖。同年七月,他到鎮子上參加集會,晚上開車載著一位名叫瑪麗的姑娘同行,途中車子掉入河中,愛德華成功逃生,瑪麗卻不幸遇難。愛德華因此被判兩個月監禁,同時被迫退出總統競選,但公眾認為他因權勢逃脫了應受的法律制裁。歐茨選擇對此事件重新書寫,并在小說中不斷插入凱莉對于美國政治和社會的看法,以強調外界環境的壓制力量對個體造成內心沖突與仿徨,進一步體現了歐茨對于現實的強調與重視。
歐茨以暴力為筆記錄了當代美國的真實生活,作品中大部分主人公皆為女性,使讀者從女性的視角審視美國社會。歐茨筆下的女性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將女性置于人與人、人與家庭、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之中,探究資本主義家庭倫理、社會道德、人際交往規范、道德責任對個體,特別是對女性的異化,以及由此產生的暴力問題。歐茨的暴力美學皎如日星地體現在她對作品人物的刻畫中,《黑水》中的凱莉一生都受制于無形的暴力中,形成一種“意志暴力”,在這種意志暴力的摧殘下,凱莉的自我身份日漸破碎。歐茨在作品中揭示了作為統治工具的資本主義道德對女性的異化,女性通過暴力反抗種種的不公與剝削。這些暴力的背后隱含著歐茨諸多的倫理關懷。歐茨對被痛苦、焦慮和無助困擾而被迫訴諸暴力的底層人民給予極大的同情,肯定了他們生命的激情與意志,使人反思生存倫理。
《黑水》源于現實,又高于現實,堪稱歐茨心理現實主義的典范。小說開篇就描寫車子不受控制地掉入水中,凱莉閃出一個念頭:“我要死了嗎?就這樣死去了嗎?”這一念頭產生了強烈的懸念貫穿始終,與凱莉回憶的閃回描寫相結合形成一種奇妙的壓迫感,“生還是死”像一塊大石壓在讀者心頭。隨著時間的流逝,凱莉的意識逐漸模糊,小說的標點符號也隨之減少,語句的異常連貫表現出她的思維混亂。讀者也隨之產生強烈的共鳴,心跳加速,呼吸加快。
歐茨的心理現實主義受到亨利·詹姆斯和威廉·福克納的影響,既具有意識流的特點,又善于運用內心獨白、制造懸念。她的作品情節跌宕起伏,引人入勝,又不吝惜筆墨展現人物的內心世界,以復雜而細膩的心理活動折射紛繁復雜的時代脈動。與此同時,暴力的頻繁登場勢必會有吸引讀者的大部分目光,但歐茨寫作的目的不是渲染暴力,而是要喚起讀者對暴力背后的人的真實的生存狀態的關注,歐茨的著力點不在暴力,而是暴力后的黎明、暴力后的生活的繼續。歐茨作品并非歌頌暴力的存在,彰顯了暴力背后的人性倫理關懷,她寄希望于暴力后人類的堅強存活和末日后的凌晨。
(遼寧大學)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9年度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馬克思主義道德觀視域下喬伊斯·歐茨作品的倫理研究”(項目編號:L19BWW00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馬荻夢(1996-),女,遼寧沈陽人,碩士,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