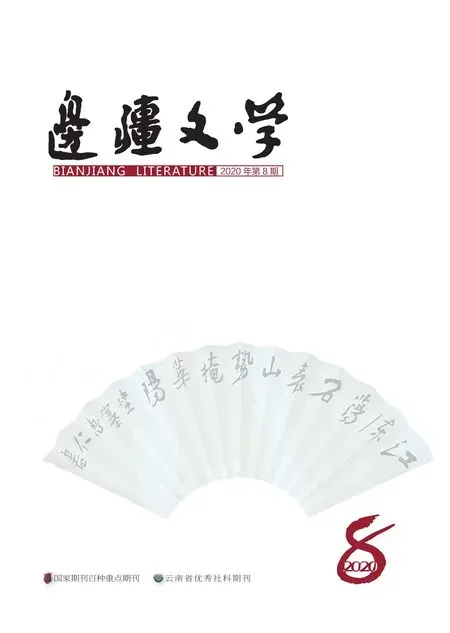漂移中的找尋
——談祝立根詩歌的否定性
☉楊碧薇
我將當代新詩寫作大致分為三種類型:肯定型、否定型、建構型。其中,肯定型寫作最基礎,也最普遍。這類寫作有著被大多數人所認可的、恒定的內在價值,對事物、情感、思想的抽取也是基于肯定邏輯,至少是潛意識上的認可。在外在形式上,肯定式寫作又多發現性、贊美性、陳述性、概括性話語。很多詩人在寫作初期,都經歷過肯定式階段。例如對他人的模仿與學習,就是通過認可他人的創作來確立自身寫作的路徑,依托于他者來建構自我詩學模式。更有不少詩人在走過了初期階段后,依然有意無意地保持與他者文本的嵌合,在他人的影響焦慮下寫作。在這種情況下,“他者經驗”其實發展成了一種“我們經驗”,即集體經驗。肯定型寫作有其優勢,它能幫助詩人在學步期就迅速找到認領的對象;聰明一點的詩人,還能成倍地吸收他者的經驗,使他者經驗在自身文本中實現內暴式增值。同時,優勢也是局限。對他者經驗吸收的有效性,首先取決于模仿者與被模仿者之間的相似度,如果他者(被模仿者)的經驗(包括心性、氣質、審美偏好等)能引發模仿者的共鳴,那么模仿者能汲取到的經驗就更可靠有效。反之,若二者差異較大,模仿者往往會選擇別的研習對象。其次,這種有效性還取決于模仿者自身的功力。在功力有限的前提下,模仿者能否將他者經驗轉換為自己的東西,就是一個未知數。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局限:對同質化經驗的偏好,在給模仿者帶來歸屬感、安全感之時,也會極大地束縛他(她)對異質經驗的吸收。換言之,模仿者不過是在效仿的他者中分辨到熟悉的自己,卻挖掘不到自身陌生的一面;他(她)陷入某一類型的審美舒適中,再難以在“我們經驗”中突圍,樹立突出的個人詩學形象。
祝立根的舊作里其實也包含肯定性的因子。他的上一本詩集《一頭黑發令我羞恥》在很大程度上可視為一個時期地域寫作的典型代表和較大公倍數。這里的“地域寫作”不是指以地域為題材的寫作,而是指在一個時期內受到云南詩人青睞的一種類型化風格。祝立根接受這種風格,與其自身經驗密切相關。而“較大公倍數”是說他在這種類型化中實現了自我經驗的增值,成為這種類型化的佼佼者。然而,祝立根并沒有滿足于此,在他的新作中,我看到了不同的變奏。從《一頭黑發令我羞恥》時期就開始的自我審判(“自己審視自己”),也裂變為寫作路徑上的審判——他審視自身寫作,開始找尋更多變化與可能性。最明顯的一點是,繼《悲慟海》《輪回》等詩后,“海”在他詩里越來越頻繁地出現,我在《煙花》《深藍》《參觀鋼鐵廠》等詩中都讀到了“大海”,較之以前的“大海”,這些詩里的“大海”更加具體。從“高山”向“大海”持續漂移,是祝立根寫作轉向的一個表征。由此我也要引出新詩書寫的第二種類型,即否定型。
祝立根的近作有更明顯的否定特征。這種否定性體現在自我判斷、價值質疑和詩歌言說三個層面。不同于一些詩人總是急于進行外在批判,祝立根首先是一位內剖型的詩人,其詩也具有明顯的內傾性(introversion)。不管是他的新作還是舊作,幾乎都有一個向內看的維度;即便是側重于對外界的觀察,他也要落實到自己的思緒和情感上。以《愛離別》為例,詩中有一個清晰的自我鏡像,“我”與“他”的對話就是一種自我辯證。詩人在寫“他”,其實在寫“我”。《參觀鋼鐵廠》則把觀察視角從外扭向內。注意,這種扭轉既是強制性的,也是自發性的。在鋼鐵廠,他看到的一切,都與自身的經驗掛鉤。隨著看的深入,詩人自我解剖的縱深感也愈發明顯。縱深感的延展,就像一個“挖”的過程。祝立根挖到了自己,也挖到了同命運的人,他從個體看到了群像,“有血有肉的/螺絲釘,一個又一個家庭的頂梁柱”,看到“那么多的我,我、我、我,和我”的辛酸和無奈。群體命運升華了個體感受,浮現出一種共性,這使詩歌無論是在深度、厚度還是廣度上都有了更多闡釋空間。
對價值的質疑,是祝立根詩歌的隱含維度,也是其否定式寫作的核心。《明月照何方》是典型的祝立根式的表達,有著回顧的姿態,他從自己的過往經歷中抽取出詩意,舊作《與兄書》《與友書》也分享著同樣的“回顧”結構。而他抽取出的詩意,是對生活的無奈、抵抗與堅持。祝立根的詩,堆滿了漂萍、傷心、無可奈何,這些情緒正是其詩否定性維度的顯要表征:“即使在這吞咽的大海上/你和我,只是一朵又一朵,風中的蒲公英”(《煙花》)、“我們已經習慣了在低洼地里,排隊/趕路,推推搡搡,領取屬于自己的/小分量的悲歡和氧氣”(《猛犸象之歌》)。在某種程度上,海,就是祝立根心境的寫照。“如果你問我我是誰/就請看看海吧,它就是我/——具體的、放大了的一生”(《悲慟海》)、“中間的海,我已不想再一一填平”(《輪回》)。無奈與堅持,總在祝立根的詩里并排出現,這就是活著——他沒有拔高現實、美化生活,也沒有輕易妥協,因為人總得活著。再來看堅持,祝立根在一個訪談里談到:“我有一百個來生還做詩人的理由,也有一百個不想做詩人的原因。如果來生的我不是我這樣的我,我絕不再做詩人;如果來生的我還是現在這樣的我,我必須要做詩人。”對詩的堅持,就是一種終極的不妥協。詩是他生命的一種供養,在他把痛的東西從生命里一點點揪出來、連根拔起,并挖了個遍后,余下的心坑只能靠詩去填補,挖開的裂痕也靠著詩去烘暖并修復。因此,祝立根的詩看似“寒”——尤其是他在審視外界時,總像在冷眼睥睨——實際上詩心又是有溫度的,他是寒里包著火、沉默壓著怒吼。
我必須提一下《永州,謁柳子廟》,這是讓我心里一動并反復回味的詩歌。這首詩從個人感受出發,推己及人,喚醒了一種被普遍遮蔽的共情性,從而在逝去的歷史中還原柳宗元作為一個真實個體的溫度,讓人物的血肉取代其符號性。這種去蔽和重新賦形,需要詩人有一副熱心腸,這樣他才能真正地感受、體量所寫的人物,而不是把自己的認識擱淺在景點的講解和介紹中。此外,《永州,謁柳子廟》還有一個文化背景,它的共情性是歷史的,我將它稱為“歷史共情性”。“歷史共情性”表明祝立根開始將歷史作為一個參照維度,將更大意義上的文化(而不僅僅是個體經驗)作為坐標,他的寫作有了更多方向。
祝立根詩歌的否定性最終落實到言說方式上。通過填補、修正和再造,他在以往的詩寫模式中尋求改變。《關于捕鳥的故事》正是這樣一首詩。如題所示,“故事”一詞帶出了詩歌的敘事性,但這首詩里的敘事不是具體的,它是作為背景而出現;詩人關于捕鳥的所思所想,才是言說的主題。在祝立根筆下,“鳥”也不只是“鳥”,還象征著更多被忽略的生命:微小的事物、渺小的人。而詩人捕鳥的過程,也是不斷認識自己的過程。在詩意的發掘上,祝立根又一次啟用了“挖”的動作,“想要捕獲它們/我還需要饑餓,持之以恒的好奇心/類同于餐刀和手術刀,一把刀的/第三面,必要時,我會減輕靈魂的體重/進入它們的身體,成為鳥”。到這里,詩歌的第一個意義層面已經完成了。接下來詩歌很快轉向第二個層面,即元詩層面:這首詩還將如何繼續?祝立根意識到“對我的講述而言,更重要的是/我首先要確認自我,確認/我應該看見什么,在意什么/憑借什么抵達什么”,詩人一邊向內轉,向內挖,一邊實驗著詩歌言說的可能,于是詩里開始出現辯論的聲調,就像是“一個人的復調”。在元詩層面,個體身份與詩歌言說都處于轉換與過渡中:“我需要邊殺鳥邊心生悲憫/我是網,是鳥,更是手舉燈塔的/捕鳥人,我還得是一個路過此地的旁觀者/一個狂熱的宗教般的環保分子/任何的立場,都改變著講述的語氣”。改變講述,就是不斷否定自己的言說,反對之前的敘述,“讓講述出現了一個個悖論”。“悖論”其實在昭示:這首探索之詩是不可能完成的,因為詩人的自我剖析不會結束,他還不會這么快地對自己、對一切蓋棺定論。因此,詩歌最后轉向了另一個捕鳥的故事:說是故事,不如說是場景,以場景描寫來結尾,靈活地處理了敘事無法終結的問題,也拋出了更多詩意。
最后我還要談談建構型的寫作。建構型的寫作有兩種。一種是“無中生有”,是在價值的空白階段通過寫作建構某種價值,《荷馬史詩》《詩經》都是這樣的建構。另一種是在“有”中破除“有”,即經過了肯定—否定,再建立一種新的價值體系。在后現代時期,建構型的寫作常常建立在對既有價值進行解構的基礎上,但它們并沒有停留于解構,而是積極尋求價值與詩學的解決方案。吉狄馬加、昌耀、臧棣、李少君、余怒等人的詩歌就體現出明顯的建構性。總的來說,建構型寫作還是當下新詩場域里的稀缺品。祝立根的詩歌,在對既有價值的反思和否定中持續地找尋新的突破,也讓我看到從否定走向建構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