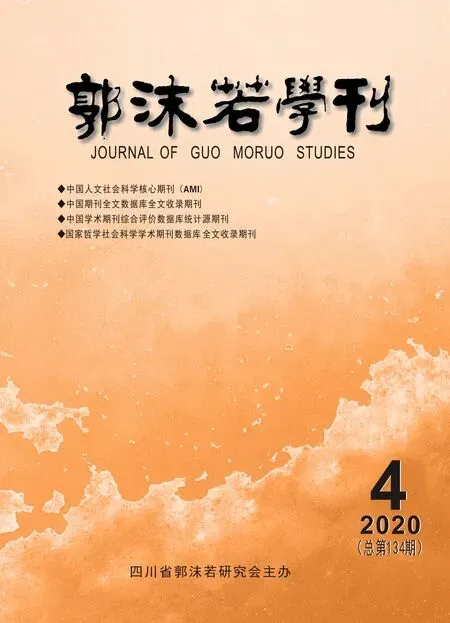《郭沫若年譜長編》指疵十端
馮錫剛
由林甘泉、蔡震主持編撰的五卷本《郭沫若年譜長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10月第一版,2368千字),是迄今卷帙最為浩繁,資料最為翔實的實錄,毫無疑問,將成為世人了解或研究郭沫若生平的案頭卷。感念之余,本著精益求精的旨趣,吹毛求疵,舉其十端,以為再版改進之用。囿于視野,指疵限于1949-1978年之條文。標舉內容,以《年譜》記錄先后為序,間有歸類。
一、手跡識讀有誤
P1308,“(1949,11)28日致信張元濟:‘國家深被重創(chuàng),新基難[雖]奠,一時尚不能使百廢待舉。’”一字之誤,意思大變。參照手跡,“雖”之繁體與“難”近似,誤在不辨繁簡及行草的書寫。不無巧合,另有幾處致張元濟的墨跡,亦有誤識。P1457,“(1953,6)8 日 ‘德宗后[信]有為’,‘未知尊處見仿[備]此否’”;P1611,“(1956,11)1 日 ‘老成今[與]道新’”。這些誤識均由不諳繁體與行草書寫規(guī)范所致(個別屬于拼音輸錄所誤)。
這類誤識,尚有幾處,如P1770,“(1959,12)6日作詩《奉和舍予原韻》:‘詩人與[興]會更無前’”;P2030,“(1965,2)23日 步(鄧拓)奉和原韻在軸上補題七律一首:‘拂素敢夸著作操[曹]’‘奴看周頌隸兼[荊]騷’‘一聯(lián)一律親[欽]趨步’”,錄鄧拓原詩或脫落,或誤識:“往來多少(幽燕客),不及立群意爭[氣]豪。”
二、重要史料失收
譜主著作浩繁,行狀事跡豐富,掛一漏萬,在所難免,但已刊布之文字尤其是重要文字則不應失收。
1979年第5期《文藝報》刊登郭沫若故居提供的譜主未刊書信多封,其中“致祖平”一通附有手跡,落款日期為“二月十七日”。收入黃淳浩所編《郭沫若書信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亦未標示年份。據(jù)手跡考證,此信的收信人當是邵祖平(知名教授與學者,因參與編輯《學衡》而與魯迅有齟齬),寫于1953-1954年間。此信之所以重要,不但在于有對魯迅的評論,而且以少有的坦率直陳心事:“足下對我,評價過高。我自內省,實毫無成就。拿文學來說,沒有一篇作品可以滿意。拿研究來說,根柢也不踏實。特別在解放以后,覺得空虛得很。政治上不能有所建樹,著述研究也完全拋荒了,對著突飛猛進的時代,不免瞠然自失。”信箋涂改甚多,是否實寄,是個問題。
由肖玫編著的圖冊《郭沫若》(文物出版社1992年11月第一版),345圖系譜主1966年秋所作《水調歌頭(海字生糾葛)》手跡,編者錄有全文(內中有一處誤識:“堪笑白雪[云]蒼狗”)。此篇是譜主在文革初期遭受紅衛(wèi)兵沖擊的寫照,具有鮮明的紀實色彩,真實展現(xiàn)了復雜的內心世界,向未公開發(fā)表。
作為政治活動家,譜主以無黨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參加于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的部分大會活動;1958年加入中共后,列席1966年5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參加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這些重要的政治活動,在《年譜》中無只字涉及。
三、引錄詳略不當
因為是多人合作,見仁見智,殊難劃一。但筆者以為,除了重要性(這標準自然也不易掌握),當以公開發(fā)表特別是收入《郭沫若全集》與否,作為詳略的主要標準。這是基于年譜具有工具書性質的考慮。詳略不當,主要是失之繁冗地全篇引錄了不少應景的作品。
即舉同一頁上的兩例。P1437,“(1952,11)10日 作七律《慶亞太和會》”,錄全詩,并標示收《新華頌》《沫若文集》《郭沫若全集》;同一天作七律書贈新鳳霞、吳祖光,僅錄一聯(lián),出處示以“據(jù)手跡”三字。說重要性,《慶亞太和會》也只是應景之作,翻檢甚易;對于讀者,則分明希望得讀從未公開發(fā)表的贈詩全篇。
P1825,“(1961,3)27 日 作詩《獻給第二十六屆乒乓球錦標賽》”,只字未錄,標示“發(fā)表于《新體育》第7期”;“31日 讀郁曼陀遺墨,題七絕二首”,錄第一首一句,第二首全篇,標示收《東風集》《郭沫若全集》。為讀者與研究者計,如欲翻檢全篇,收入集子的總要方便些,而《獻給第二十六屆乒乓球錦標賽》一詩尾聯(lián)為“萬國青年齊磊落,光明葬送戰(zhàn)爭魔”,意趣不俗。順便提及,譜主為第26屆世乒賽寫過3首詩,其余二篇均收入各類集子。
四、訛誤相沿成習
P1643,“(1957,7)1 日 作七律《紀念“七七”——用魯迅韻》二首,其一,在‘誓縛蒼龍樹赤旗’句作注:‘毛主席長征詞《六盤山·調寄清平樂》末句云:“何時縛住蒼龍”。蒼龍即指日本。東方屬青,其獸為龍。’”毛澤東于1958年12月在文物版《毛主席詩詞十九首》書眉批注:“蒼龍:蔣介石,不是日本人。因為當時全副精神要對付的是蔣不是日。”①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第650頁。雖說詩無達詁,譜主當時這樣解釋事出有因,但編者在知曉作者批注的當下仍照錄而未加說明,則有誤導之弊。其實,為便宜計,完全可以不錄這句詩。
P1765,“(1959,10)23 日 致函李宇超。‘印集題就,請轉致。’附‘雷鋒頌印集 郭沫若題’。”所標出處為“《郭沫若書信集》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一看年份,就知出錯,1959年怎么可能有關于雷鋒的印集呢?然而《郭沫若書信集》確實將此信標為“1959年10月23日”。手稿落款雖僅有月日,但根據(jù)內容當不致斷為此年。《年譜》編者未加辨識,遂以訛傳訛。
五、歸入年份出錯
P1751,“(1959,7)11 日 復信周揚。”信中有這樣的詞句:“《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道路》讀過了”,覺得“《武則天》比較還要滿意一些”。出處標為“郭沫若紀念館館藏資料”。看來手跡落款也是僅有月日,未書年份。然而根據(jù)內容,毫無疑問,此信寫于1960年。這年7月下旬舉行第三次全國文代會,郭沫若致開幕詞,周揚作主題報告《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道路》。報告在標舉第二次文代會以來的文藝成就時,提到郭沫若作于1959年的歷史劇《蔡文姬》,②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著:《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文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9月第一版,第35頁。而郭沫若以為作于1960年年初的歷史劇《武則天》“比較還要滿意一些”。1959年的書信當然不可能涉及1960年才發(fā)生的事。
P2017“(1964,10)本月作詩《十五年》”,錄全篇,出處是“郭沫若紀念館館藏資料”。因詩中有“十五年前的今天,……雄赳赳地跨過鴨綠江”,“十五年前我去過平壤”,“七年前我去過平壤”等句子,可知此詩當作于1965年。可為佐證的是,1965年10月25日條下有“詩《十五年》發(fā)表于《人民日報》,以紀念抗美援朝15周年”。
六、體例小有失衡
《編寫凡例》所列第10條規(guī)定:“年內發(fā)生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標志性事件、文化界發(fā)生的大事件,按時間順序記入本年本事敘述前。”筆者留意這方面的記錄,各年所列要事大致在5至10條之間。自然,各年發(fā)生的這類事件多寡不一,采用條目既無必要也不可能整齊劃一。但個別年份確實失之簡略,如1958年僅2條,而1960年竟只有1條。其實,這兩個年頭發(fā)生的這類大事還真不少,隨手列舉:如1958年的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八屆五中全會、《紅旗》創(chuàng)刊、北戴河會議、八屆六中全會等等;1960年的創(chuàng)辦城市人民公社、發(fā)表《列寧主義萬歲》等3篇文章、周恩來總理訪問東南亞四國、第三次全國文代會召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有81國共產黨工人黨參加的莫斯科會議召開并發(fā)表《莫斯科聲明》、中共中央批轉《關于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等等。
七、史料重復入編
P1844,“(1961,8)26 日 致函劉大年”,此信即次年同月同日之“致函劉大年”,細察譜主行止及信函內容,當寫于1962年。
P1858,“(1961,11)3 日 撰文《翻譯魯迅的詩》”,全錄所翻譯魯迅七絕的白話詩;P1880,“(1962,3)14日 錄《《翻譯魯迅的詩》中所譯魯迅的七絕,贈上海魯迅紀念館”,再次全錄翻譯魯迅七絕的白話詩。
P2160,“(1969,9)3 日 回復耿慶國”;P2220,“(1971,9)3日 回復耿慶國”。從所錄內容看,應該是同一封信,出處或標為“據(jù)手跡”,或標為“據(jù)復信手跡復印件”。究系何年所復,頗難推斷。以筆者陋見,從譜主當年的境遇看,1969年的可能性大些。
八、敘述解讀欠妥
P1940,“(1963,4)7日 作《序古巴諺語印譜》,僅四十字,并‘集其諺語為詩’全文抄錄。”雖“僅四十字”,編者卻未錄序文。細讀序文,方知此說有誤。筆者據(jù)手跡迻錄序文:“方去疾、吳樸堂、單孝天三同志,以古巴諺語三十條,刻印四十七顆。余即集其諺語為詩以序之。 一九六三年四月七日 郭沫若(其后即為分行排列的14節(jié)白話詩)”①方去疾等篆刻:《古巴諺語印譜》,北京:朝花美術出版社,1964年10月第一版。在目次之前,以8個頁面刊載郭沫若《序古巴諺語印譜》墨跡。編者刪去“(集其諺語為詩)以序之”三字,致有序文“僅四十字”之誤。譜主將并無關聯(lián)的30條諺語集為14節(jié)白話詩,雖非原創(chuàng),卻也是一種藝術勞動,略近于舊體詩的集句。因此,序文是包括“集其諺語為詩”的。在5月7日的條下,有“在《人民日報》發(fā)表由作者翻譯的《集古巴諺語》”的記載,“翻譯”當然又是編者的誤解,未聞譜主通曉拉丁文。
P2051,“(1965,7)23 日 復函胡喬木,告知22日信已接,覺得胡喬木的詞‘不宜改動得太多,宜爭取早日發(fā)表。又談了自己6月底在井岡山的見聞。”編者太過粗心,張冠李戴,將毛澤東5月間在井岡山作的兩首詞誤為胡喬木的作品(此前適有胡郭兩人間的書信往還,內容恰是修改胡詞)。茲將此信的主要內容錄出——
詞兩首,以后忙著別的事,不曾再考慮。我覺得不宜改動過多,宜爭取早日發(fā)表。六月卅日我去過井岡山根據(jù)地,在那兒住了兩天。井岡山主峰和遠處的羅霄山脈聳立云端。同志們告訴我:那些地方有原始林。又黃洋界老地,當年戰(zhàn)場猶在。
“飛躍”我覺得可不改,因為是麻雀吹牛。如換為“逃脫”,倒顯得麻雀十分老實了。
“土豆燒牛肉”句,點穿了很好,改過后,合乎四、四、五,為句也較妥帖。唯“土豆燒牛肉”是普通的菜,與“座滿嘉賓、盤兼美味”似少相稱。可否換為“有酒盈樽,高朋滿座,土豆燒牛肉”?
“牛皮蔥炸,從此不知下落“,我覺得太露了。麻雀是有下落還露過兩次面。
顯然,所談即為毛詞《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念奴嬌·鳥兒問答》。②曹應旺編:《偉人詩交》,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11月,第59頁。
九、出處標示待酌
標示出處以說明錄有所據(jù),《編寫凡例》第12條對此作了詳細規(guī)定。一般而言,凡標為“據(jù)手稿”者,最富權威性。但為便宜計,凡已公開發(fā)表者,則標為最先刊登的書刊名稱和日期。據(jù)此,《年譜》有幾處標示則有待斟酌。
P1648,“(1957,8)31日 作《祝亞洲電影周成功》。”出處標為“郭沫若紀念館館藏資料”。這當然不能算錯,但按照前例,應當標示最初刊登的報刊名稱和日期,其為“《大眾電影》1957年第17期”。
P1763,“(1959,9)本月 題《瞿秋白(筆名)印譜》”,出處標“郭沫若紀念館藏”。該書于1959年11月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1985年3月出修訂版。
P1996,“(1964,5)29日作詩《毛主席和人民在一起》”,出處標“郭沫若紀念館館藏資料”。其實,此詩發(fā)表于《解放軍畫報》1964年第9期,是與侯波的聯(lián)袂合作。畫報刊登4幅毛澤東在五六十年代會見工農兵及各族群眾的照片(均系侯波所攝),譜主分別題自由體小詩一首。詩中的一些句子(如“看到你伸出兩個指頭,在談一分為二的道理”)顯然是因著畫面的聯(lián)想發(fā)揮。一般讀者如欲對讀,卻無從查閱“館藏資料”。這就是盡可能標示書刊和出版物的好處。
另有兩處標示,情況較為復雜,亦當一議。
P2075,“(1966,4)7 日 書贈龍潛《水調歌頭》一首……后有款識:‘《歐陽海之歌》是社會主義革命文藝的力作,讀后成水調歌頭一首以贊之。”出處標為“中國嘉德2010春季拍賣會拍品965號”。筆者仔細看過網上展示的墨跡,認為是贗品。又從有關的文字中了解到,郭沫若紀念館亦鑒定為贗品。《年譜》這樣標示,在客觀上肯定了其為真跡。順便提及,筆者在網上見到一幅墨跡,系譜主于同年3月25日夜,為沈其震將《水調歌頭·讀〈歐陽海之歌〉》“書為紀念”。這確是真跡。①保利秋季拍賣會中國近現(xiàn)代書畫(四)1873,www.epailive.com。
同頁,“(1966,4)14日 出席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聽取石西民所作的關于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報告后發(fā)言”,“全文以《向工農兵群眾學習,為工農兵群眾服務》為題發(fā)表于5月5日《人民日報》”。準確的表述應當是:發(fā)表于4月28日《光明日報》,5月5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郭沫若這篇影響很大的檢討發(fā)言,其發(fā)表與轉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革之初的某些特點。略去《光明日報》的首發(fā),事實上是忽略了有意味的歷史細節(jié)。
十
考慮到譜主作為詩人兼政治活動家的身份,將與毛澤東有關的文字與行狀事跡單列指疵,諒不以“十景病”視之。于此大體可以歸納為三方面的問題:
一是重要史料失收,以“蘭亭論辯”為例。1965年8月17日毛澤東接見出席某次會議的軍隊干部時,向陪同接見的康生詢問:郭老的《蘭亭序》官司能不能打贏?康生回答可以打贏,并將郭沫若8月 7日作《〈蘭亭序〉和老莊思想》,12日作《〈駁議〉的商討》兩篇尚未發(fā)表的文章大意告訴毛。當天,康致函郭,轉告上述情況,并說毛愿意看郭的這兩篇文章。郭即于當天致函毛并寄上兩文的清樣。8月20日,毛在退回清樣時致函郭:
八月十七日信及大作兩篇清樣,均已收讀。文章極好。特別是找出趙之謙罵皇帝一段有力。看來,過分崇拜帝王將相者在現(xiàn)在還不乏其人,有所批評,即成為“非圣無法”,是要準備對付的。②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1957-1967)》,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4月第一版,第148頁。
《年譜》對此無記錄,自然郭毛信函亦失收。上述史料的出處系穆欣著《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1957-1967)》。以著者的身份(當年《光明日報》總編),這些史料的可信度極高。如果《年譜》要以信件手稿為憑的話,那么1966年7月17日,郭就毛澤東手書《西江月·井岡山》致信井岡山管理處,就當置疑,因其出處為一家省級刊物登載的普通作者的一篇文章。
二是有關背景材料的引用欠妥。如P1962,“(1963,1)1日 《滿江紅·一九六三年元旦書懷》,發(fā)表于《光明日報》”條下,背景材料引“毛澤東于8日就此詞唱和,……3月20日送《詩刊》發(fā)表,囑林克致信臧克家:‘主席詞發(fā)表時請附郭老原詞。”背景材料既說到郭致康信,并引錄毛在康轉郭信上的批語,則亦當引錄1月9日毛致康信:“一月三日信收到,大謝。郭詞很好,即和一首,請郭老和你為之斧正。”③穆欣:《毛澤東〈滿江紅〉手跡發(fā)表前后》,載《黨史文匯》2004年第12期。此信表明郭毛《滿江紅》唱和的中介是康生。“送《詩刊》發(fā)表”幾句亦當刪去,因事實上毛后來改變了主意,并未單獨發(fā)表,而是收入當年12月下旬出版的《毛主席詩詞》。如一定要引,須加說明,否則有誤導之弊,一如前述譜主關于“何時縛住蒼龍”的解釋。
三是收錄詳略不當。最明顯的例子是“文革”期間對征詢毛澤東詩詞解釋的各次答復,大抵全篇收錄,其中1968年3月15日答北京師范大學某戰(zhàn)斗組問,《年譜》竟用去6頁多的篇幅,實在失之繁冗。然而致毛澤東的信,卻有所刪節(jié),如P2052,“(1965,7,)26 日 致信毛澤東:‘《光明日報》要我寫一篇文章來解讀《長征詩》,遺憾的是我自己沒有參加過長征,只能采擷些文(史)資料來加以肊[臆]測……送上校樣一份,主席如有批閱工夫,(此處疑有脫漏——筆者注)《光明》擬于卅一日見報。”讀者極想了解省略部分的內容,但此信未公開發(fā)表過,出處在“郭沫若紀念館館藏資料”,這當然不是一般人可以查閱的,徒喚奈何。筆者之所以將此條全文錄出,還意在暴露編者的粗疏:這短短一封信,有脫漏,有誤寫。
另有一些問題,如涉及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評價,不宜對當年報刊所載文字一律照錄不誤(如為省心而照錄,宜加引號),而應盡可能作客觀的敘述。茲事體大,此處不贅。
寫于2019年9月
2020年10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