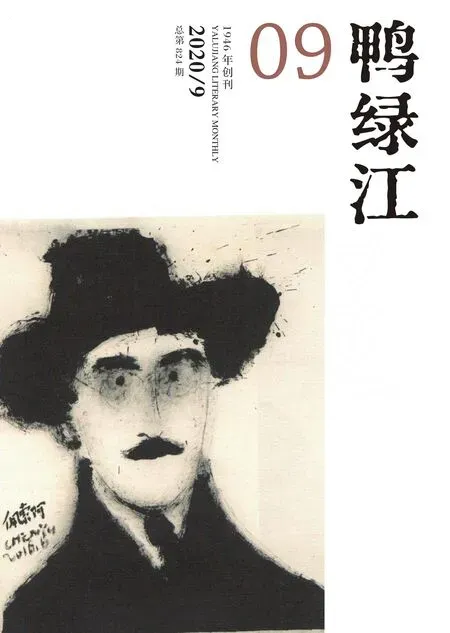花匠
白小川
花匠就是文伯。我打小起就見他種花、養花、賣花。他在街角有一個花攤,攤子前常塞滿各色買花的人,每天下班路過都能見到。文伯的花是遠近聞名的,要么國色天香,要么楚楚動人,尤其矯情的海棠和君子蘭,文伯侍弄得最好。
關于文伯的事,我問過我爸。我說文伯跟文嬸以前是你車間的?我爸說是。不知咋的,一提到這,老爺子就少言寡語,干脆岔開話。
我還問文伯的花咋種得那么好?我爸沉思后才說,一是用心,二是用情。我那時候小,不懂,也不再多問。后來我大了,也逐漸變得愛鉆牛角尖,越是不讓我問,偏偏越是好奇,總在心里面犯合計。有次下班回來,跟老爺子小酌,酒過三巡,趁老爺子酒興正酣,我就問他,說說文伯的故事?老爺子突然臉色一沉,說啥?啪一下,把酒杯蹾在桌上,轉身就走。溢出的酒香四處奔逃,又無處躲藏。
后來我還真聽到一個故事,大概是這樣的。文嬸喜歡花,早些年上班的時候,單位里有一盆海棠,開得艷美高雅。文嬸動了心,聽好友說,這花掰個枝丫就能活。她就掰了,拿到家,整盆花土,就插了進去。轉過年,那海棠竟開出了一朵小花。那時她和文伯沒孩子,回到家,文嬸就侍弄花,澆水、換土、施肥、修剪枝葉等。又過一年,那花添枝加葉,格外豐滿。“小橋楊柳色初濃,別院海棠花正好”,文嬸就邀請單位的好友們來家里賞花。她們都稱贊文嬸的花好,真是“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后來有了運動,加上文嬸的成分不好,文嬸就以私拿公家財產之名給批斗了,還游了街。文嬸生來倔強好面子,就自己尋了短見。這件事對文伯的打擊很大,他辭了公職,一心養花賣花。街坊鄰居都知道文伯的心思,不然咋會種出那么好的花?
一天下班回來,我又路過文伯的花攤,我見花攤里的麗格海棠,確實很美。
文伯送走客人,就問:“你爸咋樣?”
“ICU,重癥監護室呢。”
“這老家伙病得不輕啊。”
我說:“是,這回,很厲害。”
“那你的負擔可不輕啊,孩子上學,補課,吃喝拉撒,花銷可不小。”
“嗯,那有什么辦法,我是男人,我得扛著。”
看到文伯的花,我就多了句嘴:“我辦公室那盆君子蘭像是生病了呢,葉子有些耷拉了。會不會死?”
文伯說:“君子蘭花葉姿態直,豐滿圓潤,魅力十足,猶如君子。花開金黃色,落落大方,很吸引人。但這花不好養,除了溫度、光線、土壤、水分有特殊要求外,最主要的是要學會轉盆。”
“轉盆?”
“君子蘭的葉片對光線敏感,養護時要把它的葉尖對向光源來處,且不斷轉換角度,角度不能隨意,要轉180度,才可保證兩側葉片均勻對稱生長。此外如果水分控制不好,則會腐敗爛根……”
我思忖片刻,“噢”了一聲,是想告訴文伯我明白了。我起身要走。文伯說:“急什么?我看你小子最近臉色不好,像是有心事。”
我就嘿嘿笑:“這您也能看出來?”
“那自然,我看人就跟看花一樣,哪盆花有問題,我一打眼就能看出個子午卯酉來。”
我確實有心事。我手里有一些權力,土地開發、房屋拆遷,我都能說上話。最近我跟一個美女老板聯系頻繁,她給我一張卡,讓我幫忙,我猜卡里面有很多錢。誰不喜歡錢呢?可作為敏感部門的干部,我常如履薄冰,得時刻警醒。但這回不同,家里的開銷逐漸增大,用錢的地方多了。
我說我很好,我揶揄他,我也要學著做一個花匠。我真想走了,結束這場對話,是故事終究要有結局的。
文伯又說:“當年你嬸子也是一朵花,好多男人都喜歡她,你爸是車間的一把手,也不例外。”
我放下剛要邁起的腳。
“那時你爸已成家,年輕有為。你文嬸是那撥女大學生里最耀眼的一個,偏偏就著迷上你爸,主動投懷送抱。有一次被我撞見,我把你爸給深說了一頓。你爸終究還是理性的,到此為止。后來你文嬸就跟了我,一個不能生孩子的男人。”
我不置可否。
“你小子要缺錢花,就找文伯,我一個人能花多少。你那盆君子蘭沒啥大問題,好好侍弄,記得要學會轉盆。花這東西,你對它好,它就會報以花開。”
轉盆,轉身?這回我道別了文伯,文伯沒有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