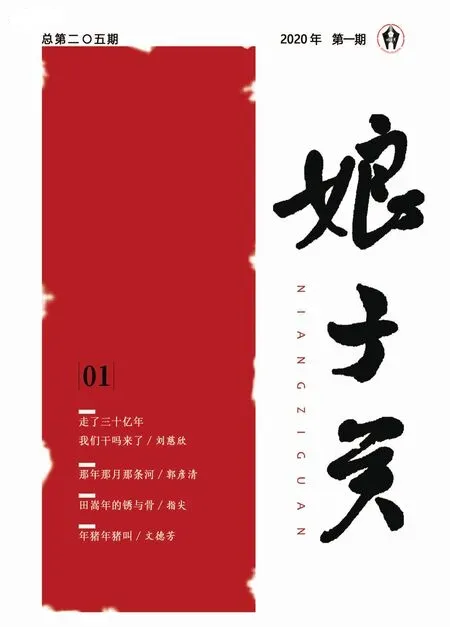那些年的有些事
文 賈晨波
圈,一般指圓環狀的物體,也用來泛指某個范圍,大小不一。大的有南極圈、北極圈,小的有同學圈、麻友圈等。
要說文藝圈,從中國到世界,那其實挺不小的,相當于個北極圈,由這個層面談論“文藝圈那些年的有些事”。咱沒那把式。人家有職業的“狗仔隊”和“御用寫手”。那些滿天飛舞,家喻戶曉的傳聞軼事,你能說清真假了?估計大多數人也只能“啊呀呀”地感嘆一下了。
我這里說的文藝圈那些年的有些事,范圍小得很,相當于個同學圈,就是自己身邊過往的陳年舊事。不好意思,臨時混同在“文藝圈”一會兒。再告你一聲,期望值不要高了,因為這里的“有些事”不緋聞、不花邊,不壯烈,不驚艷。只是我個人覺得有記下來的意味而已。
有些事或許你也經歷過
文藝工作要接地氣,是當下的一大號召與要求。回想當年在工廠宣傳隊的過往,那可不是吹,真正的接地氣,我們是毫不含糊的。
臨近冬季,宣傳隊開始集中排練,除了參加全市全局每年一度的職工文藝匯演,更多的演出是在兄弟廠礦和附近農村。到了農村,舞臺基本都是在露天的場院里或廟臺上。寒冬臘月啊,鄉民們早早就搬個小板凳占上位置了。
雪花漫天飛舞,廟臺下的鄉親們一個個已都成了白人人。然都紋絲不動,沒有散去的跡象。可見接地氣文藝“吸引力”的強大。
此時,不可尋思的事在發生,我給劉偉華伴奏二胡獨奏《奔馳在千里草原》,但他不知何故,旋律來回繞著,就是結不了尾。五分鐘的曲子快奏了有八分鐘啦,“大雪紛飛”中的“草原”可真大呀。“駿馬”也不知道“受得慌”。我的揚琴上已落滿了雪,幾乎快看不清琴弦……不知老鄉們怎么想,反正“駿馬”終于停步,獨奏終于結束后,大家的掌聲還是挺熱烈的。
那黑夜,我覺得肚子格外得餓。其實與“駿馬奔馳”的時間長短沒關系。當時下鄉演出,十有八九是吃派飯。演出前,由負責接待的各家各戶把演員們領回自家吃飯,一般是一家叫一個。先來領演員的往往都是老鄉家的半大孩們,“俺媽說來,給俺家叫一個閨女女”。如此,“閨女女”們一個個都在前面被領走。最后被領走的就是這些“小小們”了。那天,沒吃飽的原因是:我吃飯時,老鄉家那兩個五六歲的小小一直站在我身邊,眼睛就始終沒有離開過我的“大餐”:一個小碗里的四五塊烙餅。喝了一碗米湯后,我謝過老鄉,匆匆而去。騙你是狗,烙餅我一塊也沒有動。
那時候下鄉演出,連人帶道具燈光音響全部家當,常常是一個解放牌大卡車混裝了事。當然,最高級別的兩位頭頭進小轎,其他男女老少一律黑猴衣或軍大衣裹身擠在卡車上面,一路“歡聲笑語”,卻也不亦樂乎。但就是這個“混裝車”的緣故,讓我和三毛(宣傳隊的男演員)不幸“落難”。
那一次演出是在舊街公社最邊緣的深山小村,吃派飯安排在演出之后,我和三毛同在一家吃。那地方產的紅棗不賴。老鄉給吃的是棗介糕。熱騰騰軟乎乎,特別香。“半大小,吃塌老”,估計俺倆吃了人家不少。等我倆飯后趕到約定的“解放牌”停泊處、一棵老棗樹下,卡車已無蹤影。順來路追到下山的道邊,只見一路車燈閃閃爍爍眼瞅著就晃悠到山的另一面,俺倆被“遺棄”了。時近午夜,大冬天呀,周遭萬籟無聲,當時自然牢騷滿腹,難聽話肯定也不少,因“少兒不宜”,在此不便贅述。但其實此刻有歌聲響起,我和三毛胳膊相挽在一起,唱著“男聲二重唱”,向山下走去。唱歌并不是出于悲壯之情,實際是膽兒虛,唱的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想借此嚇唬嚇唬那些可能冒出來的“鬼”啦,野獸啦。天即將放亮之時,終于走到了緊鄰馬路的舊街公社所在地。求爺爺告奶奶截了一輛拖拉機,依然坐在“殼殼”上,返回工廠。“落難”怨誰?沒的追究,只怨當時沒大轎車坐,車上如果缺了人會一目了然。“混裝車”呀,“母豬養兒,在的算數”。也怨手機發明得遲,當時的固定電話才4位數。領導見了后,首先是一番真摯的道歉,其最后一句話是:“先回去睡覺,下午2點到昔陽演出。”唉,工廠的規矩,徒弟哪敢不聽師傅的。
有些事弄不清和文化與天分是否有關
文藝圈里能“混”出點名堂來,靠什么?有人說是勤奮,有人說是文化,還有人說是天分。說不清誰是誰非。反正人家都言之鑿鑿,涵蓋古今中外,舞文弄墨的,彈琴唱歌的,耍把式賣藝的……
有一位很勤奮的專業歌者,每天對著墻“咿咿咿,啊啊啊”地練呀,感動過不少人,所以,有些場合還被冠以“歌唱家”的頭銜。一次,出外輔導基層群眾歌詠活動,教大家學唱黃河大合唱。“歌唱家”首先帶頭范唱,大家感嘆“嗓子確實不錯”。但此時,一塊兒去的另一位歌手善意地悄悄提醒他,其中的一句歌詞“怒吼吧,黃河”中的“怒吼”,不能唱成“怒孔”。不料,正陶醉在大家掌聲中的“歌唱家”竟不太高興了,手臂用力一揮,說道:“絕對的‘孔’!”同伴只好把“吼”字左邊的“口”閉上,進而默然……
勤奮能不能替代了文化?如果說不能,那“阿炳”的成就又怎么解釋?但如果有了高學歷就算是有文化了嗎?此刻,想起一位煤業集團領導(正牌中國礦大本科生)對剛召入的大學生們說的一句話:我有個建議,希望你們不要以知識分子自居,我本人就還不算是知識分子,頂多是個“識字分子”。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畢業于某著名音樂院校、曾和我國聲震海內外的作曲家施先生同桌的本科作曲生厲害不厲害?估計沒人敢說不厲害。能說是有較高音樂理論文化的人了。本人初學作曲時,也聆聽過老師的“歌曲基本作法”課。原因也許錯綜復雜,老師起初被“派遣”到了中學當音樂教師。后來聽說幾學期之后,很快又被調配成了政治教員。也許是更需要文化的崗位?一直到正常退休。假如不是政治原因,這可能就是謎中之謎。之后有音樂界的資深者“悄悄”破過這個謎,說:有些人就不具有搞音樂的天分。
天分很重要嗎?這又加了一個說不清。
王金老先生如今是我市著名笑星了。起初他在市文工團當話劇演員時,我曾見識過人家的演技。文工團改成歌舞團后,王先生被分流到了某小學當了一名音樂教師。王先生實際是很困惑的,他給我講過他上課的情景:“胳夾”能一把二胡進了教室,盤腿往椅子上一坐,說,孩們,我拉甚嗯們唱甚啊!(至于二胡能“鋸”到啥水平他沒說)反正拉著二胡上音樂課的時間不長,王先生被“調”到總務處搞更“重要”的后勤工作去了。
后來,有個被稱為小品的藝術表演形式“風聲水起”,王先生由此“如魚得水”,實際上,這才是他駕輕就熟的事,根本不用讓誰去教他,也沒有顯赫的“戲劇學院”的文憑支撐。“倒糟鬼老頭”創作和表演的小品,人們就是愛聽愛看。
王金先生是不是從小就具有語言類藝術的天分?從而造就了他在戲劇表演舞臺上的了不起?值得考究。
有人說,文藝這行當,光勤奮沒文化肯定不行。但有了文化也不可能肯定就行。那還缺了甚了?也許就是所謂的天分?你去問問王金先生吧!
故事里的事說不是就是不是,是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