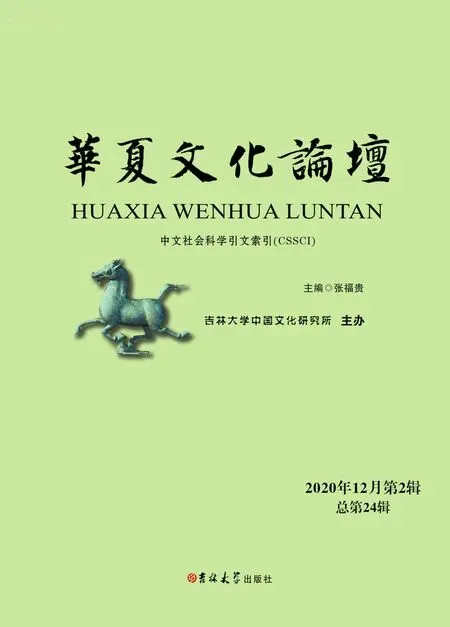鄭小瓊的“群像者”解讀及其外的詩語建構
【內容提要】被視作“打工詩人”代表的“80后”當代詩人鄭小瓊,創作初期多從自身女性打工者的視角出發書寫一代打工群體獨特的生存體驗,對其詩歌獨特意象的延伸性闡釋,清晰勾勒出當代打工者群體性的生存狀態。對鄭小瓊詩歌的“群像”性解讀使其作為女性詩人的創作個性遭受某種限定與忽視,并引發了詩人“去群像化”、展示其富有獨特藝術個性的詩歌創作的努力。本文聚焦鄭小瓊的“群像者”解讀及其外的詩語建構,力圖實現對其詩歌更多元的創作解讀與價值發現。
鄭小瓊作為“80后”當代詩人,在創作初期多憑借自身女性打工者的身份與視角,書寫一代打工群體獨特的生存體驗,對其詩歌獨特意象的延伸性闡釋,清晰地勾勒出當代打工者群體性的情感狀態和生命軌跡。長久以來,鄭小瓊詩歌的解讀與當代詩歌現象“打工詩歌”密不可分,人們聚焦于其詩歌中“打工者”這一社會階層的“群像式”建構,這使得詩人鄭小瓊成為當代詩壇一位“群像者”詩人。這種解讀方式一方面凸顯了鄭小瓊詩歌價值中獨特的部分;另一方面,又使她作為當代女性詩人的創作個性遭受到某種強行的定型、忽略乃至閹割。實際上,在鄭小瓊及其“群像者”詩人形象的構筑以外,她也進行著富有獨特創作個性的詩語世界的建構。
一
2007年,鄭小瓊憑借散文《鐵·塑料廠》獲得人民文學“新浪潮”散文獎,其獲獎評語為:正面進入打工和生活現場,真實再現了一位敏銳打工者置身現代工業操作車間中的感悟。這項榮譽使鄭小瓊一躍成為備受矚目的“詩壇新秀”。其實,早在鄭小瓊打工生活開始后不久,詩歌創作就已然成為她在繁重、無聊的流水線上疲于奔命的空閑時間里聊以自慰的方式。創作之初,“底層”是鄭小瓊詩歌的一抹底色,“打工生活”則是其創作的中心和主題,因此很快確立了她“打工女詩人”的定位,這一詩人形象的定型與她的“成名”近乎同步。一方面,鄭小瓊自身及其周邊打工者的真實生活狀態給予她創作初期的藝術靈感,以詩歌反映和思考現實成為她在創作起步階段的一個文學夙愿;另一方面,鄭小瓊以詩人的身份在詩壇嶄露頭角,在其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研究界對其打工身份的社會學判斷往往優先于她作為詩人價值的判斷,諸如“(鄭小瓊)對自己的社會身份認定有著異常清醒的認識,她以詩歌來完成了對打工者的生存素描”①張德明:《一臺大功率的機器在時光中鉆孔……》,《作家》,2008年第10期。“(鄭小瓊)作為一個龐大群體的代表,發出了一種被忽略的聲音,呈現了一種被遮蔽的狀態,這是對于‘80后’作為社會學和文化概念的一種發展和補充”②王士強:《在“權利”與“權力”面前——論鄭小瓊》,《新文學評論》,2013年2期。等等評價更多著眼于她獨特的社會身份。
當一個詩人的形象,或者說其詩歌被視為一個龐大社會群體的縮影,鄭小瓊的“群像者”形象就已產生。進一步來說,所謂詩人的“群像者”形象,指的是經由詩人本身或其詩歌,影射和反映了社會群體性的現實圖景和生存狀態,詩人身份的社會屬性往往帶有群體性,對其詩歌群體屬性的判定往往先于其詩歌藝術性判斷。從文化透視的角度來看,“群像者”并非是一種簡單的文化標簽或者創作傾向,它既是文學創作活動中,創作主體對群體性話語表達方式或有意或無意地創作追求,同時更是一種民族文化心理在文學創作領域里的反映。從創作主體來看,“群像者”的文學藝術創作帶有主觀性。《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表明“立言”“著書立說”等是文人自古潛在的追求和擔當之一。其二,文學創作本身就隱含著針砭時弊、探究人性的責任。魯迅就曾明確過自己創作小說的出發點:“說到為什么做小說吧,我仍抱著十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③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魯迅撰:《南腔北調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82頁。魯迅所謂的“為人生”自然主要指的是作為社會主體的大眾的人生。應該說,文藝帶有大眾性、集體感的創作思想根深蒂固,同時文學創作主體也傾向于在文藝作品中進行“群像”的塑造。除去作家本身為群體“發聲”“立言”的責任感與擔當感之外,研究者與讀者在作品的闡釋與解讀過程中,往往慣于朝“群體”概念的方向延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無論是大的“國”“族”抑或小的“宗”“家”都體現著對整體性的家國觀念、群體觀念的倡導。《荀子》有言:“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家國觀念、集體感等等都在強調和關注社會生活的“群體性”。“群”“眾”“們”的強烈觀念早已根植并成為固有的民族文化心理,其在文學作品中表現的尤為突出。文學自古便有“群治”的效用,《論語》有言:“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草木之名。”其中的“群”是指詩歌可以使社會人群交流思想感情,促進社會的和諧于團結。將社會群體作為書寫對象的作品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會共性的問題,如《詩經》等作品都帶有明顯的“群體性”傾向。
封建社會對“人”的個體性的壓制是以對“群體性”概念的無限放大加以實現的。近現代以來,由于現代意義的“人”的概念及其價值的重估,關注人民大眾、反映和揭示社會群體性的生存狀態,成為貫穿中國近現代文學的重要主題。當然,這與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密切相關。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革命與救亡的文學主題勢必要將人民大眾視為主要地書寫、宣傳與動員對象,群體性的文學書寫彼時是一種歷史的必然。盡管“人”的全面而自由的解放在文學創作中得以實現,但“群像”同樣也在個體形象的書寫中得以呈現、拓展與延伸。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更加明確了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指導思想,使當代文學“群”的概念更加明確下來。文藝創作深入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代言式”的文學表達方式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當代詩歌中占據主潮。及至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當代文學迎來另一個重要的、嘗試擺脫宏大敘事與集體性話語方式的收獲期,當代文學逐步呈現出濃重的個人化色彩,張揚“個性”和更具主觀色彩的超理性與超現實的現代、后現代詩歌逐漸開拓出多元化創作范式的文壇格局。不可否認,“群體性”的文藝創作是當代文藝不可或缺的重要構成,當代新詩具有經典性的詩人詩作往往多以“群”為寫作背景或以此為出發點,具有自覺的“群像”傾向。
從當代女性詩歌創作的視點出發,中國當代文壇向來不缺乏女性詩人、女性作家的聲音。尤其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舒婷、翟永明、林白、陳染等女性詩人、作家的相繼出現,一度使文壇進一步看到了作為創作主體的女性作家獨特的文學特質,乃至引發對文學概念中的“女性”意義的反思,鄭小瓊在這一點上顯然又與上述作家、詩人等不同。舒婷、林白等以詩歌及小說創作在男性作家為主流的文壇吶喊女性的聲音,它之所以能夠引起女性群體的共鳴,很大程度在于女性作家書寫的女性經驗更多側重于對性別體驗的刻畫,性別體驗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并不會產生太大的群體經驗差異。而鄭小瓊詩歌書寫的不單單是性別經驗,她將自身體驗以及其所見、所聞、所感知到的性別經驗,與自身及其書寫對象的階層經驗融合在一起,使這種經驗帶有特殊性,相對而言不構成普遍性。事實上,鄭小瓊的名字備受詩壇矚目的同時,她身份的獨特性所帶來的某種“敏感”漸漸被有些學者捕捉到、并直指鄭小瓊詩歌研究中存在的某種偏執,那就是“為了強化她的‘身份’以及公共性價值,而忽視了她作為個體的‘純粹’和獨立意義。”①張清華:《詞語的黑暗,抑或時代的鐵——關于鄭小瓊的詩集〈純種植物〉》,《當代作家評論》,2013年第4期。鄭小瓊的“群像詩人”形象及由此而來的詩歌解讀方式成為其研究中不容忽視的問題。
二
鄭小瓊的“群像詩人”形象是從其自身與底層打工者之間的身份重合開始的,她構造的是“我”即“打工詩人”的群像性詩歌影像。詩歌中“我”的第一人稱的使用,在閱讀體驗上往往容易向“我們”這樣一種群體性的閱讀經驗展開聯想與拓展:“我把自己的肉體與靈魂安頓在這個小鎮上/它的荔枝林,它的街道,它的流水線一個小小的卡座”(《黃麻嶺》)“你們不知道,我的姓名隱進了一張工卡里/我的雙手成為流水線的一部分,身體簽給了/合同,頭發正由黑變白,剩下喧嘩,奔波/加班,薪水……”(《生活》)都在以個體打工者的生存感受引入群體性的生存圖景。鄭小瓊早期呈現底層“打工生活”的詩歌里充滿詞語慌亂的碎片,轟鳴的機器、流水線、電子廠、垃圾、嘔吐物、合格率、白熾燈、彈弓、螺絲釘……正向直擊了重復而又碎片化的底層打工者的日常世界。與動態喧鬧的世俗世界呈現出鮮明對比的是對公共空間“靜”的渲染,如下面這首《藍》:
“靜謐的藍是打工生活的另一面,它的輕
它的淺,容易逝去的也容易霜凍的愛
在流浪飄泊中像微暗的藍照耀著我
除了愛,除了藍色的星光,嘆息
機臺上的鐵屑,紙片,它們用低低的聲音抹去
車間里的喧囂,奔波,勞累。剩下一片藍在愛里
開出一片憧憬,一個未來的夢境”
——《藍》①鄭小瓊:《散落在機臺上的詩》,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9年,第23頁。(節選)
工業時代人的精神與肉體在機器的巨響中被壓制、被消耗、被磨損,與鄭小瓊詩歌中頻繁出現的機器的轟鳴聲不同,《藍》以“靜謐”為主調,下工后車間里的喧囂與吵鬧終于停歇,在一片溫柔的寧靜中人也隨之從如機器般重復的動作中解脫出來,享受異常珍貴的不用再被出賣的自己的“生活”。兩種打工生活的描述清晰勾勒出被敘述者的階層屬性,同時又與日常世俗世界一并貫通。
但很快,鄭小瓊便意識到“好的詩歌是從個體生命本真出發,然后達到廣闊人群之中,是用個體本真擴展群體的特性,不是用群體意識去剪裁個體本真的獨特性。”②鄭小瓊:《深入人的內心隱密處》,《文藝爭鳴》,2008年第6期。“打工詩人”對鄭小瓊而言,帶來的不僅僅是“被標簽化”“被臉譜化”的苦惱,更深層的是對于真實底層生存狀態被遮蔽的擔憂。讀者以為讀到鄭小瓊詩作中“我”的種種,便看到了鄭小瓊“們”、觸摸到底層打工者群體性的生存樣態。而鄭小瓊卻在詩歌素材的收集中對底層打工者們的人生百態、對真實的底層生活、對現實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這些理解更多已經超越了她已有的經驗和感知。如果說在創作之初,鄭小瓊通過詩歌窺見了生存中的自己,詩歌是一面光潔而又寒栗的鏡子,映出她掙扎于生活中的疲憊與恐懼。那么,在她隨后的創作中,鄭小瓊則透過更多的打工者、底層民眾,發現了何為“生存”。
2010年,鄭小瓊的組詩《女工記》刊發于《南方都市報》,隨后于2012年由花城出版社結集出版。鄭小瓊“女工系列”的創作實則在2004年就已開始,《田建英》中那個“在風中追趕鋁罐的老婦人”開啟了鄭小瓊描繪底層女工生存狀態的圖像世界。《女工記》中幾乎每一首詩都以一名女性的名字獨立命名,使用偏“實錄”的方式加以描摹,或者干脆直接參與詩歌中的“對話”。“女工系列”中,“我”的存在已經顯露出與被述者之間的距離,當然填充其間的是詩人濃重的人文情懷。鄭小瓊在《女工記》里采取了相對理性的刻畫方式,在對形形色色的底層女工的描繪中盡可能地放棄了帶有主觀情感色彩的修飾詞,同時頻繁出現“我”與女工們直接的對話,使主人公從“我”轉移并聚焦到具體女工身上。與一種自覺的“群像詩人”不同的是,鄭小瓊察覺到自身的“代言”信號時,便有意地與公共性的“群”的標簽保持疏離:在詩歌中增加詩人與讀者之間的阻拒感,進而從被審視的空間中抽離出來,轉變為敘述的“旁白”,即與讀者共同成為詩歌作品的感受者。為了實現與書寫對象和讀者之間的距離感,鄭小瓊記錄了個體存在意義內的女工群像,試圖揭示底層生活中隱秘的部分。“有時你坐在窗口/沉默 孤獨有些憂郁 但是/這樣的瞬間 無人關注”①鄭小瓊:《女工記》,廣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第5頁。(《姚琳》)詩中的女工們有著相異或相仿的人生軌跡,在如機器般運轉的歲月中消耗著青春、愛情和生命。《女工記》盡管是一部底層打工女性的生存實錄,期間也流露出對抗傳統女性觀、女性生存方式等女性意識。更多時候,鄭小瓊融入到詩歌之中,將個體的感悟向群體性感受的方向上拉抻:“我們不斷向生活的深處潛進 現實卻/嘲笑我們 我們原以為會走向更廣闊的城市/卻不幸走進狹小的胡同”②鄭小瓊:《女工記》,廣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第7頁。(《竹青》)面對現實世界的無奈與無助、以及渴望反抗和改善生存現狀的決心顯然是群體性而非個人性的。鄭小瓊的詩里總隱藏一股向上的力,這股力猶如種子試圖破土而出,是一種生命的韌勁與耐力。這種力使鄭小瓊的“打工詩歌”在看似沉靜的外表下,暗藏著不息的生命力的涌動。盡管“女工系列”真實地呈現底層女工群體生存圖景,但似乎并未突出詩歌的文體特征,帶來詩歌與散文邊界間的某種模糊感。
對“群像”圖景的建構常常使個體形象受到忽視,鄭小瓊卻試圖以自己的方式突顯個體生命的存在樣態。在《女工記》里,鄭小瓊這樣寫道:“我們被數字統計,被公共語言簡化,被歸類、整理、淘汰、統計、省略、忽視……我覺得自己要從人群中把這些女工挑出來,把她們變成一個個具體的人……她們是獨立的個體,要從人群中找出她們或者我自己。”鄭小瓊從不規避自身的生活經歷與千千萬萬的普通女工相仿,這部分人生是她詩歌創作的素材,形成了最初詩風的平實與淳樸。同時,她又尋求在“群”的范圍內凸顯“個體”的命運軌跡,從而使自己“群像詩人”的標簽在其對形形色色、獨立生命存在的描述中逐漸淡化。以此方式“去群像化”的努力,又恰恰成為她以詩歌向公眾呈現底層打工者生存世界的一面鏡子。
不可否認,打工經驗和底層生活促使鄭小瓊走向詩歌,而詩歌又讓鄭小瓊走向更多的“自己”。當個人經驗與群體經驗相遇,一種情感便不再具有單一性,同時也不再具有私密屬性,它理應面對公共性的價值衡量尺度,而非社會學的身份界定、階層屬性等等局限認知。在群體性經驗中彰顯個體的獨特之處,摒棄群體性經驗對個人化、私人化經驗的抹殺,摒棄群體經驗書寫中的某種單一化、復制化和去個性化,無疑是鄭小瓊“到達廣闊人群之中”的一種方式。
三
“在底層 悲傷
已淪為暴唳 不幸的人用傷口
測量著大地的深度 黝黑的春天
看見底層人群不斷的分裂 他們是
麻木的器具者或者血腥的暴力者
我沒有找到與世界和解的方式”
——《底層》①鄭小瓊:《底層》,鄭小瓊著:《純種植物》,廣州:花城出版社,2011年,第45頁。(節選)
如果說以真實的生存體驗直面底層的生活狀態、以詩歌去重新闡釋和理解底層生活,是鄭小瓊詩歌創作的初心與動力。那么,當“打工詩人”的標簽預先限定了鄭小瓊詩歌創作主題及思想上的可能性時,或多或少造成了對這位“80后”女詩人其他創作才華的遮蔽和忽視。誠然,“打工詩歌”并不是鄭小瓊詩歌的全部,一次訪談中她對自己“打工題材“詩歌的評價是:“它們只構成我在現實瞬間性的對外界的部分感受,沒有構成我對外界完整的感受,它們是我詩歌理想的局部。”②何言宏、鄭小瓊:《打工詩歌并非我的全部(訪談)》,《山花》,2011年第14期。從2009年出版的詩集《散落在機臺上的詩》來看,鄭小瓊已經開始擴容詩歌主題并且語言有了明顯的提升。即使這部詩集里的多數詩歌仍以底層打工生活為藍本,由于詞語的抽象化使用和暗色空間感的營造,也使部分詩歌蒙上非現實的、虛幻般的朦朧質感,諸如“黑色工衣裹著白色的軀體與夢境/顫抖的光線間消失的白晝,沿玻璃窗/降臨的黑夜,暗淡而有些可疑的天空/那些抽象而虛無的光不小心照亮的念頭/它堅硬而冷漠,猶如陡峭的寂靜”(《寂靜》》深邃與冷峻的基調中透露著詞語的鋒利。
鄭小瓊將自己的創作劃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自己的長詩和短詩,第二類詩歌以打工為題材,第三類則是鄉村風格的詩歌。其中,長詩或許更準確地映射出鄭小瓊的內心及其精神世界。她的長詩《半島》對嘉陵江轉彎處的半島之景極盡刻畫、展開豐富的想象,沉淀出現世浮華之外的平靜與悠然。詩人波瀾不驚的內心與半島自然萬物的變化結合地如此緊密,同時又因自然之雄變生出對萬物與自我、精神與肉身之間關聯性的思考。于是,鄭小瓊寫于其中:“塵世/自有其定理,水枯石落,風吹花開/萬物以自身的完美呈現它本身”。其次,是鄭小瓊對鄉土世界的情感關照和詩意表達。關切真實鄉土中的某種凋敝和老舊成為她鄉村風格詩歌的重要部分:“被生活緊緊捆綁著的鄉村/它們溫順得有如牲畜 它們低垂頭顱/啃著寒霜似的月光”(《所見》)。這一主題與其他“打工詩人”或者說從鄉村轉入城市的群體形成精神上的共鳴。
就鄭小瓊而言,與其他書寫“打工詩歌”的眾多詩人相較,她的鄉村題材詩歌中對自我身份和文化選擇的困惑并非其寫作的出發點。它門更傾向于映射詩人本身對真實鄉土世界趨向凋敝,以及自我與鄉村自然世界肉體與精神上雙重疏離的擔憂和嘆息。《返鄉之歌》中鄭小瓊表達了人與真實鄉村現實與情感糾葛間的思考:“要用怎樣的措辭來復述我們/愛,或不愛,還有責任,無法審判/內心的背叛者,她有一百個背叛的理由。”當然,對鄉村世界中純凈、美好部分的懷戀和向往構成其間的點點亮色,諸如“蟬鳴潛泳桂花的深澗 南風梳理著/橘子樹的皺紋”“(《潛居》)“母愛像春雨樣/落著 真理像沙子樣透明而堅硬/信仰像酒液清醇 我將與牛羊歸家”(《傍晚》)等又描繪出一種避世般的恬靜、曠遠與深幽。
鄭小瓊一方面是直擊現實的,她的“打工詩歌”題材、鄉村題材創作清晰地印證了這一點;另一方面,她的詩歌又是極度超現實的、充盈著“避世”的渴望。鄭小瓊詩歌的這一部分卻也區別于虛構,長時間的直面和反映現實,詩人似乎更渴望獲得現實以外的寄托與安慰。組詩《玫瑰莊園》記敘五個女性的紅塵往事,偏散文化。六十年輪回,時間的交錯往復中,以此在的現實回溯一甲子前女性的命運軌跡,紛亂的情欲、癡兒怨女的點點滴滴在鄭小瓊的詩里勾勒得清麗動人。“玫瑰莊園”作為一個密閉的空間,似乎隱喻著詩人逃遁開外部現實世界的一方凈土,是她為自己建造的純粹的女性世界:“我必須放棄回憶中的后花園,回到/現實的世界,就像在生活中我放棄真實的淚水/戴上一張面具,在周圍形形色色虛構的人群中/活著,行走,微笑著把手伸向厭惡的人”(《玫瑰莊園》)。《玫瑰莊園》使鄭小瓊回歸女性的身份,喚醒了她作為女性的敏銳嗅覺,用以捕捉那些在機械化生產下被消耗掉、被省略掉的女性的感知和柔軟的部分,流淌著濃郁的古典氣息。
除去詩歌表現內容與主題的深化,鄭小瓊對詩歌技巧的探索也尤為引人注目。鄭小瓊認為當代的詩歌寫作,詩人的內心越來越受到來自外部世界的干擾:“詩人在寫作中陷入某種技術的偽裝,被龐大而崇高的堅殼包裹著的詩歌,無法讓閱讀者感受到詩人本身的冷暖、愛憎、肉體、內心、情感……冰冷的技術,冷漠的語言讓越來越多的詩歌變成了一種沒有生命沒有情感的物什。”①鄭小瓊:《返回內心的真實》,《作品》,2008年第10期。2011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鄭小瓊的詩集《純種植物》,可被視為鄭小瓊從“打工詩歌”主題內核中抽離的一次蛻變。這一次,鄭小瓊回歸作為詩人的起點,進行詩藝原點的探索,其間她闡發了諸多關于詩歌寫作本身的思考,譬如這首名為《失敗之詩》的詩作:
“在一首失敗的詩間 對祖先深懷愧疚
目睹權力將精致的漢語扭曲 被暴力
侵襲過的詩歌 句子與詞語
它們遍體鱗傷 像受傷的鳥只
在它顫抖與戰栗的意義中
撲閃受傷的翅膀”
——《失敗之詩》②鄭小瓊:《失敗之詩》.鄭小瓊著:《純種植物》,廣州:花城出版社,2011年,第15頁。(節選)
關注當代新詩對漢語詞語的使用和改造,詩歌在詞語的日益趨個性化和任意化的過程中,如何保護詩歌語言免受“權力”的暴力、避免對漢語言精妙部分的破壞并保有對傳統文化應存的敬意,鄭小瓊顯然在思考這樣的問題。詩集《純種植物》讓人們看到鄭小瓊以尖銳的詞語刺穿現實,從聚焦和關切個體的生存、群體的存在樣態的具象現實轉向思考時代、歷史、時間等抽象現實上。這部詩集語言高度凝練,集中反思了“自由”“獨立精神”以及“暴力”間的關聯性,整體上漫溢著思想者的凝重。無論是在意象的使用還是詩作的整體基調上都顯現出相異于此前“世俗性”寫作的詩歌風格,偏于抽象和理性。正如評論家張清華感到驚詫的那樣,鄭小瓊作為一個“80后”青年詩人,頻繁地將“歷史”“人民”“英雄”“自由”等宏大的概念融入詩句之中。在這些詞語面前,曾經在詩歌中“仰視”生活的詩人鄭小瓊蛻變為一個能夠以更宏大、更開闊的視角剖析人性、解讀社會,這或許不單單意味著一個詩人詩藝的成熟,更意味著一個獨立的人自由思考的可貴。
“群像者”的詩人定位顯然使鄭小瓊在某種意義上區別于大多數“80后”當代詩人,這一“獨異性”的呈現恰如楊克所言:“她將比同齡人有更深刻體驗的生命疼痛呈現為一種‘南方經驗’,真實地告知了當下的、中國的、底層群體的生存本相。”①楊克:《序鄭小瓊詩集〈在橋瀝〉》,方舟編:《承擔之鏡:東莞青年詩人散論》,2010年,第160頁。鄭小瓊詩歌的價值顯然并不局限于此,畢竟她已經在通過寫作實踐對此限定進行“突圍”,并且仍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