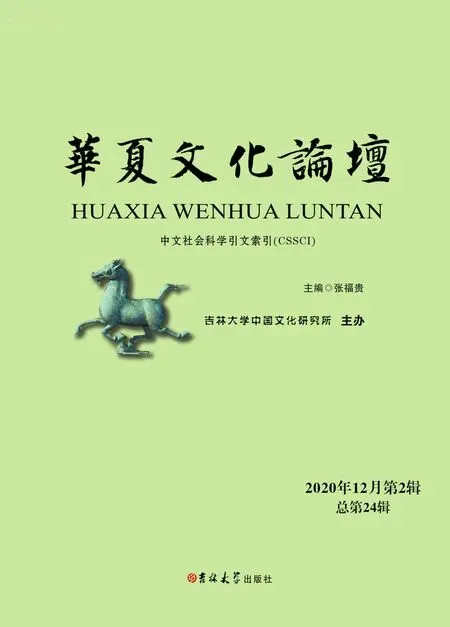成都《風土什志》中的敦煌研究
【內容提要】《風土什志》第一卷第5期以“專刊”形式刊載了五篇關于敦煌和敦煌藝術的文章,既與刊物表現風土人情的主題相吻合,又與20世紀30-40年代敦煌學在國內興起的背景對應。本文通過對這五篇文章內容的細致梳理,旨在探討“敦煌藝文”專刊在內容與藝術上的特殊性,以及刊物同人與撰稿人對于學術研究的嚴謹態度。《風土什志》拓寬了讀者觀測與了解全球風土民俗、人文歷史等方面的渠道,呈現出一幅內涵豐富、集學術性與趣味性于一體、包羅萬象的風土民俗文化圖景,并展現了編者在戰時背景下仍心系國家歷史、民族命運的精神風貌,以及遠居西南邊地的文化堅守與隱憂。
《風土什志》是四川作家李劼人于1943年(民國三十二年)9月在成都創辦的一份同人雜志,其發行人為樊鳳林,由謝揚青、向宇芳任主編。由于刊物創辦于戰時,因而無可避免地遭遇了許多問題,如缺少資金、物價波動、印刷困難等,一度停刊又復刊,過程相當波折。但《風土什志》仍堅持了六年,最終于1949年(民國三十八年)10月停刊,共出三卷14期。
在創辦《風土什志》之前,李劼人已有豐富的辦刊和編輯經驗,如1918年創辦《川報》并任總編,1919年任《星期日》主編,1937年任《建設月刊》總編,1939年任會刊《筆陣》編委等。這些經驗使李劼人對辦刊理念和宗旨等都有了一套屬于自己成熟的認知系統。不同于李劼人此前創辦或參編的一系列刊物,《風土什志》更多地是以形式多樣、題材廣泛、內容豐富的“風土”、民俗、文化知識為取材范圍,且具全球化的視野。這在1943年第一卷第1期的《發刊旨趣》中已有明確展現,“本刊性質為‘研究各地人生社會既往與現實的人文地理及地理知識,收集各方風土人情資料,作詳確廣泛的調查報告,且客觀的描述當時社會環境,闡述其衍變等歷史與地理的因果關系,作現實問題之參考’”①李劼人:《發刊旨趣》,《風土什志》,1943年第一卷第1期。,并明確表示刊物在“內容方面,摒除空泛的理論,力求真實、趣味;行文盡可能的達到生動化、故事化的原則;即是說我們將以‘雅俗共賞’的姿態,貢獻于讀者之前,從而獲得一些宇宙間森羅萬象的知識”②李劼人:《發刊旨趣》,《風土什志》,1943年第一卷第1期。。另外,《風土什志》與同時期其他表現民俗風土的刊物也有所區別(如《甘肅民聲》、《西北文化》等),它所刊的文章顯然具有更高的文學性,而非干癟的“科普性”文字,它兼具濃烈的文化意味以及較高的文學價值。
《風土什志》沒有明確的欄目設置,主要刊登介紹和研究中外風土人情的文章和調查報告,內容涉及民俗、歷史、地理、生物、社會、美術、山歌、民謠、民間傳說等諸多方面,在40年代引起了熱烈的社會反響。在第一卷第2-3合期的《這一期》中,編者寫到,“從創刊號問世后,我們獲得廣泛的愛護和各方的獎飾,不到兩月,銷路達十四省,以至國外”③編者:《這一期》,《風土什志》,1943年第一卷第1期,第5頁。,由此可見,《風土什志》的受眾面廣,影響力大。
本文將從《風土什志》包羅萬象的內容中選取與敦煌相關的部分,一方面對《風土什志》中涉及敦煌與敦煌藝術的文章進行具體解讀,另一方面則是以這些文章為窗口,探索刊物的思想內核以及編輯和撰稿人群體的精神面貌。
一、《風土什志》中對敦煌的研究
《風土什志》中與敦煌相關的文章共五篇,均發表于1945年4月第一卷第5期,它們分別是陳覺玄《從敦煌莫高窟壁畫中所見到的佛教藝術之系統》,關山月《敦煌壁畫的作風——和我底一點感想》,史泰英著、亞珞摘譯《敦煌秘藏運英記》,伯希和《偉大的敦煌藝術:中國西域探險記片段》,以及編者的《敦煌點滴》。其中,伯希和《偉大的敦煌藝術:中國西域探險記片段》與編者的《敦煌點滴》兩篇文章,未在目錄中呈現。
(一)關于“敦煌藝文”專刊
本期封面為張大千所臨的《敦煌初唐供養菩薩》,左側刊物名稱下標有“敦煌藝文”四字,另在目錄后附有張大千所臨《供養菩薩》,在文章中或文章后附有關山月所臨的敦煌各代插畫共五幅。
《風土什志》每一期都在目錄下方設置編者語,即“這一期”,其內容并不局限和固定于某一方面,而是極為豐富。或是編者用以簡介文章或撰稿人信息,或是重申和補充刊物“發刊旨趣”中的內容,或是和讀者進行簡單誠摯的交流,或是征詢讀者對于刊物改版的建議。“這一期”可以作為研究刊物風貌的一個窗口。在第一卷第5期的“這一期”中,編者提及“這期所載敦煌藝文雖不多,卻都是精湛之作,我們應特別感謝陳覺玄先生、張大千、關山月諸先生”④編者:《這一期》,《風土什志》,1945年第一卷第5期。。這與1944年7月第一卷第4期編者語中的部分內容遙相呼應,即“本志第五期準備發行《敦煌石室》專刊,已請畫家張大千、關山月、陳覺玄教授等撰述專稿”①編者:《這一期》,《風土什志》,1944年第一卷第4期。。第4期和第5期的發表時間相隔九個月,據編者所言,第5期的文稿本于1944年夏就已收到,然而因面臨戰時資金、印刷等方面的實際困難而被迫延期,但不管怎么說,第4期的“預告”終究沒有落空,編者發行“敦煌”專刊的“承諾”最終還是得到了實現。
這五篇文章也確如編者所言,“雖不多,卻都是精湛之作”。從文章表現的內容來看,《敦煌點滴》可看作是對其余四篇文章的收束和總結。文章主要是對敦煌藏經洞和敦煌藝術的概要,內容包括兩部分,一是對敦煌經卷被竊事件的說明和對經書分布情況的統計,二是對敦煌經卷語言、內容等的簡要概括。這篇文章的功能大致相當于本期敦煌專刊的“簡介”或者說是“概述”,剩下四篇文章才是專刊的主體部分。同樣按照文章內容進行劃分,這四篇文章可大致分為兩類:一是對敦煌藝術(主要是壁畫這一藝術形式)特征、風格的分析,即陳覺玄和關山月之文;二是對敦煌經卷被竊過程的說明,即史泰英和伯希和之文。因而本文對文本的解讀也就主要落在除《敦煌點滴》之外的四篇文章上。
(二)竊經者對竊經事件的講述
《敦煌秘藏運英記》是英人史泰英的自述之文,由亞珞摘譯,性質類似于“回憶錄”。作者史泰英是國外第一個發現并竊取敦煌秘藏的“探險家”,譯者亞珞則是《風土什志》編輯之一謝揚青的筆名。史泰英在這篇文章中,記載了1907年前往敦煌,發現秘藏,并設法將九千余卷經書運回英國的詳細過程。史泰英首先肯定了敦煌千佛洞經卷的價值所在,即“研究佛教藝術極佳之材料”②[英]史泰英:《敦煌秘藏運英記》,《風土什志》,1945年第一卷第5期,第13頁。,然后用大量篇幅回憶竊取敦煌藏經洞文書的始末,其中穿插他對敦煌千佛洞外觀、內部構造、藏書分布等信息的客觀描述,以及對守經道士王圓篆的評價,對藏書年代、研究價值、壁畫風格等的主觀判定。這篇文章在“敦煌藝文”專刊中所占篇幅最長,其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講述史泰英發現敦煌藏經洞,并在秘書蔣孝琬的幫助下,以王道士迷信宗教之情感為切入點,為運取經卷做準備工作;第二部分為史泰英進入藏經洞實地考察所見,以及史泰英對敦煌壁畫等的簡單介紹;第三部分主要是對藏經洞經文的信息和石室內部構造的簡介,以及竊經細節和成果。
《偉大的敦煌藝術:中國西域探險記片段》的作者伯希和,是繼史泰英之后第二個竊取敦煌經卷的法國人,他的“探險記”在內容上和史泰英的文章有所不同。伯希和不像史泰英那樣,事無巨細地描寫自己進入敦煌并取走經卷的過程,他甚至根本沒有花費筆墨去回憶這段由他本人創造的歷史,僅用一句“當我們到那里之前,我們的同志史泰英已經探訪過了”③[法]伯希和:《偉大的敦煌藝術:中國西域探險記片段》,《風土什志》,1945年第一卷第5期,第5頁。簡單略過。伯希和更多地是表達他對敦煌藝術的高度關注和贊許,他強烈認同魏代藝術的淵源深厚,并將關注的重心落在敦煌文書和手抄本上。伯希和從敦煌藏經洞竊取的文書達一千五百卷,他對敦煌攝影進行整理和匯總,撰《敦煌圖錄》共計六卷,此事在《敦煌點滴》中也有所記載。
雖然史泰英和伯希和的文章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其中所暗含的文化意義卻相似。兩人同為竊經事件的親歷者,當他們在回憶竊經成果時,作為敦煌文化(或者說是中國文化)“他者”所體現出的強勢地位和優越心理溢于字里行間。在史泰英的文章中,這種文化他者的優越感顯然更為徹底和強烈。史泰英以文化侵略者的身份強勢介入敦煌,無論是他對道士王圓篆“愚昧”的反復評價,還是他在以數目不多的馬蹄銀“換”得幾千卷經書后沾沾自喜的心理狀態,抑或是他在經卷運送回英國后“余滿足之余,憶及狡詐執拗之王道士,始覺舒展”①[英]史泰英:《敦煌秘藏運英記》,《風土什志》,1945年第一卷第5期,第28頁。的自述,都能體現出這一點。伯希和雖然沒有像史泰英那樣大費篇幅地書寫竊經過程,但他在《偉大的敦煌藝術》文本結束處“從此法國圖書館,在歐洲誰也不能匹敵,因為中文抄寫本,我們儲藏之富,中國也不能趕上了”②[法]伯希和:《偉大的敦煌藝術:中國西域探險記片段》,《風土什志》,1945年第一卷第5期,第5頁。的表述,同樣表達了他內心的自滿之意,這種心理實則和史泰英那種明顯的優越感并無多大差別。
這樣看來,《風土什志》在敦煌專刊中選取這兩篇由竊經事件始作俑者寫作的文章,或許也有自己的考慮和思量。聯系刊物誕生和“敦煌藝文”專刊發行的時間和時代背景來看,這兩篇以外來者視角寫作的文章,首先固然是為了給讀者提供一個更為直觀地用以了解敦煌相關歷史和文化藝術信息的方式,但也不排除另一種可能性,即編者想借此期專刊表達對優秀風土文化被外來文化破壞和偷盜的痛惜和憂慮,并試圖在戰時特殊背景下喚醒中國讀者對包含敦煌文化在內的中國民族文化的重視。之所以提出這種可能性,一是考慮到當時的時代語境,二是因為刊物創辦者李劼人本身就是一個具有強烈的風土、民族情懷的學者和文人。他在《發刊旨趣》中就提到,要通過對風土人情的了解,看到日本等“敵人”的“貪婪的、殘酷的劣根性”③李劼人:《發刊旨趣》,《風土什志》,1943年第一卷第1期。,并借此建立屬于中國人自己的關于風土文化的認知系統。
(三)對敦煌藝術的理論分析
陳覺玄和關山月的文章都是從敦煌眾多藝術形式中選取一種,即敦煌壁畫,對其風格和特征進行具體分析。陳覺玄《從敦煌莫高窟壁畫中所見到的佛教藝術系統》一文,對敦煌壁畫進行了細致地探究和剖析。他的文章在內容上大致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紹敦煌和莫高窟;第二部分分別介紹莫高窟六期④陳覺玄在文章中闡明是分為四期,但根據實際內容來看,應該是六期。壁畫特征及藝術風格,這一部分是文章的主體;第三部分則是對國內外關于敦煌研究成果的簡略概述。陳覺玄這篇文章的重點在于探討佛教藝術在莫高窟壁畫中的流變,他將壁畫分為六朝(主要是魏代)、隋代、唐代、五代、宋和西夏、元代這六期,其中敘述的中心又在于魏代壁畫。
陳覺玄認為,六朝尤其是魏代壁畫為健陀羅的藝術風格,其清疏和沉雄者各有其特色,并舉諸多實例加以論證。隋代壁畫則延續六朝風格,缺少新變,但中國化特征加強。陳覺玄在論述唐代壁畫特征時,將其分為初唐、中唐、晚唐三個階段,舉例論證,認為其風格源于中印度的佛教藝術,即笈多式藝術。陳覺玄對后三期壁畫的論述不如前三期詳細,但仍然采用特征分析輔以實際壁畫進行佐證的方法和模式。總體來看,陳覺玄在分析敦煌壁畫藝術特征和風格時,始終堅持結合各代社會、時代、文化背景等進行論述。他的論證并不空泛,而是聯系具體的敦煌壁畫加以剖析。另外,陳覺玄還勾勒出國外學者研究敦煌佛畫的線索和脈絡,并概述中國本土對敦煌壁畫的研究成果。在文章中,國內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通過實地考察后得出的,包括他本人亦是如此。陳覺玄的研究思路很清晰,其論述充分且有理有據,具有極強的專業性。
關山月的《敦煌壁畫的作風——和我底一點感想》一文,則更為細致地對敦煌各代壁畫的獨特風格進行具體分析。關山月在正式開始論述之前,首先肯定了敦煌壁畫的價值,他稱其敦煌為“佛教藝術之宮”①關山月:《敦煌壁畫的作風——和我底一點感想》,《風土什志》,1945年第一卷第5期,第7頁。,并借他人“一本至有系統的中國古代美術史”②關山月:《敦煌壁畫的作風——和我底一點感想》,《風土什志》,1945年第一卷第5期,第7頁。的評價說明研究敦煌藝術的必要性。他的文章在內容上可分為兩部分:一是將敦煌壁畫分為三期分述特征,二是書寫對敦煌壁畫的觀后感。
關山月對敦煌壁畫的分期不如陳覺玄那樣細致,他將敦煌壁畫分為魏代、唐代、五代宋元三期,但他同樣把論述的重點放在魏代壁畫上。關山月對敦煌各代壁畫風格的成因和陳覺玄的分析類似,他們都認為不同藝術風格的形成與社會背景相關,但相較而言,關山月更側重對壁畫本身的藝術分析。在文章中,關山月對于實際壁畫的具體論述更多,他多是從各洞壁畫中選取典型分別論述,再提取凝練出各代特點。比如,他在分析魏代壁畫的風格時,就選取三幅經典壁畫對其特征進行詳細剖析,最后通過典型,從內容、用色、造形等諸多方面得出魏代壁畫為健陀羅式風格的結論。在論及唐代壁畫時,他同樣以豐富的具體壁畫為例證,總結歸納出一個普遍性的藝術特征。總的來看,關山月的理論分析與實際情況結合得極為緊密,其論述多是從具體歸納出一般,生動且易理解,同時亦不失學理性和專業性。
關山月在文章最后一部分的“感想”中,體現了他作為中國學者對本民族文化藝術的高度關注,并彰顯他對開拓中國自己學術研究重要性的強調。他提及敦煌學在歐洲興起,已經引起全局式的研討,而中國卻缺乏這種全面的、整體的、系統的研究,多是停留在私人的研討和探索上。但關山月對這種看似慘淡的態勢也并非過度悲觀,而是從對敦煌壁畫的研究出發,強調通過時代性和充實的內容還原中國文化生命力的必要性。關山月的分析和思考,以小見大,充分結合時代語境,真正體現了中國學者為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而做出的努力和嘗試。
從這個角度來看,《風土什志》在發行“敦煌專刊”時向陳覺玄和關山月兩位專業學者約稿,實際上是一種明智的舉措。關山月曾作為敦煌文化考察隊伍的成員,前往敦煌莫高窟進行實地考察,陳覺玄則依托考察隊伍的成果進行分析,同時兩人又都是藝術領域的專業人士。因而這兩篇文章,既富有專業性,又體現了學者風骨,不僅為敦煌藝術研究領域提供了優秀成果,還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研究者們正在逐漸填補中國在敦煌學領域的話語權空缺。也就是說,陳覺玄和關山月的研究基于中國的本土文化資源而展開,這樣的研究對于中國完善對敦煌藝術的分析,以及建立屬于自己的學術批評話語體系,無疑具有明顯的推動作用。
二、基于前有成果的專業研究
《風土什志》并不是第一個關注敦煌并分析敦煌文化的刊物。在它發行敦煌專刊以前,已有不少刊物將目光投向敦煌及其文化藝術,并且發表的敦煌文章在數量上也遠超過《風土什志》。
(一)前有期刊對敦煌的研究
首先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風土什志》中敦煌文章的數量問題。段曉林在發表于《敦煌研究》2018年第6期的《民國時期敦煌學期刊文獻研究》一文中,對民國時期散見于各種期刊中的與敦煌有關的文章進行信息整理和數據匯總。在第一章“刊載敦煌學論文期刊的基本概況”中,段曉林對各類期刊中關于敦煌的文章數目加以統計,并在正文中附有表格。表格顯示,《風土什志》發表的敦煌文章數量為六篇。但不管是查詢上海圖書館“晚清民國期刊全文數據庫”現存的14期《風土什志》全部內容,還是在鄭阿財、朱鳳玉主編的《1908-1997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①鄭阿財,朱鳳玉:《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1908-1997)》,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0年。等工具書中檢索《風土什志》發表的敦煌文章,最終得出的結果都為五篇。段曉林在整理之初就已界定了以文章為統計范圍,因而首先可以排除她將本期張大千和關山月所臨的敦煌圖畫納入統計之列的可能性。那么,通過閱讀全刊中所有相關文章大致內容后可知,唯一可能存在疑點的應該是鄭象銑發表在《風土什志》1944年第一卷第4期的《旅蘭紀瑣》一文。鄭象銑是中國著名的地理學家,1943年第一卷第1期的編者語《這一期》中,有編者對他的簡短介紹——“鄭象銑先生是研究地理的,現執教于金女大,腳跡遍布青康寧諸省”②編者:《這一期》,《風土什志》,1943年第一卷第1期,第5頁。。《旅蘭紀瑣》這篇文章記載了鄭象銑對蘭州的地理、風土、民俗等方面的觀察和介紹,鄭象銑用生動的文字展示了蘭州在交通、飲食習慣、物產、教育等方面的地域特色,以及石田、水車等城外景象的獨特。從內容上來看,這篇文章并未提及敦煌,至于鄭象銑先生是否去過敦煌,還不能從這篇記游文章中得出結論。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旅蘭紀瑣》確實與敦煌無關。這唯一的疑點也因此可以排除。所以,段曉林統計為六篇,或為誤記,實際上,《風土什志》中的敦煌文章應為五篇,即1945年第一卷第5期“敦煌藝文”專欄中發表的這五篇文章。
而在它之前的許多刊物,關于敦煌文章的發表數量則遠超出五篇。這里僅選取幾個發文量多且影響力大的刊物為例。
1.《東方雜志》共發表與敦煌相關的文章十五篇,但其中大多都是對敦煌千佛洞圖片、攝影、經卷信息的整理和匯總,涉及具體藝術特征和風格分析的理論文章僅占少數。
最早的一篇文章是羅振玉發表在1909年第六卷第10期的《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這篇文章第一次向國人詳細介紹敦煌石室的藏書及其被發現的情況,也是國內敦煌遺書整理和匯編工作的開始。1920年第17卷第8期刊載了靜庵(即王國維)的《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一文,此文首次對敦煌文學進行系統地介紹和學術評論,開啟了國內對敦煌文學的研究。這兩篇文章雖然都具有開拓性的意義,但是它們所針對的研究領域與敦煌藝術研究并無直接聯系。直接與敦煌藝術掛鉤且影響力最為深遠的文章,是賀昌群發表在1931年第28卷第17期的《敦煌佛教藝術之系統》,這篇文章才是真正意義上首次表明中國對敦煌的研究“已由敦煌文獻擴大到敦煌石窟藝術”①王旭東,朱立蕓:《近代中國敦煌學研究述評》,《甘肅社會科學》,2011年第6期。,并為國人打開一個了解敦煌藝術的窗口。
2.《說文月刊》共刊敦煌文章二十四篇,其中多為對敦煌石室經卷內容的梳理之文,其中研究敦煌石窟藝術的理論文章有三篇,即姜亮夫發表于1943年第三卷第10期的《敦煌經卷在中國學術文化上之價值》,震雷發表在同期的《敦煌的佛教藝術》,以及何正璜發表在同期的《敦煌莫高窟現存佛洞概況之調查》(主要是第三章論及敦煌佛教藝術相關內容)。
3.其他期刊。《微妙聲》中刊載的敦煌文章數量為十八篇,多數為經卷題記匯編,而少理論分析。《甘肅民聲》一共發表十七篇與敦煌相關之文,但所有內容均為“拾遺”。
由此可見,雖然《風土什志》發表的敦煌文章僅有五篇,但它確如編者自己所言,“雖數目不多,卻都是精湛之作”。其精湛之處,前文已經論及,在此不再贅述。對前有期刊同題材發文量進行簡單梳理,也并不是想凸顯《風土什志》“敦煌藝文”在藝術等方面的精妙,而在于尋找《風土什志》所發行的敦煌專刊的特殊之處。事實上,像《風土什志》第一卷第5期這樣通過向專業學者約稿,并配有專家繪圖來設置專刊的期刊可能并不多見。而且,《風土什志》為敦煌專刊所選和所約的文稿,不僅包含對敦煌客觀信息的描述和介紹,還容納了集文學性與專業性為一體的理論分析和學術批評。其專刊之“專”,可從三個維度解讀,一是所選領域之“專門”,二是學者研究之“專業”,三是編撰群體態度之“專注”。這正是《風土什志》的特殊所在。
(二)撰稿人與敦煌的聯系
中國學者對敦煌的研究最初多是以倫敦圖書館、巴黎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的圖錄、攝影和經卷等為資源,直到1925年,陳萬里作為北京大學的代表跟隨華爾納前往敦煌實地考察,才開啟了國內敦煌考察之風。20世紀30-40年代,中國大批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美術家等奔赴敦煌,對敦煌的歷史、文物、壁畫等進行實地的、細致的分析和研究,促成了敦煌學在中國形成一門專門的學科。這一時期的研究有別于前人的研究,研究者直接接觸到敦煌的一手材料,所使用的都是中國本土的研究方法和學術話語。
前往敦煌考察的隊伍中,比較重要的是1941年由藝術家王子云領導的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考察團一方面調查敦煌佛洞情況,一方面準備臨摹壁畫。南京師范大學劉朝霞于2013年寫作的《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史事考證》,詳細介紹了藝文考察團的相關事宜,評價其“在極為艱苦的環境下開赴西北,足跡遍及川、陜、豫、甘、青五省,運用攝影、臨摹、拓印、復制、測繪、記錄等較為完備的資料收集方式,搶救收集未淪陷區域的各種古代藝術文物資料,成績卓著,為保護我國古代遺珍做出了重要貢獻”①劉朝霞:《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史事考證》,南京師范大學,2013年。,充分肯定了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在敦煌研究史上的獨特價值和重要地位。與王子云考察團同時進行研究的是畫家張大千的隊伍,張大千偕夫人楊宛君等到達敦煌,清理309個洞窟,進行編號共臨摹壁畫近300幅,后來在成都、重慶、上海舉辦敦煌壁畫臨摹展,在全國范圍內引起一股“敦煌熱”。《風土什志》敦煌專刊的封面即是張大千此次考察的成果之一。
1943年,畫家關山月到莫高窟考察,“用速寫法臨摹,凡得八十余幅”②陳覺玄:《從敦煌莫高窟壁畫中所見到的佛教藝術系統》,《風土什志》,1945年第一卷第5期,第9頁。壁畫,并據此分析各洞壁畫特征,撰文發表于《風土什志》。也就是說,關山月之文,是在實地考察后具體分析而寫出來的。
而“敦煌藝文”專刊理論文章的另一個撰稿人陳覺玄,其文雖然不是在實地考察后所寫,但他卻是以各個敦煌考察團的實際成果為文本基礎和藝術資源的,“茲就張氏大風堂摹本中所收并其在成都展覽時所陳,參以吳關兩氏所繪,及許氏攝影,史泰英、大谷光瑞書中所引,分別時期,比較同異,考其系統,略如上述”③陳覺玄:《從敦煌莫高窟壁畫中所見到的佛教藝術系統》,《風土什志》,1945年第一卷第5期,第9頁。,他在文章中的自述已經能夠充分體現他的分析同樣有實例可依,有實據可證。
這也就是說,《風土什志》敦煌專刊的撰稿人,與其關注和分析的對象始終保持著緊密的聯系,關山月實地考察后結合實際壁畫具體分析,陳覺玄根據當時可靠的考察結果為資源,對敦煌壁畫進行整體觀照,其研究的方法嚴謹,態度認真,成果切實,很能體現撰稿人群體作為專業學者的精神面貌。
三、遠居西南邊地的文化堅守
在《風土什志》敦煌專刊的編者語《這一期》中,編者提到了刊物發行與印刷的實際困難。事實上,這并不是編者第一次提到在刊物發行過程中所遇到的種種問題。自從1943年刊物創辦之初開始,李劼人等編輯同人面臨的困難和波折就始終沒有中斷。李劼人在《發刊旨趣》中言辭懇切地說到,“這工作太艱巨了,而我們的能力卻非常的薄弱……本志經過十個月的籌備,三個月的印刷”④李劼人:《發刊旨趣》,《風土什志》,1943年第一卷第1期。,這充分體現《風土什志》的誕生就已經很艱難了。而在此后,幾乎每一期的編者語《這一期》,都或多或少地表述了編者對刊物延遲發刊這一“事故”的深刻歉意以及對此做出的解釋。第一卷第1期提到“出版界一般所感受到的印刷困難”⑤編者:《這一期》,《風土什志》,1943年第一卷第1期,第5頁。,第一卷第2-3合期論及“受夠了印刷廠家的磨折”⑥編者:《這一期》,《風土什志》,1943年第一卷第2-3合期。,第一卷第4期表明《風土什志》在戰時既遭印刷難題又遇資金困難,第一卷第5期則提出“《風土》正自籌印刷”①編者:《這一期》,《風土什志》,1945年第一卷第5期。以解決出版問題。這樣的表述在《這一期》這一窗口中屢次出現,已經成為一種常態。也正因如此,《風土什志》一度于1946年停刊。即使是在1948年復刊以后,刊物所面臨的銷售、經營等困難仍未有緩解,1949年第二卷第5期甚至采用“夾江土紙印刷”代替,其運行之舉步維艱由此可見。
但即便是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風土什志》仍堅持出版發行,且每期所刊載的文章均為質量優秀之作。從內容上看,《風土什志》所刊的文章包含文學、民俗學、社會學、歷史學、考古學、生物學、地理學、美術等眾多方面。從集結在《風土什志》周圍的同人撰稿人群體來看,他們都是在各自領域頗有建樹的文人和學者,如前文提到的關山月、陳覺玄,都在美術和繪畫領域成就很高,又如吳其昌、鐘祿元、陳國樺、陳志良、鄭象銑等人,也都是其各自研究領域里的專家。總體來說,他們所撰之文,范圍廣,題材多,內容豐富,滿足了刊物編者欲使《風土什志》成為“學術性、研究性,而又一般性的讀物”②編者:《這一期》,《風土什志》,1946年第一卷第6期。的希望和要求。
從以李劼人為核心的刊物負責人群體來看,他們對于文稿的選擇以及對于刊物宗旨的反復申明,都體現了他們身處西南邊地但并不將視野囿于一隅的風貌。李劼人在《發刊旨趣》中明確指出,“我們對民族間的風俗,愿以激濁揚清的態度,加以闡揚和改進,籍此對增進民族間的友誼,略效綿力”③李劼人:《發刊旨趣》,《風土什志》,1943年第一卷第1期。。在實際的操作中,他也始終堅持對民族風俗文化的內涵加以關注和具體呈現。他關注的風土文化形式多樣,涉及的區域廣,既包含對國內不同民族的文化內涵的介紹,又囊括對域外獨特風情的普及。這不僅能促進國人對于中國文化的關注和理解,同時也為了解外國文化提供了一個窗口(不止是西方文化,根據《風土什志》中的不少文章,可以看出還有東南亞文化等)。“敦煌藝文”專刊只是其中的一個典例,類似的專刊在《風土什志》中還有許多,比如“采風錄”、“西藏專輯”、“紀念特輯”等。
通過這些研究,我們能夠窺見刊物編者在戰時背景下的文化堅守。即使編者身處西南邊地,但他們對民族、風俗、日常文化始終持有高度關注的態度,并暗含對文化發掘和留存的隱憂之感。《風土什志》對呈現地域、民族風土文化自始至終都飽含熱情,并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風土什志》的生命力也正在于此。盡管《風土什志》“存活”的時間并不算長,發行期數也不算多,但刊物從內到外都呈現出一種強烈的“風土”情結以及人文關懷。
綜上,正因為《風土什志》對風土民情的這種文化堅守和特殊情懷,才給后來的研究者們留下了一份份珍貴的材料。借由這些材料,我們不僅能夠窺見刊物編輯的精神面貌,同時還能一步步接近并還原《風土什志》在20世紀40年代的獨特文化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