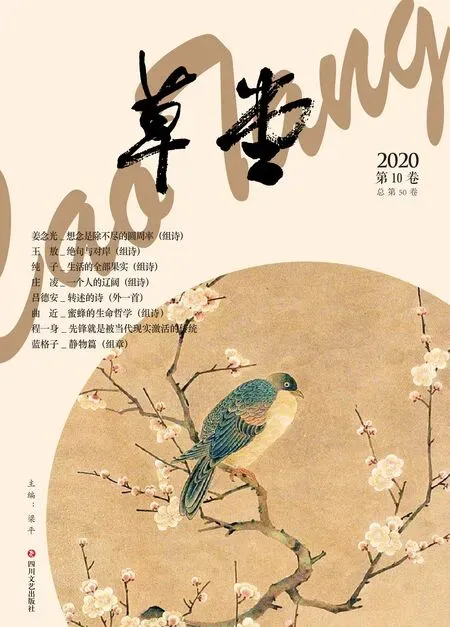轉述的詩(外一首)
1
紐約,一個星期天早晨,因為遲起
我才夢見詩歌幾句。詩閃著光。
但它不像從現實的抽屜抽出,
惡狠狠地端在手上,也不像天降神諭
要人散魂落魄,都收回到天上。
它更似在某處滴滴答答的雨點,
若即若離,中間透著幾分涼意,
只在昏暗里才映入眼簾。
但它分明是詩,分著段,分著行,
一直斷斷續續,又忽隱忽現,
叫蒼白的字里行間恍如隔世,
叫你生活在其間的世界顯得渺不足道。
但是如此細雨般地落在紙上,
讓人應接不暇,到最后又未留下
哪怕只言片語——只留下我
醒來后一邊輕描淡寫一邊繼續
在床上翻來覆去——感覺就像它
是我憧憬已久的。這才讓我驚嘆。
這般輕浮的一幕,或者就像
剛才我還渴望著,渴望著
長時間地觸摸和抵達,
可當我的眼睛虔誠地下沉,
身體卻已被憤怒地提出水面!
2
她手里抓住自言自語時
不經意地攤開的那件淡白色睡衣。
在這一天的后半天,她白日夢般的黑色眸子
正轉變成褐色。她會隨時離開。
但是在她那可見性的來回走動中,
卻始終給人不動的印象。
她赤裸,一絲不掛地隔著那道街窗
卻不易被窺視,除非她把自己點亮。
喲,上帝知道她身上天生有一種絕望
只是她把這絕望像一把受潮的琴
輕放在琴盒里。她真是寂寞孤獨慣了。
至少這段時間是這樣的。
就在她那有著很多房間的房子里
她曾經這樣說:“在這所空蕩的房子
我只喜歡這間令靈魂安靜的房間
如果那也算是房間的話。”她指的是她的浴室
她說:“當我淋浴,瞪見水從身上緩緩流下
淌得滿地,我就想著,如何才能在生活中
獲得一支可以在水中寫字的筆。”
3
然而就像蓄謀已久,那段臨窗的
百老匯街道發生了爆炸。有兩百碼長
那里下水道的煤氣管,以及所有埋伏的零件
都跟著騰空飛起——你看得見那地方
已被死死圍住,一排排刷著熒光顏色
的擋板寫著“危險”兩個字。
兩道濃煙散發著煤氣藍色的氣味。
“有好些天了,我看見
部分居民已被及時疏導
但仍有一部分不愿離開的人
在房間里被反復地勸說。”
離開此地。你住過電梯房,但是電梯不走了。
街燈還亮著,不分晝夜。街上
成群結伙走著人,互不相識。
離開此地,那里地面地獄般張著口。
穿過它一場音樂會開始了,但是
它節目單上的天堂正在推遲
和一個異鄉人的神祇正在從這座城市
的另一端出口悄然離去,
留下那末日般疾駛的車流,
一半震驚于可怕的自我轟鳴,
一半已完全陷入了癱瘓。
[幾乎是一種陳述]
這個世界忙于降雪
它幾乎像一場陳述:
我有一支白色的歌
我有一支放蕩的歌
這個世界忙于降雪
它幾乎像一場陳述:
我需要不停地唱
我需要反復地唱
就這樣一陣白過一陣
但太多太多的雪
把窗口都封住了
把房子變成墳墓
就這樣忙于一場愛
仿佛那是一生的許諾
而你還能巴望著什么
那是一生的許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