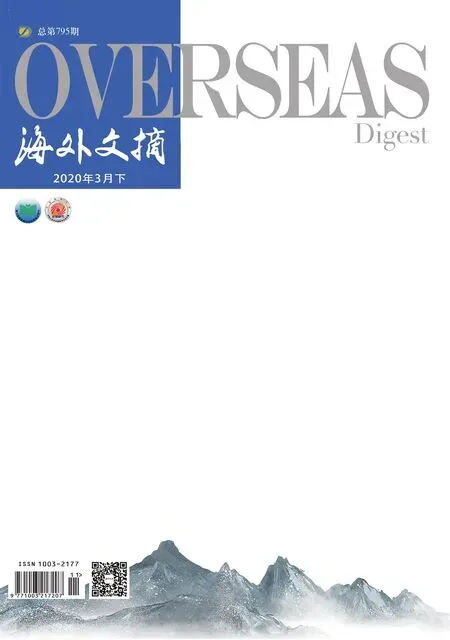從權力與規(guī)訓視角分析社區(qū)居家養(yǎng)老模式下的養(yǎng)老觀念
韓雅竹 韓春雨 于然
(吉林大學,吉林長春 130012)
隨著老齡化趨勢不斷加深以及社會的快速轉型,我國的養(yǎng)老問題日益嚴峻。而在傳統(tǒng)養(yǎng)老觀念中,老年人更青睞居家養(yǎng)老和與子女同居養(yǎng)老,但當今社會撫養(yǎng)比增大,中青年勞動者忙于工作難以親自照料老人,其次老年人口愈發(fā)高齡,失能半失能的老人群體擴大,失去了自理能力的老年人難以實現居家養(yǎng)老。針對這類現象,國家提出社區(qū)居家養(yǎng)老服務模式以滿足老年人多方面的需求,但老年人對社區(qū)養(yǎng)老機構的態(tài)度卻較為消極。針對這種矛盾本文將從權力與規(guī)訓的視角對社區(qū)居家養(yǎng)老模式下的養(yǎng)老觀念進行分析,并希望借此視角對相關問題提出解決方法,優(yōu)化醫(yī)養(yǎng)結合社區(qū)居家養(yǎng)老模式,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
1 福柯的“權力與規(guī)訓”理論
權力與規(guī)訓理論來自于法國哲學家福柯的微觀權力論、知識與權力、規(guī)訓與懲罰的思想,這些思想也構成了福柯理論的主要部分。下面將從微觀權力論與權力規(guī)訓這兩個部分進行簡單闡述。
1.1微觀權力論
福柯在《規(guī)訓與懲罰:監(jiān)獄的誕生》中說:“這些你們用來當作天經地義、與生俱來的東西,全都是被權力塑造和生產出來的。所謂歷史的進步,只是權力運作的自我調整[1]。”福柯的微觀權力理論在日常生活中體現的極為明顯。人們從出生開始就接受著周圍人的教導和指引,接受著大眾普遍接受的觀念,因而同一時代的人擁有著相似的價值觀念,也就是在微觀權力影響下形成了不同的場域。
同樣知識也成為權力的工具,權力與知識之間的密切關系讓我們學習由權力創(chuàng)造的知識從而維護現有的權力,微觀權力從思想方面控制著大部分人的行為,也影響著人們的選擇。從時間上看,我們從小到大都接受著權力和知識的制約,培養(yǎng)我們能夠適應工業(yè)社會的品質和精神,接受著學校、工廠的管制,以至于人們在老年階段更傾向于獨立生活,而拒絕養(yǎng)老機構等可能存在外界束縛的養(yǎng)老方式。同時在社會大環(huán)境中,個體的選擇會受到他人選擇的影響,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也是微觀權力的體現。
但同時權力也具有生產性。福柯認為“不應該再從消極方面來描述權力的影響,如把它說成是‘排斥’‘壓制’‘審查’‘分離’‘掩飾’‘隱瞞’的。實際上,權力能夠生產,它生產現實,生產對象的領域和真理的儀式、個人及從他身上獲得的知識都屬于這種生產[2]。”由此可見,社會中的權力可以用以生產維持權力的意識,所以我們也可以對人們進行規(guī)訓,生產符合當代社會的養(yǎng)老觀念。
1.2權力規(guī)訓
正如劉廣偉所強調的“規(guī)訓將權力擴散到日常生活,用以塑造社會想要的人。權力從上而下,從顯到隱,其效果是權力的擴散和滲透,這種復雜的權力技術與一整套現代知識話語共同構建了現代權力話語體系[3]。”思想觀念是權力帶來的隱性影響,存在于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的養(yǎng)老觀念也是受社會中各種權力的影響,因而在不同的社會背景和權力滲透下會產生不同的養(yǎng)老觀念。比如青年一代對待老年生活的態(tài)度更加積極,青年和中年注重對老年生活的規(guī)劃,養(yǎng)老需求更加全面,對老年階段的生命質量要求也較高。而老年人對養(yǎng)老更多報以順其自然的態(tài)度,并未考慮自己的晚年生活[4]。
下面則從權力和規(guī)訓的角度分析社會中的權力是如何逐漸規(guī)訓出當今的養(yǎng)老觀念的。
2 傳統(tǒng)養(yǎng)老觀念
2.1養(yǎng)老方式鄙視鏈
根據我們對長春市醫(yī)養(yǎng)結合社區(qū)及機構中50 歲及以上老人群體以及即將步入老年的群體的調研,在養(yǎng)老方式上,21.64%選擇與子女同住,48.88%選擇自己居家養(yǎng)老,18.65%選擇社區(qū)居家養(yǎng)老,9.33%選擇敬老院等養(yǎng)老機構。在進一步的調研和訪談中顯現出養(yǎng)老方式的鄙視鏈——自己居家養(yǎng)老>與子女同住>社區(qū)居家養(yǎng)老>敬老院等養(yǎng)老機構養(yǎng)老。大多數老人選擇“自己居家養(yǎng)老”是因為自己不愿麻煩別人;選擇“與子女同住”是因為這是中國自古流傳的養(yǎng)老方式;少選擇“社區(qū)居家養(yǎng)老模式”和“敬老院等養(yǎng)老機構”是因為不自在。
確實我們都覺得在家里舒服,那么這種“自在”與“不自在”的感覺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在中國封建男權和君權社會下,構建了“三綱五常”的倫理知識,同樣生產出“養(yǎng)兒防老”的養(yǎng)老觀念。然而在當下男女權力漸趨平等的環(huán)境下,社會逐漸形成了新的場域規(guī)則——“兒”指子女,但依靠子女養(yǎng)老的思想仍沒有改變,并存在著“送養(yǎng)老院=疏于照顧=不孝順=失為人之根本”的養(yǎng)老觀念。所以在老人看來養(yǎng)老機構其實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同時還伴有著自己被拋棄的感覺。
其次,社區(qū)居家養(yǎng)老模式和敬老院等機構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離不開養(yǎng)老機構這種形式。養(yǎng)老機構有它自己的紀律和管理方式,比如在12 點一起吃飯等等規(guī)則。雖然這類規(guī)則能夠幫助養(yǎng)老機構更加有效地照顧老人,但不免會“犧牲一部分自由”。正是這種無奈但必要的方式所帶來的規(guī)訓感、管理感和約束感使得老年人感到不自在。
但這些養(yǎng)老觀在養(yǎng)老方式多元化的今天已不適用,在獨生子女政策影響下,青年一代贍養(yǎng)壓力巨大,子女迫于生活壓力與父母多分居兩地故而沒有親自贍養(yǎng)的條件;養(yǎng)老機構不斷創(chuàng)新改進以期能夠提供更專業(yè)細致的照料;社區(qū)居家養(yǎng)老模式在機構養(yǎng)老和居家養(yǎng)老中尋找平衡,努力提供一個更加優(yōu)質的群體養(yǎng)老環(huán)境。但若是社會環(huán)境變了,觀念未變,矛盾便會產生。這時便需要我們對思想觀念進行正確的規(guī)訓引導以發(fā)揮權力的生產性,比如借助政府和企業(yè)的便捷平臺來進行宣傳教育。
2.2老年消極論
在我們的采訪中一位老年人表示“年輕時候好好干,老了有點自己的愛好,再老了個性就強了,自己在這呆著,自己沒有用了,沒有價值了,身體不行了,就稀里糊涂過吧。”這并不僅僅是這位老人的看法,同時也是多數老人甚至青年人和中年人心中觀念的真實寫照。這是因為在以能力論權力的社會背景下,老年人往往是弱勢群體,大多象征著衰老、無用和不體面。因而大多數老年人選擇自己居家養(yǎng)老,即不愿遠離自己的“安全屋”和交際圈,減少麻煩別人的可能性。但在當今人們生活水平提高的背景下,老年生活也可以有更多的選擇空間,也應是有意義的、值得照顧的、成為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養(yǎng)老觀念完善路徑
當今,社會老齡化問題嚴峻,社會快速轉型。只有改變傳統(tǒng)的養(yǎng)老觀念才能順應時代發(fā)展,才能更有利于擴大養(yǎng)老市場、提高老年生活質量、緩解相關養(yǎng)老問題。本文對促進社會養(yǎng)老觀念的改變有以下三個建議。
首先,樹立正確的生死觀、養(yǎng)老觀。養(yǎng)老觀和生死觀都是需要從小教育引導的,并不是老年人才有養(yǎng)老觀,才需要養(yǎng)老觀、生死觀教育。其實在社會環(huán)境變化的背景下,我們的養(yǎng)老觀已隨之變化,但政府、家庭、社會仍應該利用相關權力技術加以引導建構,使之積極適應時代的變化,以期幫助人們更加積極全面地認識人生的生老病死,并對老年生活抱有一個較好的心態(tài)。
其次,切實提高社區(qū)養(yǎng)老機構各方面水平,構建“社區(qū)養(yǎng)老機構值得選擇”的養(yǎng)老觀念。“打鐵還需自身硬”,物質具有第一性,只有社區(qū)養(yǎng)老機構真正做好了,才能改變人們的觀念。在面對老年人多樣化的養(yǎng)老需求時,要積極做好護工、醫(yī)療、養(yǎng)老等各方面工作。以“不僅讓老人養(yǎng)老,還要享老”為理念,靈活制定規(guī)則,為老年人打造家的感覺,建造優(yōu)質養(yǎng)老市場。
最后,加強精神贍養(yǎng),改變“在養(yǎng)老機構代表無人關心”的養(yǎng)老觀念。即使在機構養(yǎng)老兒女仍有贍養(yǎng)和關心的義務,養(yǎng)老機構養(yǎng)老并不意味著不需贍養(yǎng)。雖然身在養(yǎng)老機構,但家庭的概念還在,贍養(yǎng)老人需要我們的理解、尊重與關心,我們要貼近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在精神上給予其慰藉,滿足其精神需要,從而提高老年人精神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