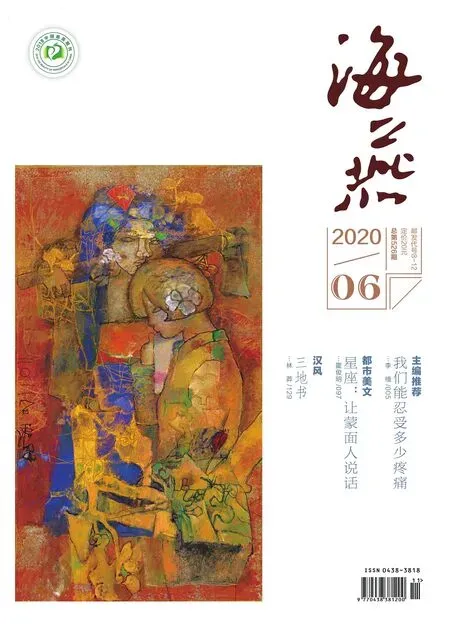我們能忍受多少疼痛
阿芬有些著急地來到布攤前,問秋燕是不是和百江商場或者什么人合作了,秋燕疑惑地搖搖頭。阿芬指著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說,那就怪了,我剛才在百江商場閑逛,看見成批和我這套一模一樣的衣服。秋燕說,這不可能,我就給你做了這么一件呢。阿芬一拍腦門子,想起一個月前和丈夫在外面吃飯時,一個女的纏著她,把她的這件衣服里里外外看了一遍,也沒說什么,誰想竟來了這么一手。
方平下班來接秋燕回家,秋燕讓他照料一會兒布攤子,便和阿芬一起去了趟百江商場,果然在那里看到和阿芬身上一模一樣的衣服,有好幾十件。翻看衣服的標簽,是本地一家很出名的服裝廠生產的。阿芬大聲說,咱去告她,一告一個準。秋燕有點兒疑惑,不知道阿芬說的可不可行。這時高檔女裝柜的柜長和女裝部的經理都來了,問清原委后,她們狐疑地看了秋燕幾眼。阿芬扯著自己的胸襟說,你們的這款衣服是新品吧,可是我這件都穿兩個多月了,這又怎么解釋呢?柜長和經理相視一笑,對秋燕說,即使是真的,打起官司來贏的可能性也不大,除非你早已把自己的設計在工商局注冊了。秋燕和阿芬面面相覷,人家說的不無道理,兩人只好怏怏離去。
那天晚上秋燕失眠了,翻來覆去睡不著,把方平吵醒好幾回。方平只好爬起來,問秋燕是不是不舒服,秋燕搖搖頭,抓住方平的手說,我想開個服裝廠。秋燕這才把下午的事情說給方平聽,方平沉吟良久,說你這個樣子,料理個布攤子都費勁,還想做服裝廠,怎么應付得來?秋燕不言語了,沉默好一會子,突然騰地坐起來,不行,我覺得我能干成。方平笑了,說好好好,能干成,不過也得等到明天再說,快睡吧。秋燕只好躺下,仍然興奮得睡不著,想起為省歌舞團一個女演員裁剪過幾套衣服,為一些朋友和顧客做過衣服的一些事情,更加睡不著了,直到天快亮才瞇過去。
秋燕租了一間小平房,把家里的縫紉機搬過去,又添了兩臺,招兩個人就干起來了。方平說你這一走可就沒有回頭路了,秋燕笑,說可不是嗎,但回頭又能回到哪兒去呢。
以秋燕的條件,能招到的工人都是不咋樣的,有時連個扣子釘得都不能令人滿意,更別說做那些修飾性的東西了。秋燕只好讓方平幫著把半成品運回家里,她再就著燈一針一線地縫制,一干就干到后半夜,有時到凌晨兩三點鐘,眼睛熬出了血絲。第二天一早,方平用自行車把秋燕送到作坊,一忙又是一整天,天天如此,秋燕卻不覺得累。事情在興頭上,干得帶勁,并不覺得苦。以致十余年來,這成了秋燕生活的基本節奏,有時病得厲害,或者不得不住進醫院才難得歇那么幾天,卻老是惦記著她的“服裝廠”,像丟了魂兒似的。
憑秋燕的手藝,把衣服做出來不算個難事,可要把產品推銷出去難度就大了。她抱著幾款新裁剪的衣服到百江商場,找到見過面的女裝部經理,經理先是看了看她,又翻翻衣服,臉上雖有歡喜,轉而卻又說,我們賣的都是知名品牌,你的東西雖好,可是沒名氣。秋燕笑了,說名氣都是一點一點打響的,就掛起來試試看吧。經理又看貨,翻來覆去地看,最后笑著對秋燕說,就上柜試試吧。
以后每天秋燕都到百江去看,第一天沒動靜,第二天還沒動靜,第三天商場便把衣服退給了她。方平推著自行車,秋燕坐在后坐上,懷里抱著一大疊衣服,兩人都不說話。
冬天很快就到了,方平走路時跌個大跟頭,腰摔斷了。這已經是他第二次骨折。方平一倒下,秋燕的整個世界就塌了,全塌了。方平好比秋燕的兩條腿,秋燕要到哪里,方平就把她背到哪里,方平靜止下來,秋燕也就沒法動彈了。
方平躺在床上動彈不得,秋燕在地上爬來爬去,給方平燒水,煮面,每次都滿頭大汗。方平也急得滿頭是汗,讓秋燕停下來,秋燕抹一把額頭說,我不能停下來啊,停下來,咱這倆個廢人都得活活餓死在屋里。這時水開了,壺嘴發出“噓噓”的尖叫聲,秋燕躬腰,雙手把著膝蓋挪到廚房,又趕緊扒住灶臺沿,這才沒有癱到地上。幾米的路,秋燕已經累得氣喘,膝蓋一軟,還是癱倒在地。她摸索著關了煤氣,手臂伸得老長,往上夠壺把,夠不著。秋燕恨不得自己的手臂能多長出一截。夠了幾次不成功,秋燕只好扒住灶臺沿,想要站起來,雙膝的骨關節發出尖銳的疼痛,站不起來。終于夠到壺把,手臂一個趔趄,水壺歪了,開水迸濺出來,潑到秋燕手臂上。秋燕“啊”地叫了一聲,屋里傳來方平緊張的聲音,問秋燕怎么了,接著秋燕又聽見“噗通”一聲,趕緊雙肘拄地爬回臥室,果然見方平從床上掉了下來,人趴在地上,動彈不得。方平痛得一頭細汗,卻咬緊牙關,生怕秋燕看出來。秋燕怎么會看不出來?疼在心里,卻不敢哭出來。他們趴在地上,鵝起腦袋互相對視,望著望著,兩人都笑了,一邊笑,兩人的眼角一邊向外涌出淚水。
那天下著鵝毛大雪,秋燕給方平喂了一碗水餃,刷了碗,做起出門的準備。方平看了看窗外,說下那么大雪,要不打個電話說改天再去吧。秋燕說那怎么行,好不容易答應見面了,不能失約呀。秋燕裹好圍巾,一瘸一拐地走進漫天的風雪中。她瘦得可憐,扶著街邊的欄桿或墻壁一點一點往前挪,像只在大雪中覓食的麻雀。兩條腿的膝蓋骨里疼痛難忍,那咯吱咯吱的聲音,像扎著一簇鋼針,痛得秋燕直喘粗氣。她哈出的熱氣一下子就被風吹散了。
到了約好的單位,秋燕顧不上歇口氣,便直接上樓。剛上到二樓就滾了下來,好在是冬天,穿的衣服多,只是摔疼了一些地方。秋燕拍掉身上的雪,往樓梯看了看,好像那是一座高高的山。秋燕咬咬呀,抓住樓梯的扶手重新往上爬。上樓的時候,她得手腳并用,一手抓緊扶手,騰出另一只手把右腿拎起來放到臺階上,再用雙手抓住扶手,把自己拉上一階樓梯。她就是這樣一階一階爬到七樓的,每一階都得使出渾身的力氣,滿頭大汗,貼身的衣服早就濕透了。爬到七樓,秋燕抹去額頭的汗水,回頭看看樓梯,笑了笑。
這家廠子要訂做廠服,如果談下來,那么整個冬天就不愁活干了,來年春天也會是個明媚的艷陽天。可是秋燕哪會想到,廠領導一看見她的樣子,眉頭就擰成了疙瘩,二話沒說就支擺秋燕回去。秋燕站在廠長的辦公桌前,笑臉以對,廠長顯得不耐煩,手一揮說走吧走吧,我們又不是慈善機構。秋燕看了看旁邊的沙發,說,那我能不能坐一會兒,實在走不動了。廠長訕笑了一下,沒抬頭,也沒吱聲。秋燕覺得嗓子眼干得冒煙,便又說,麻煩幫我倒杯白開水吧,真不好意思,太麻煩您了。廠長的鼻子里哼了一聲,看也不看秋燕一眼,便抓起電話喊了秘書來,讓他把秋燕請走。
回到家,方平一看秋燕的臉色就明白了,他嘆口氣說,房東打電話來,說廠房不租給咱了,要咱三天之內就搬出去呢。
秋燕感覺天都要塌下來了,但頂天用的柱子方平倒下了,她只好用自己沒有癱瘓的上半身頂著塌下來的天。好在第二天雪停了,秋燕喊來年邁的母親,讓母親攙扶著她去街上找房子。雪積得很厚,娘兒倆互相攙著,深一腳淺一腳地沿街問,一不當心就跌個跟頭。秋燕干脆放開母親的手說,你還是自己照顧好自己吧,我摔著了不打緊,您可不能再出什么差錯。母親不肯,攙緊女兒的胳膊說,我這把老骨頭,摔沒了才好。秋燕癱在雪地里,失聲痛哭。
搬廠房那天,方平也去了,拄著雙拐,膏布從屁股打到脖子上,行動起來特別吃力,卻不敢讓秋燕看見。秋燕正扶著一張堆滿雜物的桌子指揮工人搬東西,她看見一個人影出現在門口,籠罩在冬天的陽光下。她氣壞了,拍著桌子說,你來干什么,你想一輩子躺在床上嗎?一些塵土被秋燕拍得飛起來,嗆到嘴里。秋燕忘了自己的情況,想要奔過去攙扶方平,一挪步就“噗”地倒在了地上,更多的塵土飛起來,完全籠罩住她瘦憐的身影。方平一聲驚呼,扔掉拐杖就要跑過來,結果也摔倒了。秋燕咋呼著朝方平爬過去,迅速爬到他身邊,看著額頭冒汗的方平,柔聲說,你來干什么,你應該躺在家里呀。方平吃力地抬起一只胳膊,撫去秋燕頭上的一縷蜘蛛網說,我不放心,來看看。
原先方平追求秋燕的時候,秋燕剛高中畢業,成天呆在家里沒事情干,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秋燕的姨媽就對她說,別理他,還不是看你長得漂亮,只想和你玩玩兒罷了。秋燕明白姨媽的意思,自己這個樣子,有哪個胳膊腿健全的小伙子會正兒八經地和她談婚論嫁呢。不光姨媽,家里人都沒把秋燕跟方平的戀情當回事。
方平姊妹兄弟好幾個,他排行老三,也不知道為什么,母親獨不疼愛這個三兒子,什么家務活都讓他干,燒飯刷碗洗衣服,方平打小就干得麻利,但這些仿佛都是為了和秋燕一起生活準備的。
那時秋燕整天抱個半導體聽各種世界名曲,每聽到一首好曲子,她都寫體會,寫過滿滿一大本子。秋燕極少流淚,即使懷孕期間那么困難的情況下她都沒流過淚,可是一段鋼琴曲《少女的祈禱》,能讓她熱淚滾滾。她家有一把小提琴,秋燕從小就會拉一拉。她之所以喜歡上方平,也是覺得這個小伙子可靠,還會拉二胡、手風琴,整得都不錯。當時方平到她家里玩,讓秋燕幫他抄一些樂譜,看見旁邊的手風琴,抱起來就彈了一段電影《軋鋼工人》的主題曲,秋燕聽著聽著,不禁有些耳熱心跳。她瞥了一眼方平,正好方平的目光也瞄過來,見秋燕正在看他,趕忙低下頭。秋燕沒不好意思,依然大膽地看著方平。
那時方平每月只有200多塊錢的工資,為了解決譜曲時遇到的和弦問題,他要經常到藝術學院花錢上鋼琴課,加上日常開銷,這點兒錢簡直是杯水車薪。秋燕就用白紙畫出鋼琴的黑白鍵,嘻笑說你就在這上面彈吧。方平就在紙上彈鋼琴,指頭被墨汁弄得黢黑,也解決不了聲音問題。后來他們結婚,開服裝廠之前,有一天方平回到家里,發現家里多了架鋼琴,是貨真價實的真家伙。原來秋燕向父母借了5000元錢,從一位音樂老師那里買來了這架舊鋼琴。
兩家原來住在同一條街上,但很快就因為拆遷各自搬家了,秋燕家搬到城西南,方平家搬到城北。那時秋燕開始在城東的一家娛樂宮賣門票,方平負責每天接送她。方平每天一大早就得爬起來,從城北出發,趕到城西南秋燕那兒,用自行車把她馱到城東,再騎車趕到位于城中的無線電廠上班。傍晚下班后,路線反過來,路程還是那么遠,并沒有近路可走。不管嚴寒酷暑,這樣奔波了兩年后,秋燕到城中的布料城幫父親看布攤子,路程才變得短了些。
這兩年,也是兩人最開心的兩年。方平經常用自行車馱秋燕去布料城旁邊的市民俱樂部看演出,具體是看他演出。也不是什么正規的演出,就是街道、區里搞的一些小型文藝活動,最高規格也就是市里組織的夏季音樂會了。大多情況下,方平是在伴奏的樂隊里,或者長笛,或者手風琴,獨自上臺的機會不多。但機會還是接二連三地來了,因為他樂器玩得好,又通樂理,社區組織的活動,都要請他幫忙指導,有時候是輔導小學生排練,有時是教大爺大媽們唱歌,一來二去,方平成了一號不可或缺的人物。在一場區里組織的新年音樂會上,方平用四五樣樂器獨奏了一曲《我和我的祖國》,秋燕聽得如醉如癡,要不是全場嘩嘩不停的掌聲,秋燕還會沉醉好久。秋燕拼命地鼓掌,她也想站起來,像周圍的觀眾一樣站起來為方平鼓掌,但失敗了。她有些著急,甚至有一股子沖動,她想拉住左右人的胳膊,告訴他們這個演出的男人是自己的男朋友。
那場演出結束后,方平被市電視臺請了去,又在電視上如法炮制了一遍《我和我的祖國》。在周圍人眼里,方平一下子成了名人,他有時也不禁自鳴得意。家里人對他的態度好了起來,讓他跟秋燕散伙,說現在有好幾個大媽、媒婆都上門提親呢,秋燕是個殘疾,可不能讓她拖累咱一輩子。方平沒吱聲,他在家里已經沉默慣了。平時沒人在意過他,現在突然熱心起來,還不是在他身上看到了更多可能。秋燕這邊也不消停,先是母親含沙射影,說你本來就配不上人家,現在更不配了,你還是收收心吧。秋燕笑笑,對她媽說您老放心吧,方平是不會變的,我知道他。母親“切”了一聲,雖不再說什么,意思卻很明顯,你一瘸子,這輩子也就是個逆來順受的命,認不認都一樣,由不得咱。母親都已經替女兒的一生心灰意懶了,秋燕卻從沒這樣想過。倒是跟秋燕年齡差不多也還沒出嫁的小姨媽跟秋燕的心思是契合的,攛掇秋燕要抓住方平,說這小伙子剛開始還真沒看入眼,一副逆來順受窩窩囊囊的樣子,根本配不上你這漂亮迷人的臉蛋,現在看看,順眼多了呢。秋燕就揶揄姨媽,姨媽捏了一把秋燕的臉蛋,說你正經點,可不能讓到嘴的鴨子飛了。姨媽還悄悄地問秋燕生米煮成熟飯了沒,如果還沒,那可得抓緊。秋燕垂首搖頭,姨媽急得在屋子里打轉,給秋燕出各種主意,好像是她自個的終身大事似的。
接著,區文化館的領導就去無線電廠找方平了,說想把他正式調過去,征求一下他的意見。方平猶豫不決,去跟秋燕商量,秋燕當然一百個贊同,但方平有些苦惱,說現在廠里給他漲了工資,比到文化館的工資高出兩倍呢,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沒想市歌舞團人事部主任又去了方平單位,了解了一些他的基本情況,回去后就發來了一份商調函,要把方平調到市歌舞團去工作。這次方平動心了,揣著商調函跑去找秋燕,秋燕激動得熱淚盈眶,捧著方平的臉狠狠親了一口。沒過幾天,方平又來秋燕家,卻一臉沮喪。秋燕問什么情況,方平說不去市歌舞團了,秋燕忙問為什么,方平欲言又止,秋燕只好忍住,沉默了一會子,秋燕嘟囔說他們這算什么,先是主動下調令,結果又看不上咱了,看不上拉倒,咱還不稀罕呢!方平有些煩躁,撇下秋燕離開了。
接下來的幾天,方平都沒來看秋燕,也沒有電話。秋燕想打電話給他,幾次抓起話筒,又都放下了。她隱隱感覺到一些什么,瞅著自己萎縮的兩條小腿,一層陰霾罩上心頭。
這期間,秋燕想拾起雙拐。她有些害怕,也許自己仍然要像小時候那樣,一個人走路,一個人解決所有問題,沒有任何支撐,即便是親生父母,也沒在意過她的行走問題。她咬牙用雙腿走路,一瘸一拐,十分吃力,膝關節磨得生痛。她覺得拐杖那種東西配不上自己的人生,它們不應該出現,但現在她可能不得不放棄這個想法了,她需要一副拐杖。這天上午,她來到殘疾人用品商店,為自己精心挑選了一副,拄著拐走出商店。街上人來車往,秋燕低頭看了看,雙手握緊,向前奮力走去。拐杖敲擊地面發出“篤篤”的聲音,腫脹的膝蓋更加痛了,痛得滿頭大汗。秋燕走著,一陣大風吹起了她的圍巾,遮到臉上,擋住了視線。她停下來,抓著圍巾抹了一把額頭,又抹了一把雙眼。她知道,自己的汗水沒有淚水多,她也知道這淚水多么的無辜,哭泣有什么用呢。
這時方平出現了,像什么也沒發生一樣,奪過秋燕的雙拐,把她背起來,又回到剛才的商店,把拐杖給退了。看見秋燕水腫的膝蓋,方平帶她去了醫院,抽出滿滿兩大針管積水。秋燕的膝蓋骨關節不能生成潤滑液,醫生說再這樣下去,就要截肢了。秋燕不管這些,也不搭理方平,只管自己走出醫院。方平看著秋燕顛簸的身影,干脆強行背起她,回家翻出秋燕的戶口本,就去了民政局,辦了結婚證。回家的路上,方平仍然背著秋燕,秋燕說你放我下來。方平把秋燕往背上托了托,雙手把得更緊。秋燕捶打著方平的后肩,說你傻啊,你不要我,沒人會怪你,好好的音樂家不當,偏要來照顧我一個廢人,你傻啊!秋燕說著又哭了,臉部埋進方平的肩頭,哭得稀里嘩啦,眼淚鼻涕都流到方平肩上。
領證以后,兩人仍然住各自家里,因為沒有房子。那年冬天,他們終于拿到拆遷安置房的鑰匙,同時秋燕驚喜地發現,自己懷孕了。可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方平摔斷了大腿,那是他第一次骨折。
房子在裝修,要給裝修工人做飯,這活落在秋燕身上。秋燕會的東西不少,可就是不會做飯,裝修工人嫌她做得難吃,干脆自己做了吃。方平臥床不能起,一日三餐,把屎倒尿也是秋燕的活。一天三頓,秋燕只能下些面條、餛飩、水餃給方平吃,吃得方平直咧嘴。
住進新房后,二樓住戶的下水管出了毛病,水滲到他們家里的水池里,每天要舀走九桶水。常人做起來不算什么,可是秋燕就難了,拎著一桶水,就像拎著一桶鐵,把膝蓋壓得鉆心地痛。躺在床上的方平干著急,恨不能爬著去幫秋燕搭搭手,他也實在吃膩了一成不變的餛飩餃子。
好在小姨媽每周來幫著買一次菜,可是等菜吃完了,秋燕就又沒辦法了。哪怕是一包鹽,她也是挪到陽臺上,請在雪地里玩耍的小孩去幫著買來。秋燕怔怔地站在陽臺上,看著漫天的大雪,看著樓下的小菜市,不知道如何是好。一個菜販到樓下的水龍頭那里洗菜,秋燕像看見了大救星,大聲喊賣菜的,請他把菜送到樓上。以后菜販子經常送菜過來,老大難的問題居然就這樣解決了。
秋燕瘦得皮包骨頭,體重不到70斤,每天就這么扛著,都忘了自己肚子里還懷著孩子。那天她又要倒掉一桶水,剛拎起來,人就跌倒在煤球爐旁邊的煤渣上。秋燕心驚肉跳,這才想起來自己肚子里的孩子,不禁哇哇大哭起來,急得方平滾下了床,爬到她旁邊問怎么了。秋燕撫摸著自己的肚子,哇哇哭著說,孩子,這下孩子沒了。迫不得已,方平只好打電話請來比較要好的同事,帶秋燕到醫院檢查了一番,結果并無大礙,秋燕才破涕為笑。
孩子要臨盆了,醫生建議剖腹產,方平同意了,家里人都同意,唯獨秋燕不同意。她只認一個理,胎兒經過產道擠壓,是他來到這個世上的第一關,必須過。在產床前,方平捧著秋燕的手,還要說什么,被秋燕制止住了。秋燕說,我死了沒關系,只要能給你留下個健健康康的孩子,也沒辜負你白疼我一遭。方平騰地站起來,臉都青了,但這仍然沒能改變秋燕的決心。
誰都沒想到,瘦瘦巴巴的秋燕竟然順利生產了,是個兒子,六斤四兩。醫生和護士都唏噓不已,朝虛脫的秋燕挑起大拇指。方平抱著兒子,陽光從窗外照進來,照在兒子還沒開皺的小臉上。他只要一睜開眼睛,那就是另一個世界。方平獲得了新生一般,俯在秋燕的臉上一陣狂吻。秋燕氣若游絲,艱難地睜開雙眼,看著面前的丈夫和他懷里的襁褓。以前她還從來沒有想象過自己的生命里還能擁有兩個男人,兩個跟自己骨肉相連,愿意拿命去愛的男人。
為了照顧秋燕,方平不得不放棄音樂,放棄進入正規樂團的機會。那次市里的歌舞團要調他,他拒絕的原因,就是因為被告知要經常去外地演出。方平苦思冥想了好幾天,最終放棄了。服裝廠開辦以后,方平干脆辭了職,專職照料秋燕的生活起居。有一次外出辦事,秋燕要上廁所,可是方平總不能抱著她進女廁所吧。看看男廁所正好沒人,方平便把秋燕抱了進去,再趕快跑到門口把風。偏巧有個五大三粗的爺們急匆匆地跑來,一看樣子就知道憋得夠嗆了,悶頭就往廁所里沖。方平大喝一聲,站住,不準進去。那爺們一愣,不知道方平要干什么。他實在著急,捏著褲襠仍然要往廁所里鉆,方平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說你不能進去,等會兒才行。爺們急了,朝方平吼起來,就差沒動手。這時廁所里傳來秋燕的聲音,方平趕忙沖進去,把她抱出來。爺們看見方平從廁所里抱出一個女人,不禁呆在那里,嘟囔了一句才趕緊沖進廁所。
服裝廠在泥里土里滾爬了十幾年,現在總算有點規模了,秋燕聘用的都是跟自己一樣的殘疾人,二三十口子。秋燕是董事長,方平仍然是她的生活助理,數十年如一日。
朋友們都說方平是個頭頂鍋蓋,手拿海帶,腰間掛米袋的典型宅男。秋燕和兒子還給方平封了個頭銜:五夫,即丈夫、大夫、伙夫、車夫、琴夫。有時方平先吃完飯,就負責彈一段鋼琴給老婆孩子聽,彈完了再去刷鍋、洗碗。
“我們兩個是世上呆在一起時間最長的夫妻,就差沒長在一塊兒了,”秋燕微笑地看著我說。
要不是報社安排我采訪這位殘疾女企業家,我恐怕沒有機會告訴讀者上面的故事。
我提出想聽方平彈琴的想法,他抿嘴笑了笑,搖頭拒絕。秋燕主動請纓,手一劃拉,琴鍵便蹦跳起來,音符猶如按照秩序落到地板上的碎骨頭,連串起來就是一整根骨頭,堅硬有力。是那首人們耳熟能詳的《命運交響曲》,卻比我在磁帶上聽到的多了幾分鏗鏘和倔強。這顯然與你的經歷有關,我判斷說。秋燕點點頭,扶著琴凳彎腰站起,挪了兩步,終于坐到我對面餐桌邊的椅子上。我們伸出手掌比劃了一下,她的手掌比我的居然還要長那么一點。秋燕不好意思地笑了,因為她的手臂和手掌確實很長,和嬌小的軀體比起來并不協調。
還在上小學時,秋燕就把自己的雙拐扔了。那是一次篝火晚會,秋燕把她的雙拐扔到篝火堆里。那真是兩截不錯的木頭,火勢增強不少,秋燕癱在篝火邊的草地上,看著她的拐杖先是迸射出強勁的火苗,然后斷裂成一塊一塊的木炭,最后化為灰燼。秋燕想像火苗那樣蹦跳起來,加入奔跑的同伴,可是一下子就摔倒了。她又爬起來,不過這一次小心了些,居然有一條腿還聽些使喚,終于使她站立起來。秋燕背上自己的書包,扶著樹干,街邊的欄桿、墻壁或者成排成排停放著的自行車回家了。
那個孩子可不簡單呢,老鄰居說,過馬路時就用手爬過去,好心人找根木棍給她,硬是不要。
我想像一個正常人那樣,用自己的雙腿走路,秋燕說。
是有這么個小姑娘,天天打我這兒路過。在街邊修車子的老陳說,可不有幾十年了嗎,有時候滿頭大汗,真可惜了,那么俊的一個姑娘。
高中畢業后,有的同學進了大學,有的工作了。好友阿芬經常到家里看望秋燕,說些自己的事兒。阿芬在一家大賓館當服務員,后來傍上個有錢人,整天逛街,坐跑車,去高檔咖啡廳。阿芬做這些當然都沒有問題,因為她有兩條好腿。秋燕哪兒也去不了,天天抱著個半導體,專門搜索播放各種世界名曲的電臺。她喜歡那些曲子,一聽到《少女的祈禱》那首鋼琴曲就哭成個淚人兒。
聽到著迷的曲子就寫體會,寫了滿滿一大本子,后來在搬遷中遺失了。秋燕還收到過一封情書,是考上名牌大學的高中男同學寫的,有八頁紙那么厚。秋燕把信藏了起來,后來也不見了。
她是個殘疾,誰會相信他是認真的呢,只是看上了我們秋燕的臉蛋吧。秋燕的小姨媽說。
他很誠懇,還把校徽給了我作紀念,可是我不來電。秋燕說。
一個瘸子還有什么可挑揀的,她肯定是覺得配不上人家唄。幾個街坊議論。
那以后的四年,秋燕基本上是在醫院的手術臺上度過的,她想治好腿,這樣就能像阿芬一樣去花花綠綠的世界逛一逛了。她拉開衣擺,讓我看她做了四次骨盆延長手術的刀口。刀口有一尺長,從腹股溝上端斜著向上,一直延伸到后腰側。每次都從同一個地方切開,第一次是把髖骨打碎,安裝鋼質支架。一個多月后,因為排異反應不得不二次手術。第三次是因為盤腔發炎,半年后的第四次手術時,秋燕拒絕用麻醉劑,她擔心過多的麻醉劑會把自己的腦子毀了。
這怎么可能呢,就這樣在你的身上劃拉開一個大口子?醫生舉著手術刀問。秋燕笑了笑說,沒事,你劃吧。
我下不了手。
你是醫生哎,這點兒事情算什么。
那,那我可下刀了?
下吧,我不怕痛。
不行,我還是不行。
你行的,就當我打過麻醉劑了。
手術刀終于從原來傷疤的一端切進去,表皮、皮層、脂肪層,要打開盆腔,刀子不僅僅需要劃開表皮那么簡單。秋燕哆嗦著,不由自主地跟隨著向前劃動的刀刃欠身子,以致于醫生無法下手。刀刃一毫米一毫米地劃開秋燕的皮肉,一直劃到三十厘米長的位置,才終于停下來。秋燕長長吐口氣,笑著對醫生說,總算劃開了,旁邊的護士正在擦去醫生額頭的汗珠。
有時候秋燕睡著了,護士會按照慣例打一針杜冷丁,但只要醒著,秋燕就不讓打。隔壁病房有個和她差不多歲數的小伙子,截了肢,沒命地喊痛,打一支杜冷丁不夠,央求護士再給他打一支。秋燕也不是不疼,可是她害怕那些藥物,于是就大聲地唱歌。她躺在床上,看著潔白的房頂大聲唱著。沒人覺得煩,一則整個病區都是差不多的病人,痛苦的嚎叫和哭喊聲此起彼伏,相比起來,她的歌聲好聽多了。秋燕有副好嗓子,病友們被她的歌聲打動了,居然紛紛安靜下來,陶醉地聽她唱歌。
后來的二十年中,許多病友紛紛死去了,大多是因為精神崩潰死去的,秋燕卻一直活著。
以為她早就死了呢,或者就是躺在臟兮兮的病床上,在黯淡的光線里茍延殘喘,沒想到她活得那么光鮮,還是像年輕時那么漂亮,真不可思議呀!一個二十年前的熟人說。
在許多人眼里,我這種人的世界就應該是那樣的,可那是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呀,我不喜歡站在那邊,那就站到這邊唄,很簡單的事情。秋燕笑著說。
多次的專家會診已經證實,秋燕的雙腿是不可能治好的了,能站在那兒,能獨立走上幾步已經算是個奇跡了。于是她就堅守著這個奇跡,無論如何也不愿意使用拐杖。可要不是這樣,現如今她的膝蓋可能也不會病變。她膝蓋骨的骨膜由于長期受重,已經磨損殆盡,膝蓋骨經常發炎,積水,每次能抽出一紙杯黃色的積液。疼痛是難免的,從她扔掉拐杖那天起,疼痛就沒離開過她,以致于她已經不再把疼痛當回事情。疼痛來時,在她這里,就是剪斷一根頭發的事。她捋起衣袖,把纖瘦的胳膊伸到我面前說,你現在拿把刀割我的肉,我連眼睛都不會眨一下。
真的嗎?
真的。
我便沖進廚房,拿出一把剃骨刀,捏起秋燕胳膊上的皮肉,一刀割了下去。秋燕吭都沒吭一聲,仍然微笑地看著我。鮮血汨汨地流出來,順著她的手背滴到地板上,鮮艷奪目。
我從上述臆想的場景中回過神來,秋燕仍然微微笑著。這個長發鳳眼的女人,瘦巴巴的,一頭長發烏黑順溜,五官精致,完全托得住漂亮這個詞。我說,你看上去要比實際年齡顯得年輕。秋燕笑了,問我她看上去多大?我很真誠地說,年輕七八歲。秋燕笑得更燦爛了,她看著坐在旁邊的方平,這個一直以來幾乎不發出自己聲音的男人,眼里依然充滿那種感恩般的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