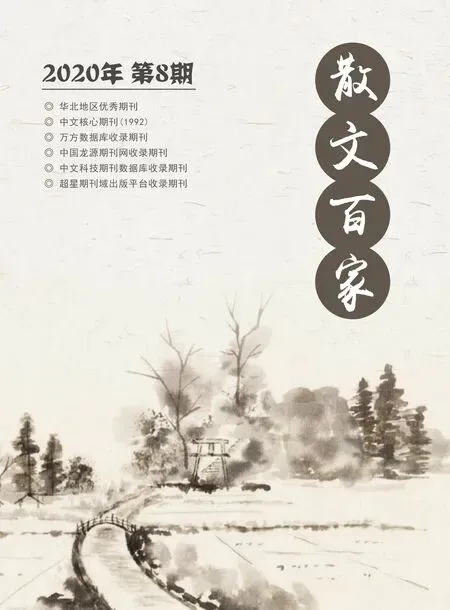克拉申“輸入假說”在漢語國際教育學界的發展文獻綜述
孫天嬌
蘭州交通大學
20實際70年代,克拉申在《二語習得的年齡,學習速度及最終成就》中提出“語言監控模式”,后來又提出“可理解輸入”和“輸入假說”的概念。1985年在其著作《輸入假說:理論與啟示》中正式歸納為習得與學習假說、自然順序假說、監控假說、輸入假說和情感過濾假說等五個系列假說,總稱為輸入假說。
我國對外漢語教育在改革開放后才進入學科建設發展的蓬勃時期,國外的二語習得理論傳入中國也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與討論。
筆者根據在CNKI查閱到的文獻,將國內學界關于克拉申“輸入假說”的研究分為三個階段:
A.初步發展階段。20實際80年代到90年代為對該理論的引入階段。主要是對克拉申的假說進行介紹,如,桂詩春(1980)、吳丁娥(1990)等。21世紀初期,出現針對該理論的評述及與教學初步的結合,如,鄭銀芳、吳叔良(1990)等。
B.研究成熟階段。研究者將輸入假說與教學結合,在實際教學中運用,從教學技能訓練、教學內容的選擇和編排、教學方法的改進和課內外影響學習者的各種因素等方面討論該理論對本學科的影響。如,劉清平(2001)、張莉(2001)、程相文(2001)、周健(2003)、楊惠元(2000)、王永陽(2009)、賈冠杰、林磊、蘭蕓等。
一、初步發展階段
克拉申的假說起初是由國內外語教學界的學者引入的,用于研究中國學生的英語教學。桂詩春最早將克拉申的假說引入國內外語教學,他在論及心理語言學和外語教學的關系時提到克拉申的“監查模式”,“運用‘照顧式語言’把‘輸入’變為‘吸入’”“自然順序”等,他認為該假說很值得結合中國學生的實際深入討論。
隨后,吳丁娥在其文章中系統介紹了克拉申第二語言習得理具體內容論的5個及影響第二語言習得的因素,她提出,克拉申的第二語言習得理論所提出的習得輸入語及語言環境等學好外語的重要因素正是我國外語教學的弱點所在,借鑒其理論,我國的外語教學定會有所發展。
隨著該理論在學界的傳播,對外漢語教學界的研究者也注意到了這一理論,并對此展開討論。大致分為支持和質疑兩種態度。鄭銀芳認為“輸入假說”無視母語習得與二語習得的差別,理論缺乏科學依據;強調輸入的重要性,然而對“輸入”的定義過于狹窄,只重視自然輸入,忽視和排斥非自然輸入;過分強調輸入,忽視輸出,不利于學生交際能力的培養;過分強調外界輸入,忽視學生的主體性作用等。
吳叔良認為在要樹立多元的教學認識論,注重教師、學生和內容的關系,用學習、習得整合觀來統領課堂教學;創造生動活潑和諧融洽的教學情境,最大限度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對教學過程、課程與教材等作整體的合理安排。這是首次在理論層面上對次假說進行論證并結合教學提出自己的觀點。
這一階段的研究還停留在描述與評價層面,部分學者開始突破傳統的教學理念,結合克拉申假說提出整改建議,但作為新傳入的理論,沒有形成系統,多數研究深度不足。研究的重點主要是該假說的內容并初步與教學結合,深度和廣度都有待提高。
二、成熟階段
進入21世紀,對于“輸入假說”的研究出現多樣化,與實際課堂教學結合,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有所發展。
輸入假說的核心“可理解輸入”啟發徐海銘闡述了語言輸入的一些特征,如可理解程度、語體正式程度、輸入內容的難度等,分析這些特征對教學的影響,為提高吸收語言輸入的效率,他提出信息模式和認知實踐模式。
施家煒利用實驗,研究分析“漢語中介語語料庫”的語料,以“自然習得順序假說”為基礎,實際考察留學生對22類現代漢語單句句式的習得順序,得出“留學生22類現代漢語句式的習得順序表”,并結合該表提出留學生漢語習得中的問題。
劉清平認為在留學生口語糾錯時要注重“情感過濾”因素,應該照顧學生的情緒,注意學生對糾錯的反應,避免因糾錯使打擊學生口語表達的積極性,避免使其產生畏難情緒,從而降低吸收率。同時提出,要利用錄音、復讀等形式是學習者自己監控自己的錯誤,進行自我復查。
趙雷提出建立任務型對外漢語口語教學系統,強調要“以真實的交際任務為驅動,最大限度地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調動學生積極性”克拉申假說在技能訓練方面得到了廣泛應用與研究。特別是“可理解輸入”和“情感過濾”假說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視。
在教材的組織安排方面,周健提出,“增加可懂輸入”增加語言輸入量,并重視信息的可懂和價值,難度應稍高于學習者的語言水平;要注意“語法點先后順序及等級安排”。
錢旭箐通過實驗調查指出“大部分詞語都是通過大量閱讀習得的”第二語言的詞語可以通過“以閱讀為主要目標,詞語習得為輔”的伴隨性學習學會,不需要專門學習詞語。
朱志平認為在漢字教學中,應該關注漢字的構形,即字符的表意功能。給予成人學生能夠理解的漢字材料,符合“可理解輸入”的漢字構形的特點和理據分析能極大推動學生的漢語習得。
總體來說,對教學內容的研究依據學者研究的興趣和方向體現出零散性,多角度研究,從不同角度進行分析,從更加具體的教學角度結合該假說,拓寬了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三、總體狀況評價
筆者通過對以上文獻的整理分析,發現克拉申“輸入假說”的研究呈現以下特點:
第一,研究的重點偏向“輸入”,強調體現“i+1”的輸入原則,而教師作為向學生輸出語言和信息的核心人物,其語言輸出情況與學生“吸入”情況密切相關,但研究教師語言的文獻較少,如何切實有效地在不同課型中規范化、系統化教師的教學用語,使其更好地體現“i+1”的原則,為教學提供可行性參考是接下來應該考慮的問題。
第二,克拉申“輸入假說”仍是未經驗證的假說,目前的研究仍然沒有利用腦科學、生理學等自然科學充分論證該假說,仍是在假說的基礎上與實際結合,理論基礎相對不夠牢固。
第三,輸入假說的核心是可理解輸入,體現“i+1”原則,但在真實的教學中,學生因學習目的、文化背景、個人學習能力等方面的差異,各自的信息理解能力無法通過分班考試完全體現,“i”的標準界定模糊,混合班教學效果與預期有差距。
第四,克拉申的“輸入假說”強調習得先于學習,習得是首要的,學習是輔助的,而目前我國的實際教學情況、學生通過HSK考試的需求以及已有的研究都更趨向教學為主,習得的途徑較少,也缺乏對習得成果的檢測手段。
第五,為減少情感情感過濾,防止學生產生畏難情緒,用學生自我監控代替教師糾錯,造成偏誤,降低教學質量。
針對以上問題,筆者認為:
教師語言系統化有助于為教學提供規范化、書面化、標準化的參考,可以通過嚴格教師篩選制度、崗前培訓、教學反饋等手段實現。形成系統化的、成體系的、符合國內實際情況并能夠體現“可理解輸入”的教學用語,這對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教師隊伍的培養工作也會起到輔助作用。
針對學生信息理解能力有差異的問題,可以通過在入學測試中偏重交際測試,直接考察學生的溝通理解能力、加強對學生階段學習成果測試、細化等級分班制度等方式使“i”在教學中盡可能精確化。
國內的教學環境決定了教學為主,習得為輔,針對這一問題,可以通過加強教學中的交際成分、發揮學生主動性、設置自主習得環節并定期通過實際交際檢測習得成果的方式,在教學中增加習得比重,也可以通過組織戶外學習、沉浸式學習等輔助教學。
在教學中應該以正確的態度對待偏誤,不能因為怕影響學生積極性而無視偏誤的存在。首先,從學生交際的需求出發,通過任務型、開放性問答、詢問意見等方式刺激學生表達的欲望,并在交際過程中提供正確范例,交際中出現偏誤可通過教師再次詢問、重復等方式提醒學生,在交際結束后通過總結正確規范的話題句加強記憶。絕對不能無視偏誤以致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