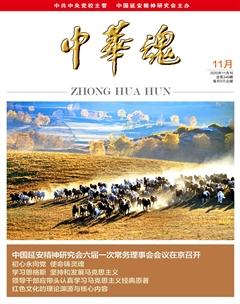綠皮車
姬皓婷
我所經歷的很多年的春節,都是始于綠皮車的汽笛聲,又終于綠皮車的汽笛聲的。
小時候回縣城里過年,就是乘坐綠皮車。路上沒有什么娛樂節目,爸爸就帶著我們姐妹倆,挨個兒數鐵道邊光禿禿的行道樹上的喜鵲窩。“半天一只碗,落雨落雪裝不滿。”小鳥的家一路數過去,我們離老家也就不遠了。
在沒有高鐵的日子里,綠皮車就是開往春天的列車。在拖著大包小包,費勁地爬上車廂門那高高的三級臺階,在奮力擠過稠密得幾乎無法流動的人群,踮著腳把行李向頭頂的架子上一扔之后,在終于能一屁股坐在梆硬的位子上長舒一口氣時,內心涌動的是滿滿的幸福感。汽笛聲拉響,家似乎就已經咫尺可待了。為了回家,我曾經好幾次買站票捱過十幾個小時的路途,但那時并不覺得苦,大概全憑一股思鄉之情做內力了。
最早的綠皮車沒有空調,只能半開的窗戶進不來多少風,吹不散車廂里的煙味和腳臭味。夏天的時候,能聞到你鄰座乘客滿身的汗味;而冬天的夜里,又凍得必須翻出大衣蓋上才能入睡。鍋爐燒的是煤炭,坐的時間久了,下車時滿面煤灰,連鼻孔都是黑的。節日期間的綠皮車應該是全國人口最密集的地方,車廂連接處、洗手池、座位下,甚至連衛生間擠的都是人。而不管人群多么擁擠,賣貨的小車總是能夠殺出一條路來。在狹小擁促的硬座車廂里共度十幾個小時,人們彼此形成了互相遷就互相忍讓的默契。啃著燒雞喝著小酒吹牛的大哥,互相依偎著呢喃的情侶,流著涎水哭鬧不止的小孩子,吆五喝六打撲克牌的老鄉,滿面溝壑一臉憨厚跟你拉家常的大伯大娘……
這是庶民熱氣騰騰的快樂,是熟人社會才有的煙火氣息。
后來,各種K、T、Z打頭的火車越來越多,反而是綠皮車的車次大大減少。有一次媽媽從老家到北京來看我,坐了一趟綠皮車,將近4個小時才到。我埋怨她為什么不選一趟快車。媽媽笑著說:“我的時間又不值錢。這趟車便宜,在車上多坐會兒受啥罪,比人家那些下地干活的農民舒服多嘞!”
21塊錢的票價,即使在當年也絕對算便宜的,因為從火車站打車到我的住處,六七公里的路都要24元。我也是從這件事才認識到,小時候被訓導的“時間就是金錢”并不適用所有人。對這世上的很多人來說,時間就是時間,金錢就是金錢。如果可以置換為金錢,他們很樂意讓渡自己的時間,有時候甚至是生命。
綠皮車那個年代是我想象可及的時代,那時的人物、希望和憂慮,陪伴我出生、長大和接受教育,它不是書中學問,而是人生百態。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時間的腳步越來越快,我們生存的空間也因瞬息可至而不再遙隔。再過數十年,當我將綠皮車口誦言傳給我的孩子,是否他們會更多地誤解為行吟詩人的浪漫情懷和自我放逐的勇氣,而非實際的人生呢?
直至今日,高鐵網已四通八達,遍布全國。綠皮車像一個曾經輝煌而今寂寂無名的演員,沒有了追光燈和關注度,只能在主干網的末端和一些非熱點時段運行。知乎上有個帖子,問“有哪一刻讓你覺得綠皮車該退出歷史舞臺?”有人說是味道難聞,有人說是環境嘈雜,有人說是硬件落后,有人說是乘車時間漫長。而我則希望那一天不要到來。綠皮車連著一個又一個的村子,一片又一片的土地,一個又一個的希望。有多少家境平平的大學生,坐在最便宜的硬座或硬臥上,搖搖晃晃地奔向他們的未來。有多少背負著孩子和養老壓力的年輕人,用一張張綠皮車的車票,在被生活壓迫的間隙,走向遠方去享受片刻遠離塵囂的寧靜。有多少在外拼搏的民工,為搶到一張春運期間回家團聚的綠皮車票在火車站外徹夜排隊,那張最便宜的車票,又能幫他們節省幾日的辛勞。
我努力不匆忙趕路。很多年以后,我不一定記得某一航班上的云是高是低,但是一定記得一個綠皮火車上那些個搖搖晃晃的難眠夜晚。無數漂泊獨行的旅客承載著睡意和疲憊,堅強和希冀,走向他們各自的遠方。